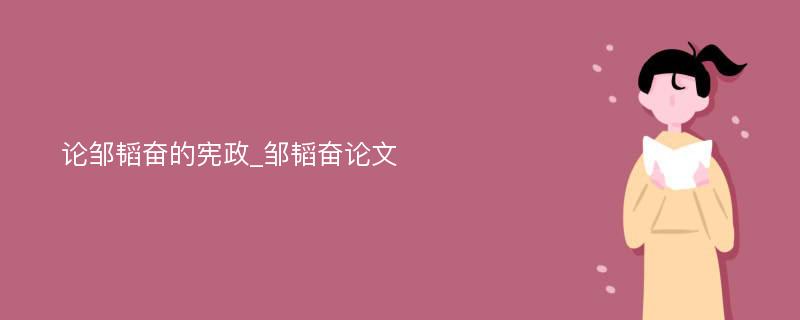
论邹韬奋的宪政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韬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誉为“爱国之士、民主先锋”的邹韬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和民主战士。他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以笔作武器,同当时的黑暗现实作斗争,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试就其抗战期间的宪政主张作些探讨。
一
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政治主张的提出,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集中反映,都逃脱不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加速灭亡中国的进程。面对民族的敌人,如何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去争取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摆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各派面前的大问题。
面对民族的敌人,韬奋认为:只有动员全民族抗战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抗战决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要达此目标,就得改革政治,保障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允许民众发表对国事的见解,并能通过宪法把这些权利用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但国民政府“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到现在……已足有三年半,在这三年半的抗战过程中,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少进步,在有些方面也有人在努力把‘意志’和‘力量’都集中到开倒车,妄图把历史巨轮拉向后转”(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6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压制民间的言论自由,封锁进步的消息,非法查禁进步书刊,杀害进步人士的事件却有增无已。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现行政策中的某些缺点,就往往会被人指为犯了“攻击政府”的大罪,被人指为“挑剔政府措施”;认为某些官吏的措施失当,就是攻击政府。对于图书杂志报刊的审查,国民党主管这方面的审查机关仅仅凭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取舍,往往是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民间的言论、出版等就得绝对服从,否则他们就要拿“国家至上”的大道理,板起脸孔训斥人,重者则被指斥为叛徒。例如,当时的许多机关人员,如宪兵、警察、卫戍司令部的特务、军委会的特务等,都可以随便到各书铺里去随便指认那几本书是违禁的,随便拿着就走,没有收条可付,也没有理由可讲。因此,韬奋先生愤激地说:“即使偶有微细失检之处,亦可按现有的出版法及其关于言论出版的现行法规,在出版后加以纠正,不应因噎废食,使整个出版事业增加困难。”(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8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面对这种现实,他说:“我只沉痛地感到做今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即在遵守法令的范围内,也不定能够得到合法的保障。”(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91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他极力反对这种政治,认为“这些与中山先生倡导的‘主权在全体国民’冲突。因为这些与国民党领袖在参政会所指出的‘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治一定是建筑在民意之上’的原则冲突”(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94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民主政治对于抗战而言,尤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只有用民主的方式和精神来共同推进国是,才能巩固团结;也只有发动民众力量,更新政治,才能加强民众动员;巩固团结,加强民众力量和动员,才能增加抗战力量,做到愈战愈强,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那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呢?韬奋先生指出:“我们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专制主义,反对挂羊头卖狗肉的有名无实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注:邹韬奋《患难蒙难记》,《经历》,第382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根据当时的形势及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政治都不是任何阶层专政的政治,而是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政治。这种政治既不同于正在溃烂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民主政治。因此,整个民族的生存靠的是全国同胞共同御侮,不是任何阶层任何党派所能单独逃避其责任与后果的。
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韬奋先生的救国行动更是不甘人后。他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积极提倡民主政治,在推进宪政运动中提出了许多主张。他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以舆论工具为阵地,用笔作武器,报道有关抗日的事实真相,揭露抗战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开展了艰难的宪政运动。
二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政治倾向日趋反动,变本加厉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实行独裁统治。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秋,韬奋先生希望用自己的笔来提高民众觉悟,来动员民众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其职业的关系,他的许多宪政主张都是通过杂文、评论等形式提出来的,因此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现择其大端进行论述。
1、关于言论自由
关于言论自由与抗战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中国在现阶段内,抗日高于一切,言论自由,亦应以抗日为范围:凡有裨于抗日的言论,尽量许其自由;凡有害于抗日的言论,绝对不许其自由……。”(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这表明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对于言论也应作具体分析,即一切言论必须以符合抗日的需要为最高准则。他坚决反对危害抗日的言论,同时对国民党当局对言论出版采取的一刀切态度也提出了批评,主张通过正当的途径,求得问题的妥善处理,以利于抗日运动的开展。
关于言论与政治的关系,他又指出:“因政治的清明革新,与抗日的胜利息息相关,故人民在言论上对于政治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亦应得到言论自由……。”(注:《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只有集中全国各界的智虑识见,才能争取抗战的尽快胜利。针对国民党对言论问题的态度,他在报上撰文驳斥国民党的“抗战与民主不相容”的论调,认为“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对外的抗战在本质上是有着密切联系,而不能截然把他们分开的,结论是抗战时期更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注: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经历》,第4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民主与抗战决不可割裂开来。
在言论出版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提案,要求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立即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他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揭露国民党当局垄断宣传、欺骗民众视听的一些做法。他认为建议和提案的提出,重要的是真正能够切实执行,而且执行时必须符合其原议的精神。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后,他又提出:“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书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日文化事业案。”针对审查书报、搜查书报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两项具体办法:(一)、检查书报须有统一机关负责执行,且书报经过合法审查机关之许可通过,给予审查证或注册后,须予统一合法的保障,各地不得再任意扣留没收。(二)、查禁书报必须由负责机关将理由通知出版者及著述人。第一项办法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当局随便派人查禁进步书刊而言的;第二项办法也十分必要,因为国民党的审查会任意删改、扣留一些进步言论,他们的理由无非是这些文章书籍违背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意志,讲真话讲实话,当然这种理由是不能公之于众的。这些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他所从事的文化事业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生活》书店发展成为有55个分店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集体。但国民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出现,自然《生活》书店也遭到了厄运,这在当时来说,无论于国于民都是一大损失。
2、关于党派
打破国民党的寡头政治制度,实行全民抗战。韬奋先生指出:“由于当时政治上的不民主,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起来战胜敌人,就有一个不能不打破的障碍,那就是国民党一党的寡头政治制度。”(注:《悼韬奋先生》,《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10月7日)韬奋先生认为,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决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在外敌入侵、民族处于灾难之时,我们应集中全力对付共同的敌人,各党各派都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对于抗战中的各党派的具体表现,则要看其实际行动。
保障各党派的民主权利,实现党派平等。在国民参政会里,他把国民党的议员说成是“陪客”,把其他各党派的人士称为“来宾”,个中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当中共代表提出“关于抗日各党派的合法保障问题”时,“来宾”一致认为必要,而“陪客”却一致大发其“不必要论”。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指出在国民参政会里除了国民党外确有其他党派的存在,但在“主人”和“陪客”的心目中,除国民党外,其他党派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他说:“明明看见在座的确有各党派的许多领袖,似乎允许开口共产党,闭口青年党,似乎是允许党派公开存在的,但同时何以又有许多青年仅仅因党派嫌疑,甚至因被人陷害,随便被戴上一顶不相干的帽子就身陷囹圄,呼吁无门。”(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33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对于国民党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的做法,他更是深恶痛绝,并予以大胆的揭露。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并不止“一个党”,但却只有“一个党”得到保障,这种政治与抗战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恢复党德”,就是实行一党专政、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专制主义。因此,在实施民主政治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国民党是否愿意放弃其一党专政,这也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国民党统治者也清楚在此民族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如果不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便会失去全国人民的支持。因此,一方面口头允诺要提早实行宪政,而另一方面则严禁宪政运动,各地方报纸逢“宪政”二字都不许出现。这表明了国民党搞的是假宪政。韬奋先生认为“国民党内反动派之所以反对民主政治,其目的无非为实行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而已。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民主自由,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拖延的政策,坚决反对这种伪装的民主政治,而主张以全国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并且要求立即实行。要办到此点,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注:韬奋遗作《对国事的呼吁》,《经历》,第402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
3、关于民意机关
民意机关必须是由民选而来的,这是宪政的主要内容之一。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参政会成立后,参政员实行“聘请制”,形式上虽包含了抗日的各党派,但几乎为国民党所包办,它对国民党的政治措施没有任何约束力,也体现不了多少民意。为此,韬奋指出:“民意机关应该是由民选而来的,参政会根本不是民选组成的,所以说不上民意机关,但是号称‘国民参政’,又似乎是民意机关。无论如何,国民参政会总比国防参议会进步。”(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70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他认为这种由政府用“请客”的方式请来,本来就不正常,虽然参政会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也经过形式上的民选、民推而来,但各省市的参政员哪个不是国民党所圈定的,许多应该被送入养老院的人,都为国民党所网罗,用来粉饰“民主”的门面,这些人大都是老得走不动,出入都须有人扶着,根本丧失了作为参政员所应有的能力。尽管国民党表面上也说参政员要从“著有信望”及“信望久著”的人中产生,但是既为“请客”,要请谁主动权全在国民党。而对于被请者来说,当然不好喧宾夺主,他们虽有听取报告、建议、询问等职权,但参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算有效,可见参政会的职权是很小的,这与参政会在抗战中应起的作用是很不相称的。在当时渴望实行民主政治以加强国力的时期,韬奋先生认为尽管这个机构的种种不合理,但仍“未尝聊胜于无”,所以“怀着一腔热忱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参加”,但日益恶化的政治又告诉他这不过是一场幻梦而已。
要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在参政会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广大群众的力量实为决定中国前途的主要因素,而不是违背广大群众要求的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所能压抑下去的。任何在政治上已具有伟力的个人,或在中国已具有相当力量的一个党,真能反映中国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否则必然要遭到最大的失败。”(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17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是中华民族的民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民意机关的国民参政会应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个机构中就得要求能真正体现各党各派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
集中民意,共抗强敌,国家要应鼓励人民发表自由言论。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事业,他们对于书报印刷品的寄费都特别予以优待,而我们在抗战期间正需要大量精神食粮的时候,却反而书遭禁,店被封,即使是参政会上通过的一些条文,也只是永远停留在纸面上,更谈不上民权有什么保障了。因此,他认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应尽速成立战时真正的民意机关,集全国优秀人才,共计国家大计,做到“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党员包办,用人先问其是否党员的作风,必须迅速加以改进;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应予以切实充分的保障。要做到这些,必须解除对抗战文化的压迫与封锁,不能以特务机关代替法庭。
4、关于民权
他说:“民主政治不能离开民权,说到民权,除了选举权、罢免权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谓四权以外,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经常听到的是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和生命的自由权,而生命的自由权尤为基本的基本,因为生命的自由权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么都无从谈起。”(注: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经历》第325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因此,要想获得正确的言论,就要求人们能说实话、真话,就得有说实话的环境。但在当时,国民参政会却不能做到这点,它没有什么力量,“不过是蒋委员长叫许多人来听听训罢了。”(注:《揭穿妨碍民主的几种论调》,《韬奋文集》卷1,第295至301页,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版)既然当局也主张搞民间政治,各党派又都赞成,这就起码应该得有对民意机关负责的政府。但实际情况是“权贵凭藉政治力量发国难财,动辄数千万,党老爷压迫人民,横行无忌,抗战阵营中的亲日派造谣生事,破坏团结。尽管道路传闻,人民侧目,已成公开秘密,但人民对他们有什么制裁力量!”(注:《揭穿妨碍民主的几种论调》,《韬奋文集》卷1,第295至301页,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版)在这种政治下,还有什么民权可言!这种政治不变,国家就不会进步,人民则倍受压榨。
这些言论和主张使他赢得了时人的尊敬,但也遭到了代表反动的势力的迫害,他“本人则几次被通缉,或被逮捕,言论和人身自由,经常是处于被剥夺的状况之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者对于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革命战士的待遇。”(注:《悼韬奋先生》,《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10月7日)
三
对如何实施宪政,韬奋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步骤、方法和主张。
1、明确宪政的具体内容,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
要明白实施宪政的具体步骤,就得明白宪政的具体内容。譬如有人想到实施宪政,只能简单地感到国民大会的召集、宪法的制定及颁布等,这虽然都是实施宪政的主要部分,但却不是唯一的。因此,他认为“实施宪政的工作可作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参政会通过决议案起至开始召集国民大会。第二个是从开始召集国民大会至宪法颁布止。第三是在宪法颁布以后的一切执行阶段。”(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244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他还认为,如果希望宪政的实施真能获得实际的功效,绝对不能坐视国民大会的自然到来与宪法的自然产生,必须在第二阶段尚未到来、第一阶段刚开始时推动宪政运动。这表明实行民主宪政,争取民主权利不能坐待当局发善心,或自上而下地赐予,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去争取,宪法的颁布不是宪政运动的结束,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贯彻执行。
2、改革宪政的内容,使之适合变化着的客观实际。
实施宪政,必须修改原来的宪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他认为宪政运动是实现抗日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大问题,决不像国民党中一些人所说的只须在房间中研究研究那样,它不实行则已,既行之,就要提高民权,实行合于抗战救国的宪法,不应遵守那已经过时的不合时代需要的旧宪法、旧法规。况且昔日“五五宪法”的起草者,许多人已做了汉奸,且客观形势也不同于以前,若不加以修正,对于抗战来说只有坏处而决无好处。而国民大会的组织法、选举法中的许多规定又抑制了人们的民主权利。因此要实施宪政,结束训政,就必须改变国民党的政治。他认为着眼点应放在“政治机构是否健全,官吏是否廉洁守法,爱护民众而不压迫民众,信任民众而不惧怕民众,服从民意而不违反民意,重视舆论而不摧残舆论,尊重民权而不蹂躏民权,绝不为少数人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注:《团结的推动力》,《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版)如果做到了这些,也就是说政治上确实有了进步。但国民党缺乏实施宪政的诚意,拒绝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一再拖延国民大会的召开时间,使这次宪政运动没能达到直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目的。
3、积极推动民众参加宪政运动
韬奋先生认为,中国在抗战救国的伟大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宪政,是要能够充分反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要求,由此使他们对于国家有更亲切的感觉,增加他们对于抗战救国的努力。因此宪政运动要有民众参加,这是很有必要的。在抗战时期,他希望每一个民众团体及学术团体,每个茶馆,每个民主教育馆,每个大大小小的事业机关都能举行宪政座谈会,使一般民众都能明白宪政是怎么一回事,明白抗战与建国的关系,了解民众对于宪政的要求。这样深入民间的宪政运动,加上得到良好的领导开展,一方面可以充分反映全国民众的要求,使将来的宪法能反映民众实际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就是实际的政治教育,加强民众对政治的认识与了解,这样就可以为实施宪政前途建立巩固的基础。
实施宪政,要正确地对待民众运动,要真正动员民众参政,动员他们抗战。韬奋指出:“凡是确有广大群众基础与救国表现的民众团体都应该允许它们继续努力,纳在政府领导之下运用起来。民众团体的力量不是挂上几块显赫的空招牌,就能像奇迹似地发生出来的,必须有多时艰苦奋斗的干部与多时在实践努力中的群众;所以动员民众必须重视民间团体的力量,只须使其符合总的抗战国策,而不必作细枝末节的限制,更不可随时解散。”(注:邹韬奋《抗战以来》,《经历》第169页,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任何一个政党如果站在民众的对立面,那么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宪政运动搞的不是形式主义,它本身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它要动员大众为民族生存而出谋献策,去改良政治,纳全国政治于正轨。因此,他认为民众是宪政运动的真正主人,要创造有利于实施宪政的客观环境,彻底改革与抗战相悖的诸种因素,推动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参政。否则,宪政而无民众运动,民众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无合法存在与合法活动之权利,则一切宪政,不过空谈一阵,毫无实际成效可言。他还认为如果长此以往,国民党仍旧实行专政统治,坚持老一套做法,则“不论宪法条文如何完备,亦不过一堆毫无意义的黑字,不论宪政名词如何夸□(原文中空缺——笔者注)自己早亦以提倡,亦不过一党一派独占政府之掩饰。”(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因此国民党必须改弦更辙,改革不良政治,从允许人民及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有自由讨论宪政自由选举国大代表开始。诚始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围绕着民主与独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他编刊物、开书店、写文章,满足大众的视听,阐述自己的主张,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宪政运动的发展,从而成为众所敬仰的民主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