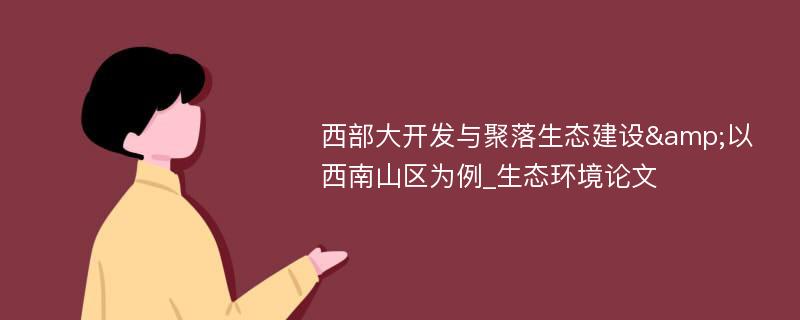
西部大开发与聚落生态建设——以西南山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为例论文,大开发论文,山区论文,生态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我国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所致。其表现形式主要有2种:(1)集中破坏式。如国有森工企业对天然林的砍伐,使短期内大面积连片森林景观变为荒山裸土景观,有的继而引发泥石流、山洪等灾害。其次,如大型矿山、工程、城镇建设等,往往也会在短期内一次性造成对物种、群落、植被等的彻底破坏,形成人工景观。(2)分散破坏式。表现为分散、长期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之逐渐退化、恶化。例如草场的过度放牧,药材、菌类的过度采集,居民以柴为薪的长期采耗,陡坡地的垦殖等。分散式破坏与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关。当前,在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建设中,防止集中式破坏已有较好控制,如对天然林禁伐,基本上就控制住国有森工企业对森林的砍伐。而分散式破坏,牵连到千家万户,不仅难以管理、调控,而且在未有新的产业、生产方式和社区管理、生活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前,制止生态退化的社会基础往往不稳固,难以收到实效。因此,从聚落生态学角度,探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途径,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2 聚落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聚落是一定人群的居住集合,由一定数量的家庭和人口组成,定居于某一特定的区域或区位。聚落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重要空间方式,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发生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时空单元和系统。聚落内及其周边生态条件,成为聚落人群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发展条件的重要内容。聚落及其周围的地质、地貌、大气、水体、土壤、植被及其所能提供的生产力潜力,聚落与外界交流的通达条件等,直接影响着区内居民的健康、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
我国西南地区人口大多分布于农村,其中山区居民又占巨大比重,山区聚落往往更具封闭性,其与当地生态环境的依存关系更密切。如果过去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大面积退化是聚落人群生存压力的结果,那么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不能不通过聚落来实现。
聚落的形成及其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表现的不同模式,是人地关系和区域社会经济历史演化的结果。各类聚落的存在和继承,有其历史的因由和生态学意义。例如,在西南不少少数民族(特别是彝、傈僳、苗、羌等民族)喜欢以海拔较高的山区为聚落选址。其原因一方面是过去为了逃避民族纠纷伤害,而选择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又较能满足自给自足的地方建立隐身蔽所;另一方面,地处高海拔,气候温凉,传染病少,在少医缺药的年代,可以避免流行性疾病的浩劫。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许多聚落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与生态建设形成尖锐矛盾。因此,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聚落模式,选择与生态、生活和发展协调的聚落区位,确定聚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已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聚落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现代社区建设和聚落对外开放联系、组织与管理;关系着区域交通、通讯、信息、商贸、能源、物质的组织与传输。
3 现存的主要聚落类型
3.1山区恶劣环境聚落
分布于三峡库区,四川盆周山区,广西、贵州石灰岩山区,西藏等地。其主要特征是:聚落分布于高中山或高山峡谷,聚落周围地形险峻,耕地资源缺乏,多为陡坡旱地;聚落周围缺乏保水储水条件或设施,若遇干旱或少雨,经常发生人畜饮水困难。由于地处山区深处,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产方式落后,不能发挥资源多样性优势,而过分依靠陡坡垦殖,以柴为薪,构成对植被的破坏,引发水土流失和山地灾害,并往往形成贫困与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例如,西藏左贡县林卡乡旭日村和西坝村地处海拔3000m以上,两村人口800人,只有耕地约40hm[2],可利用水资源量仅200万m[3],有100多人无地可耕,20%人口年缺粮3个月,人畜饮水极困难,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除非人口外迁,别无出路。
3.2地方病聚落
西南山区是我国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氟中毒等地方病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许多聚落位于上述的某一或某几种地方病区之内,成为“地方病聚落”[1]。这些聚落内地方病发病率极高,贫、病、残交加,不仅对当代居民生存、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子孙后代及长远发展留下后患。例如,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善丝村78人中完全健康的仅9人,60岁以上人口仅1人,因氟骨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8人,半丧失的9人。地方病在聚落流行,主要是存在诱发某种疾病的流行因子,如缺碘(甲状腺肿)、富氟(氟中毒)、缺硒(克山病或大骨节病)等自然致病因子。从社会环境上看,主要是聚落封闭,粮食、蔬菜、饮用水都是本地生产的,缺少与外地交流。因此,自然因子通过食物转入人体,长期积累导致疾病发生[2]。若当地居民外出变换生活环境,或从非病区调入粮食、蔬菜,改造天然饮用水,则一般不会发生地方病。因此,地方病是贫困和低劣原生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3.3游牧型聚落
游牧在川西和青藏等地草场牧区依然广泛存在。游牧不成聚落,但迫切需要建立聚落,实现定居。西部草场的破坏主要是过度放牧和畜粪被用作燃料不能回草所致。而这又与牧区原始的生产方式有关,即依赖生产力低(高海拔)的天然草场放牧,单位面积产草量低,并存在“夏绿、秋黄、冬枯、春死”的现象。
3.4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聚落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不少著名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等都仍保留着为数不少的农村聚落。例如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景区现仍有居民1000多人,分布于3个聚落(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卧龙大熊猫与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内也仍有居民上千人。这些聚落的存在,一方面威胁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特殊要求又限制着聚落的生存和发展。
3.5移民聚落
50a来,我国仅因大型水利工程引起的移民就上千万,至今仍遗留许多问题,成为水利工程的“老大难”,究其原因是移民的新聚落往往不具持续发展的条件。要解决好水利工程移民问题,关键是建设好移民聚落,不仅使移民有房住,更重要的是要使聚落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空间。例如,在三峡库区万州区长岭镇,1997年就建起一个移民新村,有几十套房子,却没有一户移民愿意搬进去,原因是移民找不到就业、生产、发展出路,直到1999年10月落实了就业问题,移民才住进“新村”。在移民工作中势必要建立移民新村、移民点,即移民聚落,如何以生态学原理建立和建设移民聚落,使其具备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是成功完成移民任务的基础。
4 聚落生态建设与区域发展关系
一般说来,对生态造成破坏的聚落,其分布都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在西南地区,四川盆周山区、川西高原区、高山峡谷区、环境容量不足的工程移民区等,都是贫困聚落和生态环境恶化聚落的集中区。因此,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应对促进贫困聚落的脱贫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支撑。另一方面,聚落的建设和发展又能促进区域的发展,提高区域的综合实力。但是,一个区域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区内的所有聚落都能同样发展,一个区域的贫困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所有聚落都贫困;同样,一个较富裕区域也并不能保证就没有贫困的聚落。因此,在聚落层次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较之区域更具体、更直接、更微观、更具可操作性。当前,解决成片大区域的温饱问题已不突出,脱贫的攻坚是落实到户、到聚落、到村、到乡。
西南地区居民聚落的建设目标是发展聚落经济,提高其社会功能,改变贫困面貌,恢复生态、重建良性循环。在西南地区搞生态环境建设,必须与区域脱贫相结合[3],必须与发展区域经济相结合。当前,其最有效的空间尺度是以聚落为单元,也即将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放在聚落上。各个聚落的建设搞好了,整体的农村经济和社会文明建设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而生态环境建设也就能有效进行。今后,随着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可在聚落建设的基础上,建设农村城镇,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那时,聚落生态的任务也就转到城镇生态小区或生态社区的建设上了。
5 聚落建设方略
5.1新建聚落
目前处于游牧状态的草原牧民应该建立定居点。定居点的建设应按聚落生态学原理进行规划、设计,特别是解决好人工草场建设,草场载畜量与草场产草量相适应,人口规模与聚落生态条件和容量相适应,创造组织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以生态能源代替畜粪,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文化教育(中小学)设施和与生活、生态有关的配套设施(如牧业、农业科技服务、医药、保健、人畜饮水等)。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区,1995年以前大部分牧民处于游牧状态,自从实施“人、草、畜”三配套牧区定居工程以来,到2000年已有3.6万户牧民定居,新建住房约300万m[2],每定居户有牧畜棚圈100m[2],围栏改良草地1.33hm[2],饲料基地0.2hm[2],大大改善生活条件,并在定居区扭转超载放牧局面。
5.2重建聚落
即对于那些目前生态条件不好,社会经济落后,但仍有改造、发展潜力的聚落,通过必要的投入,包括恢复植被、整治水土流失和灾害,解决饮水、灌溉,增加生态能源,改造交通条件等,使之具有社会经济达到小康、富裕,生态环境得以恢复,进入良性循环的条件。这类聚落在西南地区是多数,应该按各聚落的实际作出发展规划和聚落景观设计,使聚落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进行。例如,西藏类鸟齐县雅巴村有18户150人,1993年人均纯收入860元,因该村落地处则曲河旁,5a一遇洪水就会淹没30%的耕地,20a一遇洪水则100%耕地受淹,一半以上住户房屋进水,一直不能安居。1994年进行河道整治,使聚落消除洪灾威胁,1996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即达1200元以上,并有6户建了新居。又如重庆市黔江地区在脱贫攻关中,大力改善高中山农村聚落基础设施,使99%的乡通公路,建设高质梯田,增加灌溉,解决饮水困难,人均粮食已从1987年的299kg增加到1995年的500kg,使4万住岩洞、窝棚的群众住进新居,并基本消灭了地方病。
5.3迁建聚落
对一些根本不具备生存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科学技术无法挽救其生存环境,无法对其贫穷—生态恶化的恶性循环进行逆转,即聚落的生境、环境及生态位、生态系统不具备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应该进行移民,整体迁至条件较好、有发展空间的区位重新建设。例如,四川省乡城县然乌乡将分散于海拔2500m至3000m以上的16户居民,集中到海拔1000m左右的默坝子一片较平坦的台地上(约66.67hm[2]),建设新果园3.13hm[2],花30多万元建吸虹管输水,解决灌溉用水和饮用水,生产的优良水果由个体户承包卖往云南旅游区,从而大大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并遏制乱砍乱垦的发生。此类移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总之,聚落生态建设是一个新课题,但它又是区域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广大西南山区来说,生态建设的实施要落实到聚落的建设上。首先要保护好聚落居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好森林、草地、水源、耕地。其次,要加快聚落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封闭环境和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再次,要发挥聚落优势,发展特色农林牧产业和绿色产品,开发生态旅游业、天然药物、生态能源等,增加经济实力。今后,聚落建设要逐步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逐步向集镇、城镇方向发展,将聚落生态建设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