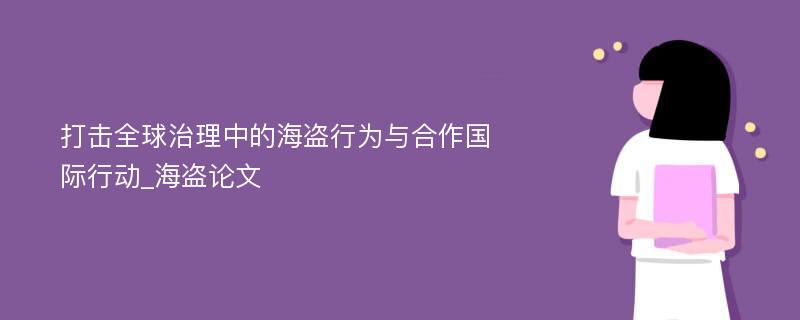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盗论文,全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8832(2012)1期0108-14
自从全球治理委员会发布《天涯若比邻》报告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政府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向。①而“治理”也逐渐取代“统治”的概念,权力的作用慢慢被淡化,国际社会中各种“权威”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国际权力结构被消解,国际社会的进程成为治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经济、环境、人口、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对比冷战时期的单一安全研究,全球治理开创了新的路径,“发现”了诸多以前被忽视和掩盖的国际现象,促进了安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然而,部分原因正在于此,既往的全球治理也出现了明显不足,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进程而忽视行为体的作用,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更是被严重低估,因而最终走向碎片化。换句话说,全球治理常常“雷声大、雨点小”,因观念、利益、机制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含混和不足,而陷于成效不大、莫衷一是的尴尬境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全球治理议程中,何为主要行为体,不同行为体之间如何参与其中,进行协调与合作,从而增加全球治理的确定性、透明度和治理绩效,使其名至实归,亦即不同行为体如何展开全球治理合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国际反海盗行动为例,重新梳理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相互关系,指出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说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同角色与共同价值。
一、“跨主权”安全威胁与全球治理议程
全球治理的兴起与体系战争威胁降低、一系列跨国威胁涌现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安全威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开始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大幅度上升。
首先,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大国战争威胁已经大幅下降,大国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布赞认为,21世纪在主要大国之间“既无主要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无严重的敌对冲突”。②罗伯特·内尔在论述新的安全形势时也认为,冷战结束后,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间基本不可能爆发体系战争,“我们正远离全球战争的时代”。③还有学者表示,冷战终结使世界大战的危险消失了,而代之以地区和地方的冲突。④更有研究者明确断定,冷战结束后,大国对相互间的战争已经“厌恶”,大国战争已经“过时”。⑤对此,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因果解释。现实主义学者如沃尔福斯从国际结构角度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为何很难爆发激烈战争的原因,认为美国单极霸权保障了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致使其他次等大国不敢贸然发动战争。⑥国内也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在美国拥有超强实力的国际环境中,大国之间传统的战略对抗成为不可想象之事。”⑦而核武器终结论者则认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力量使大国间的战争几无胜算。⑧核武器对领土安全观的破坏作用在于,核武器穿透了传统国家的保护,从而使战争胜利顿为虚妄。⑨规范进化论者则强调,随着尊重领土和主权国际规范的兴起,客观上减少了国家的死亡率,保障了国家的生存安全,大国已无必要担心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⑩
其次,在传统安全威胁下降的同时,诸多“跨主权”安全威胁不断涌现。环境、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权威,造就了所谓的“失败国家”,而不断演进的全球化则加速和放大了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与影响力。(11)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国间的安全不等于国际安全,大国关系的稳定并不能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大国间传统的战略工具如军事联盟、威慑、制衡的效用越来越低,难以应对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传统的安全界定涉及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安全与“威胁使用和使用军事力量”直接相关。(12)但在新的形势下,军事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跨主权”安全威胁无需通过影响国家的军事力量使用而上升为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已足够严重。托马斯·迪克森在与其批评者马克·莱维进行对话时,就明确解释了关注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原因。他指出,环境威胁不仅仅是针对美国一国的挑战,许多地区的环境问题正在影响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民的核心价值,引发地区冲突和不稳定。(13)一些学者在研究水资源安全问题时,不是考察水资源对军事力量使用的影响,而是强调水资源稀缺性及其在各地区间的分布不均,导致水资源问题成为新的安全威胁。(14)许多研究疾病与安全关系的学者,也强调要跳出国家安全的窠臼,关注人的基本需求,认为跨国传染病不但通过侵蚀国家的经济与军事能力而造成安全威胁,其本身就会造成国家内部的动荡和国际不稳定。(15)而坚持“人的安全”的学者更强调人的尊严、人的生存需求才是安全的主要内容。(16)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如全球环境、公共卫生、金融危机乃至人口与性别平等,也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事实上,全球治理问题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重合,是因为两者的兴起都依赖两个因素:一方面,它是冷战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局面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各大国对安全形势再反思的结果,是以各大国的政策调整为基础的。冷战终结,大国间的战争危险降低,体系安全得到保障,传统的以国家领土为基础的军事安全威胁逐渐弱化,而在美苏两极对立格局掩盖下的其他安全问题则凸显出来,跨国传统安全威胁便成为关注的焦点,从而为全球治理打开了机会之窗。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仍然在安全研究的框架内发展理论的路径有所不同,全球治理针对一系列跨主权威胁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和理论建构,强调国际多元行为体的参与,淡化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中流动的权威。然而,也正因如此,全球治理又面临着许多有待澄清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涉全球治理的基础,大国以及其他行为体在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治理合作的构建和方式。
二、大国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全球治理的努力方向是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重视国际社会进程,忽视行为体特别是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其中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更是被严重低估。诚然,某一大国或大国集团都无法独自解决一系列跨国问题。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国家性,安全威胁来源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使大国通过单边谋求自身安全变得越发困难,更使大国利用军事力量解决安全问题的效用进一步降低,传统的大国政治模式日趋式微。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应过分低估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里,“大国政治仍然是国际关系议程中的关键因素”。(17)一系列跨国安全问题的解决仍然离不开大国。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是全球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那么,大国为何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前文已经说明,全球治理所针对的问题领域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多有重合,全球治理所关注的议题绝大多数都是跨国安全问题,而在这一领域,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相互对立不同,各大国既有解决此类问题的切身利益,也有强烈的意愿。因而,在跨国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国之间的合作。具体而言,大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涉及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冷战结束后,各大国普遍面临跨国安全威胁,积极参与针对这些问题的全球治理符合各国的利益;第二,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大国更加重视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相互之间可以进行合作。
(一)大国普遍面临跨国安全威胁
在当今世界上,生态危机、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核走私、国际传染病、海盗等新的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各国普遍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促使大国更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跨国安全问题大多具有全球性。其中,一些跨国安全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稀缺和污染、跨国传染病传播、网络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整体面临的威胁,大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由于大国的利益更加广泛而复杂多样,更具全球性,大国甚至更易招致一些特定的跨国安全威胁,蒙受损害和重创,“9·11”事件就是明证。再如生态安全,它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国家无论大小都受其影响。“自然环境不会尊重政治边境”,(18)不管是生物圈自身的失衡、退化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还是资源稀缺引发的冲突和不稳定,环境问题经常会穿透主权国家的边界,也同样与各大国息息相关。而生态安全的缘起和解决恰恰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远非单一大国靠自身力量所能应对。(19)
第二,跨国安全问题的性质表明,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成功地予以应对。美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也难以应对自身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的艰难曲折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小布什政府依靠美国实力推进单边主义受挫后,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回归多边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尊重国际制度安排。另外,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安全威胁开始从对称性威胁向非对称威胁转变,追踪威胁的来源愈发困难,便是大国也难以做到,从而使大国间的国际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如网络安全威胁,一方面,实施威胁的成本和约束条件都很低,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资源积累,但造成的危害堪比战争的破坏性。(20)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信息的高速流动性、网络节点的相互交错性,不管是由黑客抑或病毒引发的网络安全威胁,都难以探察原始的威胁发源地,因而,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独自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和权威”。(21)
第三,很多跨国安全问题具有扩散性。也许部分地区和个别国家的资源稀缺和生态危机,不会直接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对大国不会产生直接的安全压力,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跨国安全问题会在国际社会加速扩散,同样危害大国安全和世界稳定。(22)巴以冲突除了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与争夺宝贵的水资源有关。(23)不仅如此,中东地区水资源匮乏,有15个周边国家争夺幼发拉底河水资源,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都曾因争夺水资源的控制权而爆发冲突。(24)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政治动荡,一方面持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损害国际安全,另一方面则危及国际石油供应,使严重依赖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各个大国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
(二)在跨国安全领域,大国更加重视绝对收益
通常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比较困难。(25)一些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一般乐于在非军事的次要领域开展合作,而且,即使国家间存在共同利益,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对相对收益的考量都会阻碍大国合作。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如果国际合作涉及三方或三方以上,相对收益难题就会缓解;如果国家在合作时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不能转化为权力优势,合作难题也可以缓解。(26)也就是说,如果大国间合作涉及三方以上,而且合作的相对收益不易转化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那么大国间合作是可能的。对此,基欧汉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强调并不一定阻碍国家间合作,当合作涉及两个行为体时,相对收益问题会显现,但是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合作潜力,从贸易自由化到气候变化,多边谈判中的相对收益不易核算,而且出现决定性权力转移的危险很小。所以,相对收益只是强调了激烈的双边竞争带来合作困难,它并不能从总体上削弱一般合作的前景。”(27)
概言之,大国间开展安全合作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合作涉及多方,二是合作的相对收益难以转换为权力优势。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如领土安全而言,安全都存在一定的地缘概念,也就是一般多涉及两个行为体,安全主要是确保国际或地区均势。(28)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收益很容易转化成军事优势,从而动摇各种层次的均势格局。但在跨国安全领域,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大国更容易进行国际合作:第一,跨国安全威胁的扩散性使大国普遍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所涉远远超出三方,甚至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参与方能解决问题,例如全球气候变化不仅给部分小岛国带来严重的生存困境,长远来看,也给各大国带来持续的安全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第二,跨国安全威胁的非军事性,也使合作的相对收益难以转换为权力优势。林林总总的非传统安全也被定义为“非军事”安全,(29)这些非军事安全威胁来源不确定,往往是非国家行为体所造成的,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更长时间,这些特征使大国进行安全合作时,很难将相对收益转换为军事、政治权力优势。比如国际传染病疫情的本质是公共健康和“人的安全”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家权力优势,所以,在“非典”与禽流感跨国流行期间,各大国和国际组织之间可以迅速展开国际合作。
三、国际反海盗行动中的全球治理合作
全球治理进程强调要发挥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在解决跨国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洞见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就具体的问题领域而言,国家、NGO、国际组织各自的作用为何,却是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以往的全球治理研究不考虑“谁是治理者”这一问题,过分强调了进程的重要性,忽视了agent的能动性,特别是忽视了大国合作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30)关于国家、NGO、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行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尤其是大国仍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NGO、国际组织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是全球治理的先锋力量。
冷战终结后海盗活动日渐猖獗,其中,索马里附近的亚丁湾和马来西亚附近的马六甲海峡是海盗袭击最为高发的两个地区,而索马里海盗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海盗事件频发,给各国、特别是高度依赖海外贸易和能源供应的美、中、英、法、日等大国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各大国均纷纷表态,并采取实际措施打击海盗活动。在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多边安全治理机制,其中,既有大国间的安全合作,也有专业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居中发挥重要作用,既有“政府间组织框架下开展的反海盗集体行动,也包括海上保险公司和船东与国际海事局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31)
首先,各大国在安理会积极合作,先后通过多项决议案,为打击海盗铺垫了国际法基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海盗的定义都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发生在公海或沿海主权国家司法管辖以外区域;第二,发起方和受害者都必须是非国家行为体;第三,海盗的目的必须是非政治性的、私人化的。虽然国际法授予各国打击海盗的普遍管辖权,但是关于海盗问题的国际法难以操作,有两类情况使海盗难以被有效打击,第一是海盗行为在公海发生,罪犯随后逃进主权国家领海;第二类是在一国领海实施海盗行为后逃往公海。(32)索马里海盗就明显发生于主权国家领海水域,但是由于索马里政局长期动荡,国家政权无力应对,而国际社会碍于主权,又没法有效打击索马里海域的海盗,致使问题不断恶化。因此,打击海盗需要安理会的授权,需要各大国在安理会的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联合行动。为此,应索马里政府要求,2008年以来安理会先后通过了1861、1838、1846、1851、1950号五个专项决议,授权外国军队在征得索马里政府同意后进入亚丁湾打击海盗。联合国安理会第1851号决议明确表示,“吁请有能力的国家、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部署海军舰只和军用飞机。”(33)随后,美国、北约、欧盟、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先后向索马里海域派出海军军舰进行护航、打击海盗,一时间亚丁湾各大国军舰云集。此外,根据安理会1851号决议,2009年1月,包括各大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了“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小组由各国自愿参加,下设四个工作组,定期交流情况,研讨对策,协调军事、政治和其他手段以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每年在联合国定期会晤三次,并召开多次下设工作组会议。(34)例如,2009年11月6日至7日,中国国防部主持了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协调会议,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北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讨论在亚丁湾实行分区护航合作,以形成亚丁湾护航国际合作的最佳做法。”(35)
除了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合作,各大国还派遣本国军舰打击索马里海盗。2008年底,欧盟由英、法、德主导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专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阿塔兰特”(Atalanta)行动,该行动由法国、德国以及希腊、荷兰和西班牙等国海军力量负责执行,“包括使用武装力量,以制止、避免、干预并最终结束海盗袭击和武装抢劫”。在欧盟成员国方面,各国海军力量也都有所行动。2008年,英国皇家海军“坎伯兰郡”号护卫舰在索马里附近海域解救了一艘被海盗拦截的商船,打死了2名海盗。2009年1月,法国反潜护卫舰“让德维埃那”号在一次营救任务中抓获了19名海盗。2009年4月,法国军舰“雪月”号又在肯尼亚附近海域巡逻时抓获了11名海盗,同月10日,法国海军动用武力营救遭海盗劫持的一艘法国游艇,打死2名海盗,逮捕3人。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多次发起海上打击海盗行动。2008年10月、12月,北约常备海上舰群第二小组中的4艘舰只开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2009年3月,来自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荷兰、德国和葡萄牙的北约常备海上舰群第一小组的7艘舰艇再次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2009年4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美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四点设想,包括美国帮助索马里政府增强警察的执法能力,尽快召开国际会议、更好地协调各国的反应,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派出使节、敦促其领导人打击海盗的陆上基地,同船运公司、保险公司协商,武装商船以增强其抵抗能力。美国海军也有单独行动,如2009年4月,美军“海豹突击队”在营救被海盗劫持的船长菲利普斯时,击毙3名海盗并逮捕1人。中国于2008年底开始向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派遣海上军事力量,两年多来,已派遣八批护航舰队,共护航3000多艘商船,其中包括1400艘外国商船,驱赶了多次海盗袭击。2009年1月,俄罗斯派遣“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赴亚丁湾执行护航,成功阻止多起海盗攻击,3月,俄罗斯又向亚丁湾派出了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艇编队。
但是,“各国军舰的核心任务大都是为本国商船护航,然后才是打击索马里海盗,这种‘各扫门前雪’,全程护航、重复巡航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索马里海盗留下了诸多‘空窗’。”(36)进而,由于大国间战略意图的分歧、领导权之争、护航海域分工不明、协调机制缺乏,亚丁湾海上护航仍给海盗袭击留下了很大空间。根据国际海事局(IMB)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16日,2011年全世界共报告海盗攻击事件119起,其中索马里海域占83起。(37)总体来看,大国合作打击海盗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有待进一步协调各自的行动。
其次,专业领域的国际组织在打击海盗安全治理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与管理作用。各大国也意识到武力打击海盗的局限性,这在联合国安理会1950号决议中即有所反映,“强调国际社会需要采取综合对策来解决海盗问题并消除其根源”。(38)因此,大国合作打击海盗,还需要专业国际组织发挥协调作用,以避免各国在打击海盗方面的无序和混乱,其中国际海事组织(IMO)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国际海事组织是拥有162个会员国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海上航运安全等问题,并进行海洋立法活动。在打击海盗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主要起到了监察和通报信息、制定海洋安全立法和相关标准的作用。该组织发布了多份有关海盗问题的报告,敦促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联合国安理会系列决议也吸收了它的研究报告成果。国际海事组织还进行海上航行安全立法,通过提升航行安全以降低海盗威胁。2002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统一详尽的《预防和制止海盗行为及武装抢劫指引》,并于2009年加以修订。(39)2004年7月1日,国际海事组织开始执行《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修正案,增加了海上安保内容,强制海上船只安装自动识别报警系统、配备保安员,实施港口保安计划。这些措施在大幅度提高船只和港口安全系数的同时,增加了海盗劫掠的难度。(40)2009年国际海事组织在吉布提召开会议,通过了西印度洋、亚丁湾和红海沿岸各国共同合作打击海盗的行为守则,守则签署方约定将按照国际法就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展开全面合作,分享和通报信息,拦截可疑船只,救助那些遭到海盗袭击和抢劫的船只和人员。(41)
再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打击海盗活动中发挥了自治作用。作为海上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会下属的国际海事局发挥了先锋作用,实际上履行了国际船运业公共事务组织治理的功能。1992年,国际海事局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建立了24小时运作的海盗报告中心。所有遭受海盗袭击的船只可以马上同中心取得联络,经过汇总,海盗报告中心通过卫星免费向所有海上航行船只发送每日海盗活动动态报告,并且在中心网站上每周更新海盗劫掠事件。(42)在国际海事局的官网上,也可以检索实时海盗事件发生地图,通过邮件索取季度或年度海盗事件报告。现在国际海事局是国际海盗信息的权威提供者和发布者。进而,国际海事局还对“海盗”加以定义,并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传统的海盗认定主要依据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海事组织的定义——海盗必须发生在公海或主权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地方,而且,海盗攻击行为必须发生在两条船只之间,最主要的是海盗袭击必须出自私人性目的。但是国际海事局的定义突破了这种严格的限定,认为没有必要区分海盗行为是发生在公海还是发生在领土国家海域内,海盗行为也不需要发生在两条船只之间,从木筏或者从码头对船只发动的袭击都可以算作海盗行为,而且海盗袭击不仅仅包括私人目的,也可以包括政治目的。(43)由于国际海事组织的定义过于狭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已经接受国际海事局对于“海盗”的定义和命名。不过硬币总有两面。虽然国际海事局“通过发布海盗警报和建立信息交流与联系渠道等方式,为国际反海盗活动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44)但其本身并没有打击海盗活动的能力,船只遇到海盗袭击时需要利用国际公用海事呼救频道向国际海事局海盗报告中心报告情况,而海盗报告中心则需要联系附近海域军舰前往护航,由于协调耗时费事,往往在军舰赶到之前,船只已遭海盗劫掠。(45)可见,海盗问题的安全治理离不开大国间的多边合作机制,而美国发起的多边反海盗联合行动倡议“151联合特遣队”(CTF151)以及“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都面临大国间集体行动的困境,(46)因此,打击海盗仍需要各大国更加深入的合作,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行为体居中的协调和配合。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的勃兴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总体而言,“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打破既往以权力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的狭隘性,为新的国际秩序和议程开辟道路,但是以“治理”代替“统治”,仍然未能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这两大难题。(47)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演进,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举凡“全球共同关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水缺乏)、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消灭贫困、冲突防止、全球传染性疾病控制)以及全球竞赛规则(核不扩散、有毒废物处置、知识产权保护、遗传研究规则、贸易规则、金融和税收规则)”,都已成为全球治理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48)本文对反海盗国际合作的初步梳理和探讨说明,解决这一系列跨国全球挑战,大国合作迄今仍然是基础性的,而与此同时,鉴于全球性问题以及全球治理的特性,大国合作又远远不够,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乃至全球公民个体等有意愿、有能力的不同行为体都需要积极参与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惟其如此,全球治理才可能取得坚实的成效。
①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Barry Buzan,"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7,No.3,1991,p.432.
③Robert O'Neill,"World Order:New Challenges at the Global Level," in Denny Roy,ed.,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18.
④J.Soedjati Djiwandono,"The Strategic Dynamics of Post-cold War Southeast Asia," in Denny Roy,ed.,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172.
⑤参见John Mueller,"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An Assess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4,No.2,2009,pp.301-303; Michael Mandelbaum,"Is Major War Obsolete?" Survival,Vol.40,No.4,1998/1999,p.20.
⑥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7.
⑦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
⑧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1991/92,p.40; 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2,1988,pp.83-88.
⑨时殷弘:《非传统安全与中美反扩散博弈——在朝鲜及伊朗核问题上》,《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5期,第2页。
⑩对主权规范减少国家死亡率的分析,参见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10,pp.42-43.Mark W.Zacher认为,国家死亡率从1648年以来逐步降低,而冷战结束后,尊重领土完整规范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尊重。参见Mark W.Zacher,"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rm: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2,2001,p.230.
(11)Ralf Emmers,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The Dynamics of Securitization,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4,"Introduction"; Maryann Cusimano Love,"Global Problems,Global Solution," in Maryann Cusimano Love,ed.,Beyond Sovereignty: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Second Edition),Thomas and Wadsworth Learning,2003,p.3;王昆义、蔡裕明:《全球化、人类安全与后SARS时代——两岸非传统安全的新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51页。
(12)Steven 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1,1991,p.212.
(13)Thomas F.Homer-Dixon and Marc A.Levy,"Correspondence: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3,1995-1996,pp.189-190.
(14)Peter H.Gleick,"Water and Conflict: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1,1993,pp.79,82.
(15)Susan Peterson,"Epidemic Disea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Vol.12,No.2,2002/3,pp.44-45; Colin McInnes and Kelley Lee,"Health,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No.1,2006,p.15.
(16)参见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第二章。
(17)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25页。
(18)Vicki Golich,"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Problem:Environmental Interdependence," in Maryann Cusimano Love,ed.,Beyond Sovereignty: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p.270.
(19)Maryann Cusimano Love,"Global Problems,Global Solution," p.9;赵念渝:《“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观察》,2004年第10期,第37页。
(20)对美国等国来说,“维基解密”的一系列外交机密披露行动,其“危害性”显然不容低估。
(21)Richard A.Love,"The Cyberthreat Continuum," in Maryann Cusimano Love,ed.,Beyond Sovereignty: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p.213.
(22)Thomas F.Homer-Dixon,"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36.
(23)Miriam R.Lowi,"Bridging the Divide:Transboundary Resource Disputes and the Case of West Bank Wa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1,1993,pp.113-138;谢立忱、黄民兴:《中东国家领土与边界纠纷的安全视角分析——非传统安全因素》,《西亚非洲》,2009年第7期,第63-64页。
(24)赵念渝:《“9·11”事件和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第38-39页。
(25)Joseph M.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7.
(26)Duncan Snidal,"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3,1991,pp.714-719;鲍威尔认为相对收益问题只是个理论命题,而不是经验问题,如果使用武力可能性下降,国家就不会担心相对收益问题,参见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91,p.1316.
(27)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28)Terry Terriff,et al.,Security Studies Today,Polity Press,1999,pp.115-116.
(29)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30)Deborah D.Avant,Martha Finnemore,Susan K.Sell,Who Governs the Glob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1)王健、戴轶尘:《东南亚海盗问题及其治理》,《当代亚太》,2006年第7期,第24页。
(32)邵维国、邵晓帆、周冠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规定的超普遍管辖权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47-48页。
(33)“第1851(2008)号决议,2008年12月16日安全理事会第6046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2008年12月16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8/s1851.htm,2011年3月24日。
(34)"Contact Group," 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www.state.gov/t/pm/ppa/piracy/contactgroup/index.htm,2011-03-29.
(35)“2009年11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外交部,2009年11月5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624916.htm, 2011年3月29日。
(36)杨凯:《亚丁湾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机制建设》,《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4期,第10页。
(37)参见IMB,"Piracy News & Figures," http://www.icc-ccs.org/home/piracy-reportingcentre/piracynewsafigures,March28,2011.
(38)“第1950(2010)号决议,2010年11月23日安全理事会第6429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2010年11月23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0/s1950.htm,2011年3月24日。
(39)IMO,Resolution A.1025(26)Adopted on 2 December 2009(Agenda item 10):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http://www.imo.org,2011-03-28.
(40)以上参见杨凯:《东南亚海盗的区域治理》,第60页;蔡万助、陈冠宇:《海盗治理与亚丁湾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台湾省中央警察大学第五届“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学术暨实务研讨会,2009年11月26日,第131页。
(41)“海事组织:吉布提会议通过打击海盗行为守则”,联合国网站,2009年1月30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1124,2011年3月26日。
(42)参见"IMB Piracy Reporting Centre," http://www.icc-ccs.org/home/piracy-reporting-centre,2011-03-28; Jayant Abhy-ankar,"Piracy,Armed Robbery and Terrorism at Sea:A Global and Regional Outlook," in Graham Gerard Ong-Webb,ed.,Piracy,Maritime Terrorism and Securing the Malacca Straits,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6,p.17.
(43)Graham Gerard Ong-Webb,"Introduction:Southeast Asian Piracy: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Graham Gerard Ong-Webb,ed.,Piracy,Maritime Terrorism and Securing the Malacca Straits,p.xiii.
(44)张家栋:《世界海盗活动状况与国际反海盗机制建设》,《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第33页。
(45)杨凯:《亚丁湾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机制建设》,第10页。
(46)孙德刚:《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第159页。
(47))关于“良治”(good governance)的讨论,参见Ved P.Nanda,"The 'Good Governance' Concept Revisite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03,Law,Society,and Democrac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Jan.,2006),pp.269-283.关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参见艾伦·布坎南、罗伯特·基欧汉:《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2011年第2期。
(48)戴维·赫尔德:《重构全球治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2011年第2期,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