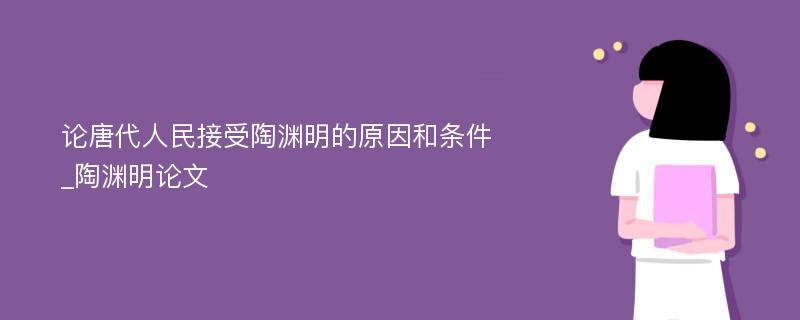
论唐代人接受陶渊明的原因和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陶渊明论文,条件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人比前人更多更广地注意到了陶的为人和诗文。唐人接受陶渊明并不是偶然的。
在唐代,隐逸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欣赏乃至效仿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尚隐是唐人接受陶渊明的一个基本原因。经过中古人的“希企隐逸”(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隐逸作为包含着高雅脱俗等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文人喜爱谈论和效仿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伴随着隋唐的社会变革,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因受时代精神的影响,以新的面貌在唐代社会蔓延。
尚隐是与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对人才的重视分不开的。出于维护王权统治的需要,李渊、李世民父子有意把道祖李耳(老子)称为自己的祖先,并编制各种关于李耳的神话。为了表示对贤才的重视,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唐代几乎每个皇帝都下过搜求“丘园栖隐”、“遁迹藏名”之士的诏书(据《册府元龟》卷六七、六八)。这股风气实际是导源于唐高宗、武则天的。《旧唐书·隐逸传》云:“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当时著名的“方外十友”卢藏用、司马承祯等的方外之交便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从他们走“终南捷径”的行为看,他们的隐逸含有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动机。而统治者又与这些“终南隐士”不谋而合,因此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大大激发了社会上的重隐之风。如《旧唐书·隐逸传》记载了许多皇帝征隐的故事,其中征卢鸿一便是著名的例子。唐玄宗征卢入朝,卢固辞官爵,玄宗只好放他回山,并作《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最高统治者如此礼待隐士的做法,对积极用世的唐代士人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大诗人李白不愿走正常的科举途径入仕,便走过以隐用世的道路。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于陶接受甚多的盛唐诗人都有过隐居的经历。翻看唐人诗作,嘉隐慕遁的言论,终三唐五代不胜枚举。只不过盛唐人的隐主要是为了用世,中唐人则主要是独善,而晚唐五代则主要是避世。
以往讲初盛唐时代精神多强调其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一面,其实是不全面的。初盛唐人的时代精神是由两方面融合而成的,除了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一面外,另一方面是希企隐逸、徜徉于山水、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这两方面融合成真正的盛唐精神:待时而起,功成然后身退。这是从初唐人便开始思考并实践的,其中陈子昂的思索因其深邃而具代表性。他上承“四杰”,在《感遇》诗中借助道教的基本哲学观、历史观对时代兴废、个人行藏作了深入思索,认为天道的周而复始决定了朝代的兴废,个人的出处行藏也应顺天应运,把握时机,待机而起,功成然后身退,即“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天”。张九龄继陈子昂之后,在《感遇十二首》中将陈子昂的思辨明确地简化为“乘运而起,功成身退”。盛唐精神的歌颂者李白,更是毫不犹疑地接受了这一观念,屡屡申述“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蒿》)的抱负和理想。初盛唐人天真地想在等级社会里将追求建功立业与人格独立自由结合起来。而事实是大多遭遇挫折、四处碰壁,此时他们采取的态度正是退隐山林江湖:“时非我与,遂厄宋而围陈;道不吾行,终乐天而知命”(杨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并序》)、“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可见融入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正是初盛唐隐逸思想的个性。当他们失意时,当他们沉浸在隐逸情思中时,便禁不住联想到高唱“归去来”的陶渊明,联想到优游于田园的陶渊明,并对陶表示欣赏认同;而当他们要乘时而起、大济苍生时便对陶固守一隅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满了。
中唐人基本延续了盛唐人的时代精神,但把“功成身退”替换成“兼济独善”,用世进取的成分因时世的艰难、理想的沦落而减弱了。中唐人面对现实,无可奈何地更多地强调独善的一面,并将“独善”同“吏隐”、“中隐”观念结合起来。大历诗人多受谢脁影响,采取吏隐态度:“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谢脁《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在官位上隐逸,不忍舍弃柴米油盐的基本保障。到白居易更是津津乐道“天下有道现,无道卷怀之”(《答〈四皓庙〉》),在官位上奉行适意人生的态度。即使遭遇不幸、被贬江州,他也能旷达自适,“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中国古代的逐臣心境,至此已基本消除了屈原、贾谊之沉于悲愤、不能自拔的特点,而渐与隐、禅结合,超脱旷达。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中唐人何以对陶渊明隐逸、淡泊、闲适的心态产生共鸣了。但中唐人身上的盛唐用世精神毕竟没有泯灭,仍然高倡“兼济”之志。白居易《新制布裘》云:“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四周垠。”时世似乎尚可有为。正由于受盛唐人之影响,兼济之志仍在、怀禄之心难除,因此中唐人也有不满陶渊明的一面。
晚唐五代,时世由中唐的艰难进而至于艰险,兼济之志似成泡影,独善之志发展成避世心理,这使他们与陶渊明的隐逸避世有相通的一面。但同时,晚唐五代人的隐逸之中渗进了冷漠幽寂的因素,对待现实持一种空漠的态度,这在司空图、贾岛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他们所推崇的带有空、冷、看破红尘等特点的淡泊,与陶渊明脱俗而不离于人间的淡泊并不一致,因此他们诗作中的淡泊之趣便与陶诗中的淡泊之趣相去较远,而对陶的接受也大多限于避世隐居,于其诗作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要之,隐逸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尚隐、寻求个体的独立自由和恬适却是三唐五代人普遍的心态。而陶渊明是前代的著名隐士,不但官修史书以较长的篇幅为之作传,而且被收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高士传》。因此唐人在表现隐逸之情、出世之志时,便大多不约而同地联想到陶渊明其人其诗。
将诗与饮酒之风进一步融合起来,是唐人接受陶渊明的又一重要原因。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启发,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了中古文人与酒的关系,并指出:“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诗和酒连了起来,以酒大量写入诗中。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确以渊明为第一人。从此,酒与文学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渊明饮酒既是对传统饮酒风俗文化(如重阳节饮菊花酒)、时代嗜酒风尚的继承,又有独具个性的发展。萧望卿在《陶渊明批评》中称陶渊明“才是更广泛的将日常生活诗化”的诗人,朱自清在该书的序言中称萧评“是很得要领的”。文人饮酒、日常生活,到陶渊明手里才诗化并显示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位和自娱自适、真率自然的个性特色。陶渊明因此成为魏晋风流人物中独具个性的好酒高士。承接源远流长的酒文化的余脉,唐代诗人进一步将诗与酒融为一体,其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酒中仙”李白,其后白居易也自称“醉吟先生”。在诗中写酒要用典、要引前代好饮之士作同调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独具个性的陶酒便成为众诗人瞩目的典故。
需要指出的是,隐逸与饮酒同属魏晋风度的两大主题,唐人对陶渊明这两方面志趣的接受是与对魏晋风度的接受紧密相联的。质言之,陶渊明独具个性的饮酒与隐逸,正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因此唐人往往陶、谢并称以表其高雅脱俗的情志,在提到的好饮的中古名士中不独陶渊明,又遍及“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山涛等人。至唐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虽有变异,但封建社会的本质未变,而且又提供了一种极为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因此,产生于特定时代和制度下的魏晋风度,舍弃其乱世背景下沉重的精神内涵,以其洒脱不羁的形式吸引了唐代文人。即魏晋风度对唐人的影响显示了文化的传承性特点,同样,陶渊明对唐人的影响当然也显示了文化的传承性特点。所不同的是,陶渊明有着鲜明的个性,因此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尚有陶渊明本人的原因促成唐人对他的接受。
唐人之所以在诗歌创作中受陶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庶族文学的兴起。“唐代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支柱是在皇权统治下门阀豪族和新兴庶族的‘品级联合’”,但“到武周时,庶族地主的势力便显然上升了,进士科更成为出仕的主要途径。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尤其是进士科,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新的官僚集团”(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庶族可以授永业田, 依法成为地主阶级,在法律上同过去的门阀士族享有同等的特权。其实,到了唐代,士族仅仅以士族制度的残余形态存在。唐代前期贞观、显庆、开元年间三次官修《氏族志》、《姓氏录》、《姓族系录》的共同原则是,重视今朝新官僚,士族地位在唐代一降再降。到后来即使士族入仕后,他们也已成为新的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成员。经安史之乱和其他战乱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大量士族后裔已失去了门阀士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他们除了几百年前有一个显赫的祖先外,其他政治特权、经济基础乃至文化修养方面,同一般地主官僚已无多大差别。因此,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不表明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有极大势力。相反,这说明他们最后已融化到一般地主的行列中,从而丧失了地主阶级中一个阶层或集团的特殊地位(详参《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总之,这是一个士族走向衰败、庶族走出低谷的时代。因此,唐代文学主要是庶族要求建功立业、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艺术显现,表现出风华清靡、劲健清真的美学风貌。这与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时的东晋南朝文学典丽雕绘、绮艳浮靡的美学风貌截然不同。文学总的发展方向是清真、自然、平畅、质朴,而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庶族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鲍照乐府诗)。当然,士族文学也有这方面的特点(如谢灵运、谢脁的一些诗)。但这些特点一直到唐代特别是盛唐之后才成为诗歌的基本特点,而盛唐正是陶诗在唐人诗歌创作上产生影响的时代。安史之乱后,由于世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浸润,出现了元、白一派的“尚实、尚俗、务尽”的美学思潮(详参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7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文学进一步走向平易、走向“田家语”。同时,出身庶族、熟悉田家生活、关注人民疾苦的文人读起陶诗来,便比不知稼穑、高高在上的士族(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读起来要亲切得多。到此时,出现韦应物、白居易等人对陶诗格外注意便不是偶然。当然,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唐人敏于审美感悟,并在感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王昌龄、皎然等人重视情景交融、重视诗歌意境的理论。因此唐人便能初步发现早已同他们诗歌理论相吻合的陶诗之美。
与庶族地位的上升、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相联系,自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均田制的日趋破坏和瓦解,唐代庄园经济的普遍化成了唐人接受陶诗的经济基础。庄园在唐诗中又被称为庄、庄墅、庄宅、庄田、别业、别墅等。在唐代,从一般地主到高层统治者都有庄园,甚至僧尼和工商业者也有庄园。它是封建地主对土地的一种占有形式和经营方式。庄园里面往往按照主人的审美观点布置楼台阁榭、花木泉石,如王维的辋川别业便是极富文化品位、审美意义的庄园。《陕西通志》载:
辋川在蓝田县南峣之口。去县八里,川口为两山之峡。随山凿石,计五里许,路甚险狭。过此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饶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转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
这里所记辋川地理形势及风物、生活,简直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正是在这种经济上自给自足、环境上优美动人的庄园里,文人士大夫“游咏其间”,进行审美欣赏和文学创作活动。庄园景色、生活进入了他们的审美视野。因此,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在盛唐发展壮大。虽遭战乱,中晚唐庄园也很发达,如李德裕的平泉庄、司空图之庄即是。即使由于战乱,有的庄园遭到破坏,但避世之地的环境和生活也俨然庄园。因此唐人在写田园诗时,便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桃花源。渊源于陶诗、壮大于盛唐的田园精神自然也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了。
陶渊明诗文和传记通过各种途径在唐代的传播是陶被唐代人接受的必要条件。
第一是陶集的流传。唐初魏征等撰《隋书》卷三三《经籍志》集部类录“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并注云:“梁五卷,录一卷。”又史部类录“《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四库全书总目》引明沈士龙说,以此书为伪托。然流传中早已录于陶氏名下,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四即称“陶渊明《搜神录》”云云。愚意不能排除其中某些作品是陶作之可能性)。房玄龄等撰《晋书·隐逸传》中陶潜本传云,陶“所有文集并行于世”。可见从唐初便一直流传着《陶潜集》及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证之以晚唐郑谷《读前集二首》之二“只应陶集是吾师”云云及唐人提到的《闲情赋》等诗文,以及后晋刘蚼等撰《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所录“《陶渊明集》五卷”等,则知唐代所传陶渊明作品集已非一种,至少有九卷本、五卷本两种。
第二,萧统《文选》在唐代备受重视是陶渊明传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萧统的基本文学观点是文质并重,并且针对当时的文风,表现出黜靡崇雅的倾向。《文选》的编纂基本贯彻了这一基本标准。而这又与唐初统治者所倡导的“文质彬彬”(《隋书·文学传序》)、“丽而能典”(《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理想文学标准是极为一致的。据《旧唐书·曹宪传》,唐初曹宪等人“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显庆三年(658)九月, 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云,《文选》为“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旧唐书·李邕传》)。唐玄宗开元年间,吕延祚等五臣重注的《文选》影响亦甚大。“唐进士科之试杂文,始于高宗末年,然未成定制,至中宗以后,才基本定下来。所谓‘杂文’,开始并非专用诗赋,在玄宗时,才逐渐定下来,但后来又两度停试”(马积高《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而“唐以诗赋取士……时主雅量其书(指《文选》——笔者按),乃至分别本以赐金城(公主),书绢素以属裴行俭。风尚所趋,尤关轻重。故唐代士人之于《文选》无不人手一编,奉为圭臬”(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因此乡学要讲《文选》。杜甫也以《文选》教子,要他“熟精《文选》理”(杜甫《宗武生日诗》)。李德裕这位自称家中世代不藏《文选》的人,在《文章论》中也注云:“《文选》诗有五韵、十一韵……”足见由于统治者提倡、科举取士及创作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唐代士人从小便受到《文选》的熏陶。萧统于《文选》中选录陶诗七题八首,并《归去来辞》一篇,另外还有江淹拟陶诗、颜延之《陶征士诔》。唐代《文选》注家无不旁征博引为之作注。唐代士人之所以普遍知晓陶渊明其人及其诗文,与《文选》在唐代备受重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选》,仅靠陶集的传播,陶渊明诗文的读者面将会大为缩小。
又皎然等人《讲古文联句》中提到“江淹杂体,方见才力,拟之信工,似而不逼”。刘禹锡《送慧则法师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云:“时也秋尽,咏江淹杂拟以送之。”又《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云:“桃源访仙客,薜服祠山鬼。……羊璇要共和,江淹多杂拟。”不论他们是从《文选》中,还是从江淹集中读到江淹的杂拟诗,江淹拟陶之作当是通过《文选》或江淹集被唐人接受的。由此推测,唐人为数不少的拟陶诗也应受江淹拟诗的启发。
第三,唐代类书的编纂是陶渊明传播的另一个途径。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开唐人类书引用陶诗文、典故之端。此后,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十四礼部下“挽歌十”条例举陶《挽歌诗》之“荒草何茫茫”,卷十八人部中“贫六”条例举陶《咏贫上》之“万族欣有托”,卷二八果部“桃三”条例举陶《桃花源记》。中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中卷四“九月九日”条、卷十五“酒”条、卷一百“菊”条,白居易都提到陶典。
第四,史书中的《陶渊明传》也是陶渊明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房玄龄等撰《晋书》、李延寿等撰《南史》,在《隐逸传》陶渊明本传中基本上综合抄录了沈约《宋书·陶潜传》和萧统所作的《陶渊明传》。此外,唐代尚流行收有陶渊明传记的《高士传》,因此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云:“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李白《口号赠杨征君》云:“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我们通过阅读唐代读者接受陶渊明的史料,会发现唐人所熟知的陶渊明形象基本是以史书的描绘为蓝本的。
第五,与陶渊明相关的地理环境也是陶渊明传播的一个客观条件。陶渊明为他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唐人对此看得很清楚。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九云:“彭泽故城在县北四十五里。晋陶潜为令,理此城。”“彭泽令”从初唐“四杰”始便一直是唐人对陶渊明的敬称。盛唐好称陶渊明的大诗人李白便游过庐山,其《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一诗贬陶渊明“龌龊东篱下”,实在是诗歌创作中的就近联想之笔。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以为“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白居易《代书》),并带着倾慕之心“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白居易《访陶公旧宅序》)。因此,诗人过庐山、彭泽等与陶渊明有关的地理环境便不能忽视陶渊明。王贞白有《书陶潜醉石》,崔涂有《过陶征君隐居》,陈光有《题陶渊明醉石》。这些与陶渊明相关的地理环境,也是陶渊明传播的一个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