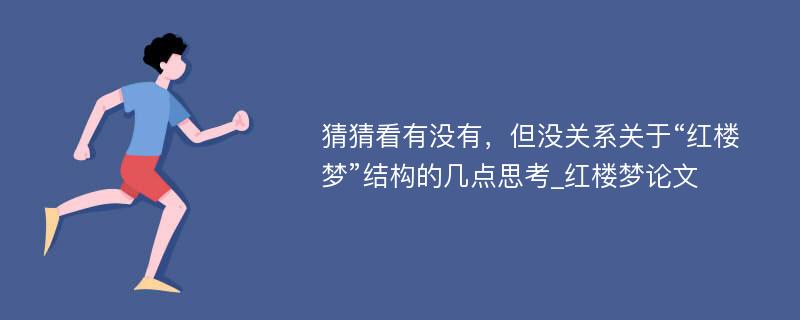
臆断其有无,可乎?——读《〈红楼梦〉笔法结构新思议》一文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笔法论文,一文论文,有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汝昌先生在1995年第2 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红楼梦〉笔法结构新思议》一文(以下简称《新思议》)读后获益匪浅。但对其中几个主要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如下看法,就教于周先生。周先生曾说过:“谁说的有理,就应服从谁的论点,这是做点学问的最起码的原则。”(见《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以下简称《多少回》)周先生胸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精神鼓励我不揣冒昧写了此文。
一、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108回吗?
周先生在《新思议》文中又一次提出“全书每9回为一大段落, 共计12个9回,合为108回书文”此论点最早见于周先生的《多少回》,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周先生以9回为一段落,这样分析结构确是新的提法且有其优点。 孙逊先生在《红楼梦脂评初探》一书中就说:“周先生的见解确有其深刻之处。细看《红楼梦》现存的前八十回,按九回分段确比按十回分段和其它分法更为合理。”(加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问题是:周先生的推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判定此书为多少回,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作者有过明确的论述,作者同时代人有过明确的记载,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证实。
作者生前没有谈过他写的《红楼梦》有多少回。退一万步说,即使他说过原计划写多少回,在写作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想法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也不足为据。作者同时代的人说过他们见到的原稿的回数,但没有一个是108回。
脂评透露小说回数有以下几处:(按小说回目次序)
第二回,戚本有一回前批:“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之,……”;
第十九回,在袭人还是“见总无可吃之物”之下双行夹批:“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
第二十回,庚辰本有“壬午孟夏两窗批语:“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
第二十一回首,庚辰、戚本批语:“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
第三十一回回末,批语:“后数十回……”;
第四十二回,庚辰本又有一回批语:“……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以上六条,其第四条,明确地指出“后三十回”,也就是说曹雪芹原著《红楼梦》应是110回,即八十回加上“后三十回”, 这也完全符合第六条。110回的“三分之一”是36回多、37回不到”, 今书至三十八回时,理所当然地“已过三分之一有余”。
“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的宗室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转述其前辈姻戚说,“《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据他说,曹雪芹作到“九十回”就“逝矣”了,这也可解释为:曹原计划是“百二十回”。 而脂评者看到的雪芹原稿是110回,说明雪芹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了原来120回的计划,写成了一百一十回,是否如此,因至今未见雪芹八十回后的“原稿”,也不敢定论。周先生确定曹雪芹原著108 回的论据是:这个数字与“牟尼珠是一百零八粒,钟楼报时敲钟是一百单八杵,小说里的英雄是一百单八将,神通变化是三十六变加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变有关”。周先生举的这些含“一百零八”数字例子,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作为“论据”,这些例证不具备“论据”的最基本的资格,不能证明曹雪芹“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的论点。
周先生也已经觉得这种推论有不严密之处,所以在未推论之前特加了一句:“曹雪芹为何单单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当然,我们既非曹雪芹,谁也不敢说能代为答复”(见《多少回》)既然“谁也不敢”,周先生怎能得出选定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的“结论”,代曹雪芹越俎“答复”呢?
《新思议》一文中为了证明108回这个数字, 周先生还提出“全部小说宗旨主题是写108位女子,108之数是从《水浒》得思的,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秦可卿语)来对‘绿林好汉’……”如果硬凑108女子之数,在《红楼梦》这样一部女性人物众多的小说里是不难办到的。但即便你凑够了108位女子姓名, 也丝毫不能证明“全部小说宗旨主题是写108位女子”这一论点。 雪芹有意地以‘脂粉英雄’来对‘绿林好汉’,这有意地,何以为证?以“脂粉英雄”对“绿林好汉”,出处何在?曹雪芹何时何地说过?这里我想起杨乃济先生一段话:“考据必须考之有据,考据的语言必须是验明正身的语言。”有意思的是文学家、诗人考察事物从不搞验明正身,他们依靠的是感觉,是依稀朦胧的隔雾看花时的心灵颤动,是梦醒时分的‘烟士披里纯’”(《红楼梦学刊》1995年3期19页),不知周先生以为然否?
二、柳五儿的名字有如此“寓意”吗?
周先生在《新思议》一文中对柳五儿这个人物特别重视,微言大义,大书特书。周先生从五儿名字分析:“她名叫五儿,表面是指‘排行’第五,但又一字未写她有哥哥姐姐;真正的意义恐怕是:寿怡红开夜宴中四位大丫环为晴、袭、麝、纹,四个小丫环为芳、痕、燕、四,排在四儿(蕙香)之下,是为第五个,其地位大约正是填补已被风姐索走的小红”。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柳五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极次要的角色。虽然作者说过她“生得人物与平、袭、紫、鸳相类”也只是就其“生得”长相而言,她的实际地位连芳官也不如,她妈柳家的央求芳官去与宝玉说情,要送她到宝玉那里服侍。连芳官也认为自己“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呢!”(歇后语,意谓不管老几,都是奴才辈的。引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843 页注)芳官的地位尚不可与平、袭、紫、鸳同日可语,更何况柳五儿乎!书中描写已经驳倒了周先生的柳五儿,“真乃除了十二正副钗以外的第一流品格,位置之高非同小可”的论点。
她的名字,只不过是排行第五而已。小说没有必要非写她有哥哥姐姐。正如《金瓶梅》中人物王六儿,书中也没有介绍她有几个哥哥姐姐。
《新思议》还说:“柳五儿明明是4月26日饯花一会的引线, 也是罪名冤案的导火线,她那名字五儿,恰好是暗点一过4月,5月便真是‘飞鸟各投林’的开始了!”为了把柳五儿与4月26日饯花会连起来, 周先生确实费了一番脑筋,他说:“柳嫂给她内侄去送玫瑰露,适遇钱槐,柳嫂早知五儿不肯嫁他,立即回避退出,告辞而回——角门上小厮向她玩笑,讨杏子吃,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正是4月26日宝玉生辰的前夕了,”这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有不严密之处,“角门上的小厮”跟五儿开“玩笑”讨杏子吃,怎么能证明‘正是4月26 日’宝玉生辰的前夕了呢?况且“4月26日”是否是宝玉的生辰,书中并未写明, 只是周先生的“孤证”。“杏乃4月中下旬之果”,5月份乃至6 月份也可吃到杏子,“角门上的小斯”都有“讨杏子吃”的充足条件,并不能证明非在“4月26日……的前夕”不可。
周先生单从“五儿”名字,这种顾“名”思议的论证方法使笔者难以苟同。如果“五儿”可以如此解释,那末“四儿”(蕙香),岂不可以解释为“恰好是暗点一过3月,4月便真是‘飞鸟各投林’的开始了”吗?这种类似测字的文字游戏往往于事无补,并不能证明任何论点。论说文的论据应该是严肃的,确凿无误的,这是写论说文的常识。
三、贾宝玉的生日等于作者曹雪芹的生日吗?
《新思议》写道:“怡红之寿,在4月26日芒种节, 书中也特笔明写暗点,更非闲文废语。盖从历法上一考察,便知康、雍、乾三朝之间,只有两次是四月二十六,巧与芒种节会同于一日:一次是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二十六,一次是乾隆元年(1736)四月二十六。这就表明,雪芹在小说中特意铸刻下了无可动摇的史证:贾宝玉(雪芹的自况)的生辰是雍正二年的闰四月二十六芒种日,而到他13岁——书中的饯花会那一年,他又在生日上恰值4月26日正交芒种。 节令的巧合这是铁印记。”
周先生为了证明贾宝玉的生日(四月二十六,正是芒种节)就是曹雪芹的生日——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二十六,竟然连“历法”也不顾了。可历法是科学的才真正是“铁印记”,不容任何人改写的,笔者有一篇小文(载1995年第5期《文学遗产》127页)指出:“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即阳历六月十七日,不是农历芒种节,该年的芒种节为闰四月十四日。”
周先生非常自信, 文中说:“这种科学的论据(指贾宝玉生日为1724年农历闰四月二十六日,笔者注)直到近年来方得揭明显示。它也给作者的生卒、著书的时序一起提供了最宝贵的内证——用任何办法都是无由考核到如此准确的历史记录的。
周先生早在1948 年就已“推雪芹生于一七二四”(见《献芹集》579页)这次“历法”上的“考察”,就是要证明“一七二四”说。 实际上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六(注意:非闰四月!)“巧与芒种节会同于一日。”如果周先生坚持的观点。“谁说的有理,就应服从谁的论点”,不知周先生是否服从“1725年”这个论点?
周先生推断宝玉的生日为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推断的方法也没有达到“用任何办法都是无由考核到如此准确的”程度。《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有一段:“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这一回中根本没有提到宝玉生日之事,第六十三回,虽然题目有“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但也没有明确交代是为宝玉过生日,如果是宝玉过生日,岂有贾母、王夫人、王熙凤不来光顾之理?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进怡红院,林之孝家的也只是问一声:“宝二爷睡下没有?”并没有对宝二爷生日祝贺的话,读者没有“书中也特笔明写暗点”的印象。
即使贾宝玉的生日和历史上某年的芒种节巧合了,也不能证明作者的生日。贾宝玉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的生日怎能与作者生日等同呢?这是文学常识问题,周先生会不知道?再说,《红楼梦》在年月时间描写上往往有不科学的地方,红学家周先生就更不会不知道。早在咸丰年间,“大某山民”(即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三十六回云明儿是薛姨妈生日,时盖壬子年夏末秋初也,至第五十七回亦云目今是薛姨妈生日,时癸丑年春二月间也,岂一人有春秋两生日耶?到贾母生日,已详叙八月初三一段事,今云十一回探春云过了灯节是老太太生日,则又何也?”
贾母,按周先生“对号入座”法,该是宝玉之祖母,即曹雪芹之祖母,曹寅之妻,那么从“历法”“考察”,曹寅之妻生日是“八月初三”还是“过了灯节”呢?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就指出小说家决不等于“谱录家”。小说为了塑造人物,使读者有真实感,必然写年月时节,但小说不可能,也不必要如编年史或作者年谱那样准确无误,如果把小说写成“年谱”,那就真的成了张竹坡批评的那种“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见《金瓶梅读法》),所以作者描写人物时“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同上)。
周先生《新思议》一文,尽管有以上几个不足之处(是否是不足,尚须与周先生商榷),但瑕不掩瑜,余撰此文,并不想否定周先生文章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