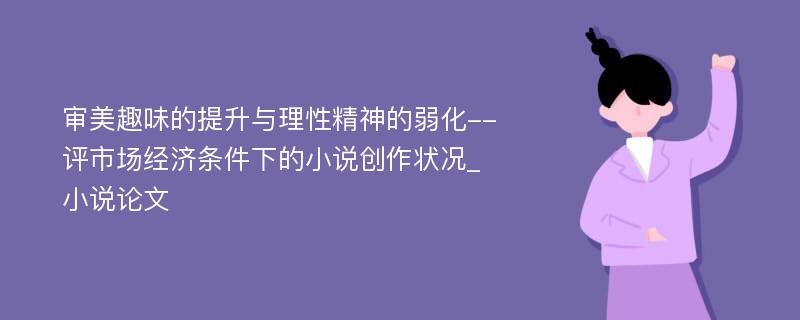
美学情趣的高扬与理性精神的疲软——市场经济状态下小说创作态势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疲软论文,美学论文,态势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时间老人的步履蹒跚地迈入九十年代的中期时,小说创作在近几年里所呈现的繁复景象,使我们有必要对其已然展示的诸种美学风采和理性内涵作一番概略的检视。这种检视,我们将不限于一般地、单纯地回顾与总结,而将着重探究市场经济状态下小说创作所显现的独特风貌,以及这种风貌与整个社会人文风尚、作家的心理状态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本文主要涉及中、短篇),最引人瞩目的几处景观,无不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密切的关联。
风情、世相与人生态度
在对近年小说的览视中,倘若我们不去以八十年代的文坛热点频出、轰动时有的热闹景象来与之对照,而仅仅是从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角度去考察,那么,我们不仅不会为眼下文坛相对沉静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而且会为小说园地所绽放的一簇簇风姿独具的奇葩感到由衷的欣喜。
以表现地域色彩和风俗民情的风情小说历来为作家们所钟情。早在八十年代,陆文夫、李杭育、冯骥才等一批作家就曾热衷于具有独特民俗色彩及文化内涵的风情小说的创作,而王安忆等作家的寻根小说,也几乎都是以边远山寨的村民们古朴、愚拙的生存状态为背景展开故事的,同样有着浓厚的风情小说的色彩。但那时的风情小说,由于承载着更多的理性追求和文化反思精神,虽然曾风行一阵,却实际上只感奋了一批圈内人,而远未在普通百姓中广为传扬。从作家的创作立意来看,理性的追求显然更胜于审美的追求。而近年处于市场经济状态下的风情小说,审美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审美追求因更多地顾及了商品时代大众精神消费的特征,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观赏价值。《市井人物》、《清凉之河》、《丁香街》、《松雪图传奇》、《清唱》、《戴白兰花的姑娘》等一批风情小说的出现,不仅以其独具笔力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而且以其轻快流畅、读来轻松怡人的美学情趣,博得了大众读者的青睐。这些风情小说的流行,实际上是以商业社会里人们普遍存在的追怀情绪为基础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多媒体时代,人们对单纯诉诸于感官的享受方式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必通过耗费眼神的阅读也能获得种种轻松怡人的乐趣。然而许多能带来乐趣的享受形式却常常不能同时带给人以情感的慰藉。市场经济下愈来愈变幻莫测的现实人生,商场角逐中令人心灵疲惫的紧张氛围,社会交际场上日益功利化的冷漠人情,不但使那些饱尝人生艰辛的人们倍加怀念昔日充满人情味的闲适时光,也使那些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有着显达地位的人们,因内心的孤寂而倍感情感和精神抚慰的迫切,而风情小说所展现的特定地域和历史环境下更具传统意味的民风民情,恰好给这些现世的赶路人提供了一个暂且歇息和慰藉的精神旅店。
如果说风情小说所呈现的美学特质给人们的精神带来某种抚慰,那么一批以普通人为描摹重点,从而表现出一种平民化倾向的小说,则给人们的现实处境提供了一面直观自身的镜子。这些小说的出现,与其说是作家对百姓生存状态的关注,倒不如说是今日的芸芸众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眼前的现实所使然。今天的人们早已厌弃了那些虚无飘渺的高远理想,也不再关注那些可以想见却尚未到来的未来世界,而似乎只对或喧嚣、或琐碎、或辉煌、或苦涩的现世人生情有独钟。理想的光辉已在人们的眼眸中隐去色泽,即使是个体人生的目的性也渐渐在琐碎而无奈的忙碌中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似乎已不再会受任何神圣理想和业绩的感召而激情满怀,也不再会轻易地为某一桩应该是十分感人的事而动情落泪,人们仿佛更容易陶醉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的既是情愿又是无奈的俗世生活。当以现实生活为主要摹写对象的作家,满眼尽是一派碌碌人生景象时,甚至其自身也身不由己地成为这一景象中的一部分时,凡人俗事也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小说世界的中心位置,显示出其独特的美学景致。刘醒龙的《黄昏放牛》、《白菜萝卜》、陈建功的《耍叉》、《放生》、《前科》、乔典运的《问天》、何申的《穷县》、陈世旭的《北京“面的”1818》、赵光的《复习班》、毕淑敏的《原始股》、北村的《玛卓的爱情》、李功达的《呆坐街头》、李贯通的《乐园》、周大新的《病例》、李国文的《世态种种》、刘庆邦的《水房》、《家道》、张欣的《真纯依旧》、《爱又如何》等,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对各色小人物的命运遭际、人生烦恼、情感困惑作了摹态摄神的生动展示,构画出一幅当代社会平民百姓的众生相,并由此折射出市场经济状态下纷繁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和丰赡厚实的理性内涵。刘庆邦的《家道》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变革时代的人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更新自身的观念,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刘醒龙的《白菜萝卜》活脱脱地为人们塑造了两个性格鲜明却类型迥异的当代农民形象,小说那种将人物置于生活的原生态中而突现出的艺术形象,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审美享受;毕淑敏的《原始股》以敏锐的艺术触角,通过人们对于股票这一新事物的不同态度,捕捉到现实生活中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观念转化的重要信息:从官本位到钱本位;刘震云的《新闻》则透视了商品经济下一种弥漫于普通人生活的无奈心态,从而深刻突现了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人生态度。与以往小说不同,这些作品中的平民百姓不论其行为是否越出了某种道德规范,都并未受到来自创作主体的道德批判,相反的却被作家赋予前所未有的同情、理解、宽容甚至关怀,这使作品在展示了丰富的理性内容的同时,更充盈着一种浓厚的人情味、人性美,成为大众读者手不释卷的精神佳品。
从以上描述,我们不难看到,不论是风情小说,还是追求平民化的小说,其产生的现实心理动因和审美动因,都与现世人们在商品经济下被迫形成或自发形成的独特的人生态度相关联。当人们一夜之间发现既往的行为道德准则与现实世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时,当人们再也无法象以往那样明晰地辨识自己的未来时,当人们已然失去从容地把握自我人生轨迹的自信时,相信命运的力量、注重现时的享受、除却道德的束缚、看淡荣辱的心态,使得寻求内心的憩所成为人们普遍尊奉的、带有某种时尚意味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所演示出的异彩纷呈的人生景观吸引了作家,并通过他们的艺术点染,构织出一幅幅现世写真图。在这里,应该说作家的取材契合了读者的口味,还只是这些作品受青睐的一个方面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家们多年修练出的艺术才情对于生活素材的提炼与构织,才使得作品闪射出耀人的光采。
历史、唯美与读者意识
现实生活毕竟只是作家艺术视野中的一部分,往事与历史所沉积的丰厚内容也常令作家驻足留连,然而,作家又毕竟是怀揣着现世的感受和体验,以现世的眼光和意识去观照历史、抒写往事。当我们把检视的目光投向近年来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时,便会惊异地发现:作家们把在现实题材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平民百姓的关注热情也带进了或遥远或不太遥远的历史中,摹写了一批在历史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即便是表现民族抗日这样的历史内容,也是以小人物的活动作为构筑作品的主框架。这一现象的出现,明白地显露了现实大众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是怎样深刻地影响了创作主体,是怎样有力地左右着小说艺术的美学走向。这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昔日作家们的艺术魔棒曾是那样灵验地引导着读者的阅读口味,而如今,事情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不是作家酿制什么艺术盛宴,读者便只有一窝蜂地哄抢,而是作家必须依照读者的口味去操持艺术的魔棒;作家已经不能再象以往那样只是一味听命自身的内心要求而写作,而是要更多地去通过琢磨和考查大众读者的审美要求来决定该写什么和怎样去写。这样一种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正是市场经济状态下所具有的特殊形态,它使得作家们比任何时候都具有更为强烈的读者意识。
不过,我们的作家在具有了读者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忘却打磨自身的艺术利剑。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作家们的艺术技巧和功力并未衰退,而是比以往更加丰富和厚实了。这首先表现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许多作家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观照方式和美学手法。一方面在读者意识的统摄下,格外注意将往事或历史编织成一个有相当可读性的故事;另一方面又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摆脱拘泥于客观化描写的套路,在强烈的主观意绪的支配下,去营造种种富有情趣的场景氛围、点染独具风采的人物性格、铺陈意味盎然的美言佳句,从而使如烟的往事和历史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卓然不群的艺术风姿和魅力。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石门夜话》、《石门呓语》、高建群的《大顺店》、周大新的《银饰》、格非的《相遇》、邓一光的《战将》、林希的《蛐蛐四爷》、须兰的《宋朝故事》、路远的《神汉》等作品,都从对历史(往事)的艺术开掘中,为人们构织了一篇篇可读性强、且有较高美学价值的精品。尤凤伟的《石门夜话》在作家奇妙的构思和想象中,将一个强盗“睡”一个女人的故事铺写得酣畅淋漓、引人入胜。小说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浩大壮阔的场面,只有一个匪首费尽口舌劝说一个被抓来的女人与其“和平过渡”到床上去的单一情节,但经作家独具匠心的点染,竟产生了独特奇崛的艺术魅力。路远的《神汉》也是一篇极具可读性的小说,所不同的是它是以曲折离奇的故事取胜:死而复生、蒙面神汉、传奇侠盗西门狼、沙漠夺宝、曲折的恋情、复仇……等情节,就足以对读者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但要知道,仅有这些情节的简单组合是不可能散发出强烈的艺术魅力的,而必须依赖作家不凡的艺术功力,才能使情节产生慑人心魄的效果。正如作家自身所言:真把小说写得好看也不容易。周大新的《银饰》在情节框架的设置上也有着跌宕起伏、曲折有序的特点,同时作者还融入了奇异的心理渴念和风流韵事的描写,使人们在领略了故事的精彩之外,还能品赏人物的内心微澜和情感纠葛,沉浸于作家所营造的独特艺术氛围之中。这些作品艺术上的成功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表明,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作家读者意识的强化和艺术手法的圆熟,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于时代审美趣味变化的路子,这使得小说挽留了更多的读者。我们切不可忽视这种挽留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挽留的成功,才使作家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并在对希望的追求中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上乘之作。
八十年代曾经兴盛一时的新潮小说,无不以怪异的形式、超常规的语言风格和特殊的美学感受出现于文坛,并带起一股旋风。但从今天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小说不仅由于属蓓蕾初绽而难免在艺术上失之圆熟,而且在美学趣味的追求上也明显地表现出对贵族化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偏爱,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那种临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优越感。这使得新潮小说事实上只在圈内人的手头上热闹地传阅了一阵,并未被大众读者所钟情;就是其艺术上的尝试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也不象当时的圈内人在传阅的兴头上所作的评价那样高。而近几年的一批依旧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审美情趣创作的小说,却有了另一番令人欣喜的景致。这些小说虽然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唯美倾向,但那种对艺术感觉的传达技巧和对特定情境氛围的营造,都较之以往更为纯熟、更为意趣盎然,也更富有美学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在这种唯美倾向中,作家那种鄙夷俗世、傲然自立的态度有了收敛,而在唯美的追求中也或多或少地顾及了大众读者的审美情趣。这一变化的背后,不能不说是与市场经济下那种越来越普遍存在、并被人们所接受的“有需求就升值,没需求就贬值”的价值规律对作家的影响有直接关连。因为不论作家如何坚守自身的艺术信仰,也很难不顾及读者的需求,很难在明知可能没有读者的情况下依旧我行我素而不作必要的调整。毕竟小说写出来是给人看的,作家的内心要求若不能与读者的需求相融合,作品就难有生命力。返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哪一部是没有千千万万个读者的?
徐坤的《遭遇爱情》运用十分娴熟的叙述语言,在作家所明示的假定情境中,铺衍出一对男女在生意场上各有所求又各有提防的微妙心态。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富有特定情绪意味的语句组合,将男女主人公微妙心态表现为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情态氛围,使人们在玩赏富有美感意味的语言的快慰中,完成了对人物在特殊情境里所表现出的复杂心理轨迹的把握。格非《雨季的感觉》已开始走出往日对形式感的表层的、肤浅的追求,而注重在主观意绪的表达和客观现实的描绘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和张力,使形式意趣能够既充分又天衣无缝地弥漫于精巧的情节框架中,构成一种独特的情境氛围和美学效果。这样的处理,既使作家能够发挥其独具个性的艺术感觉,又避免了这种感觉的无节制的过渡铺陈。小说《雨季的感觉》中,那纯净的语言和似真似幻的感觉依然是属于格非的,但这种感觉已不再是支撑小说艺术构架的栋梁,而是把这一职能让位于较为客观的情节。然而那种感觉依然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并构成了一种可以体味却不易描述的整体意境,这一意境可以说就是小说的灵魂和魅力所在。洪峰的《初恋》没有相对集中的、明晰的情节线索,而在看似散乱的片断式情境中融入了作家内心所贮存的一种情感意绪,这种意绪的渗入使情境片断获得了有机的连缀,从而将男女主人公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所透露出的一种观念,十分艺术、同时又十分富有情趣地表达了出来。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无疑是作家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感觉,对曾经拥有和存在的某种人类心性和情态进行臆想性艺术再创造的结果。而如今善于揉捏人的心性和意态的苏童也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写出了象《肉联厂的春天》这样现实感较强的作品。但苏童的艺术敏感区和所擅长的叙述技巧,似乎与这类现实题材尚有一定的距离与隔阂,这或许要有一个调整和修炼的过程。苏童似乎更适合于用不受现实拘泥的笔调去摹写人物的情感王国和感觉世界,毕竟这一领域的可塑性、随机性要强得多。《什么是爱情》就是苏童在其艺术敏感区内构筑起来的作品,其精致性自不待言,但那种可引人入胜的感染力似乎还难尽人意。而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则依然热衷于对贵族化情感和意绪的铺陈,这表明一部分作家还深深沉浸和陶醉于那种自身的艺术感觉氛围中,而不愿或不擅长去寻找这种感觉与现实的契合点。但对许多作家而言,读者意识的觉醒,使他们的唯美倾向有了更为鲜活的面貌。
理性精神:疲软与消解
不论人们以怎样的眼光和角度去检视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都应该承认: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令人欣喜的,这不仅表现在其美学风格的多彩多姿上,而且表现在其对现实生活丰富内涵的敏锐感悟和把握上,更表现在其艺术追求所蕴示的一种崭新的审美意趣的创造与成功的传达上。可以说近年的小说不论其所表现的对象如何变化多端,都能力求艺术表达上的独树一帜,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日臻完美,这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持的肯定态度更多的是从文学的审美功能的角度而作出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从文学对于大众读者的最普遍发生的审美作用入手来考察小说现象的。事实上,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其对小说作品接受与否通常是以作品是否引人入胜为前提的,至于引人入胜的艺术等其他原因,那是文艺批评家们的事,他们是不会去探究的。一部作品能够既受大众读者的好评,又得到批评家的首肯,就一定是上乘之作;而一部作品只有部分批评家们叫好,却不被大众读者所理睬,其生命力就值得怀疑。本文所论及的作品几乎都是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同时也为批评家所称道的,但这种称道却是有保留的。因为批评家在看到这些作品高扬的审美意趣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某种理性精神的疲软和丧失。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在拓展小说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内涵方面所倾注的智慧与心力,并且这种倾注的结果已经使这些作品获得了较高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使得人们在展读这些作品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沉浸于其所创造的情境和意绪氛围之中,在领略了一番心灵与情感的酣畅沐浴之后,又能毫不费力地走出来而不在内心深处留下些什么。很显然,在这些作品里普遍地缺少一种能震撼人的心灵的理性精神,创作主体似乎更热衷置身于所描绘和营造的、或主观或客观的世界之中,而不再愿意超拔于这种世界之上去作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缺乏一种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在风情小说和平民化倾向的小说里,我们虽可以感觉到创作主体对已然失去的精神憩园的追怀与感伤,也能体味到那种对普通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同情;在表现“历史”和有唯美倾向的小说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浓厚的文化意味背后所潜隐着的作家的忧思,也能领略到那种对于人生意趣的把玩中所蕴含的一种无奈的调侃;但我们却看不到那种感伤、同情后的悲悯,看不到忧思、调侃后的关怀,这使人难以触摸到那种大作品所具有的强悍的理性精神。造成这种状况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原因的。
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文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文学的市场在悄然兴起并日益多样化的各种文化消费面前,呈现出无可挽回的大幅度萎缩的趋势,应该说这种文化娱乐形式的丰富对于文学读者群的蚕食并非是不正常的。对于文化艺术的受众而言,精神享受方式的多样化只会使他(她)们感到兴奋而不会令其沮丧,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轻松便捷的享受方式总是更容易吸引他(她)们。然而这种正常的现象对于作家来说则意味着莫大的不幸。不可否认,以往作家所拥有的那种从容和自信的心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基础之上,其自身的那种价值感也是依附于此的。而如今这一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这使作家从容的心态骤然间失去了重心。但这只是市场经济下的现实状况对作家形成冲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所处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作家从昔日的踌躇满志到如今的失落茫然,那种能不为生存所困而以超然的姿态俯瞰人生并予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和激情也就因此衰微了。在这里,作家面临着一个在新的经济社会秩序下自我价值的重新认定和心态的调整问题,这种认定和调整,在一些方面需要外界力量的相佐,但主要还得靠作家自身去完成。这必定是一个充满痛苦且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过程,但这一问题解决不好,理性精神疲软的现实将难有逆转的可能。
我们切不可低估生存压力对作家从容心态构成的巨大影响,也不能简单地苟求作家应该摒弃诱惑、保持平静、坚守自己。毕竟对任何人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需要。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已不能把生存仅仅理解为活得下去。因为生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五、六十年代家中有一部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可算是生活在平均水准线上了,而在今天,一对新婚的城市青年若连一部彩电都购置不起,那就要被列入贫困户了。可以想见,如今大多数作家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了许多,他(她)们正处于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中:“许多作家的内心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冲撞得魂不守舍了”,“偌大的一个世界似乎已经安排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谈歌《坚守自己》);“今天的小说正面临着金钱淫欲的施暴,小说家们各自作着各自的抉择”,“大众兴奋点早已转移,没有谁愿意理会小说,纯文学好比路人身旁的绿色垃圾箱”(李贯通《小说的自救》);……作家们的这些慨叹,正是一种生存危机的真实写照。也许作家将永远失去往日的优越与辉煌,这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需要作家去重新适应自己的社会定位,并安于这种定位。如果作家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拥有了一种平和的心境,那么在商品社会里作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毕竟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社会里,种种有形无形的巨大反差、变幻莫测的人生命运、层出不穷的奇人异事……都会纷然杂呈于人们面前,使人们的心理情感、道德观念、人生态度等发生深刻的动荡和变化,并由此演绎出种种丰富生动的现实活剧,这一切无疑给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沃的土壤,为大作品的产生置下了一个广阔的背景。因此,作家们应该看到商品社会所带来的新契机,尽快从失重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在新的挑战面前拓展出一个新的天地。
在我们沉浸于对市场经济状态下文学如何保持人文理想的深深思索时,王祥夫的《城南诗篇》和康洪伟的《怀念一个人》所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前者表现了一个当今新贵对于改变自身精神素质的强烈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因先天的欠缺而落空;后者则叙写了一位从书香中走出投身商海,在享尽了种种物质文明和肉欲之后,最终还是对佛教发生了兴趣。很明显,两部小说向人们昭示着同一个内涵:人是离不开精神生活的,特别是在人们已然摆脱了生存困扰的时候,更会唤起对精神生活的强烈渴求。毫无疑问,这一信息能给作家带来安慰与希望——既然人们永远也无法总是远离精神生活,那也就无法远离作家;毕竟人们对精神渴求的满足,是离不开作家创造性的劳动的;这正体现了作家存在价值的永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