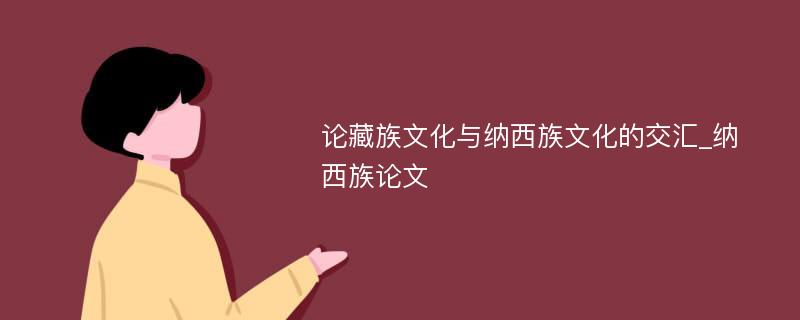
浅论藏文化与纳西文化之交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文论文,纳西论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纳西族有3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滇川藏3省区的丽江、迪庆、甘孜、昌都以及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5个地州,约在东经98.5-102度,北纬26.5-30度之间的8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①由于这一带地区正处在藏文化圈的东南缘,而且除丽江地区外均属藏区,这就为藏纳文化的交汇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条件。
本文依据有关文献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从历史、宗教以及民俗三个方面,对两种文化之交汇作一粗浅的探析。鉴于笔者主要考察范围仅及滇西北、康南一带这两个民族杂居地区,加之对藏文化的了解颇为有限,不当之处,尚祈赐教。
一、历史的交往
尽管学界目前对藏族和纳西族的族源问题尚未形成定论,但至少对这两个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古氐羌族群这一点,已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此外,从两族乃至一些周边民族的史诗、民间传说以及文献资料来看,二者确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譬如:纳西族的创世史诗《崇搬崇笮》中,就有两族祖先系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藏族是老大,纳西是老二的记载;②在普米族等族的古老说中,亦有类似的故事。③
藏族与纳西族的先民们开始交往的历史可远溯至秦汉之际,这种交往在隋唐以后更加频繁。尤其是在丽江塔城与中甸五境之间架起了“叶蕃铁桥”后,更促进了两族之间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汇;④滇西北以及康南等地,就主要是由这两个民族的先民共同开发的。据《旧唐书·叶蕃传》等文献记载,叶蕃王朝于公元七世纪前后挥军南下,并“西洱河诸蛮”,也占领了当时“麽些蛮”(即纳西族先民)居住的地区;从783年唐蕃会盟所划定的疆界看,纳西族先民聚居地区亦属吐蕃管辖。⑤在这种情形下,藏文化的大量传入是势所必然的。其后,吐蕃势力在唐与南诏的合击下有所削弱,不能再有效控制其在云南的属地;而纳西族势力不断扩大,渐形成一无需依附任何外力支持的独立政权。至宋代,尽管其南面的大理国段氏政权曾盛极一时,但纳西族地区已成“段氏虽盛,亦莫能有”的格局。⑥由于吐蕃王朝的衰败,西藏在这段时期则出现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滇西北及康南一带藏区曾一度成为未管辖之地。
元代在纳西族聚居区设置了丽江路,下辖一府七州一县,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⑦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以及藏区事务,其后又得加封为帝师和大宝法王。⑧在中央政权的支持和协助下,萨迦派结束了卫藏地区分裂混乱的局面,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亦逐渐形成。滇西北和康南一带藏区作为宣政院的辖地,这段时期不断受到西藏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和渗透,各方面的发展也较为顺利。自明朝初年开始,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势力在中原王朝的庇护下逐步膨胀,频繁发动了入侵藏区的战争。仅从1475年至1553年不到80年的时间里,就对迪庆藏区用兵达百余次之多。⑨据倪蜕的《滇支历年传》等文献记载,木氏不仅逐渐将其疆域扩张至这样的范围:“……于金沙江外则中甸、里塘、巴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北卡拉、三巴、东卡等……”。⑩而且每占领一地,便派送移民前去屯住,在芒康县盐井乡、巴塘县白松乡以及德钦县纳古乡等地,至今仍居住着自称系当时移民后裔的纳西族。根据藏族学者王晓松先生考定,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姜岭大战之部》等,便是对藏纳两族统治者之间为争夺盐地等矿产资源所进行的旷日持战争的真实写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战争已遍及滇西北以及康南等地区。(11)迤及明末清初,纳西族木氏之势力日渐式微,终于抵挡不不住藏族固始汗政权的南进,其控制范围又被逼退回金沙江沿岸一线地区。(12)
从以上概述中不难看出,藏纳两族交往的历史确实是源远流长的。尽管两族间由统治者所挑起的战争时有发生,但两族人民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关系仍是主流,并在长期的共同发展及文化交汇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余庆远的《维西见闻录》中,就记载了在维西县的一些所谓的“麽些古宗”,“散处于麽些之间”,并且在生活习俗等方面已“大致同麽些”了。(13)据郭大烈先生调查,在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乡等地,亦发现了藏族融入纳西族中的情况。(14)而在滇西北及康南一带藏区,更是有不少纳西族融合进藏族中的现象,当地人普遍称之为“藏纳西”。(15)笔者自幼生长在云南丽江的多民族杂居区,通过耳闻目染及亲身体验,深深受到在纳西人同藏人的交往与共事中,总有一种天然的相互尊重与信赖、亲如兄弟之感,这种亲情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ulart)于本世纪40年代在丽江居留时就注意到了这一奇特现象:“丽江的藏人社会,人少名声大。藏族商人和显贵们住着最好的房屋,纳西人无论大小事都为他们服务,使他们舒适满意。当然,这种特殊的照顾和亲热的关系是由于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语族亲姻关系造成的。后者总是称藏族为‘我们的大哥’”。(16)这种现象有不仅在两族交往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存在,迄今仍显示出有增无减之势!究其原因,从很大程度上看不能不归结为两族人民具有颇为相似的心理素质以及相当的认同感。这正应验了一句著名的藏族谚语:“不像铁一样地相碰撞,就不会像心一样相友爱”。
二、宗教的交融
藏族和纳西族在宗教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在整个纳西族社会都受到藏传佛教及本教观念很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纳西族传统的宗教东巴教与达巴教,从内容到形式均渗入了藏族本教的意识;而纳西族对藏传佛教和本教在滇西北以及康南地区的传播,则又起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藏族本教最初发源于阿里南部(象雄)地区,尔后自西向东逐渐传遍了整个藏区。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将早期本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获取天神善趣之果的五种本教,另一类则是可获财的四种本教。据《土官宗派源流》记载:整个本教又可按时间可先后分为笃本(聂墀赞普时期)、迦本(止贡赞普时期)以及久本(变革时期)三个时期。(17)久本时期,在赤松德赞禁本(公元六世纪下半叶)、朗达玛灭佛(公元七世纪)过程中,将大量佛经翻改后使之融入本教经典,对本教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据著名的《青史》译者俄人罗里赫(G·N·Roerich)称,本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炉霍寺发现了本教的《甘珠尔》经104卷,《丹珠尔》经160卷。(18)可见,改革后的本教经书不仅数量上有很大增加,而且还有了大藏经之类煌煌巨著。此外,本教还开始兴建寺院训练僧人,并因模仿佛教徒而使自己的神祗有所增加。这样,也就使得其流传范围大为拓宽,并远远超出了藏区。
本教传入纳西族地区的具体时间不详,但以其对东巴教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各方面情况推断,当为后期的久本,即本佛合流后开始广为流传之本教。仅举两例即可证比:东巴教的创教者和教主名叫“丁巴什罗”,实际上与本教祖师“敦巴辛饶”为同一人,系东巴教从本教转借而来;(19)而本教只是在同佛教合流之后,才创造出“敦巴辛饶”这一位人物,并模仿佛教尊其为创教者与教主的。另外,据有的学者考定,东巴教的第二祖师阿明什罗从藏区取回的经书应为本经而非佛经。(20)众所周知,早期的本教所强调的是口传心授,拥有大量的本经是向佛教学习的结果。
东巴教受本教的影响是相当深的,其神祗系统、各类仪式、乃至所使用的法器等,都与本教相类似。譬如:东巴教的第一个神灵为“古孜盘本波”意即“藏族盘巫师”;东巴教的“鹏”、“龙”、“狮”等护法神,也多来自本教,而且有的连发音都类似(如“龙”均读为“鲁”)。甚至“东巴”之古称是“boe(33,) boe(33,),当为本教经师“本波”之同音借词,东巴文所象之形,其头上所戴的“五佛冠”亦与本教类同。此外,东巴经书中专用藏语读音的部分,现已发现的就达百余卷之多!戈阿干先生在进藏调查的过程中,曾把由东巴念诵的这类经书的录音带放给本教活佛和熟悉本教的人听,得到了这属于本教经典的肯定答复。(21)可见,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
纳西族同藏传佛教开始接触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末佛教之“后弘期”。据王晓松先生调查,位于西藏昌都类乌齐地区的噶玛丹萨寺,就是由藏、汉、纳西三族人民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共同建造的,具有这三种民族的特点。(22)在藏传佛教的诸多流派中,同纳西族法缘关系最深、对纳西社会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属下的红帽系和黑帽系。(23)红帽系二世活佛喀觉旺布的“太弟子”支梅巴,曾充任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帝师”;六世活佛却杰旺秋等更是木氏的座上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帽系八世活佛弥觉多杰于藏历火鼠年(公元1516年)拒绝了明朝皇帝的邀请,却赶到丽江来同当时的土司木定相会,使佛法在纳西族地区大得弘扬。木定还答应活佛:“每年选送五百童子入藏为僧,且度地建一百寺庙。”(24)此后林氏便开始大兴土木,不仅在纳西族地区兴建了著名的“噶举十三林”,而且还在其控制的云南和康南藏区,修建了大小近百座寺庙。此外,还向许多寺庙布施过释迦、罗汉等珍贵镀金铜像等物,成为这一地区少见的大施主。木氏在弘佛方面的另一盛举,便是出巨资刊刻了丽江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部长达108卷经典的模本,是由红帽系六世活佛却杰旺秋亲自提供的,活佛还亲笔撰写了藏文题跋。刊刻工作于1614年开始,历时九年方得以完成。(25)这是藏学家公认的所有《大藏经》木刻版中最好的版本,现有一部朱印卷珍存于拉萨大昭寺中。
在藏族活佛、僧人以及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大力倡导下,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和康南地区广为传播。在维西等地区,甚至出现了纳西族的“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的盛况,可见信佛已成为一种时尚。(26)丽江五大寺等寺庙的首任活佛,均须由藏区选派来的藏僧充任然后才用“转世”之法由纳西僧人继任。(27)在纳西族的众多僧人中,还出现了圣露活佛等多位的藏传佛教著名活佛,有的僧人当上了西藏甘丹寺的住持。(28)民国前期中甸归化寺(噶丹松赞林)寺主松谋活佛的经师鲁茸宜玛,曾进藏留学35年并获格西学位,也是白地纳西人。(29)在宁蒗纳西族地区,不仅长期以来已形成由喇嘛及达巴共同主持法事的习惯,甚至出现了近似于藏区的政教合一组织。
同藏纳两族宗教交融以及滇西北、康南一带各教传播情况密要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究竟是本教还是藏传佛教先传入纳西族地区?笔者不同意学界长期流行的本教先行传入之说,而认为纳西族同藏传佛教的接触应在先,与本教的交往则在后。其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在东巴教发源地中甸县白地的白水台畔,有纳西族土司木高于明朝嘉靖甲寅年(公元1554年)题刻的摩崖诗碑:“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30)这说明了早在公元11世纪前后,就已有该诗落款处题的号称“释哩达多”的僧人在此传教;而当时的白地属“佛地”,并非东巴教之“圣地”。其次,中甸白地有一远近闻名的“阿明乃科”,系东巴教真正的祖师阿明什罗藏经与修行的灵洞,各地东巴均须来此朝拜。这位东巴教祖师为何不得不将其从藏区偷运回的本经藏于洞穴,并只能在暗地里修行和传教呢?唯一的解释便是当时白地的佛教势力仍占统治地位。(31)其三,从多位学者迄今为止所搜集到的所有阿明家谱来分析,这位阿明什罗最早只可能是清代人。(32)笔者曾亲向当地老东巴和阿明家族后裔调查,并根据阿明家人珍藏的“阿明展兰”(板铃)等圣物的制作年代推断,亦不可能早于清代。其四,在目前世界各地所保存的二万余卷东巴经中,成书年代最早的一册为清康熙七年的写本,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33)因此,只要实事求是而非牵强附会地看待这个问题,便不难得出纳西族接触藏传佛教先于本教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纳西族先民中曾存在过较为原初古朴之宗教。但它是否可称为东巴教姑置不论,至少是难以同受本教及藏传佛教影响,经过改造后的东巴教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藏纳两族在宗教方面的交融确实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交融不仅加深了两族人民的亲情,而且对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康南一带的弘扬及本教的传承,都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三、民俗的交汇
藏族和纳西族在民俗方面的交汇,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笔者仅选取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中甸县小中甸乡和三坝乡这两个毗邻地区,从微观角度对这两个民族当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交汇情况作一简述。
笔者在这一带地区进行四野考察时体验到,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十分密切的。每年六、七月份三坝乡的夏收结束后,就会有大批小中甸等地藏民用马驮着酥油、奶渣以及小竹筐物品前来换取小麦;许多人家互相已结交了“老庚”,建立了较长期和固定的交往关系。一般情况下,50斤小麦可换一饼两斤多重的酥油,一个一斤多的奶渣换5斤小麦。这种约定俗成的交换量并不因年成的好差而有所变更,有时可以互相赊欠乃至赠送。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单纯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关系,而成为互相支援、互通有无的友谊与亲情的体现。到了八、九月份藏区农作物成熟时,三坝的纳西族村民便前去藏民家帮工收割,每工可获取五、六元的报酬(有时还可以实物支付)。另外,藏民家建盖房屋等活动,也往往有纳西族木匠与石匠加入其中。
由于这种交往关系的长期存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不少相似习俗:纳西族村民的早餐原先以煮汤或炒菜为主,但因从藏民手中换取了酥油等物,现已变成常喝酥油茶,糌粑和奶渣亦成了他们所喜爱的佐餐食品。甚至在逢喜丧节庆等场合,许多人家也是先请客人喝酥油茶,然后才正式入席享用洒宴。在小中甸的藏民家里,喝酥油茶时的佐餐品已不单是炒面,很多情况下吃的是小麦面粑粑,其制作方法亦与纳西族相类似。尤其是乡公所所在地“古孜宗”村,因村民原先多由纳西族“藏化”而成,所以这些人尽管平时操藏语,生活习俗亦已类同于藏民,但仍在衣饰、屋内装饰以及宗教意识等方面保存了一些纳西族文化特色。村内每年农历正月初五都要举行“素矻”(即迎请素神)活动。(34)该仪式须由东巴主持,这一天全村人都讲纳西话而不准讲藏话。此外,在这一地区,无论是藏族节日还是纳西族节日,都是两族村民共同参加,一起欢庆。长期从事云南各族艺术研究的杨德鋆先生认为:滇西北藏纳两族在曲调、乐器、舞蹈以及绘画诸方面,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35)这一带的情况确实证明了此点。
藏族和纳西族的婚礼都操办得十分隆重热烈,其婚俗也有些相似之处。据该地藏族的传统婚俗,新娘应在旭日初升时迎娶至夫家,这样才会使婚后的日子过得和睦美满,吉祥如意;当地的纳西族亦有同样的习俗。此外,小中甸乡藏族的迎亲队伍将新娘迎进夫家时,须由伴娘将夫家事先备好放在门口的水挑进家门,意为新娘从此正式成了夫家的人;而三坝纳西族的新娘送出家门时,便得由伴娘背一桶水随至夫家,其意亦为从此成为夫家的一员,可开始以主妇的身份待客。
在藏纳西两族治丧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类同点。由于这两个民族都是远离祖先世居之地到这里开辟新天地的,因而总是十分怀念故地,希望死者的灵魂能返回远方同祖先团聚。为达“魂归祖地”之目的,须为亡灵举行一系列仪式:首先,在人刚落气时须放入一些口衔物。藏族放的是一种圆形藏药“批当仁布”或碎金银;纳西族放的是一称“sa(55,)sa(55,)”的小纸包,内装少许碎金银、茶叶末及几粒米(男九粒女七粒)。这些口衔物一方面可作阴曹地府内的“买路钱”,让亡灵能顺利通过重重关卡与祖先团聚,另一方面又被视不有接续祖宗珍贵的“气”,使之代代相传的作用。(36)其次,两族的送葬仪式中皆有给祖先“寄物”的习俗。藏族在起灵前须由丧家放一麻袋于门口,让附近的村民和亲友往袋里装酥油、糌粑和茶叶等物,托死者亡灵带去给自己的祖先享用。纳西族在出殡前亦有“弃饭”(ha(33,)pi(55,))的仪式:由各家主妇捧一碗上覆煎蛋或腊肉的米饭送到丧家,倒入灵柩前的竹筛内,托死者带给自家已故的亲人。此外,这两族的葬仪中还有一种“马送亡灵”的习俗,即送葬行列中至少都有两匹马相随,一匹备好鞍鞯供亡灵乘骑,另一匹则专驮死者衣物及食品以备漫漫族途之需。(37)
由于这两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了不少相似的习俗,甚至在日常语汇中也出现了一些相互借用的现象。在东巴经书及纳西语中有许多藏语借词,这一点在前面已提及;下面将略举数例,说明这一带地区藏语中亦有不少纳西语借词:“序刻”:(xu(55,)k (35,))─意指豺狼;“索你”:(suo(33,)ni(35,))一意为明天;“本虽”:(ben(33,)sui(33,))一指“伙头”或村官,系木氏土司统治中甸等藏区时设置的基层组织头目;“巴喇”(ba(33,)la(31,))一指衣服或外衣;“班涛”(ban(33,)tao(13,))一意为甜面饼;“单嘟”(ban55d (53,))一意为青蚕豆。事实上,类似的语言互借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加之藏语和纳西语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以至难以分清究竟哪些词原系藏语,哪些词原属纳西语了。这一带的藏族会讲纳西话,唱纳西调和跳纳西舞的情况十分普遍,纳西族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能跳热巴舞及唱藏歌的也是大有人在!
总之,仅从上述一些民俗事象的粗略观察中,便可看出藏纳两族在民俗方面已到难分彼此的地步。这种交汇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对促进两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极作用。
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究竟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这是当前国际人类学界所关济并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话题。从我们对藏文化与纳西文化交汇的情况的初步考察中,似乎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据1990年人口普查,纳西族为28万人,加上近3年来的增长数,现已超过30万人。
②参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69页。
③陈宗祥:《普米族源流新探》,载《民族学与现代化》1987年第1期。
④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概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载:此铁桥建于公元680年,毁于794年。
⑤详见《旧唐书·吐蕃传》。
⑥引自《丽江木氏宦谱》(甲)“牟西牟磋”条。载《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⑦见《元一统志》。
⑧王辅仁:《西藏密宗史略》,台湾佛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⑨载《中甸县志资料》第三辑。
⑩倪蜕:《滇支历年传》。
(11)王晓松:《浅谈(姜岭大战之部)的“姜”》,载《迪庆方志》1991年第2、3期合刊。
(12)冯智:《明至清初滇藏政教关系管窥》,载《中甸县志通讯》1990年第3期。
(13)余庆远纂:《维西见闻录》。
(14)敦大烈等:《纳西族史》(油印送审稿),第613页。
(15)据格勒先生调查及笔者在迪庆等藏区调查札记。
(16)引自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李茂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17)参见《土官派源流》德格版,第164-165页。
(18)王辅仁:《西藏密宗史略》,台湾佛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19)参见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0)戈阿干:《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其源流考》,载《边疆文化论丛》1989年第1期。
(21)戈阿干:《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其源流考》,载《边疆文化论丛》1988年第1期。
(22)王晓松:《浅谈〈姜岭大战之部〉的“姜”》,载《迪庆方志》1991年第2、3期合刊。
(23)根据王辅仁先生分类,噶举派(白教)可分为塔布噶举和香巴噶举两大系;塔布噶举又可分为噶玛噶举、拔戎噶举、蔡巴噶举以及帕竹噶举四支系;而噶玛噶举还可分为黑帽系、红帽系以及其它的小支系。
(24)冯智:《明至清初滇藏政教关系管窥》,载《中甸县志通讯》,1990年第3期。
(25)王尧:《藏文大藏经丽江——理塘版甘珠尔经述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26)余庆远纂:《维西见闻录》。
(27)张波:《关于纳西族的藏传佛教问题》,载《中甸县成通讯》1988年第3期。
(28)参阅清光绪《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仙释志》等,载《中甸县志资料汇编》(2)第91-92页。
(29)段绶滋撰:民国《中甸县志》,载《中甸县志资料汇编》(3)第204页。
(30)有关此诗碑题诗及照片,参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封二拙照与说明。
(31)据笔者调查,白地有多处寺庙遗址,而东巴教是无寺的,因此它们只可能是藏传佛教寺庙。
(32)参见杨正文搜集的“阿明世系”,载《纳西东巴圣地民间文学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戈阿干亦搜集了几份“阿明世系”,可参阅戈阿干:《滇川藏纳西东巴文化及其源流考》,载《边疆文化论丛》1988年第1期。笔者手头亦有数份。
(33)此册东巴经年代系李霖灿先生考定。详风李霖灿:《麽些研究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1984年版,第147-149页。
(34)关于纳西族的“素”神究竟何指,目前沿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指家神,有的称生命神。据笔者调查,这是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神灵,其涵义要远比家神或生命神丰富。
(35)杨德
:《云南藏族舞蹈》,载《舞蹈论丛》1984年第2、3期。
(36)关于纳西族的“气”观念,可参阅即贵、耕勤:《纳西丧葬习俗》,载《丽江文史资料》第8辑。
(37)关于中甸纳西族的葬俗,详见拙文:《中甸白地纳西族的丧葬礼仪》,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