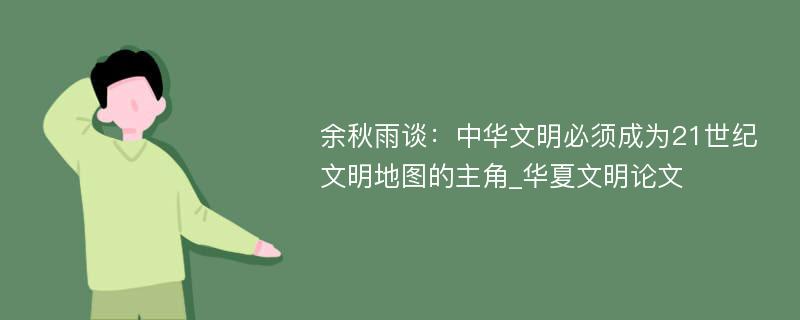
余秋雨散谈:中华文明一定是21世纪文明图谱中的主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谱论文,秋雨论文,中华文明论文,主角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20世纪中期以后,所有文化学者都在思考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的思维环境变了,学者们面对着新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内外环境,不再用过去那种因为浩劫造成的悲痛目光,而是用正常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中国。我现在进行的“世界行走”,就是想审视15年前“国内行走”所得结论的正确性。那么,产生了怎样的结论呢?
文明的基本支撑点是后代人是否了解上代人
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文明的灭亡和衰落。由此,突然发现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千不是、万不是的中华文明,是那样了不起、那样伟大。在“世界行走”后,当我们从尼泊尔踏入西藏自治区的国门时,真是热泪盈眶,觉得我们过去太不了解自己的民族了。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文字,连埃及人都不认识。希腊克里特岛也是个文明的发源地,但先人的来源、去向、亡国的过程,一无所知。它的文字是线性文字,也没有人认识。而孔子、孟子的著作,我们能够阅读。几千年前的文字,就像外公写给我们的家信,亲切随和。
战争的最后目的,是打掉你的权威、你的自信心、你的尊严。而消灭文字,是消灭这一切的最简单的办法。让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那儿来。站在尼罗河岸边看那些读不懂的文字,我突然感念起秦始皇来,他统一中国后,很快统一文字。文字统一后,就不可能因战争而毁灭。文明的基本支撑点是后代人是否了解上代人。金字塔下牵着骆驼的埃及人,和中国人看金字塔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金字塔的真正内涵。文明死亡的特征是:文字断了,文明被藏在历史暗箱里,文明没有被继承;人也找不到了,埃及的人种已经不是法老时代的人了,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大多是古埃及人和罗马人通婚的后裔,开罗的居民是阿拉伯人。还有一个可怕的情景是,发明文字的祖先的后代,很可能已经不识字,像两河文明地区是如此。还有一些党派还在提出议案,争取孩子不受教育的权利。
于是,我进一步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灭亡。中华文明就像老母亲一样,以前总觉得她文化差、没有风度、不懂外文。后来发现,与她一起生存过的老姐妹们已一一亡故,而只有她带出了一个庞大的家业,真不容易,真该好好寻找原因。
中华文明是不事远征的文明
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中华文明是一上场后就没有下过台的文明。
中华五千年史,国内战争不少,但基本上没有远征过。不远征,也就不会遭受外来者报复性的毁灭。再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没有想到要打到埃及、希腊去。成吉思汗远征了,但他那时也没有问鼎过中原。我过去讲古希腊戏剧史时,常常要提到希波战争。希波战争,就是希腊和波斯打,波斯是今天的伊朗,这有多远。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从希腊一直远征到印度。汉民族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远征,最多是在边关扫一下胡人。杜甫就说过:“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很能代表中华思维。郑和七下西洋,从来没有一点点领土的欲望,只是表表大明的国威。所以,今天世界上有人讲“中国威胁论”,我就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是农耕文明,讲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播秋收,不靠占领别人的领土来发展自己。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是400毫米降雨量线。万里长城大体与这条线重合。因此,造万里长城是保护农耕文明,扎好篱笆怕人家打,不是自己要去打别人。中华民族是守土民族,不是攻势民族。我在世界行的一路上,看到许多城堡,都是用来打人家的,而不是守自己的,比如十字军城堡,它是为了征服建造的,与中国的长城建造目的和功用完全不同。远征的结果一定某种文明受到毁坏,远征者即使获取了军事胜利,但其文化在水土完全不同的空间,也会变形。因此,在古代远征中,任何军事的胜利,都是文化自杀。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东征后,也就一蹶不振了。
我在德黑兰地铁工地上,曾为中国工作人员讲过一个故事:伊朗古代叫波斯,政权经常变。有一次,发生政变,波斯国王希望唐朝发兵保护。唐朝皇帝头脑很清醒,不发兵,设一个波斯都督府,让这个国王来做都督,住在中国,领一份钱过日子。不远征,就不会有文化自杀,也不会有毁灭性报复。
中国没有长时间陷入无序状态
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工作是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秩序是什么样的情况。没秩序太恐怖了。我来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来自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上海,但到了印度才知道人口爆炸的“威力”。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亿,国土却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只需十几年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印度教鼓励生育,但现在有七八亿人是住在窝棚里。
文明会亡于战争,但亡于无序的状况更严重。无序也可能是文明发展的结果。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没有秩序将会怎样?民族肯定会分崩离析。
文明其实就是一种秩序。如果要给文明下定义,我认为,文明就是保护人类创造的一种秩序。
中国社会长时期保持着有序状态,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正确评价科举制度。它是一种开放的文官选拔制度,不分阶级、出身,都可通过应试而做官,使得管理人才源源不绝。一个国家坚持这个制度坚持了1300年,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这个制度提供了稳定、秩序的基础,很了不起。过去,总觉得状元的诗没有李白的好,但科举是选官员的,不是选诗人的。通过科举的人做官,确实也能管理一方土地,因为他们学的是“孔孟之道”这套学问是入世的,教人治国、处理人际关系的。通过科举,儒家文明作为主干传了下来,无数人用生命去支撑它,年年代代有人在背诵、在研究。儒家文明有了无数的传承者,社会就有序了,社会秩序后面又保留了精神秩序。所以,科举是保持秩序的一种有效办法。当然,科举也有弊病,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一种人才的浪费,而且使一些应试者产生心理变态,范进、孔乙己等等都是艺术家塑造的反面例子。
中国从来没在总体上陷入过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发源于劝人向善,它以善良为起点,启迪人心,点燃高尚的火花,起到精神融合的作用。但是,宗教极端主义则要排斥异端,引发杀戮,有异教相残,也有本教内自相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人。教内一般会分成两派,一派觉得宗教需要改变生存形态,来适应时代,另一派认为,改变就是背叛。因此,始终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现在的恐怖主义大多有宗教旗帜。有的国家还普及着一种宗教化的极端生态,例如,强迫外国来的女性也不能露出头发和耳朵,就给我们的旅行、采访带来很大困难。比如,女记者包了头就没法讲话,没法采访了,要求不包头,但不可以。那么,到车里将头露出来吧,也不可以。我们对他们说:“一个国家只有发展才有尊严,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但他们不理解。
对此,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喜的道路。任何宗教都可以进入中国,但进入后都“不认真”了,也就是摆脱“原教旨主义”了。像佛教在敦煌就变得很美丽,后来又演变出了中国自己的禅宗。中华文明是一种弹性文明,它的抗毒素就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宗教极端主义转眼就能毁灭文明,或让文明变质。佛教发源在印度,但高雅精深,较难理解,反而被源于原始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取代。但佛教在中国,经过改造,有了生命力,有了佛像庙宇,变得亲切了。
年轻人要有民族自豪感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殖民时间再延长些也许会好些。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
我不喜欢一些当代青年中那种完全放弃民族文化立场的态度。我在散文《道士塔》中谴责了盗走敦煌藏经洞古物的斯坦因和伯希和,引用了一位青年诗人要和烧毁圆明园的额尔金决斗的诗,并且表示要拦下他们运载文物的大车。有的青年批评家发表文章说,拿走就拿走吧,反正他们比我们保护得好,研究得好,还是识相一点的,给他们吧。我们知道,希腊正在向英国要回巴特农神庙古物。希腊说,巴特农是联合国文化保护单位,是全人类的。但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文物要生存在原来的环境里才合适。这件事,中国比希腊更痛切,因为中华古文明是活生生的文明。活生生的文明被截去了一段,是何等的让人心痛。由此,包括敦煌在内的一切流失的文物,迟早都应该回归中国,留在中国。中国人能保护好、研究好自己的文物。在圆明园被烧80天后,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没有多久,甲骨文就被中国学者解读了。
年轻人要有适当的民族精神、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这是大文化母体子民应有的心态。其他文化也不会接受那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过激攻击态度的人。
中华文明的优点也带来了缺点。中华文明是长寿的,但长寿也会有“老年病”。有一个惊人的现象,开天辟地的人类智能大师们,都诞生在2500年前:孔子、释迦牟尼和亚里士多德。于是,我们看到,希腊哲人在海边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因此,西方自然科学特别发达,印度神学则特别发达,中国人际关系特别发达。这在当时没什么不好,相反,清新、健康、务实是孔子思想的特点。孔子不太想自然的东西,更不愿谈鬼神,他认为先把人的事搞清楚再说。这种思想一直传下来,讨论人与人的关系讨论了2500年,使得人际关系终于成为中华民族的重大包袱。
在文化上,我们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有处理好保护传统和鼓励创新的关系,也没处理好个性自由和社会公德的关系。此外,在文化生态上,还有一些关系容易出错,需要小心处理,例如: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只有在民族的整体文化获得了全球文化的坐标后,这句话才是对的。否则,将为民族保守主义留下一条不应该有的后路。我们民族有许多不好和世俗的东西,它们都不属于应该贡献给世界的财富。即便自己认为好,也要在另外的时空进行评判,获得认同。说句玩笑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如果没有前提控制,山区农民可以做联合国秘书长了。先进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上一定要获得一个人类原则。这里有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
“文化人应该坐冷板凳。”这句话也应质疑。多数学问都应受到社会检验,蹲在房子里就能检验?不能。人文科学和社会的实验室,都应该是社会现实。学者不能只坐在家里抄前人的书。社会变革需要文化引领。在这样重要的转型时刻,文化人却躲起来了,这是不道德的。崇尚记忆、崇尚关门做学问都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没有转型。大学课堂空洞、虚假、陈年八股的内容太多,学生只求文凭。
不能过分迷醉地域性文化
每个地方都认为自己好,都觉得自己是中国第一。比如,我和安徽朋友交谈,他们就说我们安徽如何如何不得了,出过7个总理级的人物;“五四运动”是什么?就是两个安徽人批一个安徽派,即陈独秀、胡适批桐城派;北京是雄伟,但也是朱元璋迁都过去后才繁华的;京剧是国剧,也是徽班进京后才兴起的等等。我的家乡是浙江,也听到浙江人自豪地说,如果中国文化没有浙江人,将会怎样?起码失去了一半辉煌。现在,一些很小的城市也在争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名人更被各地争来争去。其实,中华文明是宏伟组合,共同拥有屈原、李白、杜甫。地域文化离开中华大文化的背景就不行,不能分割出来。中华文明的魅力就在于规模宏大、气壮山河。
上海也不能迷醉地域性的所谓“海派文化”。上海文化的优点在于多方组合,上海文化不是仅仅靠上海本地人搞出来的。鲁迅是最后10年才来到上海的。他的主要作品是在北京写的。一流的文化人,可以说都是流浪者。上海了不起的地方不是海派文化,而是吞纳百川的气势。“海派文化”只是市民和一部分低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解放前,上海有较为安全的租界和发达的文化企业。当年,胡适和林琴南在北京争论白话文和文言文,不可开交,最后了结这桩中国文化历史公案的不是官府,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那时,商务印书馆掌握全中国的教材出版和发行。张元济决定来年的教科书用白话文,白话文就通行全国,逼得年迈的老祖父也得用白话文给上学的孙子写信。上海通过商业运作,创造了文化奇迹。王元化先生说,当年北京教授要印好的书,都到上海来。后来,商务印书馆请胡适这位“中国第一教授”来做编译部主任,这么小的职务,胡适还不敢当,请来他的老师王云五。梅兰芳出名也是在上海,爱因斯坦、海明威、泰戈尔等诺贝尔奖得主都来过上海,上海可以把他们住过的房子找出来,挂个纪念牌,以此来说明上海文化有人类意义。不能说月份牌就是上海文化的主要标志,海派文化也不是上海文化人所设想的。文化是流通体,吐纳量越大越能表现自己的优势。现在上海文化吐纳不够,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比出几个戏、几篇文章都重要。上海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品,都要有中华文化的大气派,不要只写小事情,否则就不是文明继承者。有了中华文明大气魄,再加上人类原则,就有意境了。
关于中华文明的复兴
1997年白先勇在新加坡预计,2020年中华文化会在世界全面复兴。他是学欧美文学的著名作家。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20年是一代,如果再过一代,文化还没有上,这个转型是不成功的。世界上有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但是文化上不去,就没有尊严。很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华文明,是舞龙舞狮、放鞭炮、描金描凤、中餐馆之类的。事实上他们对中华文明根本不了解,只知道“中国威胁论”。许多人以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就是统治别人。其实,文明复兴不是以压倒、消灭、侵犯别人为条件的。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21世纪有8种文明能够生存下来,但是能够成为主要文明的只有3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现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起了很大的冲突。在三种文明力量鼎立中,中华文明有优势,它不走极端,有可能调解前两种文明的矛盾,带动其他文明走向共荣。文明,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敌人,野蛮、恐怖就是文明的敌人。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人要让世界知道,楚辞是什么,唐诗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可避免。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仅是经济形象,还有文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