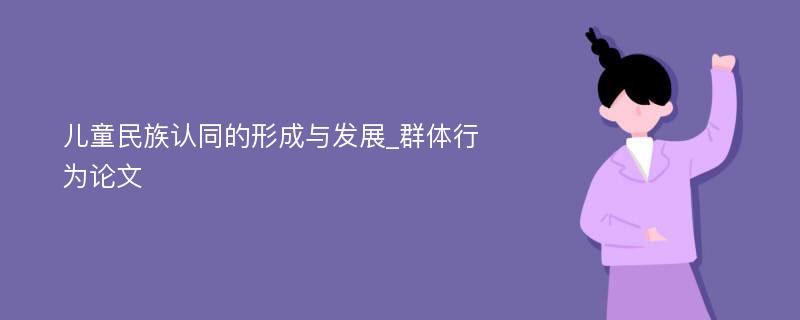
儿童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13)06-0018-07
一、引言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重要内容。民族认同与族际关系、国家的稳定与团结有重要的关系,还与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国内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与心理健康、文化适应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方面,[1-3]对于儿童在何时产生民族意识以及随年龄变化的规律,还未有研究涉及。本文对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介绍了国外关于民族认同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民族认同在族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开展本土化的研究,找出我国儿童民族认同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以便针对儿童民族态度转变的关键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民族认同被定义为是社会认同中的族群成分,即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其群体成员身份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且多维的、涉及自我概念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在Ashmore等人文献分析的基础上,Phinney & Ong提出了民族认同的一些成分:自我分类和标签,投入和依恋,探索,民族行为,民族态度,民族价值观和信念,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等。[4]这些成分包括了普遍的共同成分(如情感上的归属感),也包括了不同民族特殊的成分(如价值观和信念),研究者往往在研究的过程中选取了不同的成分进行研究。
二、民族认同的形成
儿童在几岁就已经具有民族认同意识,能够明显地区分民族,能够意识到自己与其他民族是不同的?北美洲儿童对种族分类在5岁就能达到类似成人的概念。[5] [6]Hirschfeld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4岁儿童在对人进行分类时,并不是单独地依赖于感知到的信息。相反的,儿童似乎能精炼种族类型,认为种族具有某种属性,即在人出生时就固定了而且不随着时间和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儿童的民族概念与成人是一致的。[7]
在探查学前儿童何时形成民族认同意识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传统强迫选择的方法,即先给儿童呈现一对不同种族的玩偶,而且这对玩偶与被试的性别相同。每对玩偶除了头发和肤色有区别之外其他方面都是高度相似的。主试口头上告诉儿童某一玩偶代表特定民族的成员,之后从幼儿的识字卡片中选择14个儿童最熟悉的形容词(积极、消极词各半),将这些形容词写在卡片上,并且每个形容词都附带一幅具体的插画。根据卡片上呈现的词语提问,要求儿童把这些形容词分配给两个玩偶中的其中一个。如:给儿童展示一对玩偶,告诉他一个是白人小朋友,一个是黑人小朋友。然后随机取出一张卡片,卡片上的词是淘气。主试问儿童:“这个卡片说的是淘气,有些小朋友很淘气,他们经常拿蜡笔在墙上乱画。这两个小朋友谁淘气呢?”要求儿童将卡片放在他认为能很好回答这个问题的玩偶前面。[8]
有学者认为这种强迫选择的方法混淆了内、外群态度,强迫使其产生了一种负相关。近来发展起来的多元民族态度测量方法(MRA)可以部分地分离内、外群态度,儿童可以把每一个形容词分给一个或多个群体。首先向儿童展示三个与其性别相同的白人儿童、黑人儿童和土著印第安儿童的玩偶,每个玩偶之前放置一个小盒子。这三个玩偶只在头发和肤色上有区别。之后选择20个形容词,积极消极各半,还有4个中性补充词,将每个词语写在卡片上,并且附带一幅小插画。对于每个形容词,小孩手里都有3张相同的卡片,要求他们根据问题将这些卡片放在一张或者多个盒子中。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很调皮,他们经常拿蜡笔在墙上乱画,谁调皮呢?是白人小朋友,黑人小朋友,印第安小朋友,还是不止一个小朋友调皮呢?”[9]
很少有研究能直接探查儿童的内、外群态度的关系,其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儿童早期,内群偏爱是否一定伴随着外群歧视的出现。另外也有些研究采用图片的方法,方法类似于玩偶法,将相应民族儿童的图片用来代替玩偶。有研究者认为玩偶对于低龄儿童更形象、更具体,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而且更加便于儿童识别。但是究竟采用哪种方法更能够有效地测查儿童在几岁开始具有民族意识,没有定论。
三、民族认同的发展
(一)儿童的民族认同发展
民族认同发展大多采取了横断比较的研究方法,即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进行比较。而且对于民族认同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群体中的青少年和成人,对于此类群体中儿童的发展状态研究很少。[10][11]其中的一个原因要追溯到认同发展理论所提出的假设,即在青少年期之前,民族认同发展较少,[12-14]或者说,即使发展了,也不过反应的是父母的社会化。
对儿童民族认同的研究由两条相对独立的路线开展。第一条路线主要关注儿童对内、外群成员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少数群体儿童和主流群体儿童中的表现会有所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在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时,主流群体的儿童表现出较强的内群偏爱。这种偏爱会影响各个阶段的信息加工顺序,尤其对于认知不成熟的儿童来说,更是如此。[15][16]相对于少数群体的儿童来说,内群态度先是中度积极的,而后向外群偏爱变化,并且这种态度到儿童中期还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种自我报告的测量结果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和自我表象的影响,因此需要采用内隐态度的测量方法,以降低这些动机的影响,并与外显态度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对比。
第二种路线关注的是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它较少关注民族态度和刻板印象,而更多的是儿童对其群体成员关系的理解和情感的卷入程度。[15][17]根据认知发展理论,儿童在7岁左右出现具体运算思维,这也标志着民族认同过程的开始。具体运算思维的发展被认为可以影响儿童对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理解、[18]信息的搜集,表现出与民族认同相一致的行为,识别那些可以区分内外群成员的行为、特征、规范和价值观念。[19]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说明认知的成熟可以预测民族认同的发展。也有研究结果支持此假设。如有研究发现认知水平的提高与民族认同的发展有显著的相关,因此,可以预测更高的外显自尊、提高民族身份的重要性、对于内群的态度不管在内隐还是在外显测量上都更为积极。[20]Newman认为对于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发展研究,应该放在心理成熟的水平以及时间的背景中来理解,而其中自我的发展是一个较好的指标。处于自我保护水平的个体虽能够意识到民族群体成员关系,但是对民族认同的探索较少,也很少自我反省。而在遵奉者水平上的青少年对民族群体有积极的归属感,而且认为群体关系也是和谐的。[21]虽然这些结果都支持了认知发展理论,但是民族认同是由多层次的概念所组成的,例如:内群的归属感,民族群体成员关系的重要性,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了解并引以为傲、感知到的群体成员评价,[22]此理论只解释了民族认同发展的一部分,忽视了儿童对民族认同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的解释。
相反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对感知到的社会不平等做出反应时,出于自尊的需要,人们倾向于认同他人明显肯定的或者是在价值维度上比其他群体更好的群体。[23]与此假设相一致,大多研究发现民族认同与自尊成正相关。[24]从此假设中可以得到启示,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水平的提高应该与高自尊、更多的内群偏爱、对其民族身份重要性的高评价有关系。
(二)民族认同发展模型
Erikson提出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是以自我为基础的。他认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自我作用的结果,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和确立标志着自我的发展和成熟。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对自身更为关注,会反复思索诸如“我是谁”等问题,对各个维度的“我”的整合或统一就是自我同一性确立的过程。他在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青少年期是其中的第五个阶段,主要的发展课题是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和防止同一性扩散。所谓同一性扩散是指同一性的整合失调,个体无法认识自己,处于一种充满疑惑的扩散、弥漫状态,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将来准备怎样。[12]在Marcia把Erikson的认同发展理论概念化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Phinney提出了一个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她认为民族认同的形成主要包括对民族的探索与承诺,并且根据探索和承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认为个体的民族认同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1)认同分散——缺乏探索和承诺,个体对他们民族身份有较少的兴趣,几乎没有群体归属感;(2)认同排斥——承诺但是没有探索,个体表现出对群体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但是对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意义几乎较少去探索或者询问;(3)认同延缓——探索但是没有承诺,个体努力了解和理解他们的民族身份,但是对民族归属感是模糊和矛盾的;(4)民族认同形成或者成熟的民族认同——既有探索也有承诺,个体考虑过并努力去理解自己民族对自身的意义,并且对自己民族有清晰的归属感。[14]
Phinney采用纵向研究检验她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结果发现有1/4的青少年处在第四阶段,也就是达到成熟民族认同,而且此类青少年在自我认同和心理适应问卷上的得分也较高。[14]另外的一项研究表明达到成熟的民族认同的青少年会对他们怎样受其他群体影响表现出很好的自我觉察,而且往往认为群体间接触有利于理解自己群体的文化,能够将民族多样性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同时看待。他们能够较好的理解群体间关系的复杂性,并能对这种多样性的正反情感都有很好的表达和反思。而民族认同处于分散阶段的青少年很少通过群体间接触获得这种认识。[25]
对于Phinney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很难确定个体具体是处在哪一个阶段,也没有具体年龄特征划分,而且个体认同发展的趋势也不是都依照着这四个阶段顺序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对于认同状态在一段时间里的横向研究、纵向研究都表明随着时间的增长,青少年在更成熟的认同状态(延缓型和完成型)中人数呈增长趋势,在不成熟的状态(早闭型和弥散型)中的人数呈减少趋势。
(三)民族认同的发展与族际关系
1.民族认同与族际态度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后,民族认同与族际态度的关系受到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过分的民族认同容易产生消极的民族间态度。而发展取向的民族认同观点则认为,民族认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不成熟而逐渐走向成熟的,成熟的民族认同意味着对民族群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对自己群体成员身份有强烈认同和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有助于降低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因此发展成熟的民族认同与积极的民族间态度具有正相关关系。[26]Quintana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能够采择其他民族以及主流群体的观点,增加对偏见、群体间矛盾和外群体的容忍性以及群体接触的意愿。[27][28]一项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民族认同不仅可以预测积极的内群态度,同时有助于促进积极的外群体态度(减少偏见和负性刻板印象)。[29]Phinney的研究表明成熟的民族认同与积极的群际态度成正相关。在少数民族当中,成熟的民族认同可以使个体对来自其他民族群体的成员更加开放和接纳。通过降低威胁感和焦虑感,成熟的民族认同可以促使个体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25]
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民族认同与群际态度之间存在积极的联系。但是民族认同与群体间态度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和主流群体的影响会有所不同,这种影响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表现得更为凸显。另外,民族认同在群体过程中(感知到的歧视、刻板印象、民族偏见、群体自尊)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研究者也少有涉及。
2.民族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
儿童具有民族认同意识,在能够区分出自己和其他人是不同的之后,就会产生民族态度。这种态度会影响到群体间的交往和群体行为。如在群体接触时的意愿,是否会有焦虑感,是否对其他民族有偏见、歧视和刻板印象等等。成人存在内隐态度已经得到了证明,而且也有能力用这种态度来预测一系列的行为,包括对外群体的友好度、工作的选择以及资源的分配。[30]理解儿童的内隐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群体间的态度在人的一生中都很重要。Baron等人试图探查儿童对社会群体(民族)的内隐态度在多早就已形成,这种内隐态度与他有意识地表达出来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研究选取了三个年龄段的被试,来探查他们对社会群体内隐、外显态度的发展。结果发现白人儿童早在6岁就表现出偏爱白人、反对黑人的内隐态度,外显态度与其是一致的。成人也表现出与6岁儿童同样的内隐态度,但在外显上对白人和黑人的偏爱程度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成人的内隐外显态度是不一致的。而儿童在10岁开始表现出内隐与外显态度的分离,即他们的内隐态度虽然还是保持稳定,比较偏爱内群体,但是在外显态度上对内群体的偏爱程度明显地减少。[31]但是此研究的被试涉及的都是白人,对于黑人被试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无从得知。另外一项对白人、黑人儿童的内隐群体偏爱的研究发现:白人儿童表现出较强的内群偏爱,但是黑人儿童却没有发现同样的结果,儿童的内隐群体偏爱与外显偏爱之间相关性不显著。[32]对群体的内隐、外显态度之间的关系,随年龄的发展变化趋势,国内还没有研究涉及。另外,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内隐、外显态度,还应该关注主流群体中儿童的相应态度的发展。
3.内群偏爱与外群歧视
内群偏爱与外群歧视谁先发展起来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Brewer基于她的进化论认为内群偏爱有领先的地位,因为它有保持群体信任的存在价值,这似乎也就很合理地从她的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那这个启示就很关注儿童在哪个年龄段中形成内群偏爱,而且它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33]
如果内群偏爱先于外群歧视产生,那么它会在儿童很小的时候就产生,而且在被试足够多的时候达到很高的显著性水平。Allport和Cameron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在没有不喜欢外群体的条件下会更喜欢他自己的群体。[7][34]已有对学前白人儿童研究中,或采用混淆的内外群态度测量或采用开放式的单一问题,比如“你想跟谁做朋友?”。在后一种测量中,3~6岁没有什么变化。而在混淆测量法中发现,儿童的这种偏爱白人的倾向在一些3岁的被试中很高,而在5岁时有显著的升高。[35]但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是这种变化到底是内群偏爱还是外群歧视造成的。一位以色列的研究者单独地测量了这两种态度,他发现在对犹太人的消极态度上,6岁组并没有显著地高于3岁组。但是对阿拉伯人的消极态度上,6岁组的得分却相当高。[36]这些研究表明儿童在3~6岁中的某个时段能获得民族态度。
Aboud在对4~7岁白人儿童的研究中,探查儿童内、外群态度的获得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这两种态度在民族同质学校的被试中是负相关的,在民族混合学校中并没有发现相同的结果。儿童在5岁之后才表现出内群偏爱,而且它与社会认知的发展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外群歧视的发展相对弱且缓慢。[9]
总的来说,对于内群偏爱和外群歧视谁具有领先地位,没有明确的定论。另外儿童对内群体偏爱是否一定会导致对外群体的歧视,这也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影响儿童民族认同发展的因素
儿童民族认同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父母与同伴的种族态度,家庭的社会化程度,父母的文化程度和接触等等。
Allport认为在儿童时期,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形成和价值观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社会化作用。然而青春期以后,同伴对青少年民族态度形成的社会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7]Aboud发现尽管儿童预测其父母的民族态度与他们的相似,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且儿童与其朋友的民族态度相关性也不显著,说明儿童并不是从父母或朋友那里学到民族态度。但是,父母会将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状况在生活当中传递给子女,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37]也就是说,父母会通过他们对外群体的看法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民族态度。也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家庭的民族社会化水平的高低可以预测民族认同的探索的水平,青少年的家庭民族社会化水平越高,对他们自己民族的探索就会越多,而且更加清楚民族对于自身的意义。外貌作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家庭的民族社会化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38]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影响因素。秦向荣对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本民族认同还是中华民族认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都能很好地预测之。母亲的学历为研究生则子女的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得分最高。[39]国内研究者对藏族学生民族认同的研究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民族认同有显著的影响。[40]Dennedy-Frank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研究发现,对本民族认同较高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期望会促使子女表现出对本民族较高的认同水平。[41]而且,父母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学历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有更多的接触,能够理智地看待本民族身份、文化以及主流文化。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差异,使子女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使子女民族文化的接受能力、民族历史的了解程度也产生巨大差距,这些都共同影响了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程度。
另外,与外群体朋友的接触也会影响儿童民族认同的发展。Allport的接触假说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与外群体成员接触程度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减少对该群体的偏见。[7]共同内群体模型解释了接触在减少偏见时的效应。该模型认为,通过与外群体的接触,个体对内群和外群的认知表征发生变化,把“他们”变成“我们”。这样,对外群成员产生更多积极的情感,偏见也就会减少。[42]另外,也有研究结果发现接触与更少的偏见有关,Aboud指出小学生的跨种族友谊与他对该群体成员的偏见成显著的负相关。[43]对群体接触的研究发现接触可以降低焦虑,减少威胁,并且降低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产生对自己群体成员的信任和对其他群体更大的开放性,进而改善群际关系。高承海等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得分随年级增长呈下降的趋势,随着不同民族成员的相互接触和交流,民族身份逐渐淡化。对于少数民族来讲,其民族认同与对主流群体的态度之间成负相关,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认同越高,对主流群体的态度就越消极。[3]少数民族成员通过与外群体的接触,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都能产生更好的理解,增加对其他民族群体的容忍性,形成成熟的民族认同。这些研究也说明,为少数群体提供与各民族互相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与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同等重要。
五、未来研究展望
民族认同是自我身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研究都关注少数民族群体青少年和成人,很少把研究视角投注到低龄儿童。而且也很少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一生的发展状态。另外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经验的丰富,每个年龄段处于怎样的发展状况,也少有研究涉及。
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世居在一起。而国外对民族认同所开展的研究大多是在移民国家,与我国的国情不符。另外,在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宗教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是高度重合的,这点和国外的社会背景也是不同的。国内研究大多数是对西方研究结果的验证,对西方一些研究进展和理论的介绍,但是对于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儿童民族认同发展的特点缺乏相应的研究。民族认同在群体过程中(感知到的歧视、刻板印象、民族偏见、群体自尊)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点在国内也少有研究涉及。国内也缺乏各民族认同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开展本土化的研究,构建本土化的民族认同发展理论。
民族认同是个体获得自尊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它还与民族关系、国家的团结与稳定有重要的关系。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民族认同的变化规律,能够为指导和干预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促进各民族儿童的健康发展。同时,找到儿童民族态度形成与转变的关键期,能够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取得良好的效果,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积极的互动与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