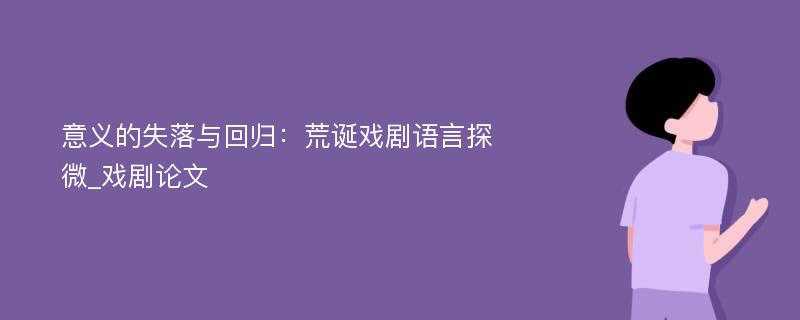
意义的失落与回归——荒诞派戏剧语言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派论文,戏剧论文,意义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戏剧迥然不同的戏剧形式——荒诞派戏剧。其代表性作家贝克特、尤奈斯库、品特、阿尔比等,由于各自的现实际遇、文化传承及个人秉性的不同,所创作的戏剧在主题、立意及风格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在表现荒诞感受、荒诞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集中体现为内容与形式、意蕴与言说在美学与技巧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实现了贝克特所说的“那种无所表达、无以表达、无从表达、无力表达、无意表达,而又有义务表达的表达”。〔1〕那么,荒诞派戏剧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了这种超绝的“表达”呢?笔者认为,其方式之一就在于荒诞派戏剧以其骇人听闻的胆识在其戏剧中对语言尤其是叙事和对话施以了极度的变异揉扯,使其旧有的意义失落,新生的意义回归,从而实现了对荒诞感、荒诞意识的揭示与显明。
一、语言叙事意义的失落与回归
戏剧通常有类于小说的叙事性,而叙事性在戏剧艺术里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说的通过人物的行动所构成的情节。古希腊以来,西方戏剧不管是悲剧、喜剧、还是后来的正剧,总是视情节为戏剧的核心,由情节而体现出语言的叙事意义,从而完成以内容、意蕴为主的二元统一。就西方戏剧而言,这种传统一直持续至荒诞派戏剧问世为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却早已在小说领域里有了突破。语言叙事早已经开始了由内容向形式、意蕴向言说的革命性变迁。具体而言,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小说,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小说已经率先从美学上拓开了表现现实的新途径。这种开拓性,除了我们所说的揭示出关于世界荒诞、人生虚无的心灵感受,并同时预告了可能渗透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荒诞性而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一种发掘荒诞性、命名荒诞感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以形式自身的符号功能,组织、整理并最后形象化地显现了人生的荒诞性,表现了人心的荒诞感。这种言说方式在荒诞派戏剧以前的西方戏剧中却没有找到自己发育成长的条件和大显身手的舞台。马丁·埃斯林曾在论及荒诞派戏剧时这样说:“荒诞戏剧不是仅仅根据主题类别来划分的,吉罗杜、阿努依、萨拉克鲁、萨特和加缪本人大部分戏剧作品的主题,也同样意识到生活的毫无意义,理想、纯洁的意志的不可避免的贬值。但这些作家与荒诞派作家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他们依靠高度清晰、逻辑严谨的说理来表达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荒唐无稽,而荒诞派戏剧则公然放弃理性手段和推理思维来表现它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毫无意义。如果说,萨特或加缪以传统形式表现新的内容,荒诞派戏剧则前进一了步,力求做到它的基本思想和表现形式的统一。”〔2〕应该说,埃斯林是比较准确地以存在主义戏剧为例,区别了以往戏剧形式与荒诞派戏剧形式的根本差异。荒诞派戏剧是以与荒诞感相统一的艺术形式、语言言说方式呈现出荒诞。这种方式却异常奇妙地与卡夫卡、萨特、加缪的小说艺术方式产生了深度契合,从而将荒诞从小说叙事延伸至戏剧叙事,真正从艺术上将荒诞扩展为一个世纪性的重大美学命题。由之,我们对荒诞派戏剧艺术的研究也就无意间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荒诞感的形式外观的研究,是对20世纪荒诞文学所开辟的以形式、言说为主的新的美学方式的研究,也就是对文学艺术语言叙事新方式的研究。此外,我们不妨以卡夫卡小说的语言叙事方式作为出发点,以求对荒诞派戏剧的叙事方式有更具历史感的理解和认识。
语言叙事方式的新变迁在卡夫卡的小说言语方式上体现为形式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所谓形式逻辑指的是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情节的发生、发展的特定逻辑。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它往往呈现出一种突兀离奇、荒诞怪异、悖理逆情的特征:人物行为全是破碎零乱的任意拼缀,事态的演化缺乏基本的理性准则和情感限度,时空背景模糊不清,怪异无比的事物被极其平常地引入了日常生活。所谓历史逻辑指的是小说中人物行为及情节发生、发展之所以突兀离奇、荒诞怪异、悖理逆情的深层次文化心理原因。由此,我们阅读卡夫卡小说的时候,不得不调动我们关于西方现代历史文化心理的所有背景知识,撇开一个个扑朔迷离的现象疑团,以心灵的感悟去体验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心理内涵,去发掘潜隐于荒诞表象下面的历史逻辑线索。于是,我们发现,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的不合形式逻辑,恰是卡夫卡凭着自己特殊的心灵感受力、创造力,深入于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范式的盲区,发掘并使其显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只有借助于卡夫卡小说中这种由主体所创造出的不合形式逻辑,人们才终于猛然深省,觉察到自我人生的真实境遇。
荒诞派戏剧的叙事也包含着形式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二元命题。就形式逻辑看,荒诞派戏剧中的人物行为完全是无情理依据和日常目的的任意堆砌,因而其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也呈现出突兀离奇、荒诞怪异、悖理逆情的特征。马丁·埃斯林曾这样总结说:“假如说,一部好戏应该具备构思巧妙的情节,那么这类戏(荒诞派戏剧,下同——作者注)则根本谈不上情节或结构;假如说,衡量一部好戏凭的是精确的人物刻画和动机,那么这类戏剧常常缺乏能够使人辨别的角色,奉献给观众的几乎是动作机械的木偶;假如说,一部好戏要具备清晰完整的主题,在剧中巧妙地展开并完善地结束,那么,这类戏剧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假如说,一部好戏剧要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人的本性,要通过精确的素描去刻画时代的习俗或怪僻,那么这类戏剧则往往使人感到是幻想与梦魇的反射。”〔3〕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戈多是谁?戈多与两个流浪汉有什么关系?两个流浪汉又为什么要等待戈多?戈多为什么不来?作为全剧人物行为、情节发生、发展之支撑的这几个关键问题完全是一串无解的谜。整个剧情所应具有的语言叙事被拆解了,语言的叙事意义也随之失落了。这种失落折射出了现代西方人面对现实人生的某种焦虑与困惑之心理失落。所以《等待戈多》1958年在美国上演时,导演问作者戈多到底代表什么,贝克特回答说:“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4〕其它荒诞派剧作也与此一样,可以对其提出一连串无解的疑问。
现在,让我们再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追寻荒诞派戏剧语言叙事意义之所以失落的深刻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当我们前面作形式逻辑判定的时候,我们无意间是遵循着一条与传统戏剧相一致的理性主义语言陈规,或者说,是以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追问荒诞派戏剧语言叙事的现实语义。这种语境与语义的错位,也就造成了语言所指与能指的断裂,从而生出了荒诞感。还如马丁·埃斯林所言:“这类戏剧,使批评家和戏剧评论家接受起来仍然莫名其妙,它们已经造成和还在继续制造的令人迷惑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由于它们属于一种新的、发展中的舞台程式,这种程式既没有被普遍认识,更谈不到对它作出解释。用另外一种评论标准和原则来衡量以这种新程式写出的戏剧,则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令人难以容忍的不礼貌的欺骗。”〔5〕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戏剧和传统的戏剧两者追求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它们所采取的方法也大不相同。只能用荒诞派戏剧的准则来衡量这些戏。”〔6〕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荒诞派戏剧所特有的语言叙事逻辑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在意蕴。一是现代西方人所处的非理性社会历史处境所赋予他们的心理感受;二是现代西方人所具有的非理性哲学意识所赋予他们的认识范式。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断裂、错位也就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逻辑解释与非理性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意识的断裂、错位。如加缪所言:“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7〕比如,当我们追问《等待戈多》中人物行为的目的和剧情发生、发展的理由时,我们的理性主义历史语境已经预先规定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理性原因和目的的坚信,从而也使我们预先假定了人类社会中人的行为被派定的角色使命,同时也让我们预先认可了文学作品里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和规则。但是,这种历史语境在面对现代西方人的现实遭遇时,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直得心应手的语言言语终于陷入了语塞的尴尬之中。正如尤奈斯库所言:“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除了使人付之一笑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的反应呢?”〔8〕由此,我们再看《等待戈多》:贝克特是以其惊世骇俗的举措从旧的历史语境中勾消了世界原因、人类社会目的的信条,毫无遮掩地裸露出现代人类生活破碎零乱的本然情状。再由此,贝克特同时也勾消了生活于世界上、人类社会中的人的理性主义角色规定,光秃秃地凸现出现代人空虚无聊的本然姿态。再由此,贝克特还同时勾消了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固有联接点,豁然醒目地显示出现代语言话语漂浮破碎的本然形态。反过来,经过数番无情勾消后的世界和社会也就成了黄昏下的荒原,人生也就成了无意义的漂泊流浪,戏剧(文学)也就成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喧哗与骚动”。于是,《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也就是现代人无所皈依、失去家园、也失去梦幻的真实写照。再进而言之,人作为人的特性又在于他们决不满足于动物样世界的狭小和窘促,他们需要对自我处境有心理上的把握和情感上的理解。所以,他们命中注定会永恒地期待着某种超验的澄明。因此,等待戈多的关键不在于“戈多”,而在于“等待”。它是注定挣扎于荒诞、又不甘于荒诞的现代西方人精神期盼的象征。这就是两个流浪汉的人生行为,也是《等待戈多》剧情的意义。当然,这种期盼由于等待的虚无又注定归于荒诞。正如加缪所说:“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9〕
语言叙事意义的失落与回归在荒诞派戏剧里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表现方式,更将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所包藏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的明确性、唯一性变得模糊、偶然、歧义。这种语境置换的内在依据是价值观念的转换,即抽象的人类集体利益、历史主义的美妙远景被具体的个人生命追求、当下世俗生活中的痛苦与欢乐所代替。生命的权力、思维的权力、价值选择的权力凭着“上帝已死”的名义,还给了每一个体意义上的人,也还给了每一个自主的读者或观众。阿达莫夫的《侵犯》以其荒诞的剧情表述了这个隐晦的思想。剧中主人公皮埃尔忠于对亡友的深厚友谊而整理其遗稿。他象忠于上帝的教义一样费尽心机从其遗漏与模糊的记忆中追索文稿的原意。结果在冥思苦想中疏离了属于自己个人的生活,忽略了属于自己个人的情感。于是,享用不到生活情趣的妻子终于同“不速之客”一起离去了。注定失败的主人公最后若有所悟地说:“我现在决定要象一般人那样生活……。只要我找不到办法过完全正常的生活,我将一事无成。”于是,他撕碎了文稿,走向了忠于自己的死亡。尤奈斯库通过在其戏剧叙事中多次转换发展方向,既给戏剧中人物行为、戏剧的情节发展提供多种任其选择的人生结局,又给读者或观众提供多种任其选择的理解和阐释。比如《阿麦迪或脱身术》的第三幕就有意安排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衍变方向和结局。由此,他将人们在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中一向坚如磐石的庄严人生变成了随时随地可以任意粉墨装扮后登场表演的游戏。宇宙规律、历史秩序、社会目的已然失去了唯一性、严肃性,变成了阿达莫夫笔下那一堆堆任孩子嬉戏玩耍的碎片。和传统的反映人生的文学相比,尤奈斯库的这种玩笑态度却真切地泄漏了现代西方人对世界人生的深刻领悟和严肃阐释。尤奈斯库在写作《秃头歌女》时,除了现在所具有的结局外,也曾经考虑设计了另外二种结局方式:一是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争吵时,女仆再次出场,宣布晚餐已经准备好。争吵停止,两对夫妇退场。二三名混在观众中的演员发出嘘叫声冲上舞台。扮演的剧院经理和几名宪兵出场,枪杀了上台的观众,并手拿着枪,命令观众离开剧场而告终。二是两对夫妇争吵时,女仆大声宣布“作者到”。演员向作者鼓掌,作者走向前台,向观众伸出拳头大叫:“伙计们,我要你们的命。”〔10〕主要是因为技术上的困难,这两种绝妙的结局设计被放弃了。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两种结局的共同特点皆是彻底推倒戏剧舞台上的第四面墙,让台上的剧情与台下的观众搅和在一起,从而使演戏与日常人生之间的界限消失。另外,尤奈斯库此剧的剧名也是他根据剧中扮演消防队长的演员的偶然口误而定下的。正象萨特对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分析中所言:“荒诞的创造者丢失了一切幻想,甚至不幻想自己的作品是必要的。相反,他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到他们作品纯属偶然。他希望能在作品上写下一行题词:‘本可不作’。”〔11〕萨特的话用于对荒诞戏剧的诠释应该说是正中其要害。但反过来,荒诞派戏剧的意义又如大卫·盖洛威的评论:“荒诞派的艺术是反中产阶级和反体制的;它嘲讽的往往是旧时代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各种信仰,这些信仰虽然已不再代表真理并已变得陈腐,但人们却依然紧抱着不放。但是荒诞派的艺术却往往必须寻求荒谬的形式和荒谬的说法,以超越现实世界的荒诞性。”〔12〕
二、语言对话意义的失落与回归
戏剧艺术象一般叙事作品一样,还有着人物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戏剧艺术中具体体现为人物的对白。也就是说,戏剧还须通过人物的对白构成戏剧对话,由对话而说明、突出人物行为和情节发生、发展的意义。应该说,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戏剧,正是通过清晰、明确的对白来完成语言的对话意义。这种传统也可以说一直持续至荒诞派戏剧问世为止。
从表面上看,荒诞派戏剧似乎还有人物的戏剧对白,但它的许多对白因为剔除了相应的逻辑性,从而也就消解了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在功能上只具有独白的性质。比如《等待戈多》从头至尾少有完整交流信息的对话,更多的只是各说各的独白。特别是当波卓煞有其事地命令幸远儿思想时,幸运儿的所谓长篇演讲,引出的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语堆砌。再如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第一场史密斯太太连续九大段台词其实只是自说自的独白,其间仅因为穿插了八次史密斯先生的“看报,嘴里啧啧作响”,才表明还有一言说的对象存在。《新房客》中也有类似的自说自独白,如新房客来了后,女门房一直在旁边唠叨,甚至对搬家具的搬夫怒叫,却得不到任何反馈性的回应。但是,荒诞派戏剧中也有一些对话交流,但因为其内容乱七八糟、缺乏内在逻辑关系而不能构成交流。还如尤奈斯库《秃头歌女》第一场,史密斯太太说至第九段话时,与史密斯先生有了相互的对话,但其内容却颠三倒四、矛盾百出。例如言及去世的博比·沃森,先说死了二年,继而又说一年半,再后又说三年、四年。更后又问及博比·沃森与其太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此后又言及博比·沃森太太年轻守寡,没孩子。后面又言及她如果再嫁,谁照看她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后恍然发现所谈的博比·沃森几乎是不同的几个人。由此,所有的对话在交流上皆归于零。《阿麦迪或脱身术》里阿麦迪与邮差之间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主人公对邮差说:“先生,这真是搞错啦。我不是阿麦迪·布西尼奥尼,我是阿一麦—迪一布西尼奥尼;我不住在将军街29号,而是住在将军街29号……”由此,真假对错全在一个平面的条线上,一切交流的可能性皆由于差异的缺失而全然丧失。
另外,荒诞派戏剧里还有些对话既没有自身矛盾,内容也算完整,但没有相互交流的语言契机,实际上只是一大堆废话的排列。如《秃头歌女》第七场里,马丁太太以讲故事的洋溢热情讲她看见一个人单膝跪地、身子前倾系鞋带。马丁先生讲他看见一人在地铁长椅上看报。第八场中,一个消防队长上场讲了一通关于灭火的话,又讲了一个狗和公牛的所谓寓言,再后来讲了一个感冒的故事,串出一大堆说不清的关系。第九场中,玛丽背了一首所谓起火的诗。品特的《看管人》中的人物对话,除了被称为愚钝的哥哥阿斯顿之外,其它二人即米克与戴维斯的对话中几乎全是谎话、废话。不仅无助,实际上更是有碍于语言的交流。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一开场,陌生的杰利便对陌生的彼得说:“我去过动物园了,我说了,我去过动物园了。先生,我去过动物园了。”对话的开始由于其特殊的封闭性,也就意味着对话的结束、交流的阻隔。品特的《生日晚会》里,歌德伯根与麦坎对斯丹利的一大通咄咄逼人的质问中的言语自身并不矛盾,也有其固有的内容,但与斯丹利的景状交流却形成了若干难以连接的断裂错位,因而构成了交流的阻断。荒诞派戏剧中还有些对话自身意义完整清楚,但因为与相应的行为指认割裂而变成了荒唐的废话。如《等待戈多》中,两幕的结尾都说到“咱们走吧”,但都坐着、站着不动。尤奈斯库的《椅子》中的老头儿不停地说着客人来了,可舞台上终究没能出现真正的客人,只有不断增添的椅子。热内的《女仆》中的二位女仆分别扮演主仆,以此控诉女主人的无情专横,倾吐对女主人的仇恨,但最后装扮主人的女仆却真的将给女主人准备的毒汁一饮而尽。语言对话由此被抽空了内涵,成了悬浮在虚无中的偶然声响。
更有甚者,荒诞派戏剧里的许多对话干脆只是无内容的语言空壳,在《秃头歌女》第七场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打招呼后,先后各自“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紧接着几句关于天气、年龄的话。其间穿插十八次沉默。第十一场,史密斯夫妇与马丁夫妇的对话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句子,如“人们走路用脚,但是人们取暖用电或煤”,“天花板在上,地板在下”等等。后来对话干脆变成了无意义词语的重复,如十次重复“卡夫卡埃斯”,九次重复“拉什么屎”、“拉了那么多的屎”,两次重复“狗身上尽是跳蚤”。这些重复句子之间毫无关系,全是突如其来的孤零零的句子排列。这种排列之后又是乱七八糟的词语:“仙人掌”、“尾骨”、“球菌”、“猪啰”。再后又是莫名其妙的句子:三次重复“可可园里的可可树不结花生结可可”,“老鼠有眉毛,眉毛没老鼠”,“碰一下苍蝇,别擤出琴键来”等等。再后是法语的五个元音、十六个辅音。十一次重复模拟火车声“特弗”。最后全体一致六次重复“不从那儿走,从这儿走”。据说尤奈斯库是受了英语会话手册的启发而写出了《秃头歌女》。正是这日常会话中包藏着现代西方人的若干生活信息,尤奈斯库从中发现语言“只是一些陈词滥调,空洞的俗套和口号”。〔13〕语言的对话意义在荒诞派戏剧的对白中彻底失落了。正如马丁·埃斯林所说:“假如说,一部好戏靠的是机智的应答和犀利的对话,那么这类戏则往往只有语无伦次的梦呓。”〔14〕
如果让我们从历史逻缉的角度追寻荒诞派戏剧语言对话意义失落的深刻含义,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此处的逻辑矛盾其实仍然是戏剧人物语言与传统理性主义历史语境错位后的结果。传统理性主义历史语境始终假定了人类历史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则规定了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从而规定了人物之间对话的目的性、有用性。由此出发,也就规定了人类文学艺术形式之一的戏剧势必突出并彰明这种有目的行为及对话的严肃性。但在现代西方人看来,人类历史并非那么合乎目的,世界人生也并非那么具有目的。人生其实就是活着而已。它就是一系列琐屑无聊的任意堆积,就是一串空虚而无意义的偶然排列。加缪就曾这样形容现代社会的人生状态:“起床,公共汽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公共汽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15〕生活就是重复往返的日常习惯。一切历史的、道德的、社会的内涵在这习惯之流中融解成了虚无。这种习惯成自然的平庸生活与传统理性主义的意气风发、庄严崇高的梦想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这就是荒诞感的源泉。尤奈斯库曾经这样说:“我试图在《秃头歌女》中描绘的‘社会’是个完美的社会,我的意思是说,在那里,一切社会问题都被解决了。遗憾的是,在生活里这实际上并未产生效果。这出戏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烦扰已成为往事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隐秘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至少对于人类的某个部份来说,一切事物都在平稳地运行。”〔16〕也就是说,人生随着一切重大生存命题的解决而变得空虚无聊起来。这种空虚无聊使自古以来人类为征服自然、战胜野蛮的相互合作变得多余,使每个人皆处于各自命定的漂泊流离、自我放逐之中,这也就形成了现代西方人语言对话的新的历史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人与人因为没有需要实现的共同目的也就没有了语言交流的必要。反过来,语言这一交流思想、沟通心灵的传统工具,在现代社会或许由于意识形态的控驭、毒化而成为骗人的有效武器。如同汪义群先生在论及荒诞派戏剧时所言:“政治上的空口许愿,外交上的口是心非,商业广告中的欺人之谈,新闻报道中的失实歪曲,绵绵情话后的虚情假意,凡此种种无不表明语言不是用来解释事实、澄清事实,而恰恰走到它的反面,成为掩盖事实、歪曲事实的工具,这样语言便失去了意义。”〔17〕正象萨特的小说《恶心》中洛根丁的独白是表现人被无端抛人世界后的孤寂、恐惧,以及面对充满敌意的外在世界既格格不入、又束手无策的心理惶惑。荒诞派戏剧中人物的自说自的独白、颠三倒四的对话、大堆大堆的废话排列、语言与行为的严重割裂、以及语音空壳的重迭倾泻,皆在于展示人物行为的无内容、无意义,语言交流的无必要、无价值,从而确证世界人生的无目的、无理由。如同马丁·埃斯林所说:“在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里,语言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嗡嗡声。”〔18〕所以,《等待戈多》中幸运儿的所谓思想因为试图在日常语词里灌注庄重严肃的词句,不但自身意义空虚,且使在场的其它三人或垂头丧气、紧张厌烦,或痛苦呻吟、大声抗议。最后,三个人皆忍无可忍地扑到了幸运儿身上。难怪乎,幸运儿后来终于成了哑吧。另外,尤奈斯库的《椅子》中那位替老夫妇宣讲伟大真理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哑吧。因为,作为人类协调行为、互通情感的语言的对话意义不仅失落而且变得多余甚至有害,人类毋宁保持缄默。所以,《等待戈多》、《秃头歌女》、《送菜升降机》等等荒诞剧作中几次、几十次反复出现“沉默”的情况。这便是现代人面对世界、人生的最好姿态。
荒诞派戏剧中的人物对白,除了构成作品人物自身的喃喃自语,从而阻断了剧中人与人相互交流外,还从根本上阻隔了我们观众(或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沟通交流,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错裂的荒诞关系。当然,这种荒诞关系实际上是我们由于传统话语的长期熏染而形成的关于世界人生的习惯性理解与现实人生新命题的错位。加缪曾经这样说:“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从智力方面看,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19〕加缪这段话的要害在于指出荒诞的主客观关系意义。这种主客观关系在荒诞派的戏剧语言对话上也就体现为历史语境与现实话语的关系。我们观众(或读者)是置身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根据这个语境的规定框架,我们观众(或读者)总是不由自主地坚信语言的明澈与清晰,坚信语言的公正与中立。通过语言,我们能对人与人的关系有明确的感知、理解,也有明白的交流、沟通。这种历史语境必然与荒诞剧中人物的对话形成荒诞性的脱节,比如上述举例的人物自说自的独白,内容的颠三倒四、乱七八糟、缺乏内在逻辑,以及大堆废话的排列,甚至无意义的语音空壳堆砌等等,除了阻断了戏剧中人物之间的沟通理解外,我们观众(或读者)也莫名其妙。为此,我们必须置换我们接受者的历史语境。根据现代西方人的理解。人是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陌生人、漂泊者。理性主义所坚信的语言命名功能其实并不那么清晰明了,而是包藏着含混、模糊,甚至还由于对理性主义宇宙观、历史观、认识论的依附而拖着掩盖人类真实景状的阴影,从而可能遮蔽人与人的真实关系。特别是面对人类感情这种深邃无比的东西时,传统的语言命名方式不得不保持缄默。人们更需要的是以某种整体性的符号来暗示出某种体验与感受。这种符号可能非常怪异、繁复,它所暗示的体验与感受也可能非常晦涩、暖昧,但它却能传达出某种深沉无比的心灵顿悟。由此,我们终于明白荒诞剧人物对白的诸种荒诞离奇其实也就是一种整体性的符号,它暗示出现代西方人在宇宙中的尴尬无奈、空虚无聊、平庸卑微、单调乏味。再由此,我们终于看见了现代西方社会另一难以言说的负面场景。
荒诞派戏剧武断地将语言的叙事和对话扯离了理性主义的语言框架,借以撞击、改塑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应该说,它起到了给人“当头一棒,使之大为震动”的超常作用。但是,荒诞派戏剧在帮助人意识到世界荒诞、人生虚无的同时,是否也无情地将人赶出了寄寓人类心灵的文学家园呢?
注释:
〔1〕欣奇利夫:《荒诞》,梅森出版公司1969年版,67页。
〔2〕〔3〕〔5〕〔6〕〔7〕〔12〕〔14〕引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675、673、674、633、666页。
〔4〕引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6页。
〔9〕〔15〕〔19〕引自《文艺理论译丛》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331、318、333页。
〔8〕〔16〕引自《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68、302页。
〔10〕引自高强:《约纳斯库和〈秃头歌女〉》,见《当代外国文学》1981年第2期。
〔11〕《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80页。
〔13〕〔18〕《荒诞派戏剧》,1982年塘鹅版,130、84页。
〔17〕《痛苦人生的探索——论荒诞派戏剧》,见《外国戏剧》1987年第4期。
标签:戏剧论文; 荒诞派戏剧论文; 等待戈多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贝克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