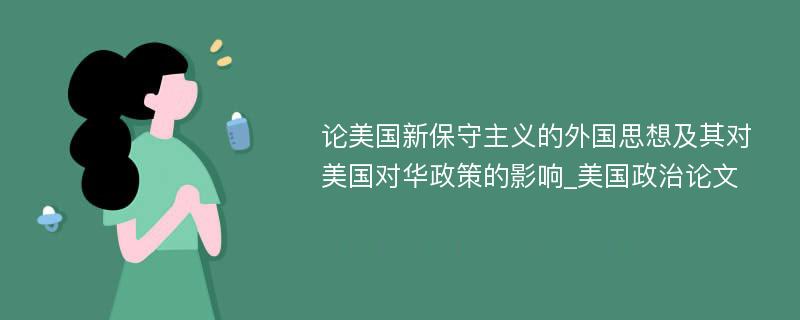
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保守主义论文,外交论文,也谈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简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 期发表的题为“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一文,是近年来国内的国际关系论坛上难得一见的力作。这是因为第一,元文抓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新保守派是当代美国政治思想流派中最活跃也是最危险的一支。它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上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我国学术界过去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元文在弥补这一不足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第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政见特征以及人物派别的分合沿革极其复杂,在美国学术界不乏歧见。元文经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筛选、分析,为读者勾画出一幅简明准确的历史图景,殊为不易。本文拟在此基础就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
新保守派系由自由派中的冷战强硬派转化而成,其外交政策主张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信奉美国特殊论。而这又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美国优越论,认为美国式文明,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远比其他民族优越,堪为世界楷模;其二为美国使命论,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 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文明的天赋使命,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注:关于这一信念的历史渊源,可参考王晓德:“美国‘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因此, 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在道义上高人一等,别国的外交政策都只顾追求本国利益,而惟独美国的外交政策注重道义和理想,以维护全世界的福祉为己任。第二,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认为输出意识形态从长远看符合美国根本利益,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国际竞争中抢占“道德高地”,取得舆论优势,另一方面经由美国模式改造的国家及世界有较大可能对美友好并接受美国领导。第三,它强调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推崇实力外交,主张以美国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美国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为把美国意志强加于各国,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从而实现以美国意识形态为主宰的一统天下。
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狂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扩张性和进攻性。持这种主张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能量较大,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影响在八十年代前期达到高潮,当时一批新保守派骨干纷纷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外交要职。里根政府对苏极端强硬的“推回”(roll back )政策和“以实力求和平”的军备竞赛升级就是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在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新保守派是主张“道德征伐”(moral crusade)(注:Crusade这个字原意是中世纪基督教十字军对伊斯兰民族的远征圣战,后被引申为一切以宗教或意识形态征服为目的的讨伐,形式包括宣传攻势到武力征服等等,其实根据道德政治论的实质内容:“道德征伐”应改称“意识形态征伐”更为确切。)的所谓“道德政治论”(Moralpolitik)的先锋和主力,竭力鼓吹应以向全世界强行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作为冷战后美国外交的新宗旨。九十年代初期克林顿政府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与这批人的煽动关系极大。
早在苏联解体前,这派人物就以其特有的高度政治敏感预见到冷战后世界将出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主张美国应当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新保守派的本·魏登堡在1989年冬季号《国家利益》季刊讨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战略目标的专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天赋使命”(注:原文中的Neo-ManifestDestinarianism是Manifest Destiny的变型。Manifcst Destiny是19世纪中叶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时出现的一种论调,宣称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的选民”,其人口增殖和领土扩张都是顺天意,行天道的正当之举。这一论调后来经常被用来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作强词夺理的辩解。)的文章,露骨地把冷战后美国向全世界的扩张同当年向南部、西部的移民和领土扩张相比,籍此表明美国主宰世界是“神授天命”。他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民主,”宣称今天“只有美国人才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胆量去进行……全球文化宣传”,甚至毫不讳言地承认“我们的确犯有那些反美分子指控我们的部分罪名——我们确是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帝国主义”。(注:Ben J.Wattenberg,"Neo-Manifest Destinarianism,"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1990,pp.51—54.)新保守派的主力查尔斯·克劳塞墨还不满足于把“民主征伐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认为这不过是冷战后“打扫战场”而已,而他所要的则是“全球主宰—走向一统天下”。根据他的设计,今后世界的核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邦联,核心的外围是实行了非共产化的前共产党国家,最外圈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类似世界帝国的国际体系中,周边国家对核心国家的关系是依赖与服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由此得以确立。这一主张的帝国主义性质如此露骨,以致连老保守派都觉得过分。老保守派的另一主力,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鲁塞尔,柯克(Rusell Kirk )指这些人为“文化与经济帝国主义者”,成天想用“异想天开的民主全球主义来代替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注:Charles Kraulhammer,"UniversalDominion:Towarda Unipolar Worl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1989/1990,pp46—49.)
新保守派的另一主要成员乔舒亚·穆拉夫切克在1991年出版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一书中试图对“道德政治论”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尤其想要解决这一主张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他指出,“促进民主事业可以成为最有成效的美国外交政策,不仅在道义上如此,而且对本国利益来说也是如此”。其依据如下:第一,“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美国所处的环境就愈友好”;第二“世界上民主国家愈多,世界就愈倾向于和平”。(注:Joshua Muravchik,Exporting Democracy:Ful-filling America' s Destiny.Washimong.D.C.:The AELP ress,1991,pp.6—8.这里的两条论据都是很有争议的, 其中第二条又以“民主和平论”著称,是近年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激烈争论的课题之一。)在此前提下,穆拉夫切克归纳了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文化交流,对外广播、对外援助、秘密颠覆、经济制裁、外交压力甚至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等等,为美国总结过去的经验,设计未来的蓝图。此人原拟以该书作为挤入当时新上台的克林顿政府的进身阶,以期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发挥某种指导性的影响。结果非但“官梦”未能如愿,连他的政策主张也渐受冷落。
新保守派想把克林顿外交政策置于“道德政治论”控制之下的用心既然未能得逞,就把希望寄托在1996年大选上,期盼共和党保守派一旦入主白宫便能象当年里根政府一样起用新保守派主持外交,让他们重温旧梦,再显身手。于是两名新保守派少壮人物选择大选进入高潮的1996年夏在美国外交论坛杂志《外交事务》上推出了他们为保守派拟定的外交政策纲领“新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篇新保守主义外交主张的新总结中,作者提出美国外交在冷战后的首要任务是把美国目前享有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或者“全球霸权”“尽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必须奉行新里根主义外交政策,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和道德信念”,让美国外交政策“重新道德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专制国家和极权国家施加压力”,包括对“诸如伊朗、古巴、或中国”这样的国家积极推行“最终会引起政权变更”的政策。作者宣称,这一政策不但旨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目标,而且具有“现实意图”,最终会给美国带来“战略利益”。作者并据此断言,“鉴于道义目标和国家根本利益几乎总是和谐一致的,美国外交政策应当以明确的道义目标为指导。”
对美国公众而言,新保守派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提出的“道德征伐”的外交路线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感在美国人中一向很有市场,加上如今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不受制衡和约束,对外扩张干涉也不像过去要冒同苏联对抗甚至发生核冲突的危险,因此,目前正是实现美国一统天下的良机。此时不干,更待何时?然而另一方面,“道德征伐”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高昂代价,又使多数美国人望而却步。美国公众自越南战争以来对美国在海外干涉行动中的人员伤亡一直极为敏感,而冷战之后又对美国在海外承担义务的财政负担非常厌倦,要求政府集中精力优先解决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情绪十分强烈。如果按照道德政治论的设计去“改造世界”,美国的扩张干涉无疑将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旦卷入军事行动还会导致美国公众难以接受的人员伤亡。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到处对别国发号施令会引起多数国家的不满与反对,疏远友邦,制造敌手,削弱美国优势;侵犯各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等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做法,也必然会损害现存国际秩序,破坏国际稳定。所有这些对国家利益潜在威胁的顾虑和担心,是“道德政治论”迄今为止未能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正论为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其反论则为反共主义。坚决反共一向是新保守主义坚持的原则立场,在冷战时期体现为对苏强硬,冷战以后其矛头就转向世界上仅存的共产党大国—中国,力主用高压手段在人权、贸易、台湾、西藏、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逼迫中国就范。然而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过去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也意味着共产主义威胁的消亡,反共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目标对美国公众已不再具有号召力,因此新保守派便抛出了“人权外交”用作反华的幌子。事实上,新保守派鼓吹反华的真正动机,不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狂的征服欲和改造欲,而且也出于民族沙文主义和霸权心态,就是要逼迫中国“就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内集中于经济建设、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自认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意识形态作低调处理,可以说是“与世无争”,没有给意识形态的斗士们留下多少口实去挑起一场“征伐”。其实,籍人权为突破口以瓦解美国视为“敌对”国家的手法并不新鲜,早在里根时期就曾被用来作为对付苏联的政治武器,而新保守派正是这一策略的始作俑者。当时一批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就此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作,全面阐述了以人权为外交政策中心的理论根据,为这一政策构筑舆论基础,并以政府声明和其他官方文件的形式确立了这一政策的正统地位。
然而最初缺乏外交经验的克林顿政府不久就从实践中领悟到,打压中国、同中国对抗非但无助于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有损于美国的根本利益,于是逐渐排除新保守派的影响,转而采取接触、对话等比较现实的政策处理两国关系。以新保守派为主的反华势力眼看煽动意识形态狂热没有奏效,便在舆论界掀起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歇斯底里。其中最狂妄的代表作就是查尔斯·克劳塞默1995年在《时代》周刊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为了论证反华的必要性,克劳塞默不惜重循陈旧的政治逻辑,妄称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要求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其方式是外部遏制,包括不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让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支持吴宏达之流的反政府活动,再加上内部颠覆等。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虽然并未得势,但其主要论点已经对美国朝野上下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人尽管与新保守派毫无关系,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却明显带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印记。新保守派随时都在观察动静,等待时机。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大消极因素,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二、新保守主义的本质和特征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通过比较得到深化,而对一新概念的理解需要借助与已经熟悉的旧概念相比较,在了解它们的异同后更容易抓住新概念的实质。对新保守主义的理解更是这样,因为它的得名和定义就是由它同两种主要的美国传统政治思潮—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而来的。新保守派是从自由派蜕变而来,对自由主义先认同而后摒弃,歧见之外尚存共同思想渊源;虽转投保守阵营,却并不与传统保守派融为一体,而是独树一帜,求同存异,也是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只要我们把握住它同这两种思潮的异同,新保守主义的独特本质也就一清二楚了。概言之,新保守派与自由派在外交政策立场上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主张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美国至上论”而后者以“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界定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由此派生出前者主张以美国模式改造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r Americana), 而后者则至少在纸面上主张民族平等和自决,反对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国家实力和实力外交的态度:新保守派极为推崇实力和实力外交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把美国意志强加于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后盾和手段;而自由派的传统是崇尚道义理念,反对实力外交,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另一方面,新保守派对实力的崇尚又构成了它同传统保守派的共同语言,只不过前者倚重实力的目的是为了意识形态扩张而后者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差异表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新保守派主张依仗美国的实力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世界各国,把美国式的世界秩序强加给国际社会;而传统保守派则反对这种过度扩张,认为这是对美国实力的滥用,会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传统保守派以实际利益为重,不太注重意识形态。以处理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为例,这两派都反共,但传统保守派在条件合适时,可以同共产党国家进行互利合作;而新保守派却认为同共产党国家的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后者在冷战期间反对对苏缓和,而在冷战之后又竭力反对同中国改善关系。可见,新保守主义外交主张的本质特征是由突出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以及强调国家实力作为政策后盾这两条所构成的。
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主张具有极大的负面性,是由其意识形态扩张的特征所决定的。在美国外交思想流派中,自由派皈依的是理想主义,或称威尔逊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理想主义正如它的名称所提示的只能停留在理想上,就连威尔逊本人的外交政策也常常与他鼓吹的理想主义自相抵牾)(注:见张睿壮:“世界秩序与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一期,第62—63页。)。保守派尊崇的是现实主义。新保守派虽然自诩为理想主义信徒,实际上信奉的是特定的霸权式或扩张型的理想主义。一般人往往容易误以为理想主义倾向于道义,理性与和平,而现实主义则迷信利益、实力和战争。其实,新保守派的理想主义要比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危险得多。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扩张会损害国家利益;但是按照理想主义的逻辑就不会有节制,因为西方大国常常自以为是公理和正义的代表和化身,而公理和正义的扩张自然是多多益善,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因此,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圣战到本世纪的意识形态征伐,都是没有止境的。表现在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上,现实主义代表一种保守、谨慎、节制和稳重的主张。由于它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宗旨,所以在需要为之付出巨大代价时也能获得国内公众的支持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由于它以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为准绳,因而进退有据,具有较高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这对国际政治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相比之下,理想主义不是流于意识形态狂热便是失之伪善,其政策主张往往过激、冒险、扩张性强而且自以为是。由于它所依据的是没有坚实基础也没有明确界限的主观意志或意识形态,所以不易得到公众持久的支持而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当然就谈不上政策的可预见性了。这样的政策既无益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也常常给别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威胁和灾难。
新保守派对美国外交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其政策立场所固有的侵略性和冒险性,而且还由其人员构成上的特点所决定。如前所述,新保守派系由自由派转化而来,不少元老早期曾卷入过左翼运动,曾是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同情者甚至同路人。换言之,他们曾经是“革命者”,只是后来改换了门庭。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和煽动性。这是因为第一,革命者为推翻旧秩序,往往采取激进求变的策略,这同主张社会进化的自由派的温和、渐进以及因循守旧的保守派的被动、防守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第二,革命运动面对强大的旧势力往往在物质力量上处于劣势,在道德上却享有优势,表现为新思想对旧秩序的意识形态批判和道德超越,以及革命方面对宣传和论战的重视和精通。第三,不少新保守派人物出身左翼理论家,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革命理论相当了解,运用自如-到后来就成了批判自如了。新保守派的这些特点从其成员在美国外交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大批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与同情、支持它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同维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旧秩序的西方国家进行较量,在国际舆论界特别是在联合国这个重要国际讲坛上对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当时美国老保守派面对来自左翼的意识形态攻击不知所措,除了重复一些老掉牙的保守主义教条外别无良策,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还有些保守势力对舆论战并不重视。以为只要保持实力优势就行了。新保守派敏感地看到事态的严重性,提出美国一定要夺回国际舆论阵地。这一努力从曾属新保守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5—1976)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开始,直到新保守派柯克帕特里克出任这一职务期间(1981—1985)发展至高潮。后者表示要坚决改变联合国论坛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意攻击美国而不负责任的局面,威胁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为攻击美国的言论付出代价”。在她任职期间,曾多次出现她对批评美国的外国代表当面横加训斥并引起激烈争辩的场面,(注:Linda
M.Fasulo,Represning America:Experi-ence of U.S.Diplomats at U.N.,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pp.284—291.)事后还不惜以减少或切断军援、经援对一些国家进行报复。这就是元文提到的“反对反美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她还不满足于此,而是要转守为攻。她曾表示不能容忍在她看来当时西方国家外交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怯懦,即不敢在反西方舆论面前理直气壮地为西方信仰作辩护。她力主把重新肯定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优越性作为里根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鼓吹在同国际进步势力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动抢占道德高地的攻势。(注: John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Press,pp.154—155.)作为这一攻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保守派发表了一批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对社会主义揭露批判的作品,乔治·古尔德于1981年发表有代表性的《财富与贫困》一书,(注:该书中文版于1985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笔者也是译者之一。)从理论上反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道德上论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该书一出,立刻博得美国媒体的一片喝彩。
新保守派的进攻型策略不仅应用于舆论战,而且也是里根政府针对苏联扩张的推回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新保守派主张美国放弃奉行多年的遏制政策而采用反守为攻的推回政策。新保守派元老诺曼·波多里兹率先鼓吹对苏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美国在全世界发动反共圣战,向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在内的各国反共叛乱势力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持,为苏联制造它本身的越南。(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Poverty of Realism",New Repubic,Feb,17,1986.第143—144页。)这一主张立即得到采纳,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不久,里根政府在新保守派的怂恿下又在中美洲开辟对苏、古外围战的新战场,把反政府游击战的战火烧到了为美国所不容的桑地诺阵线统治下的尼加拉瓜。柯克帕特里克硬把桑地诺政府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用暴力篡夺政权的一小撮极端分子,鼓吹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叛乱。另一方面,她又把萨尔瓦多进步力量反对腐败暴政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外国势力挑唆的叛乱,扬言美国负有道义责任帮助右翼军人集团进行镇压。(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Povertyof Realism",New Repubic,Feb,17,1986.第154—155页。)正是在新保守派带头制造的舆论基础上,里根于1985年抛出了所谓“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声称“我们的使命是培植和保护自由民主,……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民主盟友,决不让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每块大陆上那些为抵抗苏联支持下的侵略……而甘冒生命危险的人失望。……支持自由斗士就是自卫。”(注:Linda M.Fasulo,Represning America: Experi-ence of U. S. Diplomats
atU.N.,New York:Facts on FilePublications,pp.677.)正是在新保守派设计的“推回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出钱、出枪、出教官支持右翼势力在几个加勒比小国大打内战,甚至不惜采用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手段,直到把不肯充当美国随从的政府颠覆殆尽才算罢休。
新保守派主要是由纽约的犹太裔知识分子所组成,(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词在美国的用法与在中国略有不同, 不是指一切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而主要指从事学术研究或创作活动的自由职业者,尤指人文领域内的思想家、批评家、与中国的“文化人”接近。)这一种族文化背景注定了这派人物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能量。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发展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到国会参众议员,从大学教授到报纸主编和专栏专家,从华尔街金融巨头到好莱坞编剧导演,犹太裔美国人以高得异乎寻常的比例占据着美国社会的权力要津和舆论阵地,对美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犹太人远非铁板一块,并不总是舆论一律、步调一致。然而共同的血缘、历史和文化传统成为他们声应气求的纽带,他们往往借助对舆论媒体的操控,自成气候。新保守派中间不乏理论功底深厚的政论家,才思敏捷、笔锋犀利的雄辩家,以及博学广识的学问家。在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思想运动像新保守派那样创办、控制了那么多著名的期刊杂志,除元文提到的《评论》月刊和《国家利益》以外,重要的还有《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舆论》 (Public Opion)和新近创刊的《旗帜周刊》等等。另一方面,新保守派对不受其直接控制的杂志也加强渗透,其影响在一些权威的专门刊物中明显可见,如《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等,甚至还打入了一贯属于传统保守派势力范围的《国民评论》 (National Review )和《福布斯》(Forbes)。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影响甚大的《纽约时报》上也常可见到新保守主义的踪影。
新保守派不仅善于占领舆论阵地,而且还掌握了一大批思想库、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更直接地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在新保守派控制的思想库中,最重要的当属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nprise Institute)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enational Studies),他们在那里网罗了一批政界、评论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研究评估,通过不计其数的研讨会和政策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在社会团体方面,新保守派在七、八十年代曾利用“当前危险委员会”和“自由世界委员会”发挥了极大的政策影响,嗣后又把工作重心转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for Democtracy)等组织,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并向海外输出美国式自由民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民主基金会”,它于1984年在新保守派的力促下经国会批准组成,各为民间组织实为官方机构,主要通过资助外国政治组织的宣传、组织、竞选等方式达到干涉、操纵外国内政的目的。过去这些活动多由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美国开发署等官方机构暗中进行,但事发后容易被抓住把柄,所以改由国会每年拨款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由它将款项分拨给工会、政党下属的各种“民间组织”,再由它们出面资助对美国友好的外国组织在当地进行反政府活动。
三、结束语
新保守主义思潮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不仅因为其内涵的丰富和繁杂,而且由于该派人物的多样和多变。美国评介新保守主义的文章书籍连篇累牍,新保守派却抱怨几乎所有作品都充满谬误或偏见。新保守派主力诺曼·波多雷兹曾对采访他的一位作者声称,有关新保守主义的文献的95%都是“毫无价值”的,并说他在“他们写我的东西里从来未曾认出自己”。(注:Gary Dorrien,The
NeoconservativeMind:Poli-tics,Culture,and the War of Ideolog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p.x.)这固然反映出这批人的傲慢与乖戾,却也说明了准确描绘和剖析这一思潮的难度。有些问题即使在新保守派中间也颇有争议,例如对待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有些新保守派如麦克·瓦克等把现实主义大师莱因霍德·尼布尔尊为新保守派之父,(注:Michael Novak,"Father ofNeoconserva-tives" ,NationoalReview,May ll,1992:pp,39—42.)认为现实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然而尼布尔一贯反对后来成为新保守派信条的“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更反对自以为是的“道德征伐论”。在具体政策上他早就主张美国承认中国,并率先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所有这些都同新保守派的主张格格不入。难怪穆拉夫切克在《输出民主》一书中要用两章的篇幅批判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的“愚昧”并指名抨击尼布尔,而克劳塞墨也曾著文抨击“现实主义的贫乏”。(注: CharlesKrauthammer,"The Poverty of Realism",New Repubic,Feb,17,1986 .)正是因为新保守派在道德征伐问题上的走火入魔,使原先对新保守派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的阿瑟·施莱辛格和曾是该派主要外交理论家的罗伯特·塔克尔相继与其分道扬镳,转而采取批判立场。及至冷战结束,更有新保守派的元老欧文·克里斯托和另一主要外交理论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回到现实主义立场而同坚持道德政治论的少壮派分手。
可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谁是新保守派的正宗传人?谁代表新保守派的方向?元文认为,塔克尔和柯克帕特里克的现实主义倾向得到多数新保守派的支持,“成为有代表性的主张”。我认为这个问题得商榷。从人数来看,恐怕还是持相反意见的为多。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尽管改弦更张的多为大佬级人物,其影响举足轻重,但他们毕竟是离经叛道者。反之那批名气不如他们的少壮派,倒是得新保守主义真传、坚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卫道士。因此,不能因为少数头面人物的转向,便认定整个思想流派就改变性质了。其实,新保守派的元老们倒无意以新保守派代表自居,因为他们认为产生新保守派的环境——冷战和新世界苏联的威胁既然都已不复存在,新保守派的历史使命也就大功告成了。该派创始人之一波多雷兹甚至在《评论》月刊上为它发了讣文,另一创始人克里斯托也为它写了盖棺论定的传记。部分少壮派眼看大势已去,也不再坚持高举新保守主义大旗,而想融入传统保守主义阵营。照这样看来,新保守派似乎真的完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新保守主义在思想路线上同传统保守主义有实质性的分歧,不是单单改变旗号能解决的。其次,老保守派一贯心存疑虑,从未接纳他们作为保守派一员,现在更把他们挤入自己阵营的作法看成是企图把共和党引向“左”转而安插“特洛伊木马”。(注:《世事》杂志攻击《旗帜周刊》及其主编威廉·克里斯托语。见NormanPodhoretz,"Neoconservatism:A Eulogy,"Commentory.March,1996。)因此,不管今后打什么样的旗号,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影响;一遇适当时机便会东山再起,再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