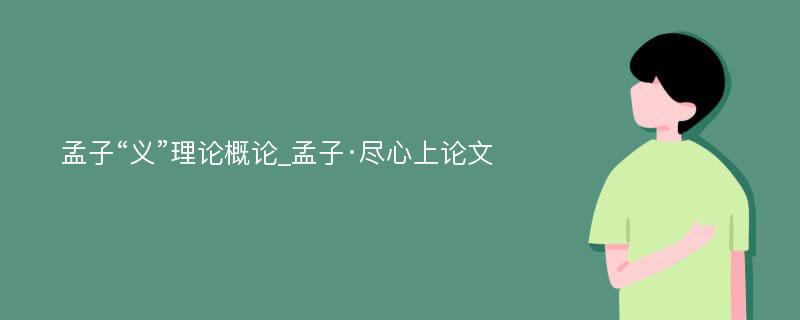
孟子“义内”说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说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孟、告“义内”、“义外”之辩
《孟子·告子上》篇,记载了孟子与告子就“仁义”究竟是外在于人还是内在于人的问题展开的辩论。在第一个回合,告子用“以杞柳为桮棬”来比喻“以人性为仁义”说明人性本来并不具备仁义的内在要求,仁义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
孟子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反驳道:“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在这里,孟子只是从可能产生的后果方面来驳斥,意思是说如果认为仁义是外在的,不是人性中固有的,那么推行仁义就变成了残害人性的事情,这样天下人就会反对仁义。所以如果宣称“仁义”是外在的,也就等于毁了仁义本身。这里隐含的逻辑前提就是,如果一种论点不利于推行“仁义”(孟子认为告子的观点就是这样),就应当放弃;至于这种论点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甚至都不必进一步讨论。把价值论意义上的而非知识论意义上的是非作为讨论问题的标准,在先秦思想家那里是具有代表性的。
接下来告子用了个“湍水”的比喻,试图说明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但这个比喻的确选得不高明,孟子恰恰也用这个比喻,反过来说明人性之善。这一回合的交锋,与其说是逻辑上的辩论,不如说是语言技巧上的斗智。
第三个回合,告子提出了“生之谓性”的命题。这是告子的核心命题。但是孟子并没有对这个命题进行具体的反驳,只是反问道:“你告子是不是认为人性与犬之性、牛之性是一样的?”对此告子哑口无言,他很难否认人性与犬、牛之性是不同的。毕竟不能只把人看作是动物界的一个类,把人性简单等同于人的动物本能。但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孟子在此尚未作进一步说明。
接着告子又提出了“仁内义外”的观点。告子论证“义外”的理由是:“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告子在此犯了双重错误:一是把主体“义”的行为和这个行为的对象混为一谈,二是把“义”与义的行为混为一谈。因为“长”只是客体的属性,“长之”才是主体出于“义”的行为。而“长之”这个行为,是出于“义”的选择,并不就是“义”本身。即使“彼白而我白之”也并不是纯粹由外在的客观因素引起的。“白”并不等于“白之”。“白”可以独立于我而存在,但“白之”这一过程则非有“我”的参与不可。
孟子在这一段轻而易举地并且非常成功地驳倒了告子,也涉及到了“义不在彼之长,而在我长之之心”(朱熹《孟子集注》语)这一问题的实质。但显然这还远远不是对“义内”问题充分的正面论证。
接着告子又以“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和“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作比较,来证明“仁内义外”。孟子则用“嗜秦人之炙”与“嗜吾炙”作比喻来驳斥告子。这是针对告子的两个前提:其一,告子认为内外无别(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便是外在的;其二,告子在前面认为食色之欲是性,是内在的。而“嗜炙”属于食色之欲,当然是内在的。可是“嗜炙”也是不分秦人之炙与吾炙的;既然不分内外的“嗜炙”可以是内在的,为什么不分内外的“长长”就只能是外在的呢?从逻辑上看,孟子这一驳斥显然使告子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然而从实质内容上看,孟子只不过再次强调了“义”的内在是一个事实,并未将辩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告子》篇关于“义内”问题的最后一段讨论是在孟季子、公都子和孟子之间进行的。这一段涉及“义”与“礼”的不同,为理解“义”的本质以及“义”与“礼”的关系提供了材料,但是,对于“义”为什么一定是内在的这一问题,最后仍然只是以“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冰”的比喻来作结。理论分析上较前面几段并无新的突破。
总的来看,孟子在与告子的辩论中,并没有从“义”的实质、“义”在人的精神活动和道德实践中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来对“义内”这一命题进行正面的深入的论证。也许是迫于“不得已而辩”的情势,孟子主要是抓住告子在使用比喻和运用逻辑方面的一些漏洞,以巧妙的言词、机警的辩术在口头上驳倒了对方。所以后人读来难免有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义内”这个命题在孟子那里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假设,没有学理和逻辑上的证明。恰好相反,“义内”这个命题在孟子的思想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是有其理论和逻辑上的必然性的。而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义内”说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拟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经典中的有关材料对“义内”说的深刻含义作一些阐发。
二、从“仁”“义”关系看“义内”说
我们认为,弄清仁、义、礼三者的实质和相互关系,是理解“义内”说的关键。首先看仁与义的关系。
在儒家经典中“仁义”经常并提,后人也经常笼统地将“仁义”合在一起作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但其实仁与义在儒家学说中是有区别的,甚至还是一对矛盾对立的范畴。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仁”源于一种天然朴素的情感,更接近于人的本能;而“义”则是一种经过反思后的自觉的意识,带有理性色彩。儒家认为“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韩诗外传》卷四);“义者循理”(《荀子·议兵》);“义者,德之理也”(贾谊《新书·道德说》)。可见“仁”与“情”联系在一起,而“义”则与“理”联系在一起。仁义二者作为伦理道德的本原和标准,在内容上当然有许多相通相容的部分,但二者有本能与自觉,感性与理性的区别。
“仁”在孟子看来,是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于同类、特别是对于生育自己的亲人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天然的。而源于“羞恶之心”的“义”则不同于源于“恻隐之心”的“仁”。“恻隐之心”是本能地由主体向客体的外推,而“羞恶之心”则是从主体到客体,又从客体返回到主体的自省,或内视。因为所谓羞恶感,必须是自我从别人的立场和角度反观自我时才会产生。孟子说:“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孟子·尽心上》)所谓“受尔汝”,就是“我”这个主体被客体(别的主体)反过来指着鼻子称作“你”,也就是“我”这个主体被别的主体客体化了。只有这时主体才更深一层地意识到“我”是怎么回事。这种从客体反射回来的自省与内视,也即意识由认识对象进展到认识自身的阶段,便是主体的自觉意识。而“义”就是从这种自觉意识中逐渐产生并生长起来的道德理性。
单凭好心肠和同情心,有时也能做到仁。但要做到“义”则必须有理性的自觉。“仁”是把自己原有的本能的情感向外推,由“亲亲”而“仁民”乃至“爱物”。而“义”则是自觉地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加以限制,从出于羞耻感而有所不为的小事,进而自觉控制自己不去做另一些道德上不适宜的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忍,义也。”(《孟子·尽心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还是对“仁”的一种节制。因为“仁”是天然本能,处于“仁”就象住在自己家中,是安然自若,放任情感的感觉。所谓“仁者安仁”、“仁者静”、“仁者寿”,或把仁比作“安宅”,都含有这个意思。但是完全一任本能情感的发展而无所节制,也会出问题。《礼记·礼运》说:“用人之仁去其贪”,可见“仁”超过了限度就可能变成一种贪欲。这就必须由“义”来加以节制。所谓“节爱理宜谓之义”就是这个道理。《礼运》篇说“义”是“仁之节也”。荀子也说:“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荀子·强国》)后人所谓“大义灭亲”,也说明“义”是对作为“仁”的核心的“亲亲”之爱的限制。孟子把义比作“人之正路”,出门走路当然不能象在自己家中那样放任,必须头脑清醒,看清方向,也就是要有自觉意识和理性的指引。所以“义”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节制与约束。
总之,从本原上说,仁出于人的本能和情感,而义则代表人的自觉意识与理性。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的本能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如果没有自觉意识与理性,人就不成其为人。动物和它的本能是同一的,只有人才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并把这种本能当作自己意识的对象,从而有了自觉意识和理性,也就是“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光做到仁,还不能成为人。《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我们由于受了从西方引进的语法逻辑的干扰,总是倾向于把这种句子译为“仁就是人”。这样,“仁”就好象成了“人”的充足条件和全部内容。其实先秦时期古汉语中并无“是”这个系词。上面这两句话中的主词“仁”和“述词人”之间究竟是什么一种关系,是可以推敲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为:“做到了仁,才有可能成为人”,或“能行仁者,方能算作人”等等。不可否认,“仁”的确是成为人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如果不仁的话,不仅不能算人,而且禽兽之不如。庄子曾说:“虎狼,仁也。”(《庄子·天运》)本能的亲情之爱在动物中也存在。但是,这恰好说明“仁”只是成为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儒家认为“仁”与“爱”相联系,“义”与“敬”相联系。孟子说:对人“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蓄之也。”(《孟子·尽心上》)可知光有属于“仁”的“爱”,而没有属于“义”的“敬”,则还没有完全脱离禽兽。所以仁与不仁还不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标志,人禽之辨的根本标志是“义”。荀子即曾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
可见“义”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个“几希”的一点东西。人性中必然包括“义”,没有“义”的性就不是人的性。所以“义”必须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义内”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的。
三、从“礼”“义”关系看“义内”说
“礼”虽然也是原于“四端”中的辞让之心,但作为对人们行为与习俗的具体规范及其仪文程式,在形式上是外在化了的东西,是人们所创造的客观精神产品,它反过来从外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制约。
但是,外在的礼必须以内在的仁义为根据,尤其是以“义”为根据。所以古人说:“义以出礼”(《左传》桓公二年),“义生然后礼作”(《礼记·郊特牲》)。一方面,内在的仁义有待于外在的礼来表现,并在现实中得以完成,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另一方面,礼又必须以内在的仁义,尤其是“义”为根据,否则礼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把“义”和“礼”都看成是外在的,人性之中也就只剩下食色之欲和出于本能的“仁”,人只知根据本能欲望和情感行事,那么作为外在约束的“礼”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没有内在的“义”,就不可能有外在的礼。即使“仁”也必须经过自觉的“义”才能表现为礼。
退一步说,即使有了现成的外在的礼,如果没有内在的“义”,人们在遇到“嫂溺”是否要“援之以手”之类的道德两难时,还是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人不可能在所遇到的一切情景下都有现成的礼法条文和行为规范来指导其行动。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内在的“义”来判断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在这方面孟子自己为人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如《公孙丑下》记载孟子对陈臻问:“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的回答便是一例。这个例子说明在道德实践中遇到具体问题时,还是要靠道德主体内在的“义”来作出决断,所以义必须是内在的。
“礼”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人们自觉意识到的“义”的客观外在化的表现形式。“礼”所代表的“义”不是个别人的“义”,而是群体的、也包括祖先们的“义”。如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所指出的:“这些‘礼’是前人赋予这个世界的‘义’的载体。”(注: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72页。)虽然任何时代的礼都有其局限性,但至少在其形成时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合理的东西才可能是现实的。而且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任何时代的具体的“礼”,都是人类在追求完善的、绝对合理的、终极的礼的进程中所经历的必要的环节。但是“礼”一旦作为客观化了的外在形式确立下来,就成了相对静止的东西,就总会有过时的一天。这就需要新一代人们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义”来作新的选择与判断,对礼进行修正。“义”作为人的理性之路,永远指引着人性的正确方向。
总之,外在的礼离开了内在的义就成了没有生命的僵死的教条。礼是死的,义是活的,因为义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如果把“义”和“礼”同样看成是外在的,那么两者都成了僵死的东西,礼就失去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因革损益的内在动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义”必然是内在的。
四、“义”的普遍性的论证
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义”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但却又不是人的自然动物性本能。它源于人的羞耻之心,也即源于人不同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其成熟的形态则是人的道德理性。孟子也承认人有食色等感性欲望,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除了感性欲望之外,人还有理性之“义”。人类社会之所以有道德规范和礼法制度,就是因为人能够用理性之“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感性欲望,使自己不至陷于禽兽的境地。
作为道德理性的“义”既是内在的,同时也必须具有普遍性。关于“义”的普遍性,《孟子》书中也是有所论证的:“《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所谓“有物必有则”,即凡有一类物存在,就有该物内在的规则存在。这个“则”和这个“物”是不可分的。既不存在离开了“物”的“则”,也不存在没有“则”的“物”。“则”对这一类“物”中每个个体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人作为一个类,也有与这个类相应的“则”,这就是所谓“懿德”,也就是“义”。这个“义”对属于这个类的所有个体而言,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孟子论证道:“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理也义也”就是人心所同然的东西。
从时间上看,“义”的普遍性表现为当代人与古代人在道德观念和礼法制度上的继承和连续性。前代圣人先我而得义,并使之外化为礼法制度,所以现存的礼法制度乃前人之“义”的载体,后人应当对之加以敬重。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先知先觉”们创制的礼法,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应当继承下来。个人不管多么聪敏,多么富于创造力,在一生当中所能创造的东西,比起他能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当然,礼法制度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变革的一面。无论是礼法制度还是人性本身,都永远处于生成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但是礼法制度的变革,终究不能背离人类基本的理性之“义”。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见《孟子·万章上》引)。唐虞三代礼法制度不同,但都遵循着“义”却是一样的。所以,“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证明。
从空间上来看,“义”的普遍性可以用“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忠恕违道不远”(《中庸》),通过忠恕的方法,可以获得对于义的普遍性的体认。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忠恕也就是要在人我相对待的关系中来体认自己所意识到的道德标准是否具有普遍性。“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孟子·尽心下》)由此可知“杀人父兄为不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行为,我愿意这样施之于别人,而别人这样施之于我,我也很乐意,这种行为便具有普遍合理性,便是合乎义的。否则便可能是不义的。“义”的合理性正在于它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普遍的。如黑格尔所说:“人性只存在于意识与意识所取得的共同性里。违反人性的东西或动物性,就在于只以情感为限,只能以情感来进行彼此的交往。”(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79,48页。)
儒家也用“天”来作为“义”的更深一层的本原,以强化其普遍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义”既是内在的,同时也是超越的。而且内在与超越在儒家那里是统一的,这就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含义。但是先秦儒家一般不再对“天”作进一步的形而上学的深究。尤其是孟子,着重强调的还是“义”在人的心性中的本原。即使对于“天”,也要通过“存心尽性”的途径才能了解。其实先秦儒家所谓“天”,在很多情况下不妨理解为自然。所谓“天生蒸民”、“天命之谓性”,不妨理解为自然生成的人类、自然生成的人性。“义内”说认为天生的人性中即包含“义”的要求,也就等于说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类从自然界和动物群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就有其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自由意志与理性。换言之,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时,就已经有了作为自觉意识和理性之“义”的萌芽,因而“义”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一项要素,这样说也是言之成理的。
五、“义内”说的道德实践意义
关于人性和道德问题的讨论,最终目的应当是有益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无论是持“性善论”的孟子还是持“性恶论”的荀子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孟子的“义内”说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义内”说确立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主体地位。因为人有内在的义,所以人才是不同于动物的,是自由自主的。他既不是听命于神灵的权威,也不是听命于动物性的本能。听命于神灵的权威,固然谈不上人的自由;而人如果象动物那样,只能受本能的驱使,那他就跟动物一样,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的。然而人却不是这样。“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而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同上)人能够战胜本能,超越动物性的食色之欲、生死之念而根据理性之“义”作出自主的选择,不象动物那样,除了本能之外,别无选择。这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和内在的理性的体现,也是人的高贵之处。
其次,“义内”对于塑造儒家所提倡的特立独行、独立不倚的君子道德人格有重要意义。如果把“义”看成是外在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只能顺从外在的规范,服从外在的权威,依照现成的条文、礼法行事。这样就只会训练出一个又一个“乡原”,而塑造不出特立独行的君子,更产生不了圣人。而“义内”说却告诉人们道德和正义的本原就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因此,君子不应当只是时时处处死守外在的现成的礼法规矩而不敢有突破和创新的人。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所谓“义之与比”、“惟义所在”,就是说内在的“义”才是君子行为的最根本的依据。因此,率义而行的君子,面对富者贵者,当无所缺憾,亦无所畏惧。所以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孟子·尽心上》)“穷不失义”之所以谓之“得己”,就是因为这个“义”就是人内在的自由意志。坚守住自己的合乎理性的自由意志,也就把握住了自己,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因而能够穷则独善,达则兼济,自己决定自己的言行出处,无往而不自得,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决不牺牲道义而为之“诡遇”。
最后,“义内”说使人们认识到了人的道德行为最终是由自己的理性作出选择的,是由内在的“义”的尺度来衡量的。因而他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勇于承担自己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外在的礼法不可能规定所有的细节,人的每一次行动也不可能都是机械地遵守现成的规定,最终还是要凭自己内在的“义”去作出选择。“礼”虽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然而“嫂溺”而不“援之以手”致使嫂溺而死,这个小叔还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是有能力根据自己内在的“义”作出合乎理性的决断的。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有能力用理性之义来判断应当作什么和怎么做,所以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一个人放弃“义”,也即放弃自己道德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就叫做“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没有勇气承担道德义务与责任,否认自己具有“居仁由义”的能力,那便是自己与自己作对,自己将自己抛弃了。再进一步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与前途,终究还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理性之“义”来选择方向,命运是掌握在人自己手中的。人类并不是一群迷途羔羊,需要“上帝”来指引方向。匹夫匹妇,每个人心中都有理性之“义”,都有为群体和人类的发展尽心尽力的义务。人类有能力通过适当的方式,根据人类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普遍之“义”,为自己选择适宜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标签:孟子·尽心上论文; 孟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告子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