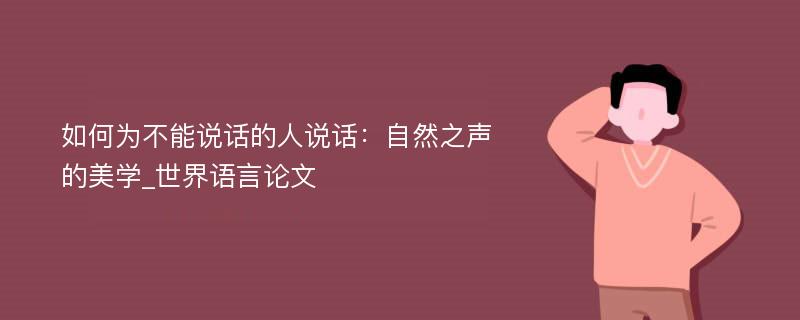
如何为无法言说者代言:自然之声的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声论文,美学论文,何为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1-0112-11
一、人类与非人类关系:从生态批评观点看自然
从环境耗损与迫近的生态危机威胁观点看来,许多生态批评家正在处理生态危机是心灵危机这信念,强调新自然概念的急迫性,希望借此在生态圈造成较小的破坏行为。相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生态批评家不只假设自然环境的确真实存在,也要求重新评价“近在眼前”的自然。他们最后坚持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全新关系,刻意激进地重新定义人类与非人类的概念。这一新关系发展的主要步骤是扬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不再被视为主宰或优于宇宙其他组成,而要更谦和地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物质地嵌合在活的有机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中。深层生态学,属于激进的生态批评团体,甚至走得更远,否定任何人类与非人类间的阶级差异。其主要发言人挪威哲学家阿尔·聂思(Arne Naess),提到地球所有生命的内在价值,提及“生物中心平等”与“生活与绽放花朵的平等权”,这构成其“直觉上清楚明白且显而易见的轴心价值”(1972:95、96)。虽然以基于直觉的自然概念作为批判分析的基础是有问题的,这概念也未被所有生态批评家共享,聂思强调连结非人类这真实存活的、有价值的实体,仍是常见的生态批评假设,这假设与修正过后更谦和的人类地位紧紧相系。
聂思质疑科学作为了解自然的方法,也要求“从科学转换到智慧”(Devall and Sessions,1985:74),然而,除了他之外,几乎所有的生态批评家都宣称需进行跨领域研究,跨到努力探索研究非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自然科学。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也曾警告“绿色批评将冒着注定要失去连结的危机,如果它忽略自然科学描述赋予美学表达的贡献与挑战”(1997:5)。这特殊重要性得回归生态,它将活生生的有机体视为相互依存的体系来分析,因此也成为自然与文化层叠交织概念的模型。虽然有些浪漫主义倾向的生态批评家提出像“一致”、“整体”、“平衡”或“合作”等词汇去表述奠基于生态的伦理观(Oates,1989),大部分生态批评家否认这种对当代科学的感性研究,这科学已察觉到生态系统内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对大部分人来说,生态是理解非人类世界的有效工具,它教导阅读自然符号的方法。因此,科学地、更确切地说来,在文学批评范畴内对自然的生态研究,是个强调物理、物质、“近在眼前”世界的重要方法,以达到唐·绪埃思(Don Scheese)所谓的“主角意识中的典范转移,从自我中心(人类中心)世界观转向生态中心(生物中心)观”(1996:9)。
生态批评家来自多元的批判团体,因此没有一致的生态批评理论。对有些人来说,物理、物质世界最重要的应该要回归需天真理解的文学写实主义,同时背离当代文学理论。举例来说,格蓝·乐夫(Glen Love)同意约瑟夫·凯罗(Joseph Carrol)的主张,后者早就主张在后结构理论中“现实中丰富经验世界已然被淘空,在这地方我们玩的是那单薄、纷扰的自我反省式语言功能的游戏”(1999:565)。他认为没有文本以外的现实这主张,必须被理解为对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思维的回应,只被某些生态批评家认同。要解决自然作为先于论述的实体概念与自然总是建构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居中协调的位置已被证明有效。这位置假设自然是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主动体,尽管不以人类语汇发声,但它也总是被文化铭刻。人类以文化方式定义自然,但他们自己也是深深依赖着生态体系的生物存在。居中协调的位置,一方面接受人类嵌合于物理、物质世界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接受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生物的差异。从这角度来看,自然与文化不能被截然二分;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相互影响。①
生态批评家的特殊挑战,是以生态中心观点出发探讨美学,这可能性尚需考虑自然与文化的互惠关系,考虑人类更谦和的位置,重要的是重新定义自然性。劳伦司·彼罗(Lawrence Buell)已然在1995年这样问道:“如果我们扬弃孤绝人类的神话,哪种文学还保有其可能?它必然是种文学,抛弃了,或至少质疑了,什么似乎才是文学最基本的焦点:角色、人物、叙述意识。”(1995:145)这种文学不只重新思索自我的角色,而且至少同等重要地重新思索自然作为他者的自主性与主体身份。对有生态关怀的作者来说,让自然发声一直是个中心议题,尽管自然不能言说,尽管它可能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作家使用何种美学策略为不能言说者代言呢?他们如何想象非人类中心的自我与非人类作为主动体,有时甚至是会言说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呢?接下来的论述笔者将针对语言作为沟通工具与文学再现的概念,质疑它描述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能力与限度,同时,察觉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笔者将以贝瑞·罗培兹(Barry Lopez)的《北极之梦》(Arctic Dreams)作为文本范例举证,阐述有生态意识的作家以何种策略全副武装解决为非人类自然发声这一难题。
二、语言和文学的生态批评观点
长久以来,在西方文化中,语言与理性已被视为文化的关键标志,因为它区隔了人类与非人类,也将人类抬升到高于非人类的位置。这概念强调自然与文化的严格分野,例如动物与人类的分别。它也强化了有阶级意识的二元主义,这主义不只认为自然注定要完全对立于文化,自然也劣于文化,需为文化服务。然而,就像唐纳·海若威(Donna Harraway)在她颇具影响力的“人机合体宣言”主张中所阐明的,物种之间的清楚分野不再站得住脚:“二十世纪晚期的美国科学文化中,人类与动物的界线已经彻底断裂了。最后一片诉求单一性的立足点已被污染了,如果它还没有转变成游乐场的话,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心理事件——没有一件事真正有说服力地区隔人类与动物。”(1990:193)海若威的陈述暗示了更宽广的语言概念,这概念超越(言说或书写)文字作为意义制造工具的特权。从一方面来说,它暗示语言概念本身就是个自然的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强调语言与非语言沟通的关联。盖瑞·史耐德(Gary Snyder)是这观点雄辩的代言人。他认为语言与文化并没将我们与自然隔离,相反,却“从我们生物—社会的自然存在中浮现出来,因为我们曾是/现在仍是动物。语言属于与心理需求与身体神经共同逐步形成的心-身系统。语言就像想象力与身体,主动浮现”(1990a:17)。他认为学习语言的能力超越了智识与理性,连结到“野性的无意识”(1990a:17),因此,他将先于论述存在的自然理解为拥有制造文化的力量。此外,语言不是固定与静态的某种东西,它是活跃、流动的事件,是“缭绕的气息,松树群间的微风”(1990b:69)。对史耐德而言,自然本身就是文本,然而我们不将它理解成是我们的(各种)文化产品,而是“透过时间储存的讯息。策略是岩石、沼泽中的花粉层、树干向外不断延展的年轮……”(1990b:66)。这是自然自己“书写过”的文本,吊诡的是,它却只能以人类文字来阅读与诠释。
土地概念,或者——更普遍说来——自然作为文本,早已被罗福·华尔罗多·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畅谈过。他将文字理解为自然事实的符号(1960:31)。但是当艾默生的自然语言最后超越了物质世界,当代的生态批评家仍稳定地身处其中,这当中通常指的是各种口语文化。对这些批评家而言,土地是“口语表达的主要视觉对应体,是所有口说意义可见的相应物”(Abram,2003:259)。根据这观点,抽象系统,像书写语言与当代论述,倾向消抹土地并将它与人隔离。马克斯·欧罗斯拉杰尔(Max Oelschlaeger)宣称人们已在绿色世界错位,我们曾从这世界获得读写能力,但我们可再透过语言回归这世界。他提出“地球-谈话”这发展,“在这谈话中人类以外的存在可再被赋予声音与被倾听”(1995:50,51)。“地球-谈话”例子之一,根据欧罗斯拉杰尔的说法,是吉姆·契尼(Jim Cheney)的生物区域论述,它“没有将生物物理世界化约成语言,而宁愿将那世界吸纳到从生态角度出发的微妙人类论述中”(Oelschlaeger,1995:51)。另一个例子是克里斯多福·莫尼斯(Christopher Mones),他也表示自然在笃信理性、智识与进步的宰制论述中变得沉默。这沉默来自于人们将自然视为象征而非动物性存在的文化观点,视其为沉默物体而非有价值的主体。根据莫尼斯的说法,我们必须学习新语言,即所谓“生态谦逊的语言”,他也相信这语言是以原始、口语的文化来言说(1996:17;Oelschlaeger,1995:52)。最后,欧罗斯拉杰尔提到戴维·埃伯拉姆(David Abram),后者探索语言,视其既是自然的过程,也是像身体论述这类非语言的沟通,他相信这些都隐藏在通常的语言表达形式中(Oelschlaeger,1995:52)。另一位探索非语言沟通的批评家是丹尼尔·怀特(Daniel White)。归功于格瑞国尔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丹尼尔说出“身体附属语言的密码”,意指一种理性几乎不了解的身体语言,“却将人们彼此连结,也连结到哺乳动物社群……我们是‘主体’,注写在社会、生态与生物语言,还有附属语言密码,再次回应贝特森,我们所有的行为,包括我们胃肠,都在沟通”(1998:188)。
“地球-谈话”或许能克服人类与自然世界疏离这概念,暗示想要回归到与非人类和谐的原初状态,但这跟人们要完全与生态圈分离的概念一样,都是假象。然而,以上提及的语言概念明显表达出对自然和文化相依相存的理解,而语言是构成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既是自然的过程,也是文化的工具,由于言说者意识形态的倾向各异,语言要不就帮助人们处于物理世界之上,要不就帮助人们察觉与物理世界的连结。同时,人类语言也不是唯一的沟通形式,假设它有使人类高于其他物种的特权,纯粹是傲慢态度所致。若谨记语言概念既是自然也是文化现象,生态批评家必须追问这概念如何被有生态批评意识的作家用来赋予自然声音,这自然以它自己的方式沟通,这方式人类无法完全掌握。
在极具影响力的《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研究中,劳伦司·彼罗列举详细的文学策略清单,展现自我与自然的关系的新概念。他以梭罗的《湖滨散记》作为环境书写的原始文本,但也提到其他过去与当代的自然作家。笔者无法公断这本书搜集的丰富材料,但会针对一些最相关的面向,指出有帮助的范畴进行非人类在环境文本的分析。根据彼罗的说法,最重要的生态中心文本的发明是扬弃的美学。它暗示叙事者自发地追求简朴风格,不断质问监督意识的权威性,最后扬弃了物质世界的战利品,也消解了情节(1995:144)。然而,要创造非人类中心的自我已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生而为人,我们难以放弃自我意识却还能书写与反省感知。彼罗说,要表达新的个体意识,美国自然作家要不就发展出自然环境的管理或社群概念,在这当中杰佛逊式的农业改革主义是主要典范;要不就激烈地拒绝同一中心论的形式,就像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清楚表达的非人类主义(1995:159,162)。非虚构的环境文本倾向边缘化人类角色,进一步使角色失去稳定,借以彰显其不稳定性(1995:168)。有些作家,像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以多种声音诉说故事,包括土地与其居民的声音,创造“意识多中心的扩散”(1995:176)与“主角多种地位的多样性”(1995:179)。这种扬弃从不意指完全失去自我,而是需要想象“非人类个体作为真实有意义的伙伴”(1995:179)。
重新评价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不只是原初、口语文化的元素,从去神话化的形式来说,也是现代生态的元素。亲密关系这一概念需要先将自然认知为主体。根据彼罗的观点,文学文本通常以拟人化的策略来达成,有时候难免导致情感误置,赋予无生命体人的情感,有时要努力将自然看成合法的人,就像克里斯多福·史东(Christopher Stone)著名的文章《树应该有立足点吗?》(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所论。或者,地球也被拟人化成盖亚假说或新异教徒女性主义地球之母形象。生态批评文本通常重新创造神话形式来再现自然的人性,他们拒绝将自然看成为人类利益存在(1995:第6章)。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依存的概念暗指重估地方与“唤醒察觉了局限也尊重了在地的地方意识,它塑造我们,反之亦然”(1995:253)。用来唤醒环境反省的策略之一是以崭新、令人惊奇的方法看待与重新感知熟悉的事物(1995:262)。要去创造这具生命力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小心翼翼地使用比喻、神话,甚至幻想(1995:266)。最后,这些策略都需要基本的文学创作与虚构能力,“不是为了创造另类现实,而是要看看如果没有想象力给予一臂之力,有什么是似乎一点也无法被看见的”(1995:102)。
三、贝瑞·罗培兹的《北极之梦》与自然之声
贝瑞·罗培兹的《北极之梦》(1986)是目前经典的当代环境文本,展现了典型的环境批评对土地和居民的探索。这是自然书写的范例,作者试图赋予北极客观、细致的描绘图像,同时反省他这么做的能力,像写到一段与完全陌生、甚至对大部分的拜访者怀有敌意的土地进行对话时,他结合科学与个人观察,还要让遥远生态圈“发言”的哲学省思。将彼罗用来分析美国自然书写的范畴谨记在心,我将会询问罗培兹以何种特殊的文学策略去赋予自然——土地与非人类住民——声音。他们有呈现出像许多生态批评家渴望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新关系吗?为什么他一开始要选择像北极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呢?
本书一开始,罗培兹主要焦点就在于人类态度与型塑土地的各类感知,同时,他清楚表明除了这些之外,土地自己的存在。因此,他强调自然概念由文化铭刻,但也是免于人类算计估量的主动体。人类的感知被强调,因为没有感知,我们无法察觉非人类。然而,我们愿意看到什么,我们想从这里获得何种结论,我们的渴望如何形塑知识,这些都造成很大差别。罗培兹选择北极,因为在那里我们基于观察与经验温带气候的平常感知开始动摇。我们绘制地图、画线与清楚划分界线的渴望都挫败了。举例来说,由于地壳构造活动与其他影响,地球稍微晃动,致使其轴心偏移,无法确定北极的确切位置(1987:18)。太阳无法东升西落,一天也无法清楚区隔成清晨、正午、傍晚与深夜。所有“传统,如此深植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思考这攸关文学与艺术的传统”(1987:20)。对我们而言,什么是似乎自然、固定的事实——太阳或地理地标位置的课程——转变成相当有弹性的某种东西。在北极,我们面对的是知识的局限与进一步观察的需要,要重估长久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显然因为在北极,光线与时间的起落如此不同,以至于地景能够以惊奇的方式揭露出一般人对土地思考的自以为是”(Lopez,1987:12)。要探索非人类环境,前提之一当然是要体认人类偏见与认知不足,还有对目前“近在眼前”的存在所知甚少的谦逊体会。
罗培兹展现给读者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多加留意,土地与其居民会依然保持静默。如果我们将先入为主的概念与错误认知带到像北极这样的异地,把它想象成“原始、刻板,与异教徒的”,我们不只永远不会发掘其繁复与美丽,我们也可能滥用与剥削,可能会“毫不考虑地储存毒物或测试武器”(1987:255)。是什么带我们到这些地方,是探索的想望,经济的动机,或是要发现较不复杂生命的浪漫想望,这些都将影响我们的视野。“欲望会导致想象力误解其发现”(1987:256)。不留心的态度常会造成对土地、其无辜住民与动物的有害后果,这态度也可能会反挫,真的杀伤对“近在眼前”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一个确切的例子是19世纪英国海军军官的殖民心态,很多都死于北极。“它的(探索的)失败出于民族优越感,以为道德与技术优于爱斯基摩的态度,把土地当成蛮荒与不堪一击的认知”(1987:360)。这些军官不相信毛皮衣、雪屋与新鲜肉食的好处会大过他们自己的制服、帐篷与罐装食品。队长克罗计尔(Crozier)是富兰克林(Franklin)的副司令,和他的队员一样,死于“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们旅行时穿着的茧状防护衣裂开,把他们暴露在许多元素中。权威失效了。这些军官太多了,而他们不知如何是好”(1987:383)。另一个例子是许多现代钻油者的殖民心态,他们把北极视为科技无法破坏的广大荒原。虽然没有在北极伤亡,他们却也不尊重这块土地。所有男人工作的大部分帐篷就像监狱,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在那里的工作者目的就是为了赚钱,然后尽早离开那地方。无论它有什么尊严与多样的生命形式,他们都没有感觉。
罗培兹警告别去开发像北极这样的异地,基本上与两种试图与其进行对话的选择互为消长。其中之一是科学方法,另一个是他称为“地方之眼”或“察觉的技术”。所有关于北极地理的章节,牦牛、北极熊、独角鲸、鸟的迁徙或冰山的移动,都饱含他本人细心观察、个人轶闻与科学资料。举例来说,北极熊的解剖细节,像是大小、重量、毛皮的厚度与颜色、熊迹的描述或族群密度,都为生物学家的工作提供精确与值得尊敬的数据。罗培兹甚至将颈挂无线电项圈的熊走过的土地范围地图放进来,同时分享许多科学报告信息。熊脱毛的描述传达出细心、精密观察的意识,同时也以诗般的眼欣赏其美丽:
毛发本身传达出视觉上的透明、无色感。最明亮的白出现在春季换毛时,那是这些年幼小熊皮毛最纯净的时分。暴露在阳光中,毛发透露出细致色调;柔软的黄色调出现在臀部,沿着两胁,直到双脚——淡淡的柠檬水色、杏仁黄、奶油黄、麦秆白。色调每年随动物的成长加深。秋天午后低沉的阳光中,年老公熊的皮毛也透显出成熟麦田的金黄。
赋予自然现象精确的描述,梭罗已经在测量瓦尔登(Walden)湖区冰的厚度时实践过,这是不以偏见或无先入为主的想法探索非人类世界的方法之一,让搜集的资料给予读者对非人类世界特殊与繁复的第一印象。当然,这还不够,因为显然动物生活的复杂度无法在实验室中正确分析,或单纯以科学范畴解释。以北极熊例子来说,“相互作用……在休息、运动与觅食之中,带他们安稳舒服经历生命的是无法被拆解成碎片的某种东西。就像溜冰者深长、优雅的弧形,它是生命的叙述,是关于美的完整实践”(1987:89)。田野研究者倾向简化与概念化,然而这也是要了解“近在眼前”自然的重要步骤。非人类的时间一再以无法预期的行为使人震惊,它可能永远与已记录的事实相反,因为土地与其居民彼此适应,因此也随时间改变,他们从不在精确的科学范畴之内被固定或认知。唐娜·海若威已明确指出,当我们试图将非人类理解为主体时,“没有特殊的再现原则、解码或发现保证任何事情”。她偏好以北美土狼或魔术师的神话形象来描述人们目前对自然的了解,“认知到我们放弃支配却仍持续寻找忠诚的处境,也明白我们将持续被蒙蔽”(1992:199)。对罗培兹而言,科学探索也很快地暴露诸多局限。许多西方生物学家知道他们也只能了解动物的一小部分,“当实验可以被设计来呈现动物的多种面向,动物本身将永远比任何实验设置的总数量还巨大”(1987:269)。统计不能充分了解永远存在的神秘。然而,对罗培兹来说,我们对非人类的衡量,最需要的是认知到想以人类语汇了解他者时的严格限制。谈到动物迁移,他承认“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回应;我们选择自认为适合的空间向度与时间长度去描述,但我们无法确认其关联”(1987:177)。这类陈述透露出扬弃自我,了解到人类不是生态系的唯一主体,了解到还有超越智识与科学领域的其他复杂生命形式。
为了更接近“近在眼前”的自然,人们必须超越科学研究。在北极当地居民中,在必须生存在宛如沙漠国家的爱斯基摩族群中,罗培兹找到另类认知模式。他们是不屈不挠与务实的族群,他“察觉到环境中最模糊的生命鼓动,这环境对未经训练的眼睛来说似乎缺乏特色与冗长不堪。这群爱斯基摩人有掠食者对琐碎的机敏,进而透露出细节”(1987:96)。他称呼这群人观察与发现土地最微小变化的能力为“地方之眼”(1987:96),这是文明化的文化已然失去的。它要好一段长期时间细心观察,尤其是狩猎时,还要与自然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这是自然与个人经验的结果。此外,爱斯基摩人也不反对动物,将每个动物视为独立个体,以让人无法预期的方式行止坐卧。这准备好要面对预料之外事物的意愿依靠“想象不熟悉的能力”(1987:176)。对西方心灵来说,它指的是承认非人类大于科学领域的意愿,“动物使我们困惑……因为他们终究与生命的复杂度无法分别”(1987:178)。对罗培兹来说最重要的是爱斯基摩人相互依存的知识,“到目前,事情只存在他们与其他事情的连结中”,这种关系包含所有却并非静态,“这模式总是在活动”(1987:200),将自然认知为流动、无法预期与个人的已导致对爱斯基摩的“技术觉醒”(1987:113),这技术基本上指的是西方人倾向视为迷信的行为,但它事实上基于尊重与畏惧。罗培兹将这种畏惧理解为爱斯基摩人必须为他们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付出的代价,“这畏惧联系到他们的知识,认知突然、激变的事件既是生命与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停下来观看某种美丽的片刻”(1987:201)。他绝非理想化或浪漫化当地人,他看到其暴力与冲突。他的确强调科学思考之外,还有价值的是以自己的语汇了解非人类的能力,这了解牵涉到关联感,这知识奠基在土地、动物与人生活在彼此互相依存的百年经验中,以深层生态语汇来说,他们是生物中心平等的。
一旦非人类不再被视为被动、无生命的物体,而是活动、复杂的存在,像罗培兹这样的生态批评作家可以开始“想象不熟悉”,想象这世界对动物来说像什么,举例来说,让动物自己“言说”。从海边悬崖俯视鲸鱼浮动在海面上,他惊奇这特殊的哺乳类生物的进化,惊奇它如何经历与水与空气的互动。为了对它有进一步了解,他比较了动物跟他自己基本生物的特性。同样,科学数据只是开始:储存在肺、血液、肌肉、其他器官的含氧数量,氧如何与肌肉中的血红素分子与肌球素分子结合——这些事实被用来注记他自己与独角鲸的异同。根据罗培兹的说法,两者的差异在于我们住在二元世界,而独角鲸并非如此。它味觉与嗅觉对化学器刺激的反应能力几乎消失了,它几乎看不到,可它的触觉高度发展(1987:137,138)。这些事实没有解决鲸鱼的神秘,却让我们欣赏到另一种生物的复杂生命,也让它们不再被视为蠢笨物,接着是惊奇与敬畏:“‘这世界’对这生物来说如此不同,对它们来说视觉只不过是末梢感官,然而,这生物具有三元的听觉空间。”(1987:139)此外,在《北极之梦》中,罗培兹不只将这世界想象成独角鲸,也想象成狐狸、潜鸟、大黄蜂、短尾黄鼠狼、北美驯鹿或北极熊(1987:267)。他试图想象土地的地理如何适应生物的个别经验,举例来说,出于生物特性,从狐狸视角来看,这岛屿土地面积势必更拉长,因为这动物的体型比较亲近土地,土地也必须在不只一年的演进中为狐狸改变。
这种以动物般思考的研究去除人类意识中心,也为扬弃自我与延展到其他意识形式作出贡献。它也重新评估“近在眼前”这世界,它不仅只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文本,也是以许多方式存活的实体,仰赖观看者的感官系统。凯瑟琳·海勒司(N.Katherine Hayles)提出“有限制的建构主义”是种有效模式,指出心灵与世界互动的崭新认知。对她而言,这世界就像它“果真如此”,并不以每个物种为它自己建构的不同世界存在。追随智利神经生物学家洪门托·马特罗讷(Humberto Maturana)主张青蛙的感觉器官以高度物种特殊方法向大脑说话的说法,她主张“我们最有能力谈论的认知之前‘近在眼前’的存在,就是它是无媒介的流体,是潜能经验的流体,面对不同处境的观察者会以不同方式触发。身为这些角色,人类与非人类与无媒介的流体互动,他们的世界成为一体”(1995:413)。她的结论是:“对人们而言,所谓重要的现实既不存在世界自身,也不存在观察者身上,而是在观者与世界的互动中。”(1995:425)罗培兹对独角鲸的世界与其他动物的揣测,可与心灵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相互比较。他们传达出从自我到生态中心意识的转移,同意非人类他者以不同的复杂性去为自己发声。人类自身不再被理解为阶级高的优越者,却受限于他或她对动物的了解,这些动物有自己的表达形式。
对罗培兹而言,土地也可为自己发言,只要人们愿意耐心观察,接受自然是活生生的实体。同时,这更新过的认知成为我们评估土地的前提,尤其这异地是像北极这完全陌生的地景时。只有透过敏锐察觉,我们看到的才不只是荒地。罗培兹对人们以欲望与想象力形塑土地、驱散疏离感的方法感到兴致盎然,然而,同时,“这物理地景是难解的,它有能力超越我们对它的任何了解”(1987:xxii)。他假设人类心灵与“近在眼前”的自然语言是某种令人惊叹的活体。为了“聆听”这土地必须“说的”,罗培兹仅是观察,然后尽可能具体描述他的印象。他的方法是从某一地图知识开始,告诉读者河流、海湾与山的名字。进一步聚焦在丰富的细微生物细节,这传达出苔原生命的丰富感与多元性。“举例来说,人开始在单一棕色调的苔原草丛间注意到鲜艳的红、橘、绿。狼蛛扑向闪烁的甲虫。一团牦牛毛松软地趴在虎尾草属的熏衣草花中”(1987:xxiv)。对罗培兹来说,彰显生物丰富性的必要姿态是弯腰。只有弯腰,才能看到筑巢地表的角雀眼中闪耀的野性(1987:xx),只有透过这种姿势,才能表现谦卑与尊敬。
敏锐察觉与谦卑态度不只帮助他探查细节,也让他看到被观察的元素如何融入更大的系统,如何完美地与生态网配合。他可以科学专有名词描述这种互动关系,同时表现出动物与背景何以需要保持原有身份。然而,土地的神秘无法以语言正确言说。当他以所有感官察觉环境,有时候会被回馈以神秘美感与超越文字的经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人类范畴不足,时间与目的不足,尤其是语言。举例来说,身处冰山墙内,他感觉到身体的美感,在肉体上,这知识“被获得,不以文字,而是以,仿佛,祈祷”(1987:404)。再一次,非人类他者,像是动物与这里提到的土地这些例子中,以比理性分析部分还要巨大、伟大的实体被了解。像深层生态学者,他提到自然“与生俱来的特质”,提到这种尊严“超越启蒙哲学家的说法”(1987:405),那说法无法被有殖民心态与不愿放弃他们先入为主成见的人所经验。一次次,罗培兹强调耕耘感官认知的必要。他敬佩那生活在阿纳卡菟卜卡山隘(Anaktuvuk Pass)的人,他告诉罗培兹,当他说一个字前,他甚至会“绷紧‘他的’感官感激‘土地’好长一段时间”(1987:257)。只有那时土地才向他开放。罗培兹也鞠躬、倾听、观察以达到与土地的深层亲密关系。只有那时他才了解到土地与其居民、人类与非人类互相形塑,双方都是不同面向的主动体。这种互惠也作用在食物供应层面,像人们认知自己对自然的亏欠与感激时。可这也更难定义了,罗培兹说,这地景“提供各类隐喻和象征来引发人们打探神秘”(1987:404)。最后,他对《北极之梦》的主要兴趣在于语言和文学与环境互动与相互影响的方式。那么,罗培兹的语言概念是什么?暗喻与象征,还有神话与故事如何进入与非人类的对话?
就像史耐德与其他有生物中心意识的作家和评论家,罗培兹也相信语言不只是分别人类与自然的文化工具。举例来说,他不同意华尔福(Whorf)的观点,对后者来说“语言只是人类在心灵创造后投射到现实的东西,是他强加在地景上的东西,仿佛土地只是他想象力的储藏所”(1987:277)。对罗培兹来说,这观点两处有误:首先,地景并非被动、无力的空间,而是活生生的地方;第二,语言“在‘人’与土地的交谈中进化——在用雪靴的指头检测海冰时,在吃野梅时,在借着海豹油灯修理雪橇时。长久的调查创造有辨别力的语言。就是这语言秩序,声音与思考的生态,来自心灵与地景的交流”(1987:278)。语言回应土地,同时也形塑环境,因此相互依存不只是物质世界的现象,也包含人们的心灵和特殊表达形式,尤其是语言。
只有这网络关系内的元素拥有某些共同特质,这互惠才成为可能,但这不是说他们基本上都一样。罗培兹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仍在作用。对他而言,人类的差异,真得将我们区隔的不是工具使用或语言作为沟通方法,而是寻找隐喻的热情。隐喻是“人类心灵的崇高成就”(1987:391),是“想象的基础工具”(1987:250),用以帮忙探索他者的差异。他主张隐喻能让成年人优雅地生活在矛盾之中,因为借由让两不同的事情同时平行存在,而不连结他们,可使两者远离矛盾(Bonetti,1988)。举例来说,鸟类的迁移,一开始以个人观察与大量科学数据被探索,可最后,它的意义在“呼吸,像土地的气息。春天吸纳大量的光线与动物的迁移。夏天缓和呼吸。秋天吐露催促他们往南的气息”(1987:162)。这些例子充斥在《北极之梦》。他们彰显的是想象的力量可让异地、荒地转变成充满精力与生命力的地景。这能力是特殊的人类特质,不该在与非人类融合的欲望中被忽略。拟人法,通常被指责为“智识上的癌症”,并没有困扰罗培兹。它应该被用来作为“比较询问的工具,也许是心灵运作的唯一道路”(1987:250)。它的技巧并非“重新认知熟悉”(Buell,1995:262),而是借拟人法的帮忙去熟悉异国情调。对他来说,扬弃自我并不是将它消抹掉。这样的话会失去人性,也不可能去言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了。他甚至认为自我是人类存在的必要部分,尽管这自我需要被检验。更重要的是伴随它而来的责任感。举例来说,写作是种“自我的宽广行为”(Aton,1986),而作家必须特别留意他的工具,尤其是隐喻。他必须一直接纳自然环境的细微复杂,他必须驾驭自我,同时演练雪尔曼·保罗(Sherman Paul)所谓的“谦逊”(humilitas);他必须“将他自己呈现为询问者,永远非专家”(1997:103)。
具有与生俱来矛盾特质的隐喻是言说人类心灵与非人类生活何以格格不入的管道之一。另一种再现形式是叙述。再一次,罗培兹仔细观察北极“原住民”,探索他们的土地经验如何成为故事。故事,神圣或亵渎的,都有将人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功能。罗培兹称他们为“固着在地的故事”(1987:297),他区别以神话地景为背景的神话时间故事,还有关于旅行与每人每年都可回顾其发生的通俗故事(1987:298)。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地景“证实两种故事”,这故事让人们一直活着,也让故事里的人们活着。“语言,各类故事,将这观点连结在一起”(1987:289)。再一次,就像隐喻的例子,想象力从土地开展,也紧系于土地,滋养了人类与非人类的互惠关系,允许双方继续存在与茂密开展。相对于仅只是记录事实,这是关于土地的可见面向,故事可以诉说关于记忆、神话、欲望与恐惧等肉眼看不见的特质,这些都来自于某个特殊地方的实际经验。许多不善接纳土地神秘特质的欧洲探险家所说的故事无法评价异地。他们只是反映出想占领仍是陌生、有敌意、甚至“安静”的地方。相对说来,生态中心的心灵,“可以想象美丽与召唤亲密。它可以在字面分析仅能发现树木、岩石与小草处,却能发现抚慰”(1987:391)。这种想象力终结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疏离。它并非浪漫地融合观察者和宇宙,而是允许他的心灵反省“近在眼前”生命的丰富性。根据罗培兹的观点,要做到这些,除非“将我们的世界带到异国地景去澄清他们……土地驱策我们苏醒,以了解自我”(1987:247)。
最后,什么是像《北极之梦》这种有生态批评意识文本的叙述角色呢?罗培兹发展出哪种新感性去发展非人类中心的自我呢?尽管他努力强调非人类自然有其激发敬畏的异质与美丽,有其活力与完整,他仍无法放弃人类心灵的重要,才能进而进入他渴望与自然环境的对话。举例来说,雪尔曼·保罗甚至主张罗培兹争论的议题不是隐喻,“而是我们用它来让心灵获得特权的方法,赋予它超越事物的统治权”(1997:102)。罗培兹的议题是心灵如何使不熟悉的事物产生意义,我们如何将见闻组织成语言,或者,根据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沉思外在自然世界的行为,已经牵涉到共同行为,这行为是有关细察有观测力的自我与自然的关系。”(1992:153)尽管最后特许给人类心灵特权,《北极之梦》的自我仍被扬弃了。一次次,罗培兹以生动的细节认知与展现出人类的自我不是唯一有意识且“近在眼前”的活体。他也表示意识到要完全了解非人类生命的复杂与多元的自身限制,两者相遇时,只有谦卑以待。尽管叙事者“我”将许多细节选择与安排进他自己的故事,他也让其他丰富的声音被听见:观察、轶闻、科学资料、当地与非当地的故事,这些都被交织进北极生活。没有一种声音有优先权。然而,罗培兹说,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容忍不同认知的价值,要提醒的是,要比较这岛屿上各种动物的环境”(1987:313),而且,“没有人可以诉说整个故事”(1987:273)。就像玛丽·奥斯汀、罗培兹创造的是“意识多中心的扩散”(Buell,1995:176),包含了不同的人物、事实、情绪、想象与欲望,还有土地自身。这样的态度不得不以个人观点言说,但它并不选择宰制或排除,而是邀请进入对话,读者也受邀在内。最后,要达成对“土地自身更特殊的了解”(1987:12)表示要从与非人类环境的生态中心关系观点出发,以对自我产生更特殊的了解。其回馈是心灵富足与非人类环境的联系经验,发现地景的完整与尊严反映在人类心灵。这并非静态给予,是需要不断更新的过程,需有生态批评意识,要谦虚,也需要机灵地与富含想象力的心灵互动。
注释:
①关于自然、文化与其相互的层叠关系的概念,更仔细的讨论请见Grewe-Volpp(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