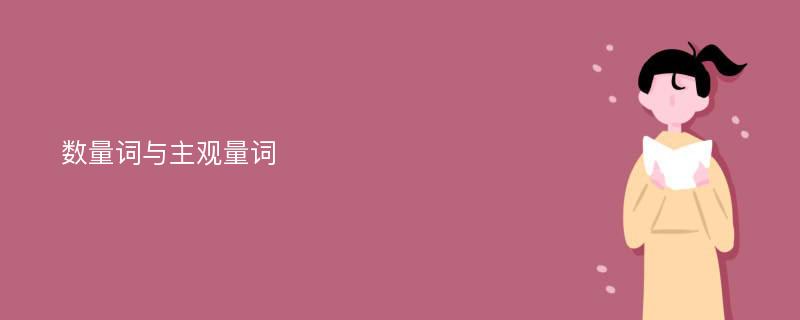
数量词语与主观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论文,词语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1999)06-0090-08
主观量是客观世界的量范畴在语言中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含有说话人主观评价的量[1]。陈小荷(1994)讨论过有关主观量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就”、“才”、“都”表达主观量的情况[2]。王弘宇(1996)讨论了“仅…,就…”这种格式的主观量问题[3]。李宇明(1997)论述了主观量的三种成因:异态量、直接评价和量的感染;并据此把主观量分为异态型主观量、直评型主观量(包括直赋型主观量、夸张型主观量)和感染型主观量[4]。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讨论由数量词语本身(包括带有直接修饰成分的数量词语)所表达的主观量。
为有利于本文的讨论,有必要先粗线条地描画一下表达主观量的各种手段。主观量的表达手段有语表手段和语境手段两大分野。语表手段指结构本身带有主观量的标记;语境手段是结构本身不带主观量的标记,但通过一定的语境可以把握。例如:
(1)预考后拿到准考证的只有二十二人。……只有八个人坚持到考试终了。(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第1期第141页)
(2)几十块钱罢了,何必言谢?
(3)回沪才一周,亲友们就探访完毕。(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378页)
(4)一看票价,这两个人的脸色就无法自然——每张票十八元。老天,讲理不讲理,不管吃不管睡只不过听几首歌,却要这一大笔钱!“太贵了。”鲁智胜说,“等我发了财再来!”(秦文君《男生贾里》,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5)每张票十八元!
(1)~(3)是语表手段。(1)中的“二十二人”和“八个”这两个主观小量都是通过副词“只”来显示的。(2)中的主观小量“几十块”是通过加在小句末尾的“罢了”来显示的。(3)中的主观小量“一周”是通过“才…,就…”这一格式显示的。(4)的主观量表达使用的是语境手段,“十八元”在“每张票十八元”中并不能显示其主观量的身份,主观大量是上下文中的“环境语”来点明的:“老天,讲理不讲理,不管吃不管睡只不过听几首歌,却要这一大笔钱!”;“太贵了。”鲁智胜说,“等我发了财再来!”语境还包括言外语境,(5)如果是在(4)的环境中使用,“十八元”也是主观大量。
表达主观量的语表手段又可以再分为四类:A.数量词语,包括带有修饰成分的数量词语(简称“数量标”);B.加在句末的标记词(简称“句末标”),如(2)中的“罢了”;C.充当状语的副词(简称“副词标”),如(1)中的“只”;D.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固定格式(简称“框架标”),如(3)中的“才…,就…”。
本文讨论的数量标只是主观量诸多表达手段之一种。数量标大体上有如下一些情况:a)数量词语的复叠;b)一些特殊的数量结构;c)受一些词语直接修饰的数量结构。下面分别讨论。
一、数量词语的复叠
1.1 复叠
数量词语的复叠包括重叠、叠加和重复三种现象[4][5]。例如:
(6)这些日子天天忙到半夜才睡……(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第40页)
(7)不能有了一点点成绩就翘尾巴!(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
(8)饭不能两口两口地吃,要一口一口地吃。
(9)不同的药混在了一起,只好一一分检一遍,反而耽误了时间。(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19页)
(10)我们老知青,用我们的千千万万双脚,走了二十七年,走出了这样一条线,一条奉献于乡土中国的具有完整内涵的精神与文化的生命的浩瀚银河。(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第3期第65页)
(11)风儿掀起一排接一排的轻浪,激起一片哗哗的喧响。(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52页)
(6)~(9)中的“天天”、“一点点”、“两口两口”、“一口一口”、“一一”是数词和数量词语的重叠现象,重叠是属于词法范畴的现象;词法又分构词法和构形法,这些重叠从总体上看可以划归到构形法中。(11)中的“一排接一排”是数量词语的重复现象,重复是属于句法范畴的现象。(10)中的“千千万万”是数词的叠加现象,它不是“千万”的重叠,而是“千”“万”分别重叠之后的加合;叠加是介乎重叠与重复之间的复叠现象,纵跨词法和句法两个层级[5]。
从复叠的材料上看,数量词语的复叠,有的是量词复叠,如(6);有的是数词复叠,如(9)和(10);有的是数量词语复叠,如(7)、(8)和(11)。
数量词语复叠可以表达五种语法意义:a)所有的(包括“每一”),如(6);b)多量,如(10)和(11);c)少量,如(7);d)定量反复,如(8);e)逐一,如(9)。a)和b)表示主观大量,c)表示主观小量。而“定量反复”和“逐一”一般不反映主观量,可以暂不讨论。
1.2 表“所有的”的复叠
表示“所有的”数量词语的复叠形式一般是量词的"AA"式重叠,但有三种情况需要特别交代。
第一种情况是,如果名词(限于单音节)采用"AA"式重叠,也具有量词"AA"式重叠的功能,例如:
(12)人人都有妻子,但不见得人人的妻子都会写小说,这跟同样是春雨如油,不见得每根枯树桩都能长出蘑菇的道理极其相似。(王树增《禁止忧郁》,《花城》1990年第4期第8页)
(13)小米由“进口”转为“出口”,家家大囤满小囤流,粮车的金色长龙直达南宫。(贾浸《沧海一粟》,《当代》1992年第1期第123页)
“人人”、“家家”也都表示“所有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时“一AA”式的数量重叠也可以表示“所有的”,如:
(14)都不作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耷拉累了,便都抬起头来瞅我大嫂。(马其德《命独如我》,《当代》1997年第3期第169页)
(15)大哥当时年已三十,二哥、三哥、四哥也都不是小孩,一个个都是当了爹的人,再添个小弟弟的确有点滑稽让人笑话。(同上,第166页)
(16)可意搬到妈妈卧室的头一晚,肖晶安排他上床以后,唤弟、剩儿、石头一个个都跑来观瞧,嫉妒艳羡溢于言表。(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第3期第133页)
“一AA”式多数表示多量,表示“所有的”是特殊的用法,其条件是,在“一AA”式之后带有或可添加上表总括的范围副词“都”或“全”。(14)的“一个个”后可以加“都”或“全”,(15)和(16)的“一个个”后带有“都”。总括副词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皆是如此。总括的范围有时直接说出,如(15)中的总括范围是“大哥、二哥、三哥、四哥”,(16)的总括范围是“唤弟、剩儿、石头”。
第三种情况是,有些"AA"式重叠的量词并不一定表示“所有的”,例如:
(17)满天灰云,冷风阵阵。(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第3期第53页)
(18)父亲专心致志,一面揭起层层柔软的白纸,反复擦拭着那块墓碑,一面口中喃喃地念着……(赵江《十七棵杏树》,《花城》1990年第4期第126页)
(19)团团烟气不时冒出鼻孔口腔不时虚化我的视野。(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第4期第187页)
(20)先锋分子们回到城里后,传来了遥远边寨的风声雨声——种种令老知青们欣慰、忧虑、牵挂、渴望的消息。(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第3期第61页)
“阵阵”、“层层”、“团团”(注:“团团”还有引申用法。例如:“牛老茂死活不离恩少岩的宿舍,在门口倔倔地蹲着,惹得小刘团团转悠。”(关仁山《老陵》,《当代》1997年第3期第82页))、“种种”虽然也是"AA"式的量词重叠,但不表示“所有的”,而表示多量。它们都不能受“都”、“全”的总括。
1.3 表“多量”和“少量”的复叠
表示“多量”是数量词语复叠最常见、最重要的功能。例如:
(21)整齐的长条性状的盐畦紧密排列着延伸向远方,看上去那一道道的畦埂像一根根黑线切割着白瓦瓦的水面,把它们切割成一面面有棱有角的镜子。(路远《青盐垛》,《当代》1992年第1期第50页)
(22)他想到了自己几天来的一幕一幕,想到了准考证、医院、徐北华和那姑娘。(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第41页)
(23)你的眼光一次又一次凝聚。你被一个又一个潇洒男士的风度吸引。(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第4期第181页)
“一道道”、“一根根”、“一面面”、“一幕一幕”、“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都是表示多量。
同“多量”相比,表示“少量”的数量词语复叠现象则是较为少见的。在搜集到的材料中只见到“一点点”,“一点一点”和数词的叠加形式“三三两两”的用例,例如:
(24)我们只有不计年华的流逝,才能干成一点点事。我们只有突破一般人的人生常律,才能期望有一点点收获。(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第3期第69页)
(25)然后又有三三两两的人上来了。(徐迟《江南小镇》,《收获》1991年第2期第157页)
但是,“点点”却表示多量而不表示“少量”,例如:
(26)萤火点点在他前后飞舞,在夜色中划出一条条优美的光辙,如同一个个探马飞骑,频繁地把季蒙的消息报告给林子里所有的生命。(张波《五羊》,《花城》1990年第4期第117页)
“一点点”和“一点一点”作状语,虽然也有少量的含义,但那是“一点”的作用,而不是复叠式的作用,且“一点点”和“一点一点”作状语的主要作用是描写动作的进程,而不是表示主观小量。例如:
(27)鳗捧了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来,有两颗荷包蛋,一点点给爹喂了下去……(路远《青盐垛》,《当代》1992年第1期第68页)
(28)韩佬佬心在一点一点缩。(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第3期第58页)
二、一些特殊数量结构
有些较为特殊的数量结构(包括数词结构),本身就可表示主观量。较为重要的是“一+量+的+N”结构、一些“一+量”结构和一些特殊的数量性词语。
2.1 “一+量+的+N”结构
“一+量+的+N”中的“一”当“满、全”讲,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29)溅了一身的水。
“一+量+的+N”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换为:
(30)一+量+N如:溅了一身水。
(31)一+量如:水溅了一身。
“一+量+的+N”的这些变式,也都表示主观大量。当然,它们在语法分布和表量功能上还是有些许差异的,这些差异值得专门研究。
2.2 “一+量”结构
“一+量”结构(除2.1所讲的情况外)有表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之分。其不同主要取决于量词的不同。当量词为“通”、“番”等时,“一+量”结构一般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32)因为我们估计日本人就是放我们出去,也难免要进行一番搜查……(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当代》1992年第1期第88页)
(33)爹,你狠狠骂我一通吧……打我一通也行……(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第3期)
表示主观小量的“一+量”结构比较多。除了“一点”、“一些”、“一丝”、“一线”、“一缕”这些表示“细小”的量词所组成的“一+量”结构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重视。第一种情况是,“一+量……也/都……”的强调格式中的“一+量”,表示主观小量,例如:
(34)一分钟也不能等。(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35)这几天里,我们一口粗粮都不吃。(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
“一分钟”、“一口”都是极力往小处说。这种结构的谓语一般都是否定形式,有些“一+量”结构前还可以加“连”来增加强调意味。这种格式还可以凝缩为“一+量+否定”的熟语性结构,如“一声不响”、“一钱不值”、“一动不动”等。
第二种情况是“一+量”结构作状语。最常见的是“一口气”、“一下子”、“一下”等表示时量短、动量小的动量词语,时量短、动量小本身带有主观小量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当它们充当状语时,如果它们所修饰的成分中带有数量词语,则该数量词语表示主观大量。例如:
(36)章友法一口气喝干了一大缸子开水。(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第1期)
(37)原来这个战士就是八日夜间凭着银光闪闪的大刀一口气杀死了七个日本兵……(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当代》1992年第1期第85页)
(38)这天早晨,话剧团院子里一下子来了五辆面包车。(吴海民《大陆音像圈》,《当代》1992年第1期第159~160页)
(39)使板鸭产量一下提高到三十万只。(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第1期)
“一大缸子”、“七个”、“五辆”、“三十万只”都表示主观大量。“一口气”、“一下子”、“一下”等后面可以出现“就”、“竟然”等,以加强主观小量与主观大量的对比。例如:
(40)一口气竟然跑了几十里。
(41)一盒粗制滥造的录像带,连香港人都懒得看,拿到大陆一下子就发几千盒。(吴海民《大陆音像圈》,《当代》1992年第1期第162页)
(42)后来,他们竟然来找章友法,结果,一下就得到了五千元的捐款。(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第1期第121页)
数词为“一”的其他动量词语作状语,也往往可以形成类似于上六例所代表的情况,例如:
(43)一跳三丈高。
(44)一玩就是四年五年。(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第34页)
(45)一个跟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
这些句子往往都含有小夸张的意味。在不含夸张意味且“就”不出现的情况下,数词为“一”的动量词语作状语并不必然表示主观量。例如:
(46)一拳打倒一个。
(47)一拳才打倒一个。
(46)中的两个数量完全可以作客观量理解,甚至可以出现(47)的用法,在两个数量词语之间加“才”,形成与(36)~(45)相反的“主观大量—主观小量”阵列。这就是这类数量词语与“一口气”、“一下子”、“一下”不同的地方。
2.3 一些特殊的数量性词语
一些特殊的数量性词语也可能表示主观量。一般说来,带有夸张意味的数量词语往往表示主观量,例如:
(48)理论上的问题可以争论一千年一万年,但录像片的现状却向我们发出了紧迫的警告。(吴海民《大陆音像圈》,《当代》1992年第1期第159页)
(49)他们捐的五十元,在价值上超过我们捐的成千上万。(张曼菱《让心再跳一次》,《当代》1997年第3期第64页)
(50)梦虹焦急万分……(航鹰《蒺藜女》,《当代》1997年第3期第150页)
(51)他睁大眼,张着嘴,半天不动。(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第3期第57页)
“一千年一万年”、“成千上万”、“万分”、“半天”等表示主观大量,在句子中都带有小夸张的意味。但是,就本质上来讲,哪些词语表示主观量,是表示主观大量还是表示主观小量,具有一定的语言规约性。例如“成…上…”、“…日(天)…夜”、“千…万…”、“千…百…”、“成群结队”、“七嘴八舌”、“十万八千里”、“千里迢迢”、“不远万里”、“亿万”、“半晌”、“半天”、“一辈子”、“一个劲”、“接二连三”、“一年到头”、“十分”、“整个”等格式或词语,一般都规约为表示主观大量。相比而言,表示主观小量的数量性词语较少,主要是“三…两…”格式,例如:
(52)汉子想了想,便三把两把将她的湿衣服扯下来,放在火旁烘烤着……(路远《青盐垛》,《当代》1992年第1期第71页)
(53)这烟怎么这么不经抽,三口两口就烧尽头了?(谷代双《探幽:华夏女烟民》,《花城》1990年第4期第182页)
三、受一些词语直接修饰的数量结构
数量结构直接受某些词语修饰时,也表示主观量。这些词语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可加在数量结构之间的;第二组,只直接出现在数量结构之前修饰数量结构的;第三组,既可直接出现在数量结构之前又可出现在状语位置的。下面分别讨论。
3.1 可加在数量结构之间的
可加在数量结构之间的词语,主要有“大”、“小”、“长(cháng)”、“满”、“整”等[6][7]。“小”表主观小量,其他表主观大量。例如:
(54)走出一小截,金满囤心里便有了底。(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
(55)我在外边存着一大笔钱呢!(同上,第8页)
(56)除了一长串提问她还带来个坏消息……(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57)手扶拖拉机拉着一满车麦草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
(58)那首诗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印上一整版(注:“整”有时还可以出现在数量词语之前或之后。)。(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第38页)
“大”还可以同“长”、“满”、“整”等直接组合成“一大长串”、“一大满车”、“一大整版”之类的结构[7]。而且,含“大”、“小”、“长”、“满”“整”的数量结构,如果数词为“一”,在一定条件下“一”可以省略(注: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性成分。),例如:
(59)大批海鲜酒楼纷纷倒闭,纺织及印染业减产几达五成,工农业损失以亿元港币计。(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第3期第9页)
(60)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61)汪一清整天呆在病房里。(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23页)
含有“大”、“小”、“长”、“满”、“整”的数量结构,包括省略“一”的结构,还可以有复叠的形式(注:“成”也有这种用法,如“成群的鸟雀在空中盘旋”、“成批成批的农民涌入城市”。),例如:
(62)木头被锯成各种规格的长度,分门别类地归在一起,堆成一大垛一大垛。(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63)人们一整天一整天地靠着被褥摞默然呆坐……(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10页)
(64)小股小股的寒风沿鸡嘴山山脚肆意穿行,使嶙峋的山脊显得依然秃冷。(赵江《十七棵杏树》,《花城》1990年第4期第126页)
3.2 只直接出现在数量结构之前的
只直接出现在数量结构之前的修饰数量结构的词语,主要有“短短”、“区区”、“寥寥”、“小小”和“上”、“数”等。例如:
(65)短短八个月,八千亩千年老林一场浩劫,一扫而空。(陈康瑾《他走向莽莽林海》,《十月》1984年第1期第54页)
(66)深圳河在中国的江河中最没地位,全长才三十七公里,干流区区十六点一公里。(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第3期第12页)
(67)作家口才极好,寥寥几句话,就把漆家骏一生的成就概括得辉煌如日,简直可以直接抄进将来漆家骏的悼词。(孙泱《远行》,《花城》1990年第4期第149页)
(68)卷缩得只有小小的一团。(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50页)
(69)而她只是中国上千个县治之一。(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第3期第6页)
(70)延续数百年的殖民时代已经寿终正寝……(同上,第7页)
“短短”、“区区”、“寥寥”、“小小”表示其后的量为主观小量,其中“寥寥”之后不能出现确定量。“上”、“数”一般都表示主观大量,其后的数词只能是位数词,“数”后面也可以直接跟数词,如“数年”、“数月”、“数个世纪”等。而且,“上”、“数”之后的数量词语越大,其主观大量的色彩就越浓。
3.3 既可直接出现在数量结构之前又可出现在状语位置的
这类词语为数众多,例如:
(71a)花圈摆了满满一屋子。(刘思谦《昨夜梦见母亲》,《花城》1990年第4期第158页)
(71b)韩佬佬借来一辆板车,将炉子锅盆活动顶棚小桌小凳满满装了一车。(小牛《上路谣》,《当代》1997年第3期第40页)
(72a)我在小床上躺了整整一天,好像是一次漫长的昏睡。(秦文君《女生贾梅》,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
(72b)按他原来的计算,他们顶多需要在这儿等5分钟,结果整整等了20分钟,这20分钟真难熬!(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6页)
(73a)等了足足一个月。
(73b)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章友法,不分日夜地足足准备了三个月。(陈世旭《天鹅湖畔》,《十月》1984年第1期第141页)
(74a)类似的账,最近几个月已经开支了好几笔,总数怕有三、四万,都是出的“暂付款”科目。(陈冲《历史拒绝眼泪》,《十月》1984年第1期第70页)
(74b)叫人好等了一阵子。
(75a)刚刚十天,现在她却让老高查起原先科长经手过的账目来——这合适吗?(陈冲《历史拒绝眼泪》,《十月》1984年第1期第70页)
(75b)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也就是深圳特区刚刚成立一年多之后,百业待兴,深圳河治理问题就摆在了深港双方的桌面上。(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第3期第12页)
(76a)搬来刚5天,还没顾上整治这片菜园。(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
(76b)刚搬来五天。
(77a)非常幸运,距离朝阳宾馆仅仅一百米,果真有一座××医院。(贾漫《沧海一粟》,《当代》1992年第1期第126页)
(77b)而现在急救室与病房仅仅隔着一层苇席!(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24页)
(78a)就在距香港回到中国怀抱仅两百来天的时刻,她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杨继仁《绝无仅有》,《当代》1997年第3期第8页)
(78b)一条仅长十六公里界河的治理,谈判了十多年、几百次。(同上,第11页)
“满满”、“整整”、“足足”(注:“足”不重叠,一般只能作状语,例如:(1)这二三十人的队伍,在大堤上拉开足有半里长。”(陈冲《不自然的黑色》。《十月》1989年第6期第26页)“足以”也可以出现在状语位置上,但数量词语一般出现在它的前面,例如:(2)3到4枪足以把来人吓跑。(同上,第7页))、“好”、“刚刚”、“刚”、“仅仅”、“仅”等词语,在(a)中直接修饰数量结构,在(b)中充当状语,但语义仍间接指向数量结构。其中,“满满”、“整整”、“足足”(注:“满满”、“整整”、“足足”还可以同“大”、“满”、“整”依照一定的规则配合使用。例如:(1)装了满满一大车。(2)印了足足三整版。(3)写了整整九大本日记,厚厚的,沉沉的。(4)足足装了四满碗。)、“好”等表示主观大量,“刚刚”、“刚”、“仅仅”、“仅”等表示主观小量。
此外,像“只”、“才”、“都”、“就”等也有类似的用法,但是这些词语在主观量的表达上要复杂得多,拟对它们进行专门讨论,本文从略。
收稿日期:1999-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