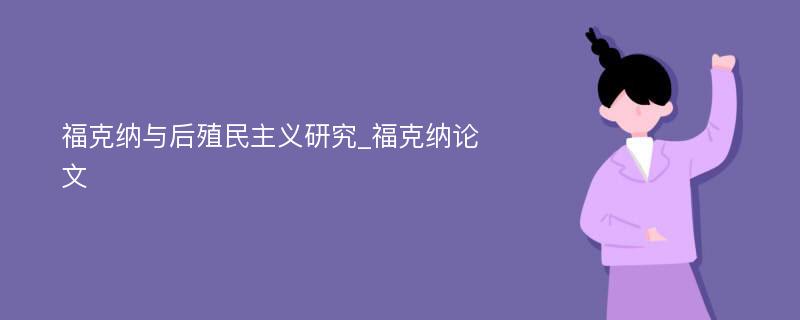
福克纳和后殖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克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5-0008-05
美国南方研究在对后殖民分析的有效性展开调研的同时,有关这一研究的局限和机遇 的讨论也有序地进行着。尽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源于其脱离英国统治的反殖民运 动,尽管南方后来发觉自己实际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北方的一个殖民地,我们还是可以通 过确认这些严重的异常情况,来认可美国南方的后殖民地位。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什 么典型特征,因为它本身是惟一一个由前殖民民主政权变为殖民强权的国家。后重建时 期的南方积极参与了诸如此类的新殖民活动。而且,尽管美国南方在重建期间和重建之 后饱尝了国内殖民般镇压的苦痛,但它却在对土著居民实施内部统治、在内战前贩进奴 隶后,就参与了新殖民活动。
殖民化这个比喻主要出现在内战后有关南方战败、处于从属地位的论述中。尽管把重 建时期的南方看作殖民地有它的局限,但还是有众多南方历史学家使用了这一术语,用 以指代20世纪早期——从联邦占领到国家最终统一的几十年内——南方所处的状况。C.范·伍德沃德用明晰的殖民语言对重建后该地区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北方在征服南 方后所实施的策略已从传教和政治阶段进入了经济剥削阶段。”(Woodward,1951:114) 他继续描述北方制造商对南方廉价劳动力的兴趣——相对雇主来说,劳动者都是“‘本 地人’,有白人也有黑人”(Woodward,1951:114)。埃里克·福纳则依据南方上层商人 对北方资本的依赖及对被剥夺财产的南方精英的蹂躏,描绘了战后重组的场景。加文· 赖特总结道:南方成为殖民地,实际上是由于战后重建依赖于北方资本。这种看法在当 代的论述中也不乏其人。在论述美帝国主义和国内种族主义关系的新作中,彼得·施米 德呼吁大家注意历史学家约翰·W.伯吉斯1902发表的主张,即联邦政府释放南方被解放 的奴隶,实际上是对前雇主阶级的殖民。对伯吉斯而言,一旦外国殖民政府坚信其正当 的统治对象就是地球上肤色较黑的人群,这个“错误”就更加明显了。乔治·亨德利在 他最近一本关于美洲后奴隶文学的书中指出:美国南方是美利坚的第一个“外国”殖民 地。福克纳用他一贯复杂幽默的笔触捕捉到了南方对北部殖民化的体悟:在《村子》中 ,像北方佬一样贪婪的威尔·凡纳及其被保护人弗莱姆·斯诺普斯被描述得跟“非洲边 远村落的白人商客和当地鹦鹉学舌的酋长”一样。
当然,就“南方”来说,内战后对殖民地的人物刻画特指由白人男地主构成的原统治 阶层。他们发觉自己的各种资本都被剥夺了,如已得到解放的奴隶以及土地、劳力、政 府公职、武装力量等。但我们不要忘记,南方另一种针对前奴役人口的殖民形式已破土 而出。也就是说,我们的原统治阶级在处于被统治的从属地位的同时,正试图再殖民其 前奴隶。后殖民研究的可贵之处可能就在于它描绘了统治集团的双重地位、被统治团体 的积极抵抗、统治和从属身份的同质性以及集团间特权的复杂的双向协商。
一、美利坚帝国
一般认为,内战后美国南方脱离殖民状态有赖于它在美利坚帝国的发展中所扮的角色 。由于一些常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南方人普遍支持由美—西战争引发的扩张主 义,而且对由此带来的国家重新统一的机会表示欢迎。最近的学术研究已从新的角度说 明了上述因素与南方的关系。例如,玛丽·兰达用翔实的资料证明了美国南方家长作风 的意识形态,对1915~1934年间美占有国海地的政治辩护、行政管理和文化表征等诸方 面影响的重要性。其它对美帝国的新近研究则将南方黑人的从属关系与新占殖民地对当 地居民的政策联系起来(Kaplan,WB Michaels)。尽管美国最终在20世纪之交开始攫取外 国土地,起初也照搬欧洲直接殖民占领的体系,但它通过发展所谓的“新的”或“非官 方的”帝国主义证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统治注重经济威胁而非军事力量,注重私 有剥削而非官方管理,注重统治霸权而非政治控制。因此,美—西战争后,美国虽然相 继接管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古巴,但其扩张的主导模式却依赖于贸易和发展。艾米· 卡普兰把这种构成称为“无实体”帝国,杰根·奥斯德海默则提出“美国是一个没有大 殖民帝国的帝国主义典范”(Osterhammel,1997:22,as quoted in Young,2001:42)。
19世纪20~30年代的许多南方小说都记录了南方后殖民和现代美帝国相交错的现象, 这些记录集中体现了种植园文化和农业的重要性。安东尼奥·拜尼迪斯·罗鸠演示了种 植园,作为新大陆殖民经济和社会的中心“机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尽管拜尼迪斯· 罗鸠把加勒比种植区定义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区域”(Benitez-Rojo,1996:38),而内 战前的美国南方显然已经享有了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一战后,现代种植园在某些方面 卷入了美国国内外大事的争论。美国最近的范德比尔特平均地权者把内战前的种植园当 作一种想像中反现代性的化身。与之相反,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向种植园的存留提出挑战 ,把它视为种族间经济和文化不平等的典范。查尔斯·约翰逊称其对城市黑人贫穷的研 究“《处于种植园的阴影下》”。在国外,美国的商业利益促进了以生产水果、蔗糖和 咖啡为目的的现代种植园体系的发展。这些活动证明外国领土可以被“南方化”,而且 美国对外政策的资本主义家长作风远比政府干预来得多。本世纪之前,虽然次文类已经 取得了极大成功,但种植园小说在这几十年涌现的数目依然令人吃惊:其中比较出名的 有斯塔克·扬的《玫瑰如此红》、艾莲·塔特的《父亲们》、朱莉娅·彼得金的《黑色 四月》、埃伦·格拉斯哥的《贫瘠的土地》、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和《上帝 的小田地》、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玛格丽特·米切尔的 《飘》和琼·图默的《甘蔗》。
二、拜物(注:Fetish一般译为恋物、拜物,fetishism可译为物神崇拜或拜物主义, 考虑到文章表述的一致性,分别将上述两词译为拜物和拜物主义。)、语言和殖民历史
通过后殖民研究,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美国南方与新大陆种植园社会的 关系重又变得明朗起来。我们毫不奇怪,马提尼克岛诗人、克里奥化理论家埃都阿·格 里让的新书会透过半球种植园的历史,将目光锁定福克纳。格里让把约克纳帕塔法视为 福克纳想像中斗争的地方,用它来调节南方对种族清白和自我满足(隔代遗传的社会)的 渴望和对克里奥化现实(混合的社会)的认可。这种变换福克纳之兴趣的做法提醒我们, 西印度群岛对托马斯·萨德本的事业和对福克纳再现南方种植园的故事有多重要。我想 就这部小说作两个相关的陈述:《押沙龙,押沙龙!》表明新大陆和南方内陆种植园的 关系很重要;小说本身面临着问题——习惯于讲述南方而模糊了这些更广泛的殖民联系 。
押沙龙的叙述者相信南方例外论的神话——美国南方种植园体系作为半球殖民模式一 个独立而特别的形式得以发展。叙述者对萨德本海地之行的遗忘和误解相当于一种技术 性的认知,即后殖民分析所讲的拜物。《押沙龙,押沙龙!》的读者,与它的叙述者一 样,眼前经常会浮现出福克纳提供的证述:南方种植园的设计来源于新大陆模式,其形 成要感谢西印度群岛以奴隶为基础的农业,它通过非洲—加勒比海的奴隶贸易获取劳力 ,榨取利润,对另一半球的殖民政权实施种族和性别控制。但是,有一种知识,被人忽 视时却可以掌握;有一种景象,被人关注时却看不到。这种知识不会消逝到它受压抑的 深层(这种模式主要用于研究福克纳风格中的遁辞和延迟),而是公然藏匿在福克纳文本 的表层,就像爱伦·坡的被盗的信,可能过于明显而令人视而不见。
在一篇著名的关于陈规的文章中,霍米·巴巴描述了《文化的定位》中的“另一个问 题”——文化拜物的操作。虽然在讲《八月之光》的时候,我应该讨论一下巴巴论述的 具体的殖民拜物——陈规、外皮、血,这里我还是希望用他关于否认性知识的概述,来 支撑我对福克纳再现美国南方的加勒比视域的讨论。巴巴从拜物知识(如陈规)的文化研 究一直追溯到它的心里机能:“拜物主义,作为对差异的否认,就是围绕阉割问题而重 复的场景。”(Bhabha,1994:74)弗洛伊德将男性对性别差异的焦虑定位为拜物的初端 。男孩依据阉割的焦虑来诠释女性。拉康把这种精神创伤的时间推回到早期阶段。在这 个阶段里,孩子第一次体验自己与世界的分化,也就是说,他了解到自己的非自我满足 和对母亲的依赖。在拉康看来,在这个由分裂到主体形成的过程中,性别差异的问题成 为另一表现形式。如果决定把差异的焦虑作为缺失来处理,就有可能造成使用拜物客体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在取代缺失成分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缺失的了解。拜物客 体的功能是即时的置换和移置,是一种巴巴相当重视的,关于陈规的、结构上动态的矛 盾性。种族拜物像性拜物一样,用以调节白人的焦虑:黑人是白人潜在的被毁坏的变体 ,而非决然不同的他者。巴巴评论道:“拜物描述了作为替换的隐喻(隐藏了缺失和差 异)和转喻(不断地记录察觉到的缺失)的共同游戏。”(Bhabha,1994:74-75)从这个立 场出发,巴巴得以强调拜物主义何以“是一种非压抑型知识,使同时皈依两种对立的信 仰成为可能”(Bhabha,1994:80)。
福克纳的戏剧性从来不在知与不知之间,而是在对已知是承认还是否认之间。福克纳 在早期的小说中播撒了很多有关加勒比海的资料,但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他对 拉丁起源的留意却以同新大陆殖民相联系而告终。有迹象表明,小说中几个故事的每位 叙述者都掌握了不少萨德本的罪恶历史。一连串的叙述都弥漫着对他的猜疑:不仅讲他 在海地抛弃混种妻子和孩子不管,还讲他可能为了给自己种植园提供劳力和资金而卷入 非洲—西印度群岛奴隶市场的非法活动。杰弗生大庄主政权的继承人昆丁·康普生假装 自己对南方背后更为广泛的殖民文化一无所知:他说到萨德本在海地是作“监工或工头 或法国蔗糖种植园主什么的”,而且在叛乱期间他一定看到火焰烧毁了“谷仓或粮仓或 任何存放你收割糖料的地方”。昆丁对蔗糖业的最初猜想源于他的棉花业小农知识。他 的“一无所知”制造出一个历史的副本,在这个副本中人们会发现南方内陆的棉花覆盖 于西印度群岛的糖料之上。这样一些知识使得福克纳决定让萨德本的事业与新大陆从蔗 糖到棉花这个历史支点完全相符。英国于1833年废除农奴制,削减了加勒比蔗糖工业的 利润,并为英国制造业的棉花生产扩张铺平了道路。1831年,萨德本离开他在西印度群 岛的蔗糖种植园。两年后,在密西西比建了一个棉花种植园。如果说昆丁确实是各种声 音的“共和体”(Faulkner,1990:7),那么他从小到大听到的一些故事一定包含了被南 方抛弃的西印度群岛母体的信息。
萨德本与西印度群岛的物质联系在小说叙述者口中趋于隐晦。罗沙叙述了萨德本的到 来,却未表明他的来历。然而罗沙自己的表述方式暗示,她有意拒绝承认萨德本得益于 殖民机遇且南方商业和劳力具有复杂性。她的风格起的作用不是压抑而是自我欺骗。在 萨德本到来的这个世纪,罗沙学会忽视对种植园规划的全角叙述,这个规划的代表人既 是她父亲的生意伙伴、妹妹的丈夫,还是她自己的财政专家。
“那是他20年来传统的一部分,在这期间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也常听父亲讲起这个 男人的事;那也是个小镇——杰弗生镇,有着同样空气的80年传统的一部分。那个男人 本人呼吸过这里的空气,从1999年这个9月的下午一直上推到1833年6月的那个星期日早 晨,当时那人初次骑马进入本镇,他的过去无人看得透,他的土地怎么弄到手也无人知 晓,他显然从虚无里建起自己的房屋、宅邸,并且和埃伦·科德菲尔德结了婚,生下了 两个孩子……”(Faulkner,1990:7)(注:文中所有出自《押沙龙,押沙龙!》和《八月 之光》的引文皆采用了李文俊和蓝仁哲两位先生最新译本的相应译文。)
像罗沙一样,尽管昆丁和杰弗生在那80年中学到的远多于此;康普生将军也是在萨德 本抵达那年才听说他在海地的故事的。昆丁知道的那些事与事实没多大关系,大多都是 些无关紧要的事。
拉康在注意到拜物客体作为非自我满足和差异的象征性控制发生作用时,提出语言本 身便是拜物的原型。假如语言“知道”它取代了语言之外无法接近的事物或思想,它却 装作自己似乎只是在全面表征的过程中临时代替他们。语言如拜物客体一般停留在否认 性知识之上:我知道能指并不指向所指;可我说起来好像它就指向所指。拜物要你透过 它去审视方能识破它。假如在特殊情况下福克纳开始创造“他自己的原土壤小邮票”, 他也免不了会遇到语言问题。作者想用语言再现南方的一切尝试,最终揭示了语言时常 为产生的分裂性殖民主体所困扰。语言作为拜物继续调节着种族和性别分割的初始裂缝 ,并且处于与历史的非自我满足的永久协商的状态。
在押沙龙一书中,对语言之不足最刻薄的抱怨是随着对南方隐晦起源的潜在认识产生 的。康普生先生对亨利谋杀朱迪斯的未婚夫一事百思不得其解,而后他把萨德本的百里 地比作荒岛,耸耸肩说出非常著名的一席话:“那真是不可思议。简直说不通。不过说 不定就是这样的:他们未作解释而我们本来就不该知道。”(Faulkner,1990:80)康普 生继续盯着“那些字、那些符号”,可他们还是“难以琢磨”(Faulkner,1990:80)。 然而,面对语言的确定性,他重申语言无法描述过去。康普生的抱怨确实和语言作为拜 物的结构状况有关。他看透了语言试图描绘真理的骗局,既而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觉得像康普生这样一帮有特权、有地位的南方人是在知其所不知中,在展现了历史现 实却无法使其清晰的语言中得到了庇护。当康普生先生把字凑到一起时,“那些缺失的 东西”,我认为他已经知道:就是新大陆种植园的整个历史,透过它可以完全清晰地看 出:萨德本从海地到杰弗生镇的事业就是一部殖民罪恶史——对美国印第安人有计划的 灭种和屠杀、奴隶贸易、人性奴役、重婚、强奸、乱伦、对土地无情地蹂躏。
对南方“一无所知”,福克纳指出,不是没有去了解,而是有意忽视。如果说有任何 风格向这种文化习惯提出了挑战,那一定是福克纳的。从新大陆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的有 利视角去阅读福克纳的小说,我们就可以有鉴别地(即便是简要地)反思美国南方与西印 度群岛的关系。加勒比地带使南方未被沾染的起源梦折衷为与二百年殖民压迫无关的仁 慈和充满田园风光的温情主义。福克纳的风格使可见的让人看得见,而且强调非自我满 足的拜物神秘化中那些不能解释的过分行为。
三、殖民欲望和南方混合性
在巴巴的系统里,恐惧的矛盾情绪和陈规中的渴望要归咎于种族社会里身份的双重不 稳定性。“陈规”是“一种知识形式,是一种在定式、故知和焦虑的重复物间摇摆不定 的认同……相当于[例如]非洲人野兽般的性放纵无需证明,这一点在话语中永远无法真 正得到证实”(Bhabha,1994:66)。陈规既为社会的大多数也为少数成员而对抗种族认 同中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按照种族差异的对话方式来阐明身份,主体的完整性依赖于 种族化的拉康分裂理论。在巴巴看来,结果是“恰好发生在隐晦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一 种认同结构的矛盾情绪,其间他者的阴影落在自我之上”(Bhabha,1994:60)。焦虑不 仅来源于疑惑:他者是否可以被定型为彻底隔离、下等、可见和可知,它更源于来自对 非我批判的缺失感。种族陈规显示了对可怜的他者欲望的极度束缚和禁绝。
这样的对抗性态势确认了身份的根本的共同本质,而且这种矛盾情绪导致了种族间的 犯罪欲望,它基于单一种族身份对非自我满足的确认。罗伯特·扬把这种现象放置在更 广阔的历史框架中,为巴巴相对狭隘的心理学解释作了有益的补充。此处我可以这么说 ,巴巴汲取了法侬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的养料并将其发展为自己的观点:深埋在陈规中 的殖民欲望的矛盾情绪。因此这个后殖民理论版本,无论多像弗洛伊德学说,都是从法 侬反殖民主义思想的背景中承袭的。很显然,法侬借助了拉康身份形成的模式,这有助 于理清后殖民分析与后结构理论之间的联系。扬的《殖民欲望》一书考察了19世纪英国 文化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与种族问题、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扬 发现,种族作为一个范畴显现出来就是为了让文化为自己辩白:种族是19世纪帝国主义 文化的产物。此外,通过强调欧洲欲接触和控制土著地区和居民的扩张需要,他把矛盾 情绪定位于殖民主义的运作方式中,实际上把它变成了获取他者性的欲望机器。尽管我 现在还无法对扬的历史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还是允许我引用他对殖民话语中不变主题 的评论。因为此类接触不仅授权和丰富了殖民文化,而且力图“改善”那些被殖民的野 人。扬发现欲望在殖民主义操作中处于中心位置,性是介乎种族和文化之间的第三个术 语。(Yang,1995:98)
在福克纳对被隔离南方的种族和欲望的探索中,陈规最初介入似乎为了带来快乐而非 禁止。白人乔安娜·伯顿和她的黑仆人乔·克里斯默斯违反了南方的原始禁忌,他们这 么做并不是为满足对方的性欲,而是从种族陈规中获得满足。乔进入伯顿的屋子就像走 进田地。他吸拾着阵阵“充满黑油油的沃土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的潮湿气息”——那种令 他联想起黑人的气息——像“猫”一样偷偷摸摸地溜进门廊,从那儿爬进窗口。(
Faulkner,1990:229-230)感觉自己“像个贼,像个强盗”(Faulkner,1990:234),乔 每个夜晚都要乔安娜,“每一次都像是偷偷摸摸地窃取她的童贞”。乔安娜则怂恿这种 陈规仪式,嘴里嘘叫“黑人!黑人!黑人!”而且坚信“她一直抵抗到最后”(Faulkner,1 990:235)。对于他俩来讲,性快感就在将他们分开的拜物里。乔安娜的快感来自黑人 的强暴而不是克里斯默斯,而唤起克里斯默斯性欲的也不是那个依旧年轻的单身女人, 而是那个没了男人的庄园女主人。福克纳精彩绝伦地演绎了精神构想如何使他们从自己 的性快感资源中获取能量。
扬希望从自己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当代某些后殖民政治酷爱的术语,如“杂糅性 ”,实际上都带有一段被遮蔽的性种族主义史。杂糅性是一个用于表述种族混合的术语 ,它强调的是通过杂交创造混合有机体的生殖问题。由于在给种族下定义时总免不了要 关注诸如杂交生育会不会有后代,白、黑混血儿是否能生育之类的问题,今天用杂糅性 来表示可能替代种族的文化融合,恐怕不是最佳用语。《八月之光》的结尾,福克纳提 出了自己的用词,希望超越那种性别化、种族化的后殖民身份的传统。人物刻画展现了 贯穿乔·克里斯默斯的悲剧和莉娜·格罗夫喜剧的面孔:“这些面孔都有点相似,融合 了他所见过的所有面孔。”(Faulkner,1990:491)而且,这种融合超越了对黑人种族歧 视的势不两立的二元体系;海托华的幻觉定位在两张特殊且重合的面孔上——乔·克里 斯默斯的脸和疯狂追杀他的白人珀西·格雷姆。福克纳关于混合性的概念恰到好处地改 进了那些联合性和杂糅性的狂热话语。
四、福克纳的问题
尽管用后殖民研究的方法分析福克纳的小说已为人接受,但在当代南方文学研究的领 域,他的作品却已被定为疑难问题。迈克尔·克里林和帕特丽夏·伊格最近就福克纳对 区域文学史的观念和表达模式范围的控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克里林指出昆丁·康 普生被一部分南方的男性白人学者当作福克纳的一种提喻法,他们把昆丁对南方愧疚、 矛盾的爱当作自己与该地区悲剧命运之间关系的象征。南方文学通过突出白种男人的自 私自利、“犯罪与补偿”、种族和暴力的必然性及南方性的实质,将“福克纳”的思想 推向高潮。克里林希望南方文学批判“昆丁命题”并强调,后福克纳作品(尤其是出自 非裔美国男性和所有妇女之手)无法解决福克纳作品中刻画的南方问题。伊格在克里林 的基础上付诸行动:依据性别对南方文学进行细分,从而“炸毁了轨道”(克里林只是 建议抛弃它),她指出“南方文学研究领域一直被巨大的福克纳工业控制着,它不仅支 配而且压制着我们用来解读南方妇女小说的术语”(Yaeger,2000:xv)。《泥土和欲望 》——建立在这些变换的理论基础上的研究,完全归功于其对福克纳的边缘化。
正当人们以为公园里的狮子已被关进了笼子时,格里让的《福克纳,密西西比》却提 示我们,通过全球化观点来审视南方这条路有可能引导我们走进福克纳,而不是围着他 打转。福克纳在美国南方文学和拉美文学的先锋研究中地位显赫,不足为奇,此类作品 如黛博拉·科恩的《两个美国南方》和乔治·亨德利的《美洲后奴隶文学》。或许格里 让的书已经把重新关注福克纳的重要性带给了像威尔逊·哈里斯这样的加勒比作家。我 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半球观来看,福克纳,尤其基于他对拉美作家影响的事实, 在重组美国南方的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