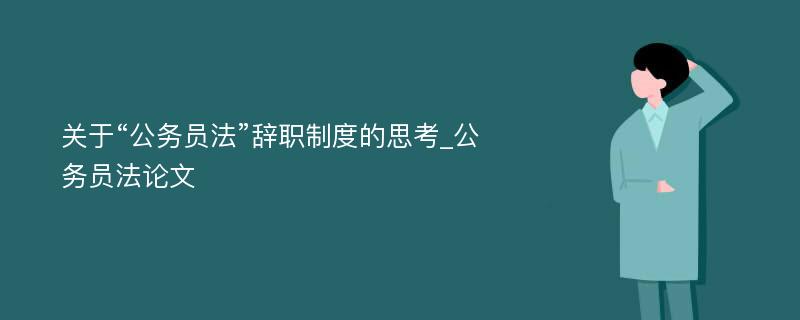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咎辞职论文,忧思论文,公务员法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14(2007)06-0060-(07)
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标志着引咎辞职成为了我国的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应当肯定,引咎辞职的法律化,对于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减少工作失误,降低重大事故的发生,疏通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出口,使公务员在这个队伍中能进能出,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勤政高效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制度,实施该制度后能否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实施这一制度以后可能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国外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会有怎样的评价?我们将引咎辞职这种源于西方的基于官员自己道德要求而主动承担的政治责任形式,转化为一项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责任形式,这究竟是在与国际接轨进行制度创新,还是在画虎类猫贻笑大方?对这些问题,笔者心存疑虑。本文的写作动机就是给那些以为将规定引咎辞职的规范性文件从执政党党纪升格为国家法律①,就一定会大大强化它的正面功能,取得更加显著的积极效果的人们提供另一种思路,以引起大家对引咎辞职制度作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防止和解决引咎辞职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为将来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或者修改完善《公务员法》,使引咎辞职制度回归应然、适得其所作好理论准备。
一、含义不明,难以执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要想得到很好的实施,前提是法律规范本身必须含义清晰明确,易于理解和执行。如果法律规范的语义含糊不清,歧义丛生,可操作性差,轻者可能会出现执法不统一的现象,重者可能导致法律规范的无法执行。遗憾的是,我国《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制度的规范,恰恰存在着条文内容过于模糊的缺憾,很有可能使有关各方在执行这一条文时无所适从。
首先,引咎辞职的标准不明。依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引咎辞职的适用条件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判断领导成员是否应当引咎辞职的标准。但是,何为严重失误、失职?何为重大损失?恶劣社会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事故才是重大事故?对这些引咎辞职的基本问题,《公务员法》都没有予以明确。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在具体执行这项制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一是把一些不属于“咎”的事项也引以为据。如深圳市某区把“所在单位连续两年年度任期目标责任制综合考核排名”和“干部考核中民主测评结果不称职票超过30%”等明显不属于“咎”的事由也作为领导必须引以辞职的依据。另一种是把应当承担直接法律责任的罪错,也作为引咎辞职的“咎”来看待,引来作为只承担政治责任的“咎”。如江苏省某县规定“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致使国家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和“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干部群众反响强烈的”应当引咎辞职。实际上这两种“咎”已属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以引咎辞职来替代对这些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处理,则引咎辞职制度就异变成违法犯罪行为的保护伞了。
其次,应当引咎辞职的主体不明确。什么叫应当引咎辞职?由谁来认定应当还是不应当?谁应当引咎辞职?是只限于正职行政领导引咎辞职,还是主管的副职领导也应当一起引咎辞职?如何分清谁是主管领导②?党委领导是否要辞职?是仅仅辞去行政职务,还是辞去一切职务包括党内职务③?地方发生的事故、事件要“引咎”到哪个级别?到目前为止,我国引咎辞职的官员最高级别为正部级,引咎辞职能否引咎到更高级别的官员?什么情况下高于正部级的官员应该引咎辞职?《公务员法》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疏漏。
再次,责令辞职的标准和主体也不明确。《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怎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其判断标准是什么?“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中的“其他原因”究竟包括哪些原因?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明确,执行起来就可能出现差异性甚至随意性,有违法治的目的。此外,如果本人认为不应当辞职,不引咎辞职,那么,谁来责令其辞职?上级吗?是上级组织还是上级领导个人?是上级党组织还是上级行政组织?是上一级还是上几级?如果某市的环保局长应当引咎辞职而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的,究竟是省委、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是省环保局?还有,这次《公务员法》将法官和检察官也纳入了公务员队伍,如果要责令法院院长辞职,应该由谁来进行?法院院长的上级是谁?上级法院是否有权责令下级法院院长引咎辞职?在我国,法律上规定地方检察院实行的是同级人大和上级检察院双重领导的体制,如果要责令地方检察院领导成员辞职,是由同级人大还是由上级检察院来责令?倘若这两个上级机关在下级检察院领导成员是否应当引咎辞职的问题上意见存在分歧,究竟以哪个为主?还是必须要两个上级意见一致才能共同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此外,如果应当引咎辞职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在被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后仍然不愿意辞去领导职务的,该怎么办?是免职还是撤职?依据是什么?如果该官员是选举产生的又该怎么办?
二、制度运行,变形变质
或许有人会说,上述条文含义不明确的问题,只要由有关机关颁布一个实施细则就可以解决了,实施细则一颁布,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何忧之有?笔者却不以为然。由于“官本位”意识在我国长期盛行,在多数官员眼里,职务就是命根,保官犹如保命。在这种扭曲的权力观支配下,指望官员主动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官位,自愿依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引咎辞职,实在有点不切实际。所以,笔者有理由断定,即使国家出台了引咎辞职的明确标准,它在实施过程中也肯定会受到肆意扭曲,发生变形变质,实施效果不容乐观。
引咎辞职是官员对发生的重大事故或者重大损失内心感到不安、自我谴责,并且以辞职来谢天下的制度。故官员是否引咎辞职,除了要依赖于重大事故或者重大损失这一客观标准的明确以外,还取决于官员本人的责任心和廉耻心。对于同样甚至同一的事故或者损失,责任心和廉耻心强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引咎辞职,而责任心和廉耻心弱的官员,则可能认为自己不需要引咎辞职;同样是有过失、应该承担责任的官员,严于自律、良心不安的官员引咎辞职了,而厚颜不惊、笑骂由你的官员,依然赖在官位上,久而久之,我国留在公务员队伍中的可能多是些缺乏责任心和廉耻心的官员。引咎辞职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公务员队伍的出口,但是,如果从这个出口淘汰出来的人比留下的人更有良心和责任意识的话,那么,这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淘汰不仅显失公平,而且完全背离了《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我国已经发生的一些引咎辞职的实例或许可以支持这一论点。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有官员出来主动引咎辞职,期待了半个月也没有结果,就在大家快要失望时,12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在发布的通报中称:松花江重大水污染发生后,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为此,解振华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这一请求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这一消息发布后,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有媒体甚至以“为什么是解振华?”为题撰文公开表示困惑:“虽然事出有因,但解振华12月2日的引咎辞职还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解局长去职的消息公布后,有人提出疑问:同样是中石油造成的事故,为什么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后,辞职的是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而这次却轮到了环保总局局长?”[1]还有媒体为解振华抱不平,解振华的辞职,显然太过孤独。如果引咎辞职已成常态的话,那么与他一起引咎辞职的,恐怕会是一长串官员,比如吉林市环保局的局长、吉林省环保局的局长、中石油的总经理、地方分管环保的官员等等。然而,那许多的官员都无所表示,只有环保总局的局长“引咎”了。这样的现实,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正常。[2]
倘若要宽容点说,引咎辞职运行中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淘汰现象,还只是使这一制度发生变形的话,那么,“重辞轻处”的现象则使引咎辞职制度发生了变质。所谓“重辞轻处”就是过错重的领导成员受到的是较轻的处理——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而过错轻的领导成员反而受到较重的处理——行政处分。从本源意义上说,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者自己是没有“咎”的,所以不可能因“咎”而受到行政处分,只是自己责任意识强,才主动引咎辞职,承担一种比行政处分法律责任要轻微的政治责任或道义责任。因此,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公务员受到行政处分比引咎辞职和被责令辞职后果要严重,公务员只有违法违纪了,才有可能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形式的行政处分,如果没有违法违纪,顶多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如果允许官员自己选择的话,他们应该选择性质轻微的引咎辞职,而不太可能选择性质严重的行政处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行政监察机关要对官员进行追究的话,一定是情节轻微的同意其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情节严重的才给予行政处分,这样才体现了“过罚相适应”的原则,如果情节轻微的反而从重处理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反而从轻处理同意其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这种“过罚倒错”的现象,就使引咎辞职这种承担政治责任的方式异变为比行政处分还重的法律责任!例如,震惊中外的劣质奶粉事件曝光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连线采访了阜阳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张国庆教授,当张教授听了杜长平的话后,认为她已经严重失职,希望她引咎辞职时,杜长平说她不想引咎辞职,还想继续干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杜长平的选择,她愿意选择受到行政处分而不愿意选择引咎辞职。事后,安徽省省委、省政府根据监察部的建议,给予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杜长平行政记过处分而没有责令其辞职,给予分管工商工作的副市长马明业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许多网民对此发表评论说,只给杜长平行政记过处分太轻了,应当责令其辞职。在这一事件中,无论是杜长平本人,还是广大网民,无论是专门从事政府管理研究的专家④,还是监察部、安徽省政府这样的国家机关,都无一例外地认同这样的观点:受行政记过处分比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后果要轻得多!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遭到如此变异,不仅使人难以理解,而且对其继续运行的结果更是表示担忧。
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发生的另一种变质现象是“以辞代罚”。有的官员的行为已经严重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了,本应被撤职、开除,甚至应负刑事责任,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于是主动引咎辞职,避重就轻,“以辞代罚”。例如,原青岛市公安局局长万国忠,就曾因下属四方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伟在统一扫黄行动中故意泄密而主动“引咎辞职”,以逃避万本人为“黄、赌”提供保护而该负的责任。万国忠的举动引起当时媒体的称赞,多数媒体称万国忠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好局长。可是,在他辞职后不久即被双规审查,双规期间,万国忠畏罪自杀。万国忠的引咎辞职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和媒体的称赞,说明引咎辞职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万国忠利用,成为他逃避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的避难所。这种企图把引咎辞职制度异变成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伞的人,万国忠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其中有一部分人的企图得到了实现,那么,引咎辞职就从官员严格自律的政治责任形式蜕变为特权者应负刑事责任的替代品。如果任其发展,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将会成为封建时期“官当”制度之现代变种的危险。
三、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将引咎辞职制度纳入《公务员法》以后,除了实施该制度时出现的难以操作或执行不能,实施起来容易变形变质等现象令人堪忧以外,实施这一制度后,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在引咎辞职的做法比较成熟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务官员的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官员应该对选民负责,官员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会失去选民的信任,通过公众舆论表达出来的民意,不仅直接决定着该官员的去留,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选民对政府和该官员所在党派的信任度。为了回应舆论的要求,给人民一个交代,官员主动引咎辞职以谢天下,“直接向人民表达一个官员的良心和道德可靠性,从而间接地向人民表达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良心和道德可靠性,以此换取人民信任的恢复,为以后的政治生涯创造条件”。[3]因此,谁会引咎辞职,应由民意所决定,以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官员是人民公仆的民主精神,这也是引咎辞职意义的精髓所在。然而,我们的引咎辞职却与此相距甚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官员引咎辞职似乎不是规范程序和公众舆论作用下的产物,而更像上级组织施压甚至政治力量博弈后的结果,那些决定谁会引咎辞职的主宰力量总是游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如广东兴宁矿难这样“官商勾结、监管不力”引发的特大恶性安全事故,“谁会引咎辞职”的答案依旧只掌握在“知情人士”手中。[4]劣质奶粉事件曝光后,阜阳市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对全国电视观众表达了“自责”和“痛心”,并说自己是否还留在副市长的位置上“这要看群众的呼声”。看过这个电视节目后,如果结局是杜长平引咎辞职或被责令辞职,相信这肯定在大多数人的意料之中,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杜长平仍然呆在副市长的位置上,这恐怕是出乎许多电视观众的意料。阜阳事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是否引咎辞职并不取决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随后发生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又以相反的方式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事件发生后,民众纷纷猜测中石油的总经理、吉林省环保局的局长等人可能会引咎辞职,而没有想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会引咎辞职,所以,当解振华辞职的消息公布后,很多老百姓都感到意外,心里在纳闷,为什么是解振华辞职?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辞职?老百姓没想到解振华会辞职,意味着民众希望另外有人更应该辞职。有的人甚至同情解振华并为他抱不平。可以说,当时的舆论或者民众的心里并没有给解振华施加多大的压力。本来引咎辞职制度是迫于民众和舆论的压力,官员辞职以谢天下,而现在,辞职者谢天下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受到同情,应该出来谢天下的,却没有辞职!西方国家的引咎辞职,是由人民的呼声决定官员的去留,它弘扬的是官员应该对选民负责的执政理念,而我国的引咎辞职实践中,民众的呼声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不但难以决定一个官员的去留,而且民众的压力还有可能被利用来指向其他目标,它彰显和强化的恰恰是引咎辞职制度所摈弃的权力本位观念。这种乖离制度本质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官员引咎辞职后,如何安置?“引咎”之后能否“东山再起”?这些引咎辞职的后续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同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严重的有可能使引咎辞职制度脱变为有过错的官员本地下台、异地做官、明辞暗升的合法通道。由于《公务员法》目前对引咎辞职官员的安置和复出问题尚无明文规定,实践中仍然依照中共中央的文件办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29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这里的“适当安排”一词极富弹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从目前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对引咎辞职者一般采取仍保留原级别,享受待遇基本不变的做法,尽管没有实权了,但是也不用承担任何工作责任,上班来去自由,还能够轻松地享受原职级待遇,显得自在又潇洒。这难免使其他官员和公务员产生有失公平的感觉,因为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也只是享受同样的待遇,有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引咎辞职者。难怪有人不无情绪地调侃引咎辞职者是“因咎得福”,也有人讥讽我国的引咎辞职是“引咎辞责”,辞掉的是责任,保留的是待遇。尤其是引咎辞职者被重新任用以后,所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激发了更多人的不满情绪。按照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意味着,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者,只要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后,不仅可以重新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还可以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事实上,我国过去几年中引咎辞职的官员甚至是被免职的官员基本上都被重新任用,有的甚至得到了提拔。一般而言,由于领导职务的职数非常有限,许多人即使工作表现很突出而且没有什么“咎”,往往也没有机会晋升职务,而那些引咎辞职者和被责令辞职者,在他们“因咎辞职”后的短时间内即获得重新任命,这难免使人产生以下的困惑:难道他们就真是这么不可或缺的人才吗?难道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就这么奇缺人才吗?以至于不得不再去请回那些已经“引咎辞职”者?如此一来,与过去的“一地失职,易地为官,能上不能下的官僚体制”又有何区别?这对那些无咎而职务没有晋升的人岂不有失公正?岂不挫伤了他们勤勉工作的积极性吗?这不是背离了建设一支勤政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的立法目的吗?
从本质上讲,引咎辞职是官员道德自省的结果,是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是官员出于自律而进行的自究。引咎辞职一般适用于实行任期制的政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的业务类公务员是不适用引咎辞职的。“按逻辑,引咎辞职不可规范、不可强制,天然地不具制度相。引咎辞职的本质,决定了它只能被倡导,不能被规定。”[5]非正式性、不成文是引咎辞职在表现形式上的特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从法律上把引咎辞职作为一项正式制度予以规定。例如,法国公务员总章程和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中,都没有与引咎辞职相关的条款。而我国却把“不可规范、不可强制,天然地不具制度相”的引咎辞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公务员法》中予以确认,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不仅如此,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我国的引咎辞职不仅适用于机关的领导成员,而且还适用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⑤,换句话说,我国的引咎辞职不仅适用于实行任期制的政务类公务员,而且还适用于实行常任制的业务类公务员!这又是一种对国际通行做法的乖违。笔者不知道那些引咎辞职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引咎辞职”是怎样评价的,国外的学者会认为我们这是在与国际接轨吗?可是引咎辞职的国际之轨与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度并不能对接啊!或许有人会辩解说,我国的引咎辞职是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这倒是个表面看上去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几年前司法改革热潮中出现过的一个笑话,那就是由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首创的司法改革措施“法院干警弹劾制”,由法院自己内设的弹劾委员会来“弹劾”有问题的法官⑥!当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司法改革的一项新举措!后来的结果是,这项创新改革措施无疾而终,这一措施的发明者本想走在改革大潮的前列,却反而因暴露了自己对“弹劾”含义的无知而贻笑大方!那种认为我国的引咎辞职是一种制度创新的辩解,与“法院干警弹劾制”是司法改革的一项新举措的观点,真可谓异曲同工。
四、何以解忧,惟有回归
或许有人会坚持说,任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的立法目的,都有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引咎辞职制度也不例外。今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使这一制度逐步得到完善。笔者赞成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观点,但是认为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完善的价值不大,而且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得到完善,相反它的副作用却有可能不断扩大,影响深远。
引咎辞职是针对那些本身没有咎只是因内疚而自愿引别人的咎来自究的少数政务类公务员,它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狭小。而且完善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法律上的公务员出口(如惩戒、辞退、罢免等等)已经非常畅通,为了满足民众更高的民主要求,才另辟一个道德上的公务员出口(引咎辞职),让官员承担“无过错”政治责任,以达到“政府向人民负责,官员是人民公仆”这一民主政治理念的至善境界。如果一个国家法律上的公务员出口都已经严重淤塞,在这个宽大的法律出口还没有得到疏通的情况下,又去另外开设一个狭窄的道德出口,这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当今中国,我们的民主显然还没有发展到不实行引咎辞职就无以完善的那种高级程度,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许多领导干部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都难以得到追究,依然稳坐权力宝座甚至青云直上。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放着现成的比较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不用,而去引进什么只能让官员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的引咎辞职制度,以为这样就完善了公务员制度的监督机制,就能够使那些只讲‘政绩’,不讲实际,甚至祸害一方的领导干部再异地为官成为历史,实在是与痴人说梦无异。因此,我认为与其舍本逐末地去打造一件软绵绵的公务员监督武器,不如集中力量,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正道和捷径。
即使我们十分看重引咎辞职有限的价值,实在不忍放弃它,并且有决心对它加以完善,那还要看支撑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如果短时期内它所需要的条件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那么引咎辞职制度就是再好于我也无益,这好比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引咎辞职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支撑:一是政务公开透明;二是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足以形成巨大的压力;三是公仆意识流行而不是官本位观念盛行。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政务不公开透明,民众就不知道谁有咎,谁应该引咎辞职,那么外部监督和舆论压力就没有对象,只有政务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分辨出某个官员是否应当承担政治责任,才能对他施加压力,促他自省自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形成不了巨大的压力,官员也可能抱侥幸心理不主动引咎辞职。即使具备了前面两个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官本位的观念很浓厚,公仆意识就很难形成,那么,在这个国家当官就不可能是做公仆,当官就肯定能够获取巨大的腐败利益,官员就会贪恋官位,保官如保命,这种情况下任凭你压力再大,恐怕很难有人会主动引咎辞职。很显然,我国目前这三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欠缺。我们的政务还远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否则,老百姓也不至于对解振华引咎辞职感到以外。我们对官员的外部监督往往没有发挥作用,舆论压力也是非常有限,西方国家的引咎辞职主要靠在野党的政治压力,而我国没有反对党,只有参政党,形成不了政治压力;另外国外的媒体比较独立,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都是官办的,撰写报道尤其是对官员的批评性报道要受到“宣传纪律”的约束,所以很难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特别是我国四处弥漫的官本位意识,跑官买官现象的猖獗,许多官员视乌纱帽为命根子⑦,寄希望于他们主动引咎辞职,无异于寄希望于水中之月。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有些属于文化的积淀,我国要想在这些条件上获得改善,显然非一时之功,这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民主进程。因此,与其花大力气去制定详细的引咎辞职的标准、程序等精神西餐,还不如强化官员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使做官不但没有丰厚腐败利益的回报,而且还要担负巨大的职业风险,一句话,使官位不再具有魔幻般的吸引力,再辅之以政务公开,加强外部的监督,只要坚持不懈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一个时期过后,我们即使不规定引咎辞职制度,官员主动引咎辞职的现象同样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行文至此,笔者完全有理由主张,应当让引咎辞职回归它的本来面目,今后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来倡导,而不能作为一种公务员的法律责任来规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引咎辞职牵手制度,将与严肃的追究解职制度搅混不清。强行的结果,只会导致互伤,既使引咎辞职的道德自觉难以发展起来,又消解了制度的严肃性和法律的严肃性。”[5]因此,笔者建议不久的将来修改《公务员法》时,把第82条予以删除。如果有人坚持非规定不可,那么,只好退而求其次,建议还是放在执政党的文件中去规定,但是必须明确它只能适用于执政党党内人士辞去党内职务,对非执政党员的引咎辞职以及执政党员辞去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能适用。否则,就会陷入以执政党的文件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境地。
注释:
①一般认为,我国关于引咎辞职的规定,最早见于1995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而对引咎辞职作出比较系统规定的,是2004年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②例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有人认为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是主管领导,也有人认为主管工商的副市长是主管领导。再如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有人认为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是主管领导,有人却认为中石油的总经理或吉林省环保局的局长才是主管领导。
③解振华辞去的是国家环保部局局长一职,但依然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党内职务。
④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没有丝毫指责张国庆教授的意思。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我也会持与张教授相同的观点。
⑤《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⑥“法院干警弹劾制”由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首创。2002年12月,某当事人怀疑审判长王某接受案件另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并拖延办案,遂以“不信任”为由向法院举报了这名法官。法院立即启动“不信任弹劾程序”,对这名法官存在的问题进行“不信任质询”。经详细调查后认定,该法官有违法办案、接受被告宴请的可能,并提出相应的证据。随后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农村干部群众中,聘请18名弹劾委员,并在法院内部由干警投票选出8名弹劾委员,成立弹劾委员会。弹劾程序启动后,法院从全体弹劾委员中随机抽取15人出席听证会。经投票表决,一致认为该法官有办理人情案的行为。该法官即被磐石市人民法院弹劾委员会“弹劾”,随后被免去现有职务后待岗。参见李云:《弹劾法官与法官裁判权的保障》,《人大研究》2004年第1期。
⑦河北涿州市委副书记王天琴,因在防非典中失职而被撤职。他泪流满面地说道:“一听被撤职,我差点晕倒。”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足见市委副书记的职位对王天琴而言可谓重于泰山。参见潘多拉:《引咎辞职难在何处》,《法律与生活》200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