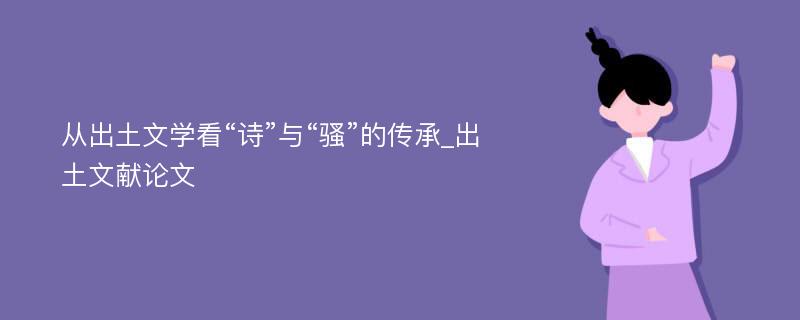
从出土文献看《诗》《骚》之承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133-05
《诗》与《骚》之间究竟有否承传关系,虽然此问题自古似乎并无多少人提出怀疑。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因素的聚合遂使研究者议论蜂出,莫衷一是。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进步,大批出土文物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大批古代典籍的出土,使我们得以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与比较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个问题,相信能够由此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骚》出于《诗》,又在《诗》的基础上有了大步的发展,被称为诗体的一次革命,这原是不争的事实。许多研究者之所以否认其间的传承关系,主要是对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性质的认识问题有偏差。
自20世纪初,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许多著名学者都将中国文化作类型的区分,提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概念,认为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北方文化和以楚文化为主的南方文化是先秦中华文化的两大分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形成过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先秦文学中形成了代表北方文化特色的《诗经》,其特点是质朴尚实的,后来又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与此同时,在南方,南楚文化在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的环境中,诞生了构思奇丽的《楚辞》,其后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虽然有交融,但彼此之间主要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因而是一种平行的发展,而不存在谁继承谁的问题。
形成这种认识最重要的时期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当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几乎同时被发现时,更出现了推翻中华文化一元说的浪潮。一些学者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的,不存在由黄河文化首先发展而后向四周扩散的黄河文明中心说,中华文明是像天空的繁星一样多元发展起来的。因此,一些学者致力于考证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并无传承关系,乃至有人提出楚文化不是华夏文化的一支,不承认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有关楚族渊源的记载的真实性。
近百年来,我国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大批地下文物的出土,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大量出土的是文物而较少先秦的文献资料。相比之下,先秦出土的文物,以楚为最。上世纪80年代的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那林林总总的楚文物,可谓令观众眼花缭乱,也更增添了南方文化独立发展说者的信心。在《楚辞》研究中,则是由日本学者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说的传入,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北方文化为史官文化,南方文化为巫官文化的说法得到理论依据。因此当时召开楚辞会议时,巫风盛行,所有楚辞作品,均被贴上“巫”的标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于1984年发表了《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①与《河南在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②的文章,提出了我的不同意见。
在1984年开始动手撰写的《楚辞论析》③这部书时(1984年动笔,1987年完稿),我坚持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个方面谈了我对《诗》和《骚》承继关系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关于楚族族源记载证明,楚族来源于中原。虽则后来“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然而没有证据说明司马迁所记有误,因而另立新说于史无征。况且楚国国君一直自认为是华夏的一员,以为楚君伪造其族源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二)出土文物已经证明,楚文化在春秋中期之前和华夏各国基本一致,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只是在春秋中后期,随着楚国的强大,才逐渐显露出地方文化的特色,但也仅仅是一种变形,而非另一种类型的文化。
(三)楚人和中原各国交往频繁,文化上也是秉承中原文化的教育体系,这在《国语·楚语》中记载得十分清楚:当子亹请教楚大夫申叔时应当如何教育楚太子的,申叔时列举了一系列应当教育的科目,其中就有“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这是典型的“诗教”的传统,而所开列的各种科目,主要的也是中原儒家传统教育的内容。况且据《左传》记载,楚人在春秋时期,在多次外交场合赋诗言志,颇为得体,绝不亚于中原各国,这也证明其熟悉《诗》的内容和程度。
(四)《诗经》结集至《楚辞》的产生,其间长达二百年之久。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既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也已明确指出《楚辞》承继《诗经》而又影响于赋文学的时间顺序。
就楚辞的体式与思想内容、美学风格等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其具有对《诗经》的承传。这方面的特征,其实西汉的刘安、刘向,东汉的王逸等都已指出。“五四”以来,我们批评楚辞研究中的“儒化”倾向,并不等于前人的研究便一无是处,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巫化”倾向恐怕离作品的真实状况更远。由于这方面的内容比较长,我在此不作过多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我那部小书的相关部分。
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学人以厚爱,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的40多年来,先秦、秦汉、三国的金文、简帛等古代文献资料陆续出土并被整理出来,使得我们能够逐渐走进古人生活的年代,了解到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真实情况,从而重新审视前贤所提出的观点与结论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
这半个世纪以来,是我国古代典籍出土的高潮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的60—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都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简帛古书。由于这些墓葬均为西汉早期,因而其中保存数量丰富的先秦典籍。不过,由于其为西汉人抄本,人们还很难确定其成书时代。
第二阶段为20世纪的80—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荆门包山楚简、湖南慈利石板村楚简等,这些先秦时期楚简的出土,其中所展示内容的丰富多彩,让我们大开眼界。这些秦火之前的著作能够保存至今,实在是太可宝贵的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十年,是这一领域继续辉煌的十年。湖南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是以其数量庞大而震动学术界(里耶秦简有三万余枚,长沙走马楼吴简达十余万枚)。同时还有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战国简。清华简就其数量而言,比不上里耶秦简和长沙吴简,但据李学勤先生介绍与《清华简》整理出版的第一、二辑内容,我们已经看到它所蕴含的难以估量的价值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时期,也是这些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时期。从2001年起,上博简的每一辑的出版,都引来学术界关注的目光和研究的热潮,到2011年8月上博简第八辑出版,可以认为,上博简的整理已近尾声。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清华简的整理出版,其第一、二辑已先后于2010年、2011年底出版,第三辑整理报告成果发布会也于2013年元月4日举行,这三辑的内容都十分重要。④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间,这些出土文献依然会不断牵动学术界的心。当然,除了上述这些主要出土典籍外,据透露的还有北大汉简、浙大简、岳麓简等,虽然这些文献许多是盗墓贼的杰作,但它们一样让我们关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就已知的出土先秦简帛,皆属楚简(清华简未明确为楚简,但整理者认为其文字为楚系文字的风格)。
除了简帛文字外,这一时期也是金文文献出土数量最多的时期。笔者在2000年发表了《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⑤,曾经作了一个统计,在所见的金文出土文献中,仅楚国及其附属国出土的金文铭文字数已过万计,内容也是异彩纷呈、眩人耳目。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编钟上的3000余字有关音律、音阶的铭文,便是先秦音乐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多批楚地竹简,其中所载的相关文字已达十余万字。西汉早期长沙马王堆墓葬中出土的帛书,其中也多存有与楚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字资料,如《黄帝内经》、《老子》等,这批帛书可视为楚文化的延续,加上早先出土的长沙子弹库帛书,总字数也达10余万字。金文如前所述,也有超过万字。这些资料的共同特点是质量较高,其中除数量不多的遣册、卜筮简及法律文书外,大量是先秦的书籍,且有相当数量是久已亡佚的古书。正是借助于这些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我们现在可以对先前有关楚文化和楚辞争议中的一些问题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而回答前贤未能解开的一些疑问。
我认为,目前能够解答清楚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有关楚族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关系问题。关于楚人的族属,出土文献资料中,无论金文还是竹简记载均证明,《史记·楚世家》有关楚族的世系大体是准确的,楚人属于华夏集团颛顼一系的后裔,而非所谓的土著民族。例如出土的《楚公逆镈》有关楚人始祖“吴回”的记载,江陵望山一号楚墓、荆门包山楚墓祭祀卜筮简均记载楚人的祖先有祝融——鬻熊——熊绎等,而河南新蔡葛陵墓卜筮简直接载有“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以选迁处”。2010年底出版的《清华简(一)》⑥中有篇《楚居》,较详细地记载了楚人从先祖季连起至战国前期楚悼王时楚都迁徙的过程,实则是一篇记载楚族的迁徙史,其中提及的楚历代国君的传承,与《史记·楚世家》大抵相吻合,所迁徙的国都,多数研究者认为,与《史记》记载的楚族自北往南迁徙的史事一致。因此,历来对此问题的争议,可以告一段落了。
二是对楚国文化传承及社会结构的认识,较之过去明晰的太多了。以往一些研究者,在论述中原之外地区时,往往以尚处蒙昧未开发的状况来叙述。对楚国社会的认识,也多数认为其仍处在巫覡气氛浓厚的比较原始的社会状态中,因而将楚辞作品多所误读。出土的各类楚文物,从物质创造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楚国当时的文明程度,它显示出楚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的程度。而出土文献则从精神层面展示了那个时代楚国上层建筑的各种状况。出土的楚地简帛中的古籍不仅数量多,内涵也十分丰富,可以说,凡当时北方各种学派的学说,大都可以在这些古籍中找到。儒家的学说,过去被认为在楚国是影响甚微的,然而,这几批楚地竹简,却以儒家学说数量居多,从《孔子诗论》到孔子门人儒学传承者的各类著述,数量相当可观。当然,作为道家的发源地之一,楚地也出土了多种重要的道家著作,从郭店楚简中的《老子》甲、乙、丙三组简,《太一生水》等,到马王堆汉墓中的甲、乙两种《老子》帛书及《黄帝四经》,都让人兴奋不已。此外,文献资料中还有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方术、历法等,这众多学派的著作,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楚国的学术,也是和中原各国一样,在春秋战国时代,那里同样活跃着士人的身影,同样有着百家的争鸣。
我认为,认识这些南楚文化的大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对产生楚辞这一文化背景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至于有过多的奇特想象。从1981年起,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楚辞学术研讨得以开展,我参加了其中绝大多数年会,当然也参加过其他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我曾和一些同道者谈起,楚辞研究给予人太多想象的空间,时常有许多想都想不到的问题被提出,其原因便是可以拿来研究的实证资料十分有限,因而为许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想象的空间。
相比之下,近些年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凭空想象的议论大大减少。究其原因,应当与出土文献资料的发现,使得议论者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有关。即使从这一点看,出土文献资料对于端正学风和文风,其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
出土文献在直接揭示《诗》与《骚》之承传上,可说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诗经》何时南传,我们目前找不到准确的时间,但孔子的弟子中有楚国人,这是于史有载的。
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诗经》的残简。其墓主人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该残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年代最早的《诗经》抄本。学者们通过研究,同传世的四家诗作比较后认为,阜阳《诗经》汉简与传世的各家《诗经》在文句上多有差异,因此,它不属于“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李学勤先生推断“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有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孑遗,入汉后渐归亡佚。”⑦饶宗颐先生在《读阜阳汉简诗经》⑧中,从语言的角度判断阜阳《诗经》残简属楚声系统,为楚地流传的《诗经》抄本。近几年,上博简已整理出的《孔子诗论》,是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议题。由于这一内容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值得深思的是,除《孔子诗论》这样长篇论诗的文章外,其他出土的楚简帛中,也有关于儒家诗论的内容。如郭店楚简中的《六德》、《性自命出》、《语丛》等篇中,均有诗论方面的内容,显示了先秦诗学理论的丰富性。
《诗经》的抄本和诗学理论有关楚简的出土,充分证明先秦时期的楚国同样是受到儒学浸润的地域。至于战国末期,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卿入楚出任兰陵令,其于《诗经》及诗学理论的传授,更是不言而喻的。
毫无疑问,《诗经》及诗学理论的南传,为楚辞创作的勃起作了先期的积累和准备,不承认这一事实是没有道理的。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出土文献还为我们提供了楚诗到楚辞创作演进过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十分令人振奋的。
在研究《诗经》中的采风而来的十五国风时,我们都知道,其中并无楚诗。虽然,在追述楚辞的渊源时,我们常常提到十五国风中的二《南》里一些诗篇,如《南有乔木》、《江汉》、《汝坟》之类,以为其为南国诗风,与楚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南国”是个广义的概念,在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中,南方的江汉诸姬即数量庞大,此外还有大量的非姬姓国,而楚国是个很小的异姓诸侯国,号为子男五十里,所以我们无法说《诗经》三百篇中有哪一篇是楚诗。
但是,笔者注意到,楚地出土的两周金文中,有许多篇铭文,从其句式的齐整、韵律的和谐、辞句的形象化与音乐性方面看,它们几可等同于《诗经》中的雅颂诗篇。因此,1999年我曾撰写了《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一文,列举了八篇在楚及其附属国出土的器物上的铭文进行讨论,指出它们在韵律上与《诗经》用韵一致,在文字上也同属一个文字系统,仅有地域特色而非不同的文化类型,说明华夏文化是楚文化之源。《诗经》与《楚辞》间有明显的承传关系,无需另寻其源。至于楚辞,由于楚人南迁江汉流域立国之后,受南蛮文化以及南方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当然也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不足以改变楚文化源于中原文化这一事实。
简帛文献中,我们高兴地发现了产生于楚地的佚诗。上博简(四)整理出了两首诗:《交交鸣鷖》和《多薪》,多位学者对此作了研究。我赞同曹建国对《交交鸣鷖》一诗的看法,他认为,“鷖”为凤凰类的鸟,诗以鷖起兴以喻君子,与楚人的凤崇拜有关。⑨而《多薪》一诗,廖名春在《楚简〈逸诗·多薪〉补释》⑩中,补释了其中的残文,并对诗中的比兴手法进行研究,进而认定该诗也为楚地的作品。这样,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诗经》体楚诗,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这两首诗究竟是所谓“孔子删诗”时被删掉的,还是当时就没有被采录的,或者是《诗经》整理成书后楚人后续之作呢?有学者认为,《交交鸣鷖》是继《诗经》之后,楚国战国时诵习《诗经》的儒家所拟作的,并提出:该诗的出现,“填补了从《诗经》到楚辞文体发展的过渡环节——拟《诗》体……”;“正是有了像《交交鸣鷖》这样成熟的拟《诗》体作品的出现,才有可能为后来屈原创作突破《诗经》体的四言诗奠定基础。”(11)
上博简(四)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采风曲目》。如整理者所论,该文“记载的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各声名所属歌曲的篇目……这些歌曲的篇目除《硕人》见于《诗·卫风》外,其余皆查不到有文献记录”,“就内容而言,可能是经过楚国乐官整理的采风歌曲的残本”(12)。《采风曲目》中所存篇目达数十种之多,如《牧人》、《硕人》、《良人亡不宜也》、《苟吾君毋死》、《子奴思我》、《思之》、《道之远尔》、《奚言不从》等等。虽然所保存的曲目并不算太多,但毕竟让我们看到战国时代楚国歌诗的冰山一角。因此有学者认为:“《采风曲目》虽然仅余零简断章,它是继曾侯乙编钟发现之后,对上古音乐的另一次重要发现”,“从文学史的角度上,它在春秋时代的歌诗与汉代的采诗之间增补了战国时代的歌诗记录,难能可贵”(13)。这里所指的“战国时代的歌诗”,其中应有一定数量是在楚辞作品尤其是屈原之前产生的。如果这一曲目齐全的话,相信其篇目应当更多,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了在战国时代楚诗繁荣的一个侧面。
更令人感到惊喜的是上博简(八)发表的四篇楚辞赋作品。从宣布上博简入藏并介绍其中的内容时,就已经提及其中有楚赋作品,众多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均翘首以盼其早日面世。2011年7月间,上博简(八)的公开面世,终于使我们得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一年多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文章。下面我们就这几篇辞赋作一点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上博简第八辑中的四篇赋作分别是《李颂》、《兰赋》、《有皇将起》和《鹠鷅》,原皆无篇名,现篇名是整理者根据自己所理解的作品内容所加。整理者并指出,这四篇作品对于研究传世的楚辞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个别篇名可能并不是很准确,如多数研究者认为《李颂》的简文内容与“李”无关,而是咏“桐”的一篇小赋。(14)我以为这一看法是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的。
这四篇赋作的作者不可考;就题材而言,《李颂》、《兰赋》为咏物之作,犹如屈作《九章》中之《橘颂》。其中《李颂》无论从写法、遣词、用韵,都与《橘颂》有明显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相乎官树,桐且治兮。摶外疏中,众木之纪兮。晋冬之祁寒,叶其方落兮。凤鸟之所集,竢时而作兮。木斯独生,榛棘之间兮……(15)
显然,作品大力赞美桐树的异于它树的美好品格。
《兰赋》则是赞美幽兰的作品。屈作中有多处特别赞美兰的芳香与高洁。这篇作品也是如此,但它突出的是兰在偏僻幽深的山野之中,不畏干旱摧残,不惧蝼蚁虫蛇的侵害,保持自身的美德。“摇落而不失厥芳,馨谧迡而达闻于四方”,“宅位隐下而比拟高矣”等等;全篇作品仅一处用“兮”字,其他则用“也”“矣”,倒有点像汉代一些小赋的写法。但两赋都以四言为主,中间夹有杂言句式。这两篇赋作,让读者自然联想到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
《有皇将起》和《鹠鷅》是喻体辞作,以“凤凰”和“鹠鷅”比喻人,句式与典型楚辞体类似,但每句后面均有语气词“今可”,“可”释为语气词“呵”,也可写作“兮”,但“今”字作何读音尚不确知,有学者认为当读为“只”。但《楚辞·大招》句尾有“只”,却不作“只兮”。传世楚辞中尚找不到这种句尾语气词,只有《卜居》中屈原的答词十六句全用“乎”作为句尾,因为用的是疑问句式。
相比之下,《鹠鷅》短而《有皇将起》篇幅较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在校读中指出,《鹠鷅》篇幅较短,“其行文可能自第二句始,两句一组,有似《诗经》一些篇目的重章复唱”。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事实上,这四篇辞作似皆可视为《诗经》到楚辞体过渡的作品,或以四言为主,或“重章复唱”,和传世的屈宋辞作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距离。因此,如果猜想不错的话,它应当是早于传世的《楚辞》的作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脉络。其间的传承关系之线索,由是而清晰可辨了!
注释:
①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②河南省考古学会等:《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71—285页。
③汤漳平、陆永品:《楚辞论析》,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④《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发布,印证〈尚书〉系伪作》,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5日。
⑤汤漳平:《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
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⑦李学勤:《李学勤集·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⑧饶宗颐:《读阜阳汉简诗经》,《明报月刊》第19卷第12期。
⑨曹建国:《楚简逸诗〈交交鸣鷖〉考论》,《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5期。
⑩廖明春:《楚简〈逸诗·多薪〉补释》,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12日。
(11)秦桦林:《楚简佚诗〈交交鸣鷖〉札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20日。
(1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3)黄鸣:《上博四〈采风曲目〉零拾》,简帛研究网2005年12月30日。(14)(15)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学研究中心:《上博八〈李颂〉校读》,简帛研究网2011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