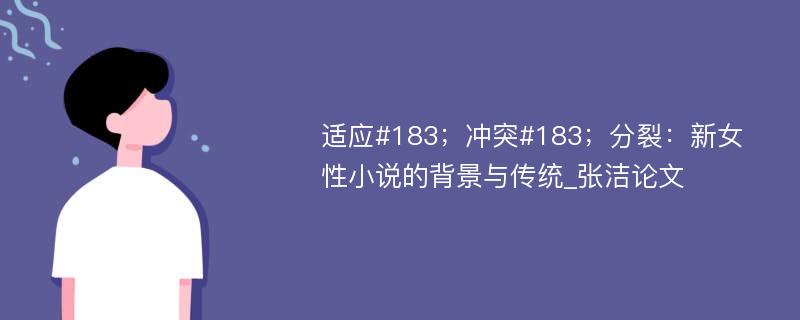
顺应#183;冲突#183;分野——论新女性小说的背景与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冲突论文,背景论文,女性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3-0017-05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女作家对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持续深化,到了90年代,终于出现了明确标榜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它同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其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有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斯妤、海男、虹影、孟悦、戴锦华、王绯、林丹娅、陈惠芬、刘慧英等。如果说女性主义因为它的激进(或偏激)而多少使人有些生畏的话,那么这些女作家、女批评家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则起到了联合起女性写作的纽结作用,它们营构出浓馥的女性主义的氛围和语境,尽可把张洁、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蒋子丹、迟子建等较为“传统”的作家,和张欣、须兰、孟晖、周洁茹、卫慧、棉棉、戴来等晚出或新锐的作家统摄其中。如果再将伊蕾、翟永明、唐娅萍、张烨等的女性诗歌和王英琦、唐敏、叶梦、周佩红、苏叶等的女性散文囊括进来,那么足能表明,90年代的女作家们,已经在“空白之页”上把自己刻入了历史。对此,有一位研究者这样说:“15年前中国文学批评的语境里,批评家们显然也不知如何对待和评价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最有可能出现的做法会是对这些著作的压制和拒绝,它们将因为某种‘美学标准’的原因而不可能放进规范作品从而进入大学的文学课程。这些文本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将因为缄默而至于最终被湮没。”[1]然而,在90年代末新出版的若干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论编著者评价如何,对于女性写作在世纪末的“造山运动”已经不能视而不见了,它在大学的教科书中赫然在目(注:这里包括王庆生主编的教育部重点推荐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如果说在世纪末的众语喧哗声中还有什么“显学”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或女性写作(注:在本文中我赋予“女性写作”以特殊的意义,以区别于一般所说的“女性文学”:从创作主体方面说,女性写作必须忠实于女性独有的经验与体验;从作品效果方面说,女性写作包含着对男权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和颠覆。)当属其中之一。
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传入是80年代初的事。研究界一般认为朱虹在1981年发表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2]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女性主义。198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的《美国当代文学》(王逢振译)有《美国当代女性文学》专章,这大约是较早译介进来的西方学者关于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专论。1986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早期女性主义者的专著。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罗里·赖安等编著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该书设专章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国内读者初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面貌。稍后又有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等女性主义的经典著述。国内学者介绍评述西方女性主义的论文也逐渐增多。1989年由英国女批评家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翻译过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专集。9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著述大量被翻译过来,辑成各种论文集出版,如《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等;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也相继出版。从1988年开始,国内批评家在介绍女性主义的同时,也开始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研究文学,十年来,这方面的专著近20余部(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王绯.《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之召唤》.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戴锦华.《镜城突围——女性·电影·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云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惠芬.《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徐坤.《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徐坤描述道:“中国女性在亿万世人瞩目之下经受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的女性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3]与此前后,在许多女作家提供的文本中,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等都不讳言女性主义对自己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其创作方面的代表就是新女性小说。
“新女性”的命名虽然颇有些落俗,但仍不失为一种区分方式,即把具有程度不等的女性主义意识和倾向的创作同一般的女性文学区分开来(注:林白在《说吧,房间》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当作家的女主人公的口,对“新女性”作了这样的表述:“像本人这样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应声而起的亮光,从我脑袋的七个通道长驱直入,瞬间就完成了能量的转换,有点像扣扣看的动画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马就长力气。新女性的自我暗示正是这样一种特种菠菜,我从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坚定无畏,容光焕发)不光不会呼天抢地,反而会有把丈夫的情人拿来开玩笑的心情。”无论这是正话还是反讽,它都能让我们感知到女性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写作姿态。这既是作品中的女作家对自己的界定,也可以视为林白等女作家对自己“异类”身份的一种认定(尽管也许是种无奈的认定——这即是以上那段话中可能包含的反讽意味)。这为我关于“新女性小说”的命名提供了依据。)。新女性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从此,批判男权文化中心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写作从无意识场景走向历史场景,从边缘楔入中心,成为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学-文化景观。
如果把新女性小说的出现理解为90年代文化上的突变,可能就显得过于简单了,无论如何都应当看到,尽管女性主义的引进促成了女性写作的自觉,但女性写作的传统却深藏在女作家自己的创作中。9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女性小说家同50年代和新时期之初、中期活跃于文坛的女作家之间有一种深固的“母女”关系或“姐妹”关系(在陈染的小说中写的母亲——那位离了婚,勤于写作,性格倔强甚或偏执的女作家,多少有些像是张洁的剪影;而张洁在《无字》中提及的自己的女儿,又多少与陈染有点类同),后者像一座桥梁,完成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过渡:她们在“文革”造成的一片文化荒漠上铺就一片女性文学的绿地,使得更年轻的一代女作家少受多少风吹雨打;她们也许并不认同90年代女性写作的观念和意识,但她们却在女性的沉默中发出来自女性内心的真切呼唤,使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从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裂隙中流溢出来,启示着后来者。不过,在以往的各种当代文学史上,女性写作的传统很难寻踪觅迹,这也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女性作家似乎更容易从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使她们的姐妹们茫然无措,只得艰难地重建那失去了的传统”[4](P.2)。
进入新时期以来,女作家群的突起和创作的活跃,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但是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是把她们纳入到主流文学史的框架中予以评价的,这也就是说,女作家在创作上的成就是依据传统的象征秩序及其标准给以认定的,即使是女性批评家大多也不例外,如在李子云、盛英专论女作家创作的《净化人的心灵》或《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注:分别由三联书店1984年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对于新时期女作家创作的评论基本上采用的是主流文学的标准。这样的批评视野固然可以将有成就的女作家纳入文学发展的线性历史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秩序中予以肯定,但是,却又很容易使女作家在写作上的差异和特质被同化在主导的象征秩序中或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沃尔特指出:文学史上的亚文化群“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5](P.20~21)。参照这样一种概括方式,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确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女作家们一方面在模仿-学习中掌握一个时代的主导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写作作为介入社会和政治的方式,在主流文学的线性时间中争得一席之地,与男性平等地进入象征秩序。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女性创作总的说来就处于这一阶段。女作家们同男作家一样讴歌革命和建设事业,书写劳动人民的英雄业绩,又同男作家一起建构起人道主义主题,推动人道主义文学潮流,并在“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行程中,留下了自己清晰而深刻的足迹。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纳入主流文学的框架予以考察,大体上是符合女作家的创作实际和她们的价值认同的。但是,即便如此也应当看到,即使是在这个“模仿”的阶段,女作家在写作上依然表现出许多男性创作所不具备的差异和特质。这些差异和特质在主流文学的框架中是受到抑制和束缚的,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
关于张洁的评价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新时期的女作家当中,很少有像张洁这样难以用寥寥数语予以概括的。这不仅是说她的创作路数较宽或者风格多样,也不单是说她的变化急速缺少稳定感,真正难以言说的是她创作中种种反差的聚集:温柔的和尖刻的、纤细的和豪放的、简约的和絮叨的、优美的和丑陋的、古典主义式的和现代主义式的、写实的和象征的、崇高的和荒诞的、理想的和冷峻的、洒脱的和拘谨的、超越的宁静和偏激的宣泄、理性的剖析和非理性的堆叠……这就是张洁的小说世界。但是张洁之所以被主流文学认可,主要是肯定她“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这一面。如给她带来殊荣的《沉重的翅膀》,从1981年下半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到1984年出版修订本,其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因而前后修改四次,删改一百多处,全书三分之一是重新改写的,可谓殚精竭虑而修改的重点,除了有些敏感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议论,便是那些女性的主观心态和个人情绪的投射,即被指责为知识女性的“偏激”和“冷傲”之所在。这样的特点早就体现在张洁的知识女性系列中,并引起争执,但在一部正面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中几乎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缺点。张光年的下述评论是极有代表性的:
现在,这位女作家从自己织造的精致的、时而织进淡淡哀愁的纱幕中走出来,大踏步地走上新时期工业战线新旧斗争的战场,这是应当鼓掌欢迎的。我们看到,作家的视野开阔了,心胸开展了,笔底也显得挺拔泼辣了。所惜的是,作家在走上这个广大战场从事时代画卷的综合描绘时,缺乏洞察复杂矛盾的思想准备;也缺乏统御众多人物、众多场景的熟练的调度经验;特别是,保留了、或者放任了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不是主客观有机的有效的结合)。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绝妙的,有些则几乎是作者心理、情绪的化身。人物对话中议论过多,作者还迫不及待地随处插进许多议论。固然有些议论是精彩的,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但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有的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引起严重的责难。[6]
这些批评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它依据主流文学的标准,对一位女作家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具个性的特点加以排斥时(当张洁自己无意于纳入主流文学的框架时,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就已经把男性的写作作为参照的标准了。作为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张洁几乎就无从找到女性的范本,唯一可摹仿的就是男性化的写作。换句话说,张洁若要写一部从正面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且为社会普遍认可,她就应当像蒋子龙、柯云路或李国文、张贤亮等男作家那样去写,克服女作家惯有的那种“以主观表现干扰客观描写的不良习惯”。而克服这类“不良习惯”,也正意味着摹仿男性写作。由此似乎便能理解,为什么最能代表张洁本人风格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不易获奖,而给人印象平淡的《条件尚未成熟》可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什么表现女性的“冷傲感”的《方舟》不能获奖,而写出女性对男性的宽容大度和“无穷思爱”的《祖母绿》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为什么“尖刻”且锋芒毕露的《沉重的翅膀》初版本不能获奖,而几经修订后变得圆熟了的《沉重的翅膀》可获茅盾文学奖。张洁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表明,女作家可以在对男性写作的认同或摹仿中提升自己在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与男作家处于同等的地位,但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以削弱女性自己的声音为代价。人们很难想象,光凭张洁的女性系列能够使她在主流文学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张洁的坎坷若是与遇罗锦相比,则可以说是无比幸运了。这个早已从主流文学框架中被排除出去的作家今天几乎已被多数读者遗忘,在她消失了十多年后,才被有的评论家称为“第一个敢于撕破千百年来裹在女性身上那层虚伪的牛皮而泄露自己稳私的女性”[7]。但正是这样一位女作家却在走向开放、宽松的时代被逐出文坛,离乡去国。一切都发生在1980-1982年的短短两年间:一部《冬天的童话》使她一举成名,一部《春天的童话》连同她的离婚案又让她倍受责难,此后便远遁西欧销声匿迹。新时期或许没有哪位女作家所遭遇的升沉起伏比她更剧烈、更富于戏剧性,更让人不可思议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她有什么触犯众怒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因为她“偏激”地将一腔怨怒泼向男人,特别是握有权力的男人,为此不惜在圣洁的文坛上公开暴露自己的隐私。这不仅为政治家、道德家、文学家、批评家所不容,更是“男人”所不可容忍的,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妖女”的头上。人们像是泼血以避邪一样,以社会舆论的力量,把唾沫啐向这个失去了兄长和家庭的弱女子,甚至在她被迫出国后,还追踪报道她是如何卖文过着乞讨的日子。尔后,这位女作家的声音和行踪连同她的“偏激”就被蒸发掉了,仿佛从来也不曾存在过。只是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林白的《致命的飞翔》或张洁的《无字》等作品的时候,才会从新时期之初的文坛上发掘出这一女性写作的传统。
张洁、遇罗锦等的遭际典型地体现了女性写作同主流文学之间存在的冲突。其实类似的冲突在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一刻也没有止息,只需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样一些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自50至8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以小说家为例)大多数都需承受批判或论争的磨难,如陈学昭、宗璞、茹志鹃、刘真、杨沫、戴厚英、遇罗锦、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刘索拉、残雪等。王安忆的看法或许可以为这一普遍现象提供一个解释:“抑或是由于社会性的原因,抑或更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女人比男人更善于体验自己的心情感受,也更重视自己的心情感受,所以她们的个人意识要比男人们更强……她们天生地从自我出发,去观望人生与世界。自我于她们是第一重要的,是创作的第一人物。这些人物总是改头换面地登场,万变不离其宗。她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个人的一切,使作品呈现出鲜明而各不相同的世界观、哲学观、情感与风落。”[8](P.416)由此可见,尽管女性文学在长达30多年的发展中力图使自己顺应主流文学,然而在顺应中仍然布满冲突——主导的象征秩序同女性写作的冲突,男性中心文化同女性的无意识自我的冲突,或者说男性话语规范与女性话语的冲突。实际上,女性写作真正的差异和特质正深藏在这些批判和论争之下,它们构成了女性写作传统的本质的方面,由于对这一传统的顽强承传,使得女作家的创作同当代主流文学多少有些抵牾之处;也由于这一传统,使得女作家的创作经常率先把一些新质掺入主流文学中,并成为批判或论争的焦点。如个人化写作的导入(遇罗锦率先把个人际遇导入伤痕文学,把表达国家和人民大劫难的宏大寓言变为宣泄个人情绪的私小说),新的题材的开掘(茹志鹃、刘真开反思文学潮流之先,张洁和王安忆把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探讨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象征秩序中剥离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一个题材而非政治题材的附庸),现代主义手法的尝试(宗璞、张辛欣、刘索拉、残雪都先于同时期的男作家表现出艺术上的先锋性或精神上的反叛性)等。因此,在当代中国女性创作的“模仿”阶段,女作家的写作同主流文学的关系其实是既顺应又偏离,而偏离的一面恰恰是在主流文学的框架中受到抑制的。例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看上去同样涉及爱情这个主题,但刘心武的作品受到赞誉,而张洁的作品却陷于论争,其原因在于张洁的小说不尽符合主流文学的标准。
不论女作家在主观上是否将自己的创作纳入或偏离主流文学,只要她们拥有一分自由,她们的写作多少就会表现出有别于男性话语的差异,且不说在新时期,即使是在十七年,宗璞、茹志鹃、刘真、杨沫均如此,这就是女性写作传统的力量所在。因此,准确地说女性写作的传统并非中断,而是被作为普遍标准的男性话语秩序所抑制。换言之,在主流文学的框架中难得听到女性特有的声音,即使有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独有的经验和体验却已被男性的观念和标准所过滤,于是我们从中更多地看到的是“男女都一样”的无性别写作,这也是造成“女性无诗的文学史”的原因。
如果调整一下我们的视野,以女性自己的眼光而非主流文学的标准去看待女作家的创作,也许就会呈现出别一番图景。王安忆曾经这样谈论过女作家在新时期初始阶段所起的“极其关键的作用”:
(《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篇迟到的爱情故事,又是以什么理由来激起人们如此热烈的情感?这一个委婉美丽的故事决没有与社会方面产生的冲突,纯属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私人的小事成为一篇公布于众的小说,这已经夺人眼目了,而事情又远远不止这些。重要的在于这一桩私事并没有与社会政治去凿通关系,而仅仅是与个人的情感发生了联系。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在一条“集体化”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人人忘我,“个人”仅在受到批评指责的时候方可上升为“主义”。人们再不曾有这样的准备:那就是去接受一桩仅属于个人的心情。这大约是多年以来,个人的、私有的心情在文学中的首次出场。假如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其中还有一些关于择偶原则的训诫,还可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公共思想挂上钩,那么紧接着出现的那一篇小小的《拾麦穗》,则是更加彻底地属于个人的了。……而一部《冬天的童话》则更加走向极端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与《拾麦穗》固然表达的是个人的东西,但我们无权判断这就是作者自身的故事,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两个创作的故事。然而《冬天的童话》却是一部真正的作者个人的故事、一部私小说,将文学的个人性推向了极致。再往后,就有了《在同一地平线上》,在此,“个人”终于上升为“主义”,而这才真正唤醒并触怒了一些纯洁的集体主义者。被触怒的人们却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作品中的个人主义与那时候其实已经走到很远的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个人意识联系起来,他们用“达尔文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深奥的批评指向它。实际上,应该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想说的是,在使文学回归的道路上,女作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8](P.414~416)
很难设想这样一种“实质性的贡献”在主流文学史的框架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不管持主流文学标准的批评家们如何评说,不管批判或论争如何纠缠,在新时期,女作家的写作是越来越蓬勃兴旺。在这一过程中,她们既与男作家们一起书写了人道的主题,推进了主流文学的发展,又在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愈益显示出女性写作自身的特质,批判性别歧视的锋芒不时地在张洁、张抗抗、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闪烁,如果我们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眼光来看,她们的创作已经开始挣脱“无性别写作”的桎梏,以尖利的呼啸打破了女性长久的“沉默”。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进入80年代中后期,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进入了肖沃尔特所说的第二或者第三个阶段。残雪、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蒋子丹等人的代表作已经难于归入新时期主流文学的线性时间中;如果说方方、池莉、范小青等人的创作后来被批评家划归新写实主义的话,那也不是由于她们追随什么潮流的结果,而是因为她们偏离了主流文学,找到了一种更适合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在90年代,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催生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写作,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和对男性话语的逃离,终于使女性写作从主流文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个边缘化的文学分野,开辟出女性话语的新空间。新女性小说家们在承袭着“母亲”和“姐姐”们的传统的同时,也承袭下社会对于她们的不解以至于责难,所不同的是她们不再沉默或者乞求理解,而是直率地剖白、犀利地反诘和坚执地抗辩,而且毫不遮掩地引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为理论机锋向男性话语霸权发起挑战。徐坤在驳诘对女性文学的指控时写道:
作为一种边缘话语的女性文学,与其他诸种新潮文学样式诸如先锋、后现代、后殖民等等一样,只是借助于外来语势才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无非是唤醒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自觉和自省,以在男权话语一统天下的缝隙中求得一线女性话语和权利意识的生机。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当整个历史与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声,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愤懑与渴望,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的举动来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里比多浮躁中的一剂镇静败火的清凉。女性因为沉默太久,缄口的时间竟然可以用百年千年为单位来计算,所以,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灭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了。……但愿人人都能冷静下来,认真从女性文学中读出她们那一份不同于男姓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惟其如此,才能让男性与女性同时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砺、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9]
这段文字被徐小彬称为“20世纪末中国女性主义的一篇檄文”[10],徐坤则以它“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出演的开场白”[11](P.71)。话题既已挑明,以后的文学史或许将以此作为女性写作由无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的一个转捩点,新女性小说就是历史的一个证明。从此,“传统”、“历史”、“经验”、“世界”、“性别”、“爱”、“精神家园”等等,再也不是男女共同拥有的“无性别话语”,而被烙上了深刻的性别特征。
收稿日期:1999-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