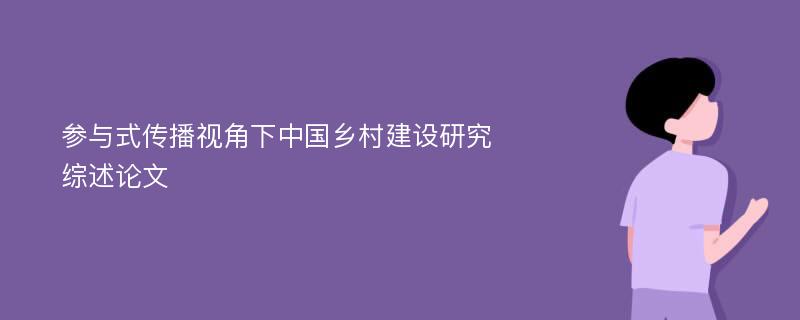
参与式传播视角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综述
□ 焦晶娴
摘要: 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参与式传播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和依附范式更注重受众的参与性。中国乡村建设过程中,激发村民群体参与更能够壮大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力量。本文将对参与式传播理论指导下我国乡村社区建设的研究进行综述,探讨参与式传播在乡村公共领域重建、地方知识再生产和民主性塑造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从赋权和参与的评估角度指出当前参与式传播在地方实践中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为国内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拓展空间。
关键词: 参与式传播;乡村建设;内生性;赋权
一、现代化下的“失落乡村”
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失落的乡村文化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建国后确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重建了国民经济体系,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民利益、加重了乡村负担。在工业化道路的制度结构下,新中国逐步建立起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中国乡村被现代性裹挟和影响,农村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在人口流动中流失,村庄边界日益模糊。城市兴起的中层阶级价值观,即通过消费行为获得主观体验的生活方式,在不断传向并渗透农村时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后果。这种本体性缺位所带来的农村价值荒漠化,催生出诸如邪教传播等一系列精神文化危机。
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媒介建设也在不断侵蚀着乡村公共空间。“饭市”作为一种乡村信息平台,通过支撑村庄秩序和规则起着社会整合的功能。电视下乡后,“饭市”的内在功能被取代或消解。“干群”交流面临的问题和“火塘”的消逝也进一步造成了村庄集体性的消解,村民呈现出原子化、异质化的特点。9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农村信息系统建设,但如“村村通”这种外来推动、国家自上而下调控的乡村信息传播模式缺乏长期效果。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参与,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社会经济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参与式传播在乡村的缘起
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发展传播在第三世界国家遭遇挫败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更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的参与式发展传播。参与式传播强调小媒介的使用和基层传播手段的普及,强调当地社区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与作为“他者的想象”的传统乡村形象不同,参与式传播中的乡村不再是被“拯救”和“教化”的对象,而是能够自主性地改变周遭环境。村民参与意味着集体共同介入发展计划从设计到执行的各个环节,在较高层面上介入传播系统。
参与式传播在构建中国乡村人文生态上具备技术条件基础和内在的文化生命力。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乡村新媒体和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的改善;另一方面,村庄内生的深厚文化和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是参与式乡村传播的基础。民间社会中传统的延续保证了一定时期内文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传统历史文化实践在官方话语鼓励下进一步发展。沙垚提出的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体现出农民群体自我表达的内生动力和对历史现实的建构、批判能力。
中钢国际(000928)全资子公司中钢设备与俄罗斯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简称MMK公司)签署了新建年产250万吨焦化项目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46.87亿元,为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的59.64%,建设工期为50个月。MMK公司始建于1929年,注册资本111.74亿卢布,是俄罗斯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之一,拥有从采矿到金属加工的完整生产链。中钢国际称,该项目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未来3-5年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集体性的重塑
传播学语境下的赋权被认为是对个人效能开发而获得的,提供途径帮助他们开发自我是赋权的关键要素之一。边缘群体应通过赋权重新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赋权通常体现在个人、人际、社区三个层面:个人方面表现为个人自尊和自信的增长;在人际上则是说出自己的观点,进行批判思考;社区方面意味着在社区决策过程中积极参与。参与式传播中的媒介赋权目的是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潜能性和村民的主体性,唤回边缘群体的文化自信。具体指标一方面包括在参与过程中表达权和话语权的获得和形式;另一方面包括在社区组织内对公共事务的监督和知情权以及自主决策。
在场地方面,社工组织开展服务需要一定的场地支持。在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实施办法》也明确提出“在场地设备保障方面,各街道要整合现有的街镇文化站、工疗站、党员活动中心、社区星光老年之家等社区服务场地资源。通过整合、新建、置换、租赁等方式,根据实际需要,多渠道解决服务中心场地,盘活国有产权闲置场地,通过‘租金’或象征性租金的方式用于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⑤。”这一政策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工组织开展服务所需的场地支持。
乡村集体性的重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草根性社区对话”催生了乡村公共领域的重建。“饭市”“火塘”等传统公共空间走向衰落的同时,诸如“参与式影像”等新的乡村公共论坛逐渐被建构。这种自发自愿的信息互动所形成的共同意见为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支持,在公共问题讨论和社区集体记忆书写中,凝聚了共同关注,建构了共同体意识。第二,在参与式传播的集体实践过程中,地方知识的再生产体现着乡村社会的维系。新知识和现代媒介涌入,乡民在共享和交流中促进着传统民间文化的生长,对异质文化的独特解读和重新编码起着创造自我、整合村庄秩序的作用。最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促进了乡村民主性的塑造。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参与者以理解为目标,公益性和公共性较强。共有信念激发乡民对于规则和责任的自觉遵守和对不良现象的民主监督,不断完善组织内部的自我管理机制。
四、参与式传播中的“赋权”与“去权”
参与式传播下的乡村建设现阶段在中国已取得不少成果,乡村舞蹈、民歌、地方戏曲等传统媒介仍是农村民俗活动的主导,例如云南苗汉双语小报《山村小报》和西双版纳勐宋村哈尼族青年妹兰的参与式绘图。“参与式影像”通过关注环保、扶贫解困、权益维护等问题,在村民相互交流过程中起到了社区论坛、社区纽带和社区教育的作用。在新媒体层面,甘肃冯村的“为村”数字社区公共领域通过虚拟在场将“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创造性地进行全球直播,与国家进行双向的回望。
如何考量村民的参与是评估参与式传播在乡村社区建设中产生的赋权效果的重要条件。在参与式乡村传播评估中,阿普霍夫确定了四种参与方式来自项目的实施、评估、受益、决策四个阶段。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参与”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集体参与,在内容选择上由社区民众决定,在观众定位上针对特定的社区成员、利益相关者与决策者,在传播方式上采取针对性的小众传播,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回馈使民众被赋权行动。对照上述指标,我国目前的参与式乡村建设过程中当地村民的参与性仍存在不足。最显著的问题是没有在每个阶段激发更多群众的意识和行动参与,旁观色彩较为浓厚。简单地将摄影机交到草根民众手里并不是参与式影像,由于决策、放映等环节缺失很难实现赋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传播网络”被编制的过程是主动和被动相交织的动态过程。由于共同参与协商并不能改变隐含的权力不平等的现状,一些参与式传播在乡村的实践仍具有自上而下的色彩。对体制外民众进行赋权时,村庄权力结构即村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乡村精英在传播过程中作为中介处于国家与村民之间,能够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知识对村民进行组织动员。曾经被排除在乡村治理之外的普通村民被纳入到治理体系时,体制内外的乡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进行不断博弈。乡村精英达成联盟时,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动员。最后,一些议题与村民的利益相关程度较弱也是村民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之一。参与式传播所讨论的赋权仍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想层面上,在缺乏更大的民主空间和制度平台的前提下,社会层面的“赋权”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专家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技术保障人才。在引进高级专业人才的同时,对现有人员进行持续教育培训,组织开展审计业务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大数据分析研究能力和内部管理能力经验交流活动与知识讲座,充分发挥审计干部教育学院与网络培训的作用,加强大数据与审计交叉学科的培训,提升工作人员数据采集、清洗、转换、模型构建能力。培养工作人员的团队合作意识,加强与不同审计小组的分工协作。
当赋权的过程仍需自上而下的推动时,当权者的“去权”谈何容易。目前参与式传播在乡村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缺乏意见对接机制的建立,普遍存在只有民意的呼喊而没有当权者倾听的现象。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传播中仍沿袭着传统的管理村民而不是服务村民的角色,还没有形成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意识。如何健全开放的双向传播渠道,进而更好地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保障公民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是仍需努力的方向。同时,由于组织者无法面面俱到而留存的民主决策的“空白地带”也需要民主决策在民俗组织中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来保障。被现代化裹挟着的乡村能否借助参与式传播理论建立起自下而上的传播体系,构建新的媒介生态和舆论空间、复兴乡土文化,有待进一步考量。
参考文献:
1.韩鸿.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J].新闻大学,2007(04):74-80.
2.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01):40-49+110.
3.贺雪峰.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研究(专题讨论)[J].人文杂志,2014(07):102.
4.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06):20-24+30.
5.吴理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40年:从“乡政村治”到“村社协同”——湖北的表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04):1-11.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