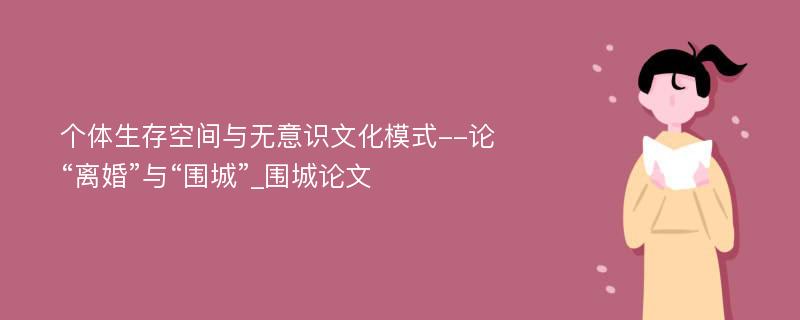
个人生存空间与无意识文化模式——《离婚》与《围城》合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围城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舍的《离婚》和钱钟书的《围城》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幽默小说”,它们在向读者输出谐趣、营造幽默氛围的同时,都能够细腻的表现出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紧扣人性层面挖掘社会心理的错综复杂,试图揭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生活背后的无意识文化模式,给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幽默氛围提供了浑厚扎实的文化底蕴。近现代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变异的内容,类似于神经末梢的个人生活选择,能够为人们认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微观可辨的信息。《离婚》与《围城》客观地展示了与现代城市规则紧密相关的个人生活选择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沉重的文化传统因袭下充满荒唐、怪诞的成分,却是以否定皇权崇拜、大人意识为表征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宗法社会的必然结果。西方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作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渐产生了表面上游离于封建家族制度的个人,这种游离状态的个人一般很难获得西方式的孤独品格,他们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求学留洋、谋职交际、恋爱结婚,却因为寻觅不到真正的个人生存空间而困惑苦闷,由失败走向逃避。《离婚》和《围城》把笔触伸向官僚机构、高等学府这类典型的现代城市生活格局,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传统社会对个人生活选择的侵蚀,以及对先锋意义上的孤独品格的亵渎和拒绝。
《离婚》中的老李与《围城》中的方鸿渐真可谓是一对患难兄弟式的人物。他们苦涩的个人生活内容不但暴露了转型社会内在机制的不合逻辑,还映照出周围人群普遍的心理倾向。他们都有向善的一面,亦不乏进取之心,然而,欲求个人生存空间而不得,在作为个人生存第一要义的求职谋生方面,他们的理想投入宛如水中求月,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老李正是带着这种生存的困惑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怎么会是北平某财政所的一名二等科员呢?虽然他文章很好,学问也不差,具有银行和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事业心强,踏实肯干,但恰是这种带有有个人价值色彩的谋生方式,促成老李对标榜秉公办事的现代衙门的疑心,他“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那么是什么力量泯灭着人们的公益之心,从而扼杀了集理想、抱负、谋职于一身的个人生存空间?人们不难看出,老李所供职的某财政所几乎就是那位胖所长(准确说是所长太太和赵科员)的家天下,在这里“公事就是没事”,小赵是所长太太的人,“所谓办公便是给她料理私事”,而“所谓所长太太的私事,正自神秘不测的往入与公事有关系。”科员们对公文的敷衍以及积极谋缺的心事,都是建立在对这个家天下的认可和虔敬的基础上的。老李曾经幻想用沉默苦闷自己的方式来抵御黑浊的家天下的吞食,但由于同事张大哥之子失踪事件的突然袭来,老李一方面倾其全力营救张大哥之子,表现了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的品质,另一方面却无可奈何地向以赵科员为代表的恶势力投降缴械,任听摆布,等于放弃了对个人生存空间的追求。如果说被看成“晨星不明”的老李干扰了财政所家天下的固有格局,那么被迁升为头等科员后的老李则雄辩地证明了家天下的无往而不胜。丁二爷虽然终于除掉了恶霸赵科员,以侠义的形式拯救了张大哥的家庭生活,但丝毫不能改变财政所家天下的属性和人情网络关系,甚至在更大的背景上,新任市长与各局所的较量和妥协,无不显示了冲突各方对家天下原理的偏爱与呵护。因此,老李的辞职回乡、以归隐的形式企图逃脱同流合污的厄运,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略不同于老李的困惑逃避,方鸿渐在求职谋生的奔波中始终挣脱不掉尴尬的心境,他比老李有更多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体验,因此也品尝了更多的更微细的人生苦涩与无奈,更长久地在“进城”与“出城”之间徘徊。方鸿渐那几年不得要领的旅欧游学生活未能带给他起码的求职谋生准备,他龟缩于挂名岳父的商人银行里,为摆脱寄人篱下的无聊而又自酿出个人情感的苦酒,倒是莫名其妙的“三闾大学”的聘请给方鸿渐送来实现个人价值的希望,当成是求职谋生的转运点。然而,好不容易只做了一学年国立大学副教授的方鸿渐,不能不对足称表率的“三闾大学”疑惑重重了。在这所标榜国家利益、传授现代民主意识的高等学府里,上至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下至讲师、助教、学生、工友,都在内心深处尊奉一种家文化,人们的才智心力毫不吝惜地投入到结党营私、捞取攀附资本之中。校长以笼络听话者作为聘用员工的看家法宝,各系主任更以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来作恰切的呼应。伪善、欺骗、妥协、勾结,都能在遵循家长权威、大人意志的规则下统一起来。方鸿渐甘愿做无派无系之人,又免不掉帮闲打杂的处境,他已经不只被诸如点名、讲书、争课时这些教学琐事弄得昏头胀脑,而且在求得个人生存空间、实现个体终极价值的精神跋涉中预感到没顶之灾了。他不无绝望地这样想着,“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像方鸿渐这样的执迷不悟的天真汉,即使不被冠以“思想问题”的罪名,也难逃被解聘的命运,他求职谋生的失败也就是利用新事物假公济私的家天下意识的一次彻底胜利。倒是方鸿渐后来主动辞掉某家报馆职务的行为,闪出了一丝创造新的生活的迹象,但人物的心理动机很是模糊,依然挽救不了其事业心颓唐的灰色走向。
应该说工商业文明和民主意识交织而成的现代城市生活格局,为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们提供了就业谋生的机会和发挥个人想象力、创造欲的可能。个性化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了历史合法性,私产上的支配,思想上的独处,交际上的距离,情感上的隐私,这些已不再是抵达人生彼岸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个人生存空间的必要内容。可是,当沿袭了千百年的尊卑观念、绝对服从心理、祖先崇拜情结、大人长官意识等陈腐思想改头换面继续支配人们的生活时,苟且偷生、不思进取的处世哲学就会滋生不止,繁衍为供奉大人意识家天下的丰沃土壤,剥夺个人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放弃个人生存选择的浮力已融为一体,实在是已经渗透在人们最平常最自然的行为规范中,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的生存模式。如果说老李、方鸿渐式的求职谋生的失败揭示了城市生活把公众领域家族化的倾向,那么围绕着老李方鸿渐们展开的吃请交际模式和婚恋风波,就暴露了城市生活以公众名义窥视个人生活领域的倾向。这时,独特叙述功能对主题的显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请吃——吃请现象在《离婚》与《围城》中始终处于叙述学意义上的重要位置。吃请作为实践性强的交际手段,似乎已无视个体的生理体验,不但可以直观展示当事人各方的交际期待和心理对撞,而且为寻求仪式化的刺激以缓和事业心的受挫感提供着舞台。在《离婚》与《围城》里,这种请吃——吃请仪式又常常同对他人婚恋生活的窥视、品味、干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怪多变的人生景观。饮食为人生最基本的物质内容,同饮共食兼交流情感愿望,是人类文明的小小点缀。老李三番五次与丁二爷把酒问心,获得了心灵的放松和共鸣,甚至迸发出不甘寂寞沉沦的生命火花;即使方鸿渐与赵辛楣形影不离的同啜共饮带有西方名士的做作色彩,也不乏同舟共济的心理支援。但在具体的生活场景里,上述这类敞开心扉的双人餐形式,发挥着准个体孤独的功能,是对仪式化的以品味他人隐秘而满足的吃请的反拨。《离婚》前后细写了财政所科员之间的四次吃请,每次吃请的因由不同,本质上却如出一辙。小说开门见山写张大哥为破解老李紧锁的眉头而邀老李到家吃羊肉火锅。精工细料,承转浑成,表现了张大哥对他人体贴入微的良苦用心。在一段恶作剧式的人情琐事穿插之后,老李隐密的个人感情世界被张大哥窥破,几乎要和盘托出,但又不可能形成共鸣,结果是老李不堪情义上的沉重负债,任凭张大哥的悉心布置。老李在被逼无奈之下宴请同事,实际上却变成恶少赵科员在张大哥并无恶意的敷衍下,对老李个人家庭生活的肆意取乐。赵科员表面上为了抬举老李而破例宴请同事及家眷,实际上是在试探老李这个怪人的虚实,伺机摘掉老李这颗“晨星”。小说最后描写卷土重来的张大哥为答谢小赵救子之恩而摆下家宴大请财政所同僚,整个请吃过程显示了张大哥劫后余生的活力弥满,而小赵与老李的意外缺席不但给吃请者增添了异性的烦闷和疑惧,也遮去了大家过去种种不好意思的羞愧。总之,张大哥稍有遗憾之外已不能不觉爽快,吃请者们也于酒足饭饱之时精神上格外感到充实满足。
吃请作为一种仪式化的生活艺术,这种多功能的人生景观在《围城》中,同样是展露人物心理揭示小说主题的重要手段。与《离婚》更多地展示古都北平传统市民气息的立意不同,《围城》是在大跨度的横向生活描写中,表现不同的文化因素的扭结和碰撞。围绕着主要人物方鸿渐,小说比较细致地描写了三次吃请过程。在买办张先生的家里,方鸿渐品味了一顿不伦不类、“中西合璧”的文化怪餐,由扳谈、玩牌、就餐、品评构成的相面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洋场上的寄生阶层歧视、取笑、厌弃方鸿渐这类不识时务的小人物的做戏。方鸿渐参加的另一次宴会则属于文化背景社会身份类似的青年留学生圈内的聚餐,动议人赵辛楣固然抱有捉弄假想情敌的叵测居心,但参加者在姿态上都摆出了愤世嫉俗、感时伤怀的架势,他们是否难以忘怀旅居欧美的见习感受,因而在重回故土后纷纷陷入令人困惑的鸟笼与围城。苏文纨以同情弱小民族的风范满足于方、赵之间的斗法,董斜川与褚慎明则分别在诗才的卖弄和向异性的炫耀中掩饰人生追求的虚空和灵魂的阴暗,褚慎明甚至于对方鸿渐的失态出丑而暗中庆幸。倒是赵辛楣颇感到虽胜犹败的苦涩,似乎为日后他与方鸿渐的和解沟通埋下伏笔,因为虚伪做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现代人品格。还有一次重要的吃请景观发生在三闾大学中文系主任汪处厚家中,是别开生面的同仁聚餐,有主仆斗法穿插,有不速之客逢场做戏,集笼络说媒敷衍攻讦卖乖猥琐于一体。在酒宴散去的归途上,赵方二人以暗中握手表示感激与理解,然而他们这次逃脱别人那居心叵测的命运安排真是一种侥幸,他们已经被选择为可以琢磨利用开心解闷的焦点人物,最终是几乎别无选择地逃离“三闾大学”这个是非之地,合乎人性的个人生存方式再一次与他们无缘。
与谋求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的职业一样,渴望真诚平等充实宽容的婚恋生活,亦成为个人生存空间的重要内容,而所遇到的来自传统社会的挑战也更为复杂持久,可以说《离婚》和《围城》在布局和命意上都考虑到了传统文化心理对婚恋这个特殊生活领域的顽强的渗透。我们不妨把传统社会关注个人婚恋生活的心理倾向称之为做媒情结。《离婚》开篇就点明张大哥生活在“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的自我陶醉与满足的氛围中,有关张大哥以做媒为核心的生存方式的多角度叙述几乎制约了全篇。老李其实很喜爱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并不想厌弃俗气的乡下妻子,他只是在内心深处勾勒了一点“诗意”,但他的独居锁眉与不苟言笑,却引发了两种关注的目光:张大哥型和小赵型。张大哥请老李吃饭完成了诊脉,热心张罗给老李搬家实现了对症下药,他在善意的奔波中享受到了难以言说的人生快悦。恶人小赵是以猥亵而阴险的心理关注他人女眷的,经他看了一眼之后,衙门中便添上多少新而有趣的谈话资料。老李去接家眷,消息便不胫而走,“老李接‘人儿’去了!”赵科员的眼睛挤得像一口热汤烫了嗓子那样,“是吗?”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无论是善意的张大哥还是恶意的小赵,他们都构成了对他人婚恋生活贪婪而粗暴的介入,以此获得精神满足,在品味可笑的老李的过程中,张大哥和小赵本质上如出一辙。
做媒情结似乎含有民族文化的远古记忆内容,它理应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衍生物,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异中,做媒情结表现为窥视他人情感隐私的倾向,同封建陈腐的婚姻观念融汇在一起,极大地伤害了个人情感的尊严。“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这句提纲挈领之语暗示了做媒情结对芸芸众生的征服,因此《围城》中方鸿渐在三闾大学遭到精神洗劫就不是孤立的现象了。方鸿渐与孙柔嘉由相识理解到恋爱结婚,其间充满苦涩,旅途中赵辛楣的调侃尚不乏善意,而李梅亭、陆子潇、高松年、汪太太的目光已受阴暗心理的支配了。身为训导长的李梅亭对方、孙两人的格外关心正是出于阴暗的窥视心理的驱使,因此,“李梅亭这两日窃窃私讲的话,比一年来向学生的训导还多。”借他人的有趣可笑开眼好玩,来消磨无聊刺激神经满足渴血欲望,几乎是无师自通,于是“吃订婚喜酒那一天,许多来宾研究孙小姐身体的轮廓。到上了甜菜,几位女客恶意地强迫孙小姐多吃。”个人婚恋生活成为人们最易于窥视的领域。赵辛楣不过是心仪于汪家少妇,方鸿渐也本无结婚之意,他们二人因失恋而殊途同归,又因周遭遍布的庸俗势力的挤压而逃亡,各奔东西。他们这种既受西方文明挑逗、又遭传统势力偷袭的心理轨迹十分耐人寻味,他们要经受充满奴性崇拜而又幸灾乐祸的劫难是文化变异过程中的历史必然。
《离婚》和《围城》通过丰满细腻的生活画面表现了现代城市规则下人们的文化适应的某种历程,透过谋生求职、人情交际、婚恋生活这些最基本的人生存在形式,剖示了家天下意识、吃请习性、做媒情结对人们生活的侵蚀,这种对社会人生的文化的历史的审视已经涉及民族文化的无意识领域,为我们寻找超越丑恶克服奴性的出路提供了又一个思想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