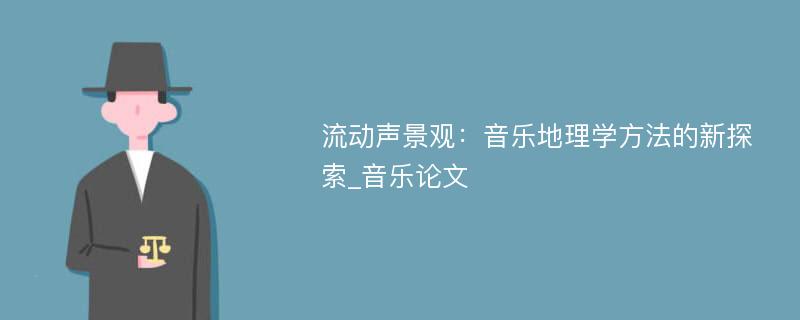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地理学方法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景观论文,声音论文,法新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71(2008)01-0083-06
“声音景观”(soundscape)一词,是近十多年来西方民族音乐学论著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近几年来,这一词汇也在一些中文音乐论著中不断被采用[1][2](第40页)[3],逐渐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新概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对于扩展民族音乐学乃至音乐美学等领域的学术论域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对深化国内正在发展中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本文即通过对这一新概念的界定,通过对其理论引申义的阐发,探讨这一概念在音乐地理学区域传统音乐研究以及变迁中的当代传统音乐研究可以生发出的新的方法论议题。
一、“声音景观”概念界定
1.“景观”词源
“景观”一词,在中文日常用语中指壮丽的自然风光。目前学术界常用的“景观”一词,则是来自西方地理学术语“landscape”的意译名。在地理学中,“景观”一般指地球表面各种地理现象的综合体,而这种综合体又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自然景观指没有受到或较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综合体;人文景观指人类创造并叠加于自然景观之上的文化景观(如农场、城市、庙宇、楼阁等)。此外,人文景观中除了视觉可见的物体形象本身外,还包括隐含于视觉形象因素中的看不见的象征或意义因素,以及与该文化的起源、扩散和发展等有关的某些“证据”,而这些隐含因素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自然景观相比,由于人文景观(包括视觉可见形象和隐含于其中的各种因素)是人类文化的创造成果和社会历史的表征显现,它形象地反映了“人—地”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表现,因而成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
地理学使用的“landscape”(景观)这一概念,在西方其他社会人文学科领域也被加以变化地广泛引用,随即出现了以“scape”(英文后缀词,表示“景”、“景色”之义)为后缀的一系列新创词汇,如:“人口景观”、“技术景观”、“经济景观”、“传媒景观”、“意识形态景观”等等[4](p.2,转引自[5])。在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下,西方民族音乐学界也有人变化地吸收了这一概念,将“sound”(声音)和“scape”(景色)两个词合二为一,构成“soundscape”(声音景观)这一新创词汇[6]。
2.“声音景观”解惑
在使用“声音景观”这一概念时,通常有两个问题会造成我们理解上的迷惑:其一,在我们的习惯认识中,声音依靠听觉而感知;景观依靠视觉而感知。既然如此,声音又如何成为可视的景观?“声音景观”这一概念似乎有悖常理。其二,音乐虽然是由声音构成,但它只是声音的一种而非声音的全部。既然如此,作为一个音乐学的概念为何不用“音乐景观”(music-scape)而采用“声音景观”(soundscape)?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与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哲学观和音乐文化观有着密切关联。本文试图通过以下两个论题的讨论来阐发与“声音景观”概念有关的学术理念,从而解释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两个迷惑。
论题A——听觉的音乐和视觉的音乐
人所共知,音乐是诉诸听觉的艺术,人们主要凭借自己的耳朵来欣赏音乐。我们只要打开收音机或将唱片放进电唱机,就可以尽情地用耳朵来享受音乐了。但是别忘了,通过唱片或电台欣赏音乐的方式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爱迪生(T.Edison,1847-1931)1887年发明留声机以后,人类才开始用蜡筒、唱片以及后来的录音带、磁盘等介质储存和回放音乐。是爱迪生和后来的音响科技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可以完全用耳朵欣赏音乐的境地。在爱迪生之前,人们只有在表演现场才能听到音乐,而现场欣赏音乐就不仅是在“听赏”,同时也在“观赏”。身临其境,视听并用,原本是人类欣赏音乐的传统习惯。爱迪生不过是部分地改变了人类视听并用地欣赏音乐的习惯,在网络科技、数字信息更为发达的今天,尽管只用耳朵欣赏音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便捷,比如,只要按下mp3开关就能尽情用耳朵享受音乐,但是,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放弃视听并用欣赏音乐的传统习惯。保留在民间生活场景中的传统歌会、仪式音乐、茶馆说唱、戏曲表演以及现代音乐厅音乐、剧场歌舞音乐、广场摇滚音乐等等,仍然既是听觉的音乐,也是视觉的音乐,是视听同时共享的音乐。
在如此视听并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尽管我们的视觉所能“看”到的并非是音乐声音本身,而只是音乐表演的现场、表演人、表演行为以及现场听众、观众的互动表现等现象,但是,只要我们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在接受外界事物时,绝对不是依靠某个单独器官去孤立地捕捉信息,而是多个器官会同时做出反应来接收和感知事物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人类在用“耳”接收音乐声音信息的同时也会主动用“目”去捕捉声音信息源,用“脑”去整合感知到的音乐事件,甚至会用整个身体对音乐感知做出反应。从这个事实去理解音乐的本质,音乐就不只是一种只能依靠耳朵去感受的声音,它还是一种可以凭借眼睛去体验的“景观”。哪里有现场的音乐事件,哪里就有可以观察的声音景观;只要音乐事件在现场发生,就有地点、场合、人、行为等景象出现;正是音乐事件发生的地点、场合、人以及由人的行为产生的音乐声音,共同构筑起一个整体的“声音景观”。民族音乐学家也正是从这样的文化整体观的“景观”理念出发,采用了“声音景观”这一概念。
美国音乐学家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在其著作《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Soundscapes:Exploring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中,对“声音景观”作了如此定义:“一种声音景观,即是一种音乐文化有特色的背景、声音与意义。”其定义中的“背景”是指“表演地点”和“表演者与听众的行为”;“声音”指“音色、音高、音值、音强”;而“意义”则指音乐本身的含义及对表演者与听众生活的含义(转引自[7])。在这一定义中,“声音景观”除了视觉可见、听觉可闻的现场情景外,情景中不可见、不可闻的“意义”甚至情景外可能具有的“意义”,都被包含其中。尽管这一定义对“景观”的涵盖面已经超越了“景观”的本身,但就民族音乐学一贯坚持的文化整体观(cultural holism)学术立场而言,从研究方法的需要出发,这样宽泛的涵盖定义也就可以理解了。何况,文化地理学在研究“文化(人文)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时,也将看不见的象征或意义因素以及与文化景观起源、扩散和发展等有关的“证据”都作为这一概念所要涵盖的研究对象了。
论题B——时间的音乐和空间的音乐
时间和空间是世界上任何物质存在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任何一种音乐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受“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这一美学命题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音乐的存在只需要时间而不需要空间。但实际上和任何声音一样,音乐的存在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音乐的声音由声源体(人嗓、乐器)振动而引发一定空间内的空气产生振波(即声波),声音的这种振波在空气中扩散就像水波在水面上扩散一样,会推动气体产生水波一样的传导式运动,人耳就是接收了传导过来的这种空气振波而感受到乐声的。如果没有空间,没有给声音振波的传导提供一定的空间范围,音乐的声音就不会存在。因此说,音乐的存在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只不过音乐存在所需要的空间不是有形的物质空间,而是无形的声学物理空间。所以说,音乐不仅是一种时间艺术,它也是一种空间艺术——一种眼睛看不见但耳朵能感知的存在于空间中的艺术。
音乐艺术的空间属性,不仅体现于音乐存在方式的声学物理空间特性,还表现为人在接收音乐时产生的心理感应过程。由于人的两耳听觉具有空间定位功能①,并且人耳还能够对不同“声场”(声音的场景、场合、声源方位等)的音响效果产生听觉记忆[8],②因此,当音乐的声音作用于人耳,感应于人心时,就会在人心理上形成一种意象空间,同时,音乐声音还会造成心理性引申反映,会在人脑中产生自然环境、社会场景等现实空间的主观联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是:音乐本质上是在一定时间过程中和一定空间范围内得以展现和存在;人在接收音乐时除了感受音乐的时间过程外还会产生音乐的空间意象。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仍是在一般原理意义上讨论音乐存在和被感知的空间概念的。如果我们把原理性结论中空间概念的范围扩大到更为宏观的社会、人文和历史、地理视野,我们就会推导出另一个结论:“任何一种音乐传统都在一定地域空间中分布。”这正是音乐地理学所关注的音乐的空间分布问题,其理论来源于文化地理学的认识,即“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空间范围不同的地形、地貌、位置、天象、气候所构成的地理环境对世界上面貌各异的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一向具有稳定而直接的作用”[9]。文化地理学之所以重视“人文景观”(亦即文化景观)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世界上不同人种、不同群落的文化历史都以其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环境空间中。这些人文景观中,就包含着由音乐传统构成的“声音景观”,或者反过来讲,“声音景观”就是分布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的有特色的音乐传统。因此可言,“地域空间”和“地方特色”是“声音景观”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而这两个意义也正是音乐地理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核心论域。
上文提到谢勒梅将“声音景观”定义为“背景、声音与意义”,正如汤亚汀先生已经认识到的,谢氏对“声音景观”的这一定义大致相当于梅里亚姆对音乐文化的“概念—行为—音乐声音”三分模式。不同的是,谢氏用“背景”涵盖了梅氏三分模式中的“行为”并增加了“表演地点”(venue或place);用“声音”涵盖了“音乐声音”从而扩展了音乐的概念[7]。其中,谢氏定义中对“表演地点”的强调,笔者认为,正是对音乐地理学空间定位的研究(包括对音乐传统空间稳定性或流动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声音景观”对音乐地理学研究的意义
从西方音乐学科发展的历史看,音乐地理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一个研究领域。它以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为基础,借鉴文化地理学的方法,把音乐与其生成的文化地理环境相联系,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音乐传统,分析出音乐的地域特色和区域差别。在民族音乐学早期(比较音乐学时期),即有德国学者霍恩博斯特尔(M.von Hornbostel)和萨克斯(Curt Sachs)通过研究全世界各地区的乐器和音乐而提出“音乐文化圈”学说;匈牙利的巴托克(Bela Bartok)和柯达依(Zoltan Kodaly)通过研究本国和邻国民歌而提出“音乐方言区”的概念;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lan Merriam)和内特尔(Bruno Nettl)通过研究特定文化而提出“音乐文化区”概念;同一时期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洛马克斯(Alan Lomax)在其著名研究项目“歌唱测定体系”中通过比较全世界各不同地区歌唱风格与政治经济环境而提出新的音乐文化区域概念。这些研究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音乐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但他们对音乐风格区域或音乐文化区域的划分,明显带有音乐地理学空间布局研究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也投身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其中代表性成果如:杨匡民的“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的《汉族山歌研究》(1982);苗晶的《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的《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的《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的《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的《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乔建中的《音地关系探微》(1990)等。尽管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取向,那就是对中国传统音乐(主要是汉族民歌)进行风格区域差异的划分。尽管划分音乐风格区域已经具有音乐地理学地域空间分布研究的性质,但初期的研究多从音乐形态(旋法、结构等)方面进行“定性”描述,较少探讨音乐风格区域形成过程中的地理环境要素。而苗晶、乔建中1985年出版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以及乔建中1990年发表的《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一文[10]和1998年发表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一文[9],不仅弥补了忽视地理环境要素的不足,而且还补充了音乐文化区域历史文化成因的分析,使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了更为明确的音乐地理学特征。
综观前人的研究,他们大都是从宏观角度对辽阔的空间范围(北方或南方)甚至全国范围内分布的传统民歌所作的比较研究,并且重点都聚焦于音乐风格的“区划”问题。这种鸟瞰式的民歌风格地图的描绘固然重要,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样的笼统性研究往往会忽略音乐地理学需要关注的“细节”——那些地方音乐传统的细节,亦即由各个地方人们的音乐的“背景”、“声音”和“意义”共同建构起来的富有特点的“声音景观”的细节表现。以往提出的“民歌色彩区”、“民歌方言区”、“音乐文化区”等各种区划概念,都强调的是音乐声音自身的特点,忽略了地方音乐的文化整体观,而“声音景观”概念所提供的学术理念,正是包含了音乐的地域环境、表演场合、唱奏行为等“背景”因素,音乐的体裁形式、形态特征、风格特色等“声音”因素,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使用方式、文化含义等“意义”因素在内的文化整体观。假如就像西方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先驱者已经犯过的错误那样,将世界各地的音乐从其生长和赖以存在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进行音乐类型和风格的比较,那么,这样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大而无当的、缺乏严谨证据的主观论断。更何况,音乐地理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对音乐风格进行空间划分(即所谓“区划”)方面,而应吸取文化地理学的学术视角,除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分布规律”外,还研究不同区域内音乐传统的“历史演化过程”,并关注同类音乐在不同区域间的“地域传播途径”。如果说,“地域分布规律”、“历史演化过程”和“地域传播途径”是音乐地理学应面对的三个重点研究方向,那么,探讨“人—音—地”三者的相互关系就应该成为音乐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像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一样,音乐地理学也需要通过某些可以涵盖其研究理念的学术概念的确立来建构本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而“声音景观”这一概念,正是涵盖了“人—音—地”关系主要内容的、对建构音乐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有用的一个核心概念。
三、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统静态样式与动态规律的辨证
黄翔鹏先生就音乐传统的变化与延续规律提出过一句名言:“传统是一条河流。”[11]③这是一个借助“河流”所包含的时间概念(即河流流经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概念(即河流流域的空间延伸)的双重隐喻,用来说明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音乐传统如同自然界的河流,是一个奔流不息、支脉纷杂、流变万千而又不离其源的动态过程。他在表述“传统是一条河流”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时感叹道:“音乐艺术亘古以来在积年累月中变化,甚至迁徙她的河道,使人不复辨认遗迹;甚至在她的任何一个瞬态当中也无处不在流动。”[11](第3页)本文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其中“流动”这一概念正是取黄先生河流隐喻之说的含义,将音乐传统看作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
在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我们总是奉行着寻找“规律”的所谓“科学”方法,不断地在总结着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种带有规律性的音乐样态模式。所谓“民歌色彩”的区划研究,同样是在寻找不同地域中民歌风格样态的模式。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在寻找规律的这种所谓“科学”方法中,实际上潜在着一个不科学的后果,即当我们终于寻找到某种规律性的音乐样态模式时,我们就把一种本来是鲜活的、动态的、变化着的音乐传统彻底固化成一种静态的样式了。本文之所以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这一概念,正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种理念:传统音乐并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静态样式;音乐传统并不是在时间上凝结或在空间上固化的“景观”;各地传统音乐是在不断衍生变化的音乐传统中不断衍生变化着的动态声音景观;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中的动态变化就是包括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在内的声音景观的普遍规律;研究者只有从这样的动态观去观察和分析声音景观,才有可能捕捉声音景观的真实面貌、发现声音景观的真正意义。
前文已提到,时间和空间是任何事物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声音景观的存在也不例外。声音景观的流动性,也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分析和理解。
时间维度的流动性(亦即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声音景观历史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近二十年来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兴趣点与以往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过程”(processes),亦即对“作为过程的音乐”(music as process)的研究。即如内特尔所说:“现在更多的兴趣在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how things happen),而不是‘事情是怎样的’(how things are)。”[12](p.381)研究“事情如何发生的”过程,也就是研究音乐历史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不过,和传统的音乐史学相比,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主要关心口头音乐传统的历史。就音乐地理学的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不再像比较音乐学时期那样,“人们实在很少有兴趣去作地理分布层的推测、进化论体系的构筑那样的历史研究”[12](p.381),而是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音乐的历史。如果说梅里亚姆关于“声音—行为—概念”的音乐三分模式体现了声音景观的文化整体观理念,那么,赖斯(Timothy Rice)关于“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造与体验”的新模式则可以被看作是文化整体观在历史学意义上的扩展,或可以作为声音景观动态演化过程的学理性阐释。梅氏的音乐文化整体观和赖斯的音乐文化历史观,正是我们研究声音景观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值得吸取的学术理念。
空间维度的流动性(亦即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声音景观地域分布的移动变化状态。这里所说的声音景观的“移动”,可以包括从微小的表演性的现场空间移动到宽广的传播性的跨地域空间移动,而无论声音景观空间移动范围有多大,都会在移动中产生变化。实际上,除了古代城市的钟鼓楼报时、寺庙的晨钟暮鼓等这些由无法移动的信号响器在固定空间中所展示的声音景观外,其他任何传统音乐活动都是以发声体(人嗓、乐器)的可移动性在非固定空间中展现其声音景观的。音乐活动在不同场合、不同场所的哪怕是微小的空间移动,都会造成声音景观的变化。即便是由微小空间移动引起的微小的变化,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细节”。此外,“地方”无疑是产生传统音乐的重要土壤。以往音乐地理学所作的所谓音乐“地方色彩”区划,正是以音乐“产品”与“产地”的依存关系为依据的。然而,除了那些与原产地的环境土壤相依为命的音乐品种(如民歌中的山歌、号子类)之外,各地流行的许多其他音乐品种(如小调、器乐曲牌等)并非局限于一个地区,也不是只有一个地理来源。正是这些可以脱离原生产地的音乐品种在区域间的传播移动,以及在传播移动中的变化,形成了音乐的声音景观在空间维度的流动性和变化性,从而构筑了无数个地方性的流动的声音景观。
声音景观的流动性变化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空间维度的流动变化以时间为前提;而时间维度的流动变化则体现为空间维度的流动变化。例如,声音景观在时间维度的流动变化,既体现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也体现在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性的流动变化。时代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即当代的变化。关注传统音乐在当代的变化,已经是西方民族音乐学多年来的重要方向。一向善于创造研究模式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赖斯于2003年发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写作中的时间、地点与隐喻》 (Time,Place,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一文[13],并在文中设计了一个“音乐体验的三维空间”模式。该文及其模式的提出,正是为了帮助民族音乐学家理解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传统音乐、音乐传统以及人们的音乐思想的变化。赖斯2006年9月曾在中国音乐学院学术讲座中解释了为什么设计这个模式的原因,他说:
我们过去通常走向乡村去研究其最传统形式的音乐,然而,现在演奏这些音乐的音乐家却在现代音响制作系统中玩味着合成器。我们曾经旅行到古老的城市去研究古代宫廷音乐,然而,现在最好的(古典音乐)音乐家已经移居到了巴黎、旧金山。这些“田野”经验已经引导民族音乐学家去理解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没有疆界的、互动的文化中,再也没有被边界封闭的孤立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群、思想、想象以及音乐向遥远的地方迁移。越来越多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④
在赖斯的这个模式中,“空间”(space)是为了研究分析而设计的一个抽象的数字意义上的空间;“位置”(location)是指在音乐体验的这个抽象空间中一种坐标轴线的定位名称;“时间”(time)是坐标中另一个轴线的名称。模式之所以如此设计,他说:“人们在他们生命过程中可能生活在许多不同的真实或虚拟位置。时间比人类的存在更为久远,它又被人们的音乐体验所延伸。人们在他们的一生中可能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他们的音乐体验和时间一起改变着。”⑤
在关注时代性尤其是“现代性”影响的当代社会音乐景观流动变化方面,前述美国学者谢勒梅《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一书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更能引发对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该书的宗旨就是“探索音乐怎样在时间(历史变迁的维度)和空间(地域变迁的维度)中传播、演变。”反映了作者关于音乐声音景观“时空背景转换变异”及“时空可以构筑音乐;音乐也可以构筑时空”[7](第92页)等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些后现代理论视角。这些理论视角,在汤亚汀近期出版的《城市音乐景观》[3]一书中,已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和引用,可参见。
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各个研究领域中,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域。尽管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仍需要不断深化,需要通过有益的方法论借鉴而使研究得以深化。有关如何深化和完善中国音乐地理学建设,乔建中先生已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如: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绘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地图”;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9]。这些建议对中国音乐地理学领域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具有学术前瞻性价值。而本文提出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者“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所作的学术阐释和理论引申,则是为了借此扩展音乐地理学领域的学术视野和丰富该领域研究方法。本文“流动的声音景观”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对它的理论辨析,更是为了促使音乐地理学研究突破以往静态音乐区划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中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也就是说,应采用民族音乐学的整体观(即包含声音、观念、行为、意义的音乐文化研究)和动态观(“过程”研究)去研究在时空中不断流动着的声音景观。
注释:
①人类的耳是司听觉和平衡的器官,听觉的方位感在控制人体平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②人耳的声场记忆包括对声音的远近、左右、大小、虚实、明暗等因素的记忆,这些因素综合构成听觉对“声场”的主观意象[8](第293页)。
③黄翔鹏先生在诸多文章中曾解释过“传统是一条河流”的寓意,并且这句名言已被他用作一部文集的书名:《传统是一条河流》,可参见。
④薛艺兵据赖斯2006年9月22日在中国音乐学院讲座课件(Power Point)英文原稿摘译。
⑤译文出处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