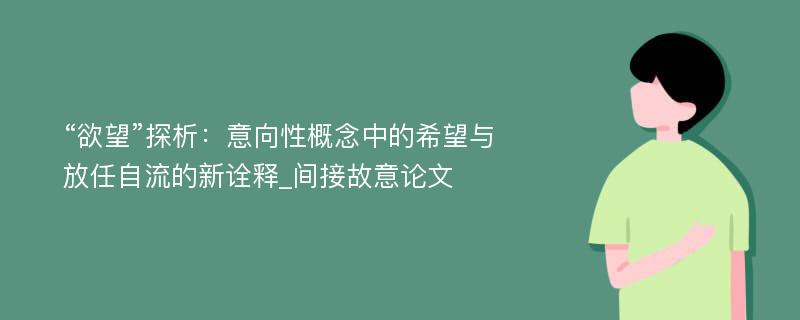
探问“意欲”为何——对故意概念中希望和放任的新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一、“意欲”含义的诠释
(一)“意欲”为何的困惑
毋庸置疑,各国刑法体系对故意犯罪实施处罚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在立法中明确故意犯罪的概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譬如,一向强调法典化、成文化的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德国、日本的刑法典都没有把故意的定义明确在立法中。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在刑法典中难以抛头露面呢?最大的困难来自于间接故意的概念难以确定。以德国为例,1962年《西德刑法修正草案》曾尝试定义间接故意,然而,在8天之后,却因为委员们在讨论会议上对“意欲要素”的用字相持不下,使得赞成的票数锋转直下,最终放弃了对间接故意的规定。[1](P56)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英国。英国刑法最初也只是将故意限制在直接故意的范围内。英国法律委员会在1989年的《刑法典草案》中,尝试给故意下过定义,但最终也是因为对于故意概念的内涵把握不定而宣布失效。
德国学者威尔采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意欲是一种原始的、终极的心理现象,它无法从其它感性或者知性的心理流程中探索出来,因而只能描述它,却无法定义它。”[2](P60)可以说,故意概念难以在刑法典中抛头露面,都是“意欲要素”惹的祸!
(二)“意欲”涵义解析
意欲是什么?我国学者中很少有人对这一名词进行追问。只是在著述中轻描淡写,认为“希望主义就是意欲主义”;或者在字里行间与意志一词穿插使用。不过,这并不奇怪。关于意欲到底是什么,即使是“原始输出”这个词汇的德国,以及理论上紧随其后的台湾,学者们也没有对意欲下过一个定论。而在刑法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关于故意要素“认知与意欲”要素的讨论,迄今也没有把意欲的概念到底为何解释清楚。所有这些都说明,意欲是一个难以描绘的心理状态。不过,我们通过学者们形象的描述和多角度的表达,还是可以确定意欲的基本含义。
譬如,德国学者许宾德教授认为,“间接故意的意欲要素是一种比较弱的实现意志”。还有的学者干脆把意欲要素描述为“情绪性的”、“非理性的”、“敏感的、易变的、流动的”一种状态。台湾的判决要旨则从有责性的角度扼要地说明了意欲的性质为:“故意之内涵,应包括认识与意欲两要件。犯罪意欲之心理状态,较之单纯的事实认识,于犯罪故意更表现其恶性,而应受非难。”[3](P10)相对而言,台湾学者许玉秀教授的著述则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意欲要素的真实面目;“我想要”和“我去要”是意欲要素的两层意思。其中“我想要”就是一种意思决定或欲望的确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我去要”就是“行动的决定”,是启动行为的决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志因素。决定行为的实施,是意欲在支配。行为人根据认识,做出“我想要”和“我去要”两个决定,这才是责难的基础。其中,“我要”是一种情绪,是行为决定;“我去要”是控制行为发生,实现行为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在一瞬间完成的。[1](P58)
笔者比较赞成许教授对意欲的理解,沿着这样的思路,尝试将意欲定义为“情绪和意志互动的一种综合状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心理学家的最为朴素的解释中获得印证。最近美国有一本畅销书,书名就是:《我想要》(I Want It),是关于解决儿童心理问题的系列书,介绍了儿童六种强烈的情绪。也就是说,情绪最为原始的、外向的表达就是“我想要”。书中开宗明义:情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与特点,它是一种复杂而又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生理反映及心理感觉。[4](P121)
既然意欲要素就是一个由情绪和意志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它们之间彼此不可分割。其中,情绪是意志的内在动力,而意志是情绪的最终体现。论述至此,猛然醒悟这与我国文辞中的“情意”二字尤其相象。而我国心理学家对于心理结构由“知、情、意三因素构成”的看法,也恰恰佐证了这种理解的正确性。譬如,有的心理学家指出:“情和意在实际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而难于分割的。情由意生,或意由情生。二者是实质相同而形式有异的东西。其实,情也就是意,所以,情和意可以而且应该合在一起,也可以成为情意。”[5](P17)
大陆法系的故意构成要素是认知与意欲,通说观点并没有把意欲要素分解为情绪和意志因素,但是,在对意欲要素的理解上却穿插了对这两种因素的思考。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意欲要素成为流动的、非理性的、难以定义的一种状态。可见,对意欲要素的理解分歧就在于其中包含难以测定和把握的情绪成分。既然意欲可以理解为情意结合而互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刑法理论关于故意概念是由“知、情、意”三个要素构成或认为故意是以“认知、意欲”为构成要素的观点应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意欲要素的表现形式
(一)我国刑法理论对希望和放任的理解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将意欲单纯地理解为“意志因素”甚至等同于“意志因素”成为理论通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才使我国刑法理论讨论故意概念的内涵时,将重心放在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上面。
根据犯罪故意的概念,“所谓犯罪故意,就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6](P109)学者们将故意的意志因素概括为希望和放任两种意志表现形式。
然而,近来时常有学者对于放任是意志因素的性质发出质疑,提出“间接故意没有意志因素,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就在于情感因素上”;甚至明言,“放任其实是一种情感因素,没有独立的意志品格”。[7](P30)应当肯定的是,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情绪因素在间接故意的心理构成中的重要位置,顺应了对故意的心理结构和机制进行探索的学术动向。但是,就此而否定放任的心理机制中包含着意志因素,不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笔者认为,无论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其心理活动都渗透着认识、情感和意志三个元素,这已经被现代心理学通过对人类心理活动的深层机制的科学研究作了证实。正是由于认知、情绪和意志这三个因素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所以,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差异要从三个因素上进行分析,并需要依据意欲的含义将故意概念中的希望和放任因素进行重新审视。
(二)对希望的心理定性
刑法理论中几乎没有人怀疑“希望”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这一基本表述。不过,体察有关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各种解释,那些对“希望”的理解所存在的分歧很快就浮出水面。
譬如,有的学者将希望定义为:“希望就是这样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人对于危害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换言之,这个结果的发生就是犯罪人通过一系列犯罪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8](P165)还有的学者将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特征概括为:在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标是明确的,其一切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危害结果得以顺利成为现实。也正是这种危害结果,刺激着行为人不顾一切地努力实施犯罪行为。其次,和间接故意相比,在直接故意犯罪中,除了自动中止犯罪的情况外,行为人对促使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力。……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9](P315)即使提出只有直接故意才有意志因素,间接故意和过失不存在意志因素的学者,也是从“目的即希望实现的结果,是意志的基本构成内容。缺乏目的的现象不能称作意志”的角度阐释直接故意的意志内容。
上述观点的要旨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具有“目的性、明确性、坚定性、积极性、和顽强性”的特征。然而,究竟什么是“希望”,为什么“希望”表达的是犯罪意志?“希望就是积极的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10](P38)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脱下“希望”一词规范评价的外衣,触摸“希望”的心理特质。
1.“希望”的心理特质
美国心理学家Frank在1968年就指出,希望与信心和勇气等特质相似,它是一种主观与广泛的概念,而且是个体内在的一种感觉,也是达成未来重要目标的动机,换言之,希望是一种动态的心理状态,为个体对未来方向之正向评估或者美好的期待。由于个体拥有正向心理状态之存在,将会影响到个人知觉、行为、判断等行为表现。另一位心理学家表达得更是简明扼要:希望就是表达欲望与需求的一种情感、思想与期待。[11](P205)
分析学者们对于希望所下的定义,足见“希望”是一种能够激发内在潜能的力量,是对未来出现正面结果的一种期待,它在人的一生中是一种可以影响生活态度的正向情绪。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承认我国刑法典中的“希望”一词是以心理学的含义为基础,那么,刑法故意概念的“希望”一词就应该兼备心理学中的希望特质。即,首先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情感因素,是一种欲望表达,是对未来而不是现在和过去的期待。尤其是,在心理学中,“希望”是一个具有正面情绪的褒义词;但它只是一种想象和期待,而且是“一种无力的想象”,没有规范的意义。
2.希望的规范含义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常将希望作为意志因素来解释,赋予它“目的性、明确性、坚定性、积极性和顽强性”的特征。而且与危害结果这一恶物相联系,使它抹上了具有强烈的主观恶性评价的规范色彩。这是否说明刑法上对于希望的解释远远地超过了它应有的内涵呢?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应当说,我国刑法对于“希望的解释”不仅没有超脱它心理学上的含义,而且仍然没有将刑法中的“希望”意蕴全部表达出来。简单地说,“希望”只是意志因素的单纯表白,而不是意欲因素的完整诠释。换言之,希望应该是直接故意意欲要素的代名词。它隐含着意志和情感的双重因素。肩负着情感和意志动态变化的双重使命。其中情绪是意志的内在动力,意志是情绪的外在表现。有了这样的诠释,就不难理解,行为人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实就是内心强烈的冲动,激发了积极的、坚定的意志。而犹疑不决、意志薄弱的人,恰恰就是少了情绪的推动。由此可见,通说所讲的直接故意比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坚定,其真正的原因是直接故意表达的是更为强烈的“我想要”的情绪动力。
(三)放任的心理定性
“放任”一词,从语义上理解,是指听其自然、不加干涉的意思。既然“希望”与“放任”是在故意概念中并列表述的,那么,按照中国的语言逻辑,并列使用的词语起码是具有相同性质的词汇。因此,如果说希望是情感因素,放任也应该具有类似的性质。不可否认,我国学者对于“放任”的讨论,一般都是以把它作为意志因素来进行的。而遗憾的是,在心理学的书籍里,目前尚未找到“放任”一词的对应解释。尽管如此,在我国刑法的故意理论通说中,将“放任”定位于意志因素来进行讨论,全然没有考虑“放任”是否还有其他内涵。当然,我国还是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放任”是一种情感因素,[12](P389)以及将“放任”置身于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中考察等观点。[13](P76)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放任”的心理机制提供了灵感。
在笔者看来,“放任”同“希望”一样,都是故意概念中“意欲”因素的代名词。因此,理解“放任”的含义,当然离不开对情绪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探究。
1.放任是意欲的表现形式
放任是间接故意意欲要素的表现形态,是对包含意志因素和情感因素的心理综合描述。根据间接故意的心理特征,“放任是徘徊在希望得到一种结果却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附属结果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感受”。因此,“放任”的情感因素势必表现为一种模糊的、复杂的、矛盾的状态。当行为人最终作出了行为的意思决定,即意志决定——尽管这种行为决定被我国学者形容为“容忍”、“接受”、“听之任之”、或者“无所谓”,甚至是“不希望”,但是,他们都是“放任”的不同程度的表现形态,而且程度排列恰好成为阶梯状:不希望——无所谓——不拒绝(不加阻止)——容忍——纵容……[14](P34)
值得一提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决定意思与情绪因素共同构成间接故意的意欲要素。虽然行为决定本身没有强弱之分,但是,伴随行为决定做出的情绪因素的强弱与矛盾,会影响做出行为决定过程中的坚定性和明确性,会造成决定前的“犹豫不决”以及决定后的“左右摇摆”或“改弦更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意志薄弱的表现。
总之,当我们把“放任”作为间接故意意欲要素的表现形态,而不仅仅是意志因素看待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对放任的涵义有如此复杂的争论。既然间接故意的意欲要素本身就是难以测定和难以描绘的,那么,放任作为包含意志因素和情感因素的心理动态的描述,就是尚待测定的一个模糊心理区域。
2.“放任的意志”有多种表现形式
我国学者提出故意的意志类型除了希望意志与放任意志之外,还有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容忍意志,即“明知必然性而决定让其发生的意志状态”。[15](P96)学者的这一主张试图解决“明知必然性却放任发生”在解释上的尴尬,但另一方面却在启发我们: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否只表现为放任意志?或者说,是否只有一种意志类型的表现?既然可以主张容忍意志,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纵容意志”、“不希望意志”、“无所谓意志”……?
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借助意欲要素这一概念。间接故意的意欲要素同样包含内在欲望和实现欲望两层内容。实现欲望的决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志的表现。但是,这种意志决定深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不希望”、“无所谓”、“容忍”、“纵容”还是“接受”,他们都不是单一的意志因素的涵义,而是夹杂着情感因素的意欲要素。如果结合间接故意的具有模糊性、波动性特点的情绪要素来分析,就可以看出,以上所有学者对于放任内涵的解释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事实上,在希望得到一种结果却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并不期待的附属结果的时候,如同面对着同时诞生的“善恶孪生姊妹”,人的感情肯定是复杂的、矛盾的、模糊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故意做的事情完全可能是他不喜欢做的,但他更不喜欢他不该做事情的后果。”[16](P40)间接故意的意志就是指不管行为人的情绪状态、喜恶如何,最终还是作出了行为的意志决定,即决定发动和支配行为的实施。这就是间接故意的意志特点。由于人的感情是复杂的、矛盾的,因此,意志在复杂多样的情绪包裹之下,表现出了不同的样态。譬如,我们来分析经典的案例:投毒杀妻害子一案。行为人意图杀死他的妻子,明知道他的儿子也可能吃这碗饭,权衡再三后,仍然在饭碗里投放了毒药,放任他儿子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按照一般的推理,行为人内心的想法不外乎这样几种:(1)真正不希望儿子死,但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2)死不死都无所谓,反正没有娘的孩子活着也可怜;(3)为了杀妻解恨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计后果);(4)儿子平时也烦我,这次如果被毒死了,“活该”(纵容);(5)说不定儿子命大,死不了。以上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解释为“放任”,但它们对“放任”程度的反映又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希望和放任之间增加容忍的意志状态,而只要承认放任本身就是一个涵盖多种心理反应的心理要素,即:放任原本就可以体现多种意志类型。
3.放任意志具有独立性和不坚定性
我国学者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放任’不是一种独立的意志形式,任何放任的心理都不是毫无情由地自发产生的,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希望意志形成的。”[17](P31)笔者对此结论的态度是肯定、否定参半。放任不是一种独立的意志形式,心理学中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推论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不具有独立性。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不能把刑法意义上的放任意志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放任意志相混淆,也不能把放任意志等同于或完全依附于希望的意志。”[18](P56)由于间接故意的放任是徘徊在为了追求一种结果却不得不容忍(接受)另外一个相伴而生的附属结果的心理态度,容忍和接受的态度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但这并不说明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不具备确定性和自主性。任何一个决定的做出都是行为人在“我要努力来满足这种愿望”的利益进取心驱使下做出的“趋利避害或两害权衡取其轻”的结果,是最终“思想斗争”的结果。因此,间接故意的放任意志或许有些无奈,但终归是行为人自主性的表现。或许有些学者会质疑间接故意意志的“果断性”和“目标性”表现何在。我们认为,意志因素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一是意志努力,二是意志态度,三是意志程度。我们研究意志因素不能把它放入真空试管中分析,也不能脱离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对它的影响。以动态的心理机制来透视意志因素,就会理解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目标模糊、犹豫不决”的情形存在。而这并不是与“目标明确、坚定果断”质的区别,仅是程度不同的差异而已。这也是我们在探讨问题时,摈除非此即彼、黑白界限分明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思考尝试。
三、意欲的落差决定了主观恶性的大小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希望与放任在其意志程度上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希望的犯意明显而坚定,放任的犯意模糊而随意。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主观恶性的差别。[19](P165)那么,直接故意比间接故意主观恶性要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如果将“希望”和“放任”分别定位于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意欲要素的表现形态,那么,对于主观恶性的比较就有了更为直观的标准。
(一)意欲是故意被责难的要素
对于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的主观方面,应该受到责难的是什么?当然是经过刑法规范评价的罪过。而罪过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的意志与刑法禁令或命令间的对立,即行为人没有根据刑法规范的要求来运用自己的意志。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的判决要旨回答得简明扼要:“故意之内涵,应包括认识与意欲两要件。犯罪意欲之心理状态,较之单纯的事实认识,于犯罪故意更表现其恶性,而应受非难。”[3](P10)虽然表明了意欲要素应受责难的态度,但并没有说明意欲成为刑法规范谴责对象的原因。而许玉秀教授则直击要害:“认知靠理性,行动靠情绪,意欲要素就是情绪要素,人不因认知而受责难,而因情绪决定而受责难。所以故意的可责难性在于有意欲,有犯罪的意欲。……意欲支配行动,作出了触犯法律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体现了行为人的法敌对意识和对法的背离。这也可以说是处罚意欲要素的根据。”[20](P11)意大利的刑法学者也有相同的意见:“就故意而言,罪过表现为它本不应追求的东西……”[21](P185-186)
在间接故意中,无论行为人的意欲要素表现为“放任”、“容忍”、“接受”或“同意”等,都是描述行为人在追求客观结果时的一种消极心理状态。确切地讲,介于积极追求和反对之间的一种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本身包含了一种不顾危害后果发生,执意实施或不实施一定行为的内容。行为人既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那么,只要停止实施预定行为,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但是,行为人为了追求另一目的的结果,执意实施预定行为。具有法律期待做出合法选择的可能性,但行为人为了一个自己追求的“目的结果”,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却一意孤行,做出了决意实施有害于国家、社会或他人利益的行为决定。虽然不是对社会强烈的敌视,但是,这种对于法律秩序破坏或漠视的心理足以遭到谴责。
(二)情感因素对故意强度的影响
意大利刑法最早的理论认为,故意的强度取决于主体的情感态度:犯罪时,主体实施犯罪时越冷静,越没有感情,故意的强度就越高。另有一种理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故意的强度决定于犯罪决意的持续时间,因为这能表明行为人背离法律规定的程度。按照这种观点,故意的强度可以分为三级:突发故意,成熟故意,预谋故意。[21](P213)显然,意大利刑法理论突出强调了故意的强度取决于主体的情感态度;情感的强弱取决于感情的强弱(激动与平缓)或犯罪决意持续的时间。人的情绪是人的本能,除非有表演天赋,否则是最为直观的标尺。从表面上看,强调“犯罪时,主体实施犯罪时越冷静,越没有感情,故意的强度就越高”。
不过,与国外刑法理论对于情感因素的重视程度来比较,我国学者在分析故意的主观恶性时,对情感因素的定位显然没有达到重要的程度。如有的学者声称:“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决定着主观恶性的有无,而情感因素只决定主观恶性的大小。”对于学者的这一论述,我们赞成与反对参半。赞成的部分在于,论者肯定了情感因素在罪过心理中的地位。不能认同的是,情感因素只决定主观恶性的大小,其法律意义与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相比较,显然是等而下之。理由如下:意欲要素包含情绪因素。故意之内涵,应包括认识与意欲两要件。而意欲要素包含“欲望的确定”和“行为的决定”,是情绪和意志的共同体现。我国的心理学家所主张的“情和意在实际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而难于分割的。情由意生,或意由情生。二者是实质相同而形式有异的东西”,恰好是意欲要素的最佳注解。如此看来,情绪因素的作用和地位与意志因素应该平分秋色。
依据本文作者的主张,构成意欲的要素有二:一是情绪因素,二是意志因素。而国内外刑法理论都认为,意志因素是应当受谴责的因素,而情绪却不能作为被谴责的对象。既然意欲包含情绪和意志两个因素,为什么责难意志因素而不否定情绪因素呢?大概除了“情绪因素是不稳定也不易描述的一种心理状态,法律对于这样波动的情形无能为力”的技术原因之外,还因为喜怒哀乐皆为人之常情。情绪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自由。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明文立法对情绪进行法律制裁。当然,法律却对于因激烈情绪而引发的行为寄予了无期待可能性的评价,将其作为刑事责任减轻的理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行为的实施,是意欲在起支配作用,故应该遭受谴责的是意欲要素。但是,情绪和意志共同构成意欲,情绪是内在的动力,能够促使意志的形成和影响意志的强弱,因此,情绪因素难逃其咎。既然我们很难再把情绪要素和意志要素剥离开来,情绪要素的作用就不可忽视。因此,即使法律没有对于情绪要素进行规范评价,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于情绪因素作用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无须回避将情绪因素视为可以斟酌量刑的重要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