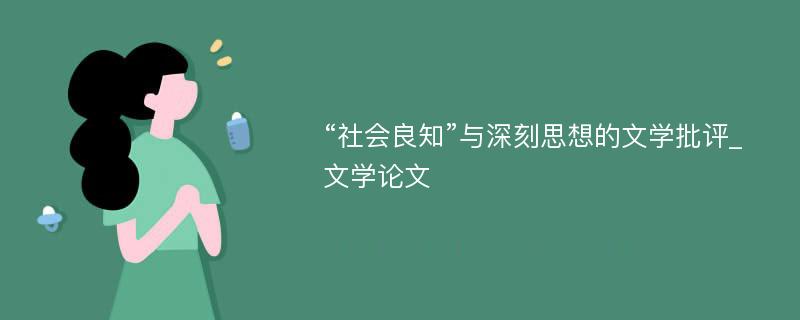
有“社会良知”和深邃思想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良知论文,深邃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哲学思想和历史知识的积累作为批评家主体的方法;没有“社会良知”作为批评价值观的基础和底线,我们的批评家只能是爬行的软体动物,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只能永远徘徊在低水平肤浅的语言循环之中。这个盘桓在我们文学批评上空的魔咒,这个几十年不被批评界所重视的批评“死穴”,应该得到学理性的梳理了。我们呼唤的是既有“社会良知”,又有深度哲学思想的批评家出现。唯此,我们的批评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
几十年来,我们不乏那种有“社会良知”的批评家,可惜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储备较少,缺乏深度哲学思考文学现象的写作者。
在对待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失语”,而是在反反复复地套用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自以为新鲜出炉的西方新理论,来套中国的作家作品。这种可悲的现象恰恰证明的是我们缺乏原创的理论,我们不会进行独立性的思考。
无疑,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语言与思想的表达,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具有艺术匠心的技艺,那么,思想的释放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的内在力量,不要怪中国20世纪以来没有像俄罗斯文学那样有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乃至“苏联时期”的巨匠产生,因为中国新文学缺乏像鲁迅那样的有思想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之所以越来越平庸,除了外在的“工农兵方向”制度限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品,尤其是代表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最高文学艺术水平的长篇巨制,最缺少的就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哲学提升。且不说西方著名的大作家如雨果、左拉、福楼拜那样在反映动荡社会时的那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考,即便是俄罗斯大作家,几乎无一不是在深深的哲学思考中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即使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巨著中流露出的对农奴制度的同情与宽宥,我们是不能苟同的,但是他用他的思考附着在语言的技巧之上完成了他自己的哲学命题,使其作品伟大而流芳百世。在俄罗斯作家画廊里(包括苏联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长长排列的面影: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柯罗连科、布宁、库普林、索罗维约夫、巴尔蒙特、安年斯基、布洛克、伊万诺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作品首先是以其伟大的主题思想征服了一个时代。当然,我不是强调语言与文学技巧的不重要,而是说,取得语言和技巧比较容易,而获取思想的腾飞却是相对比较难的,除了大量的阅读枯燥的哲学与思想史著作外,还得面对自己的时代做出苦苦的思考,从而确定自己思想价值的坐标,然后再将其融化在活色生香的人物描写之中。所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悬浮在社会生活之上、之外,只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投影而已。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当今中国,我宁愿阅读技巧二三流,思想却是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阅读那些技巧一二流,而思想末流或全无思想的作家作品。当然,既有高超的语言技巧,又有深邃思想的作品才能算是最好的作品,在当今中国文坛,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找不到“巨匠”,可以找到“匠人”,但是,我宁愿去寻找比“巨匠”矮一截的文学思想者的作品。
别林斯基的批评从来就是将其社会的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置于第一位的,是寻求真理的美学,而非有些人阐释的那样,别林斯基是从某种纯粹美学的分析角度去解析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倘若去概括别林斯基美学批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将先进的思想与哲学观念注入对俄罗斯文学的批评之中,以此来聚集一批知识分子阶层,推动俄国的民主革命。其次才是他用艺术的眼光去分析具体作家作品,当然,这些分析无疑都纳入其对社会思潮的解剖当中。
作为19世纪俄国西方派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无疑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这个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天才批评家,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大批代表性作家作品,尤其是他以十二篇评论文章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也许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文学巨匠不太喜欢他那样言辞激烈的批评家,也许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斯拉夫民粹主义者也不喜欢别林斯基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老托尔斯泰也不得不在他的身后承认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贡献。我以为,别林斯基一生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的批评成为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柱——那种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德力量和批判风骨。他没有私敌,但是谁要推翻他的信仰,谁要试图颠覆真理和正义,就必定是他的公敌!其实,他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人的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高度的评价。然而,如果即便是他欣赏和所热爱的作家触犯了文学道德的底线,他就会毫不留情地鞭挞之。作为早期就被别林斯基从重重辱骂中竖起的《死魂灵》的文学旗帜,果戈理受到了别林斯基最大的护佑和褒扬,他们曾经是同一文学壕堑中的战友,但是,当果戈理歌颂沙皇独裁专制与教会时,别林斯基则痛斥其出卖灵魂的行径,他临死前所写的那篇最犀利的檄文《致果戈理》,是其只认真理而毫不顾及友情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典范之作。“是的,我爱你,就像一个与自己国家以血相亲的人,是全副热情爱它的希望、它的光荣、它的尊严,以及带领它走上意识、发展与进步之途的伟大领导者。……你,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扬无知的叛徒、捍卫蒙昧主义和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瞧瞧你的立足之地罢,你正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这我能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皮鞭和牢狱、向来对专制独裁五体投地。……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按:指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粹》)。”
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陆对文学批评的关注和热衷,也随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普遍的诟病和不满,文学批评似乎成为中国大陆风箱中的老鼠,不仅被学界指责,同时也被创作界挞伐,甚至也被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所批评。但是,文学批评仍然在以自己的生存方式而顽强地活着,因为文学批评业已成为中国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及其各省下属机构从事现当代文学的职业,没有这张皮,就意味着许多人将没有了饭碗。在这样的体制下,所产生出来的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必然会有三种结果:
一曰学院派批评。这种批评无疑是涵盖了所有中国大陆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文学工作者,他们在体制压迫下的治学方法和出路无非有三:一是经院式的,用大量堆砌的史料和他人理论作为文章的骨架,往往证明的却是一个意义不大的小问题,此乃自慰为所谓乾嘉学派传统;二是西方派批评,从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量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成为这种文学批评的唯一资源,此种批评家往往是通过译著而借助一些关键词来构建自己的创新理论体系,从而去将一顶顶编织的帽子一厢情愿地套在一个个中国作家的头上,而中国作家都是非常乐意地去接受这样的“礼帽”,且不管这顶帽子合适与否,了胜于无,尽管作家们有时态度矜持或暧昧;三是技术型批评,或曰工具型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沉潜在对作家作品的所谓微观的分析和批评之中,像一个工匠那样去拆解一个个机器零件那样,去有条不紊、津津有味地解剖或肢解着作品而乐此不疲,他们往往在放大镜下看作家作品,难免陷入一种机械主义的怪圈之中;四是有一批尚无多少知识积累,就急于去在体制的规约下挣“工分”、评职称的年轻人,他们的文学批评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价值理念,往往杜撰和编织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话语,使一些人觉得似乎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理论创新。
二曰体制派批评。此批评的发源可追溯到苏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来的文学批评,在中国,这种批评的基础和资源可能就要追溯到上一个世纪的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配合政治的需要而进行文学批评,这种仿苏式的体制派批评其实在40年代已经定格,做专政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使他们主导着媒体和舆论的导向,往往是主流文化思潮具有权威性的代言,虽然网络时代在无情地冲击和动摇着他们的统治性地位,虽然人们不屑于这样的官样文章,就连这些批评家本人也无法自信其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行为批评”仍然盛行于世,且随着体制控制松紧而收放自如。
三曰工农兵式的批评。这种批评虽早已落伍,且被世人所诟病,但是它分布在各种主流媒体的报端,仍然有着宣传鼓动的教化作用,其标语口号式的文风虽不忍卒读,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于这样一种非文学的批评,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其蝇营狗苟之道也是不可小觑的现象。
这三种批评群体,最为庞大的群体应该是第一和第二种类型中的一大批以此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此当做谋生的饭碗,但是真正有思想的批评家却是少之又少,其价值观念的混乱就更成为了他们思考问题深刻性的阻碍。正如艾德华·萨依德所言:“处于那种专业位置,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相当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而这种精神在我看来却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贡献。换言之,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公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境下,摒弃个人的道德感、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这些大诱惑使人难以被信任。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这些诱惑,而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全都如此。没有人能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也做不到。”①既然这是全世界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的一个怪圈,那么,尽量能够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品格,无疑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确立的批评目标,打破萨义德的魔咒,应该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使然!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不是想做什么,而是能够做什么。由此我想到的是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5年写下的一篇文章《好的坏书》中批评了那种逃避现实的文学作品,虽然,有些作家在艺术技巧上是一流的,但是,他们却是不能长留与文学史的显著位置的,这就是批评家独特的眼光:“我担保《汤姆叔叔的小屋》将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乔治·莫尔的全部作品流传得更久远,尽管我不知道,才严格的文学标准判断,《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底好在哪里。”②作为一个作家兼思想家的写作者,奥威尔的这一段话既是引起中国批评家,也是引起中国作家进行深刻思考的箴言。
除了以上传统的批评群体外,当下还有一股不可小视的、且在茁壮成长的批评力量——网络派批评。这是新世纪中国大陆随着科技文化和商业文化而崛起的批评群体,虽然其文学批评的质量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是,它无疑是弥补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许多缺位,甚至于是填补了文学批评的巨大空洞。它已经俨然是迥异于前三种批评的一种新的批评模式,其鲜活的形式和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关注,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给文学艺术本身带来的本质戕害。
综上,我们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无疑是劣大于优的,其弊端的根本症结在哪里?从客观上来说,体制的约束形成的弊端不是一时就可以克服的,从主观上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缺乏的就是勇气、责任和正义感——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共同的学术和学理的认知,就不可能建立起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文学批评体系。
①艾德华·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收于王德威主编“麦田人文丛书”,台湾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
②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收于周宪主编“名家文学讲坛”,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