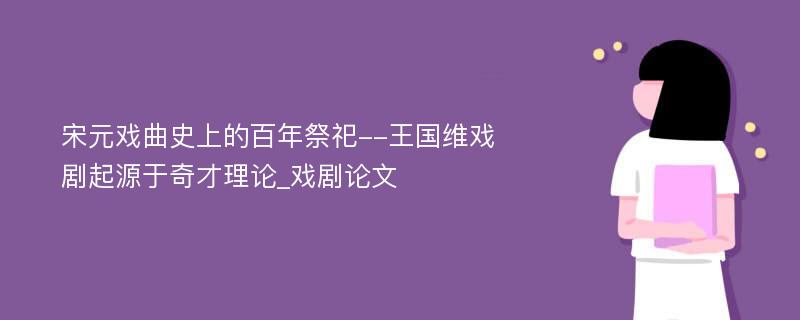
《宋元戏曲史》百年祭——王国维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说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元论文,戏曲论文,王国维论文,中国戏剧论文,巫觋说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0-0125-13 1913年4月1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出版了第九卷第十号,“宋元戏曲史”豁然出现在封面的“本号要目”上,正文署名“海宁王国维”。①对于这一划时代的学术经典,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然而王国维是人不是神,一百年过去了,《宋元戏曲史》可以被超越,也应当被超越。 总的来看,1949年以前,静安先生登高一呼,“百万的后学”(郭沫若语)踵继其后,鲜有对其质疑或商榷者。②到30年代前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大体形成了以王国维为楷模的文献考据派、以吴梅为领军人物的戏曲格律研究群体和以齐如山为代表的与舞台实践密切结合的研究流派。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戏曲研究从沉寂下僚的“小道”、“末技”迅速成长为一门显学。1949年以后,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观念的更新、理论的提升以及其他原因,《宋元戏曲史》越来越多地遭到质疑和批评。其中,任中敏在50年代和80年代两度发起对《宋元戏曲史》的批评,观点甚尖锐,言辞甚激烈。③自改革开放迄今的三十余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有一些人对《宋元戏曲史》中的某些结论和王国维的其他戏曲研究成果提出商榷或批评。学术研究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戏剧史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博弈中不断被重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批评,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细读这些批评文章之后,又不免感到一丝忧虑。这不仅在于某些批评者对于王氏百年前的成果过于苛求,而且在于他们自己或由于学养的不足、观念的差异等原因造成对《宋元戏曲史》误读或不解,匆忙之间却指责王国维“误导”了后世读者。其结果,倒是他们自己的判断有可能混淆视听,给本来已经形成的共识添上新的混乱。本人不揣浅陋,在《宋元戏曲史》发表百年之际,试对其中国戏剧起源说进行分析与阐发,并兼与近年来《宋元戏曲史》的批评者商榷,以表达对《宋元戏曲史》百年诞辰的纪念。 一、王国维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说 《宋元戏曲史》的思路很清楚,中国戏剧从起源到形成、成熟的大体演进过程是:巫觋、歌舞(起源)——俳优——以歌舞演故事的雏形戏剧(形成)——宋元戏曲(成熟)。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其戏剧起源说。 《宋元戏曲史》最初提出中国戏剧源于巫觋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看该书的第一句话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④就不难体会出作者对这一判断所持的审慎态度。但紧接着,作者即开始“小心的求证”。他举出上古巫风盛行的书证,并对巫觋与歌舞、戏剧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作者首先论证了巫和舞的关系:“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这就是说,在王氏看来,上古巫觋是用歌舞降神的人,“巫”和“舞”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那么,巫术与歌舞,究竟何者在先呢?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王氏的意思是,早期的歌舞与巫术是混沌一体的,后来歌舞从中分化出去承担娱人功能,故可以说歌舞源于巫和巫术。《宋元戏曲史》引《汉书·地理志》并分析云: 《汉书·地理志》言:“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邱之下,无冬无夏,治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郑氏《诗谱》亦云。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戒。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余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贡观于蜡,而曰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非过言也。 今存《诗经·陈风》共十篇,《宋元戏曲史》所引证者为《宛丘》、《东门之枌》。按《汉书·地理志》,陈国在淮阳(今属河南省周口市),本为太吴之墟,“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颜师古注曰:“鹭鸟之羽以为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子仲,陈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亦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娱神也。”[1]按照颜注,以上二诗中婆娑起舞的女子都是以舞娱神的女巫。这些装扮起来的女巫或手中挥舞着以鹭鸟之羽做成的旗子,或将鹭羽插在地上做装饰。30年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对巫、舞、戏三者的关系给予了补充论证,他指出:“巫”、“舞”本一字,甲骨文中“舞”字皆为求雨之舞即巫术,故“歌舞起源于巫术”,“古代倡优戏剧歌舞,一皆发源于巫”。[2] 苏轼《东坡林志》卷二云:“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3]此即上文所引《宋元戏曲史》中“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的出处。按《礼记·郊特牲》,周时每岁十二月天子要举行蜡祭,祭祀与农业有关的八种神祇,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田畯)、邮表畷(界牌神)、猫虎、坊(堤防)、水庸(水渠)、昆虫。主祭者要“葛带榛杖”,即腰缠葛麻带,手执榛木杖;还要头戴草笠。⑤按苏轼的说法,这就是“戏之道”。此外,为天子掌管鸟兽的“大罗氏”还要招致“鹿与女”,把它们当做客人予以诏告。苏轼的推测是,既然“祭必有尸”,那么猫、虎、鹿、女是动物或者是人,在祭祀它们时谁来做“尸”呢?一定是倡优。 何谓“尸”?《说文》:“尸,陈也,象卧之形。”段注:“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据此,尸的本义是陈列,而被陈列的是古代祭祀时装扮死者受祭的人。在金文中,“尸”字就像一个屈膝的人。因其形状像卧倒的尸体,后来就用作尸体之尸。其后尸祭制度渐渐消失,尸的本义也就较少有人知道了。“象神”者,就是装扮神。 苏轼能够在一千年前意识到扮演在戏剧中的作用,意识到戏剧与祭祀的关系,提出“戏礼”和“戏之道”的概念,堪称卓识。但应指出两点:其一,苏轼推断扮演猫虎之尸者为“倡优”是不准确的。正如王国维《录曲余谈》所云:“其言八蜡为‘戏礼’甚当,唯不必倡优为之耳。”[4]按照《宋元戏曲史》的推断,“尸”其实就是巫,“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远在其后”,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其二,关于蜡祭是否祭祀猫虎,以及祭祀时是否用“尸”做猫虎的替代品,苏轼以后颇有争议。例如宋罗愿《尔雅翼》卷二十一“猫”条云:“祭不宜及猫虎。祭不及猫虎,盖以物享之,则不为‘戏礼’矣。”[5]明周洪谟《疑辨綠》卷上“祭用尸”条则谓:“古者祭宗庙则有尸,其余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类盖无尸也……眉山苏氏谓祭猫有猫之尸,祭虎有虎之尸,而或讥其近于徘优。使祭天地百神而为之尸,不亦几于渎乎,善哉!”[6]照罗愿等人的说法,蜡祭的对象是猫虎“所主之神”而并非动物本身。退一步说,祭虽有尸,也只能充当人的替身,而并不能为猫、虎充当替身。这样,苏轼的“戏礼”说便受到挑战。 关于祭祀是否用尸,早在春秋末已成问题。《礼记》:“曾子问曰:‘祭必有尸乎?若厌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祭殇必厌,盖弗成也。祭成丧而无尸,是殇之也。’”[7]故知除祭祀未成年人之外,祭必有尸。那么,人以外的山川万物是否用尸祭呢?《诗·大雅·凫鹥》全诗五章,其首章云:“凫鹥在泾,公尸来燕来宁。尔酒既清,尔肴既馨。公尸燕饮,福禄来成。”以下各章皆含“公尸燕饮”句,不赘引。按照郑玄的解释,《凫鹥》首章祭宗庙,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8]如此,则周代各类神祀皆有尸。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载,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同知太常礼院陈诂上言: 每年季冬,蜡百神于坛。按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礼文乃载一百八十二位,其五方田畯、五方邮表畷十位,不载祝文。窃恐开元以来,年祀浸远,有司失传。又郊祀正辞录并司天监神位图,蜡祭猫虎,皆以虎为於菟,盖初避唐讳。请自今复改作於菟为虎,及以五方田畯、五方邮表畷载之祝文。[9] 据《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一引《八闽通志》,陈诂为宋初人,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据此,宋初“蜡祭猫虎”是确凿无疑的,但看起来并不用尸,而以“神位图”代之。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批评明王可大所撰《国宪家猷》“谓人鬼设尸之外,天神地祇之不见于经者”云: 今考《周礼》大祝云,凡大禋祀,则执明水火而号祝,隋衅逆牲逆尸。注云:“禋祀,祭天神也。”又《节服氏》云:“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尚书大传》“维十有三祀,帝乃称王,而入唐郊,犹以丹朱为尸”。《国语》“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周礼·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春秋传》“周公祀太山,召公为尸”。何谓天神、地祇用尸不见于经传耶?[10]即使如此,王国维对于祭祀祖先以外的神祇是否用“尸”仍持谨慎态度,《宋元戏曲史》云: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 可见,王国维引用并认同苏轼的说法,称其所云“非过言也”,当是建立在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之后的一种不失分寸的肯定。 值得提出的是,在诸多问题上与王国维“唱对台戏”的任中敏,对于《宋元戏曲史》提出的戏剧源头之一的蜡祭,却给予了异常的关注与认同。《唐戏弄》用整整20页篇幅,详尽分析了蜡祭的戏剧性。任氏推测,蜡祭中不但要扮演猫、虎,还可能有扮演田鼠和野猪者,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角斗,其实就是角抵表演,这恰与“戯”与“劇”二字的本义相合;蜡祭中另一幕重场戏“置鹿与女”,鹿亦由人来扮演。[11] 今天看来,《宋元戏曲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巫术中已存戏剧萌芽的论述。《宋元戏曲史》先引王逸《楚辞章句》,认同楚风好巫,屈原《九歌》乃在俗人歌辞基础上改作的说法。接着引《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诗·楚茨》中的诗句,并以王逸《章句》、《说文》、《毛传》、《郑笺》等为佐证,指出《楚辞》中的“灵”、“灵保”,《诗经》中的“神保”,都是巫,也都是“尸之异名”。在祭祀时,巫装扮成神的形象接受祭祀,飨用祭品。《宋元戏曲史》说:“《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凭)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当代原始文化研究学者朱狄在引述了王国维的上述论证过程后称赞道:“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比较深刻的。”[12] 关于“方相氏驱疫”之傩礼,《宋元戏曲史》仅说其为上古巫风之“余习”。《古剧脚色考》论之稍详,谓:“《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似已为面具之始。”[13]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傩戏的研究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此是后话。 二、王国维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学术背景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说,《宋元戏曲史》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可以说,王氏关于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的推论,有着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在欧美诞生。这门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到未开化民族或部族进行实地调查,来了解人类的童年社会。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学者们取得了丰硕成果。诸如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1894)、弗雷泽的《金枝》(1900)、列维·布留尔的《土著人如何思维》(1910)、施密特的《神的观念的起源》(1912)、哈里森的《古代艺术与仪式》(1913)、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31)等著作先后问世,为当代人了解初民蒙昧时期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尽管上述学者的学术见解不尽相同并因此分成了不同的流派,但他们在巫术和艺术的关系的认识上却相当一致,即人类早期的艺术和巫术是混沌一体的。正如朱狄所说,在当时,“最占优势的艺术起源理论就是巫术论”。[14]或许也可以说,揭示出巫术祭祀仪式与艺术的关系,是百年前欧美人文学科对世界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王国维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说,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中产生的。 提出人类童年“万物有灵”的著名英国“人类学家之父”爱德华·泰勒(Tylor,Edward Bernatt,1832—1917)指出: 宗教仪式在理论上分为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在实际上又是相互合在一起的。它们一部分具有重要造型的或象征的意义,是宗教思想的戏剧性表现方式或宗教的哑剧语言;一部分则是跟灵魂交际的手段或影响它们的手段。[15] 这里所说的宗教仪式的“两部分”,分别指的是外在仪式和内心崇拜。在泰勒看来,宗教的内在思想学说和外在表现形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外在仪式可以用戏剧的形式(如哑剧)予以呈现,同时这种形式也蕴含了宗教思想。 著名德国艺术史家、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考察了大量原始狩猎部族的艺术形式,指出艺术最初的目的不是出于审美和娱乐,而是出于实用目的,各狩猎部落的艺术“显出极度的一致性”,[16]“在狩猎民族间最有力的社会影响是跳舞”,[17]代表人类情感的摹拟式舞蹈“实为产生戏剧的雏形,因为从历史的演进的观点看来,戏剧实在是舞蹈的一种分体”,而“(舞蹈)常常利用宗教的仪式”。[18]这就不难明白,以研究古代戏剧为内容的《宋元戏曲史》,何以开卷提出的不是戏剧起源而是歌舞起源的问题。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1854—1941)的巨著《金枝》,列举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巫术行为,其中相当多的巫术仪式都具备戏剧扮演因素。该书用大量材料说明:如果说仪式在形式上是戏剧的,那么它在本质上则是巫术的;人们依照交感巫术的原理,企图利用戏剧性的仪式来保证春天里植物的新生和动物以及人本身的繁殖。通过弗雷泽对巫术仪式与戏剧表演的对比,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戏剧最初是一种巫术仪式,后来与巫术仪式分道扬镳。他说: 在北美爱斯基摩人当中,在欧洲已蜕化为单纯戏剧表演的冬夏代表之间的斗争,却仍然是一种巫术仪式。[19] 可见,欧洲的“单纯戏剧表演”,实际上是从类似于北美爱斯基摩人中尚存的巫术仪式中“蜕化”而成的。 如果说泰勒、弗雷泽等人的主要着眼点还是在巫术或宗教仪式上的话,那么深受弗雷泽影响的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1850—1928),则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戏剧与仪式关系的研究上。哈里森指出,戏剧与仪式的模仿行为完全一样,但目的变了。以古希腊而言,原来属于全民参与的祭祀活动,由于观众的出现,使大部分人成了旁观者,而另一部分人在表演,于是祭祀演变成了戏剧。她说: 传统告诉我们,在雅典,艺术脱胎于仪式,戏剧源自于行事,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剧场、观众席、乐池或者舞场的出现,就是这种转变的生动见证……几乎所有的戏剧艺术都经历过仪式的阶段。[20] 也就是说,在哈里森看来,由于巫术仪式和戏剧表演实际上都是在模仿,所以一旦巫术的实用目的让位于娱乐和审美目的,戏剧便从仪式中脱胎而出。 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 1884—1942)非常重视情感体验,他认为宗教和艺术都依赖于人们的情感经验,这是后者起源于前者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在巫术和宗教两种仪式中,人们都必须诉诸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方法,以造成强烈的情感经验……艺术的创造,正是产生这种强烈的情感经验的文化活动……古典的及近代的戏剧,基督教的神剧,以及东方的戏剧艺术,都可能是起源于这种早期的戏剧化的宗教仪式。”[21] 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影响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学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人物乔治·卢卡契写于1963年的《审美特性》一书反复强调:“产生模仿艺术的最初冲动只是由巫术操演活动中产生的”,“艺术与巫术(宗教)之间最基本的共同原理是,它们都具有拟人化的特征”。[22]前苏联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德·莫·乌格里诺维奇也指出: 在仪式中,通过用面具化妆的同伴塑造出来的各种动物祖先的神话形象“充当”这些祖先,跟这些祖先等同起来。于是,在仪式中就真正把神话现实化了。这一神话—仪式综合体必然包摄审美的方面,因为把神话改编成脚本在仪式中排演,这本身就是多种艺术连戏剧在内的萌芽。[23] 日本的戏剧理论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乃至研究方法。限于篇幅,此处只举一例。受德国戏剧学家尤里乌斯·巴普的影响,日本戏剧理论家河竹登志夫(1924—)指出,原始舞蹈中的所谓演员,“就是靠‘演技’即歌和感情姿态来‘招请’神明的人”。人们把歌舞者处于“忘我状态”的“神灵附体”的行为称为“共鸣巫术”,“正是在这种虔诚的无意识的演剧境况之中,才潜藏着戏剧根源的原始体验”。[24] 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王国维曾经阅读过上述西方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比《宋元戏曲史》晚出的著作,他不可能读过。但众所周知,在1907年王氏开始戏曲研究之前,曾埋头研究过西方哲学,而主要致力于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值得提出的有两点:一、他在为亚里斯多德写的小传中专门提到过亚氏的戏剧理论著作《诗学》;[25]二、为王氏所心仪的西方学者尼采写过一部《悲剧的诞生》。虽然尼采用诗一般的语言反复强调“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但他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祀仪式。王国维是从世界文化背景来考察中国文学和中国戏剧的。在他看来,学无新旧之分、中西之分、有用无用之分:“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26]他在《三十自序》中说,“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27]就显然是以西方戏剧为参照作出的判断。因此王氏关于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的判断,也可以看做是对国际学术潮流的一种回应。 同时,王氏关于戏剧起源于巫觋的观念,也与我国自宋迄清的研究成果有着更为直接的继承关系。除《宋元戏曲史》所引《东坡志林》外,发表同类见解者可谓不绝如缕。例如朱熹就说过“傩虽古礼而近于戏”。[28]明代杨慎《丹铅总録》卷九“女乐本于巫觋”条指出“女乐之兴,本于巫觋”。[29]杨慎这一论述被明顾起元《说略》、清沈自南《艺林汇考》、嵇璜辑《续文献通考》所引述,影响颇巨。清王闿运《湘绮楼全集》诗集卷十一《涪水道中感春寄谢刘侍郎昆三首有序》云: 优人演段者,盖始于伊耆时罗氏鹿女,其后尤盛于东周,至汉代元会,为百戏之一,明人因遂直谓为戏。[30] 此段论述盖附和《东坡志林》,后被《清稗类钞》“戏剧类”引。清杨静亭《都门纪略·词场门序》说:“尝考《周礼》方相氏所掌之傩焉。傩行于乡人,圣人为之‘朝服祚阶’,故《鲁论集注》内称‘傩近于戏’。盖以涂面狂歌,藉以驱疫,虽非演戏,而戏即肇端于傩与歌斯二者。”[31]近人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起首即说:“戏曲肇自古之乡傩”。[32] 在近代学者中,早于王国维而力主戏剧起源于巫者,当推刘师培。刘氏也是一位学贯中西、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在艺术与巫术关系方面发表的文章有《古乐原始论》、《广释“颂”》、《〈说文〉“巫以舞降神”释》、《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论文学出于宗教》等,而以1907年发表的《舞法起于祀神考》为集大成之作。 刘氏在1904年发表的《原戏》一文中主张戏曲源于上古之歌舞,他认为“夏乐有九,至周犹存,宗礼、宾礼皆用之。盖以歌节舞,复以舞节音,犹今日戏曲以乐器与歌者、舞者相应也”。他还说:“考之《尚书大传》,则古制乐歌,皆假设宾主,而武王克殷,亦杂演夏廷故事,非即戏曲装扮人物之始乎?”[33]然而三年之后,他发表的《舞法起于祀神考》,则把歌舞与戏曲的源头进一步追溯到巫觋。他先引《说文》对“巫”字的解释,指出“巫象舞形”,“乐官与巫联职”,然后列举大量先秦史料,如《吕氏春秋》、《周礼》、《墨子》、《九歌》、《山海经》、《左传》、《诗经》并汉代人对先秦文献的注解,以及《论衡》等为佐证,说明“乐舞之职古代专属于巫”,夏商周“三代以前之乐舞,无一不原于祭神”。⑥ 相比较而言,王、刘二人均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巫术,所用的论证方法亦均为文献考据;但王偏重于对上古蜡祭、九歌中扮演因素的剖析,而刘则对三代乐舞如韶乐、九歌、雩舞、皇舞、傩舞以及《诗经》三颂中巫、舞、剧三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故人舞乐以降神,故《三颂》均多祀神之作。”“盖《诗》之有《颂》,所以形容古人之往迹而记之者也。《颂》列为舞,所以本歌诗所言之事而演之者也,是犹传奇,备志往迹而复演之为剧也。”他还特意举出《逸周书·世俘解》和《周礼·方相氏》进行分析: 巫官所掌,不独舞雩之事已也。又《佚(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克殷,谒祀籥人,奏崇禹王,生开三终。此亦乐舞之形容古事者也,与后世演剧相同。然奏者必以籥人,且奏于克殷谒祀之日,是犹后世之演剧酬神也。又《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事(时)傩。”亦古代巫舞之遗风。今观中邦各直省,其僻壤遐陬,未设梨园,于祀神报赛之时,则必设坛演剧,即以巫觋为优伶,此即方相氏所掌之事也。故知舞乐降神之典,至今犹存,而古人之乐舞,已开演剧之先,此固班班可考者也。 由于刘氏诸文均早于《宋元戏曲史》问世,故有学者认为,王国维关于戏曲起源的观点应肇始于刘师培。⑦这个分析本身并非没有理由,但两位国学大师在学术上存在“某些理论暗合”⑧也是可能的。从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而言,自《宋元戏曲史》发表以来,以往在戏曲研究上的吉光片羽似乎都被它的光芒遮蔽了。而刘氏由于发表过《原戏》,故往往被当成戏曲起源于歌舞说的代表人物,而他更着力的《舞法起于祀神考》则常常被戏剧史家所遗忘。 三、20世纪对王国维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评价 王国维关于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的观点,在20世纪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遭遇到不同的评价。大致说来,50年代以前为第一时期,自50年代到“文革”结束为第二时期,自改革开放迄今为第三时期。 《宋元戏曲史》问世后虽好评如潮,但直接谈论到戏剧起源观点的文章和书籍并不多,而且多数是一笔带过。至30年代,我国现代音乐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光祈于1934年在德国写成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起首即说:“中国戏剧同希腊一样,是从巫祝与祭祀中发展而来的。中国最早的文献(公元前四世纪的《国语》)对此已有记载。”[34]此处虽未展开论述,但文中以《国语》为例,很可能受到了王国维和西方学术的双重影响。 1937年,人类学家岑家梧赴日留学期间写出的成名作《图腾艺术史》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岑氏利用国外人类学家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搜集并罗列了我国青海出土的舞蹈纹陶盆图和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舞蹈图以及鄂伦春萨满巫师装扮图、江西傩舞面具图、《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苗族黥纹图等材料,指出:“一切模仿动物动作的跳舞,可视为原始戏剧之萌芽……图腾的跳舞,即原始戏剧表演之一形式,而为戏剧产生之渊源。”[35]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附录了《周礼》、《后汉书》、《隋书》、《乐府杂录》、《东京梦华录》等文献中的傩舞材料,指出:“傩舞刻意于动物模仿”,“类似图腾的跳舞”,宋代傩舞“尚有装扮钟馗之类作戏剧的表演”。[36] 上文已述,1936年陈梦家发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补充论证了王国维中国戏剧源于巫觋的观点。此外,另一致力于巫、优关系研究并刻意为《宋元戏曲史》做“疏证”的学者是冯沅君。她先后写了《古优解》(1941)、《汉赋与古优》(1943)、《古优解补正》(1944)三篇论文。她说:“古优的远祖,导师、瞽、医、史先路的不是别人,就是巫。”[37]她认为,最初“群巫之长”往往就是“王”,巫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能卜筮预测祸福,为人疗病,通音乐、歌舞。“随着社会的演进,巫者技艺渐分化为各种专业,而由师、瞽、医、史一类人分别担任,倡优则承继它们的娱神的部分而变之娱人的。”她坚定地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是古优的远祖,我将回答道:那是巫。”[38] 孙作云于1943年撰《大傩考》一文(未刊),1965年改写为《中国傩戏史》,孙氏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秧歌即大傩之遗风”。[39] 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持戏剧起源“综合说”(多元说)的周贻白,在他早期著作如《中国戏剧史长编》、《中国戏剧史》中,也说俳优来源于“降神的巫觋”。他叙述“巫”与“优”的关系与王国维、陈梦家、冯沅君有相似之处:“巫觋,最初当然是很神圣的职业。但因祀神仪节里的歌舞,渐渐地用于娱乐人君之故,事实上巫觋便降为‘弄臣’了。一部分成为籥人而司乐,一部分成为歌人或舞人。其特立的名词即为俳优,亦即今日戏剧中的脚色或演员的滥觞。”[40] 以上所举,大体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对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认同。唯一一篇与《宋元戏曲史》商榷的文章,对戏剧起源于巫却并无异议,该文在引述“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后用两个字表态:“是矣”![41] 然而,对于巫术与艺术关系的认识不能够过犹不及,真理跨越一步便是谬误。闻一多在40年AI写作过《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什么是九歌》两篇论文,提出《九歌》是“一种雏形的歌舞剧”,两千年前的人欣赏《九歌》与今人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42]《宋元戏曲史》认为《九歌》中仅有“戏剧之萌芽”,并特意指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闻一多则说《九歌》是“雏形歌舞剧”,两种说法明显不同。 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已故民俗学家张紫晨所说,王国维提出的中国戏剧源于巫的重要命题,“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文艺起源于劳动说盛行之下,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种巫和巫术活动的因素”。[43]作为高校教科书使用的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以及1980年出版的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都主张戏曲起源于劳动,这对当时的大学教师和刚刚迈入学术之门的青年学子两三代人的学术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 80年代中期以来,戏剧研究界兴起傩戏、目连戏研究热。一次次国际会议接连召开,一篇篇论文相继发表,出版了多少种专著难以统计。这对于推动人们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宋元戏曲史》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认识也必然掀开新的一页。如朱狄的《艺术的起源》(1982)、张紫晨的《中国巫术》(1990),以及萧兵的《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1992)等,都重提“巫觋说”并给予正面评价。正如康保成等人所指出的:“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傩戏热’,其实仍是在大师(指王国维)开辟的道路上行走。”[44] 在傩戏、目连戏研究热潮中,境外学者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的论文《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地方戏的环境》、《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几本著作和王秋桂在中国大陆主持的关于仪式剧的田野考察工作起的作用最大。龙彼得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种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还仍然活跃着。”[45]可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类似欧洲研究巫术与艺术关系的热潮,八十多年后终于在中国的傩戏、目连戏研究中重新得以呈现,中国的戏剧史家们终于和人类学家走到了一起,王国维的戏剧起源说在各地依稀尚存的活态的初级戏剧中得到了验证。 2000年,廖奔、刘彦君主编的《中国戏曲发展史》在第一章“总论”后专设“原始戏剧形态”一章,指出“交感巫仪模仿”是最古老的“原始戏剧”,其特点是“混杂在祈神和娱神的宗教仪式中,呈现出宗教仪式依附物的面貌”。[46]几年后,叶长海、张福海的《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也说:“无论东方和西方,戏剧的生成大约都走着一个相同的路径,即源于宗教活动和诗、歌、舞的综合形式。”[47]“在中国戏剧发展的早期,出现了最早的‘演员’——巫和优。”[48]可见学术界在中国戏剧起源于巫和巫术这一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较多共识,戏剧史已经和正在被改写。 然而,近几年来,质疑王国维戏剧起源说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例如,有一篇文章在肯定了王国维“披荆斩棘,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探寻中国戏剧之源”的功绩后说道: 但王国维在考察中国戏剧起源、形成时,也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这种思路给后世带来相当大的误导、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中国戏剧起源的探讨,实际上也是从王氏开启的巫、优二端入手的。直至80年代以来傩戏研究者以傩蜡作为中国戏剧之源头,仍可以说是对王国维“巫觋说”的一种回应。[49] 很显然,该文的矛头所向首先是王国维,因为后来的错误都是受王氏“误导”、“从王氏开启的”。同时,按照该文的观点,不仅20世纪初以来国外人类学家的大量研究工作,3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苦心孤诣地探索,8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的田野考察及其成果变得毫无价值,而且就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些学术共识也再次化为乌有,某些新版戏剧史著作取得的一些学术突破则显得很“另类”。 同一作者在与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商榷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田仲教授‘把这种祭祀戏剧,特别是与巫术相结合的巫系戏剧看作中国戏剧的起点,来重构中国戏剧史’,其理论前提是极不可靠的。”⑨这篇商榷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颇受关注的学术论争。⑩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哈里森说过的两段话: 在现代社会,艺术和仪式确实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艺术和仪式,这两个在今人看来好像是水火不容的事物,在最初却是同根连理的,两者一脉相承,离开任何一方,就无法理解另外一方。最初,是一种相同的冲动,让人们走进教堂,也让人们走进剧场。[50] 如果说戏剧是献给神的,是从仪式中脱胎而出的,那么,为什么舞台上上演的都是些人间的悲剧和故事呢?……我们本来相信,希腊戏剧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应该最能体现出仪式和艺术之间的渊源,但事与愿违,我们发现,希腊戏剧并不具有宗教功能,甚至看不到神和女神的故事,而尽是荷马笔下那些男女在逢场作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找的线索好像一开始就断了,在最关键的地方断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满脑子的困惑。[51] 显然,让今人理解古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世事变化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但谁又能否认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与两千多年前发明的阿拉伯数字甚至史前人类结绳记数的内在联系呢?难道研究戏剧起源,不就是要追溯她那渺远而又神秘的逻辑起点吗? 四、祭祀仪式是如何蜕变为戏剧的 什么是巫术?巫术与戏剧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些问题,中外学者早就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答案,我们在上文也已经做过一些介绍。此处只拟结合《宋元戏曲史》所关注过的尸祭与广西现存师公戏的联系略作剖析,再结合巫术思维与巫术行为,以说明在绵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具有巫术性质的祭祀仪式是如何蜕变为戏剧的。 《宋元戏曲史》指出,尸在上古祭祀仪式中是由巫来装扮的。然而,尸的装扮者不一定是职业的巫。据《公羊传·宣公三年》何休注,若神主为天子,则以卿为尸;神主为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照此推之,绝大多数扮演尸的人是男童。据《周礼·春官·守祧》,“若将祭祀,则各以其服授尸”。郑玄注云:“尸当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时。”[52]也就是说,在祭祀时尸要穿上死者的服装,代表死者的神灵接受祭祀。一旦下了祭坛,尸的扮演者必须换上常服,其神圣性就消失了。可见,尸的扮演有暂时性、假定性、表演性、可转换性等特点,与戏剧角色扮演十分相似。 《宋元戏曲史》中列举的《诗·楚茨》有这样的诗句:“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祖是皇,神保是飨。”“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观其全诗,实际上记录了一个国人在丰收之后在王者带领下进行的迎神、娱神、送神的祭祀仪式。“以妥以侑”者,是迎尸使之处神座而食之;从“神保是飨”到“神具醉止”,浓缩了尸代表神灵享受祭祀的过程。 《仪礼·少牢馈食礼》记录的由卿、大夫主祭的仪式非常详细,可与《楚茨》相互参证。仪式开始,尸被迎入庙门,安入神座,“尸答拜,遂坐”。数次祭献之后,“尸告饱,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独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实”,侑。”又数次祭献和酬答后,“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接下来的环节是尸对主人下传嘏词:“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最后是主人“送尸”。”[53]这场祭祀中有两个巫:“尸”装扮先祖之神灵,“祝”是主祭者,负责沟通人神关系。二巫及主人三者间有对话交流场景,祭祀者不断侑酒并有语言和动作,受祭者也有答拜和祝词。这种亦真亦假的带有巫术性质的祭祀仪式中,甚至还有了稍许的代言成分,其戏剧因素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娱神不仅有美食,还有歌舞,《楚茨》“钟鼓送尸”者是也。又据《礼记·祭统》,天子诸侯之祭礼,先要“执圭瓒裸尸”,然后用乐舞娱尸:“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揔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诸侯之祭也与竟内乐之。”[54]杜佑《通典》卷四十九陈述周时的“九献之礼”云:“自九献之后,遂降,冕而抚干,舞《大武》之乐以乐尸。”[55]“乐尸”就是娱尸,实际上既娱神也娱人。明季本《诗说解颐》卷二十六解释《周颂》中的《执竞》云:“经旨曰:此袷祭武王、成王、康王,神既锡嘏而加爵,娱尸之乐歌也。”[56]可以推测,后世丧葬用乐舞戏剧,正是上古以乐舞“乐尸”、“娱尸”礼仪的孑遗。 礼失而求诸野。当中原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尸祭之后,南方偏僻的山村却以各种活态的方式传承着上古的典祠。《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记云: 后魏文成帝拓跋浚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殁,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黩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面人,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57] 按郴州、道州,均在今湖南省的南部,与两广交界。可见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间,我国南方的尸祭活动还相当普遍。 到了明代,广西一带出现了一种名为“跳岭头”的傩舞。明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一云:“八月中秋.假名祭报,妆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妇父母兄弟,恬不为怪。”[58]“假夫妇父母兄弟”者,类似戏剧中的假扮。清黄元基《(乾隆)灵山县志》卷六“风俗志”则云“跳岭头”的主持者是“尸公”:“六月六日,多延尸公,击土鼓以迓田祖,众皆席地而饮。”“九月,分堡延尸公禳灾,名曰跳岭头。”[59]这“尸公”主持祭祀田神和禳灾仪式,当即从上古的尸演变而来。清潭莹《乐志堂诗集》卷四《山公妪》诗云:“岁岁为尸公妪多,乐神巫自舞婆娑,山灵有知当奈何。”[60]谭莹是广州人,道光间举人,写了大量岭南风俗诗,《山公妪》即歌咏了岭南山区所保留的上古尸祭遗风。 尸或尸公,明清以来多写作“师公”,而师公就是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语”:“巫曰师公、师婆”。[61]江藩道光《肇庆府志》卷三“风俗”:“巫曰师公”。[62]而师公的巫术活动也多被称为“跳师”。邢址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风俗”:“古邵俗信鬼好祀不移,尤尚‘跳师’,号咒鼓角之声,无城内外,日夜相闻。”[63]民国广西《贵县志》卷二“节令”:“每值秋季,扮方相,打鼓、唱歌,谓之‘跳师’。次日沿门逐疫,家家以黄豆、姜丝、茶果祀祖,盖犹存傩之古俗云。”[64] 今广西流行甚广的师公戏,其主要演员即从师公(尸公)转变而来,有的至今还保留师公的身份。师公头戴羽毛装饰,或即从上古“皇尸”冠冕而来。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师公戏已经在向纯粹表演性质的娱人戏剧演化。据《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的介绍,师公戏从驱鬼逐疫的巫傩活动(俗称“跳师”,钦州、灵山一带称为“跳岭头”)发展而来。清初已有师公戏班出现,道光间师公戏明显向娱人转化。民国初,受粤剧等大戏影响,师公戏改编了一批传统剧目如《梁山伯祝英台》、《高文举》、《薛仁贵征东》等。[65]蒙光朝《壮师剧概论》说:“师公是古代自称能以巫术驱鬼降神的人……有的地方叫‘尸公’。”[66]壮族师公戏“开始是师公跳神,后来由跳神发展到面具舞,再发展到一人多角的唱故事(曲艺),再由唱故事发展到分角色演唱的壮师剧。”[67]有的研究者指出:“壮族师公戏的主要角色有生、旦、净、丑,师公们按照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穿着不同服装,戴不同的面具或化不同的装……在审美化与崇拜性双重心理条件下调整着壮族人的生活关系与心理结构。”[68]可以说,一部师公戏,浓缩着从上古巫术向近代娱乐戏剧演进的漫长历史。 不独师公戏。孔子时代的“乡人傩”,以“傩、傩”之声沿门驱疫,“国人傩”则“击鼓大呼,驱逐不祥”。到南北朝,民间傩人用“邪呼”之声驱傩,“遍往人家乞酒食”。敦煌文献中有驱傩使用的《进夜胡词》,“夜胡”即“邪呼”之音转。北宋时民间驱傩进一步向娱乐转化,出现了集沿门逐疫、沿门乞讨、沿门卖艺为一体的“打夜胡”。而南宋的路歧人,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叫做“打野呵”。路岐人,就是冲州撞府的民间戏班,而“打野呵”明显来自“打夜胡”。这样,从上古“乡人傩”到宋代民间戏剧的发展线索就被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了。进一步说,目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几个剧种,如评剧、越剧、黄梅戏、花鼓戏,均是从乡民的沿门逐疫、沿门卖艺活动逐渐蜕变而来的,而从仪式迈向艺术的一个中间环节就是秧歌。(11)此外,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高甲戏,湖南的辰河高腔,浙江的松阳高腔,乃至梅兰芳扮演的京剧,也都在其自身的表演和术语中透露出与傀儡戏或远或近、若即若离的亲缘关系。齐如山说: 据戏剧老辈人云,戏剧与提线戏有极大的关系。比如演员上场,念完引子或诗联之后,归座时,如系外场椅(椅在桌前边曰外场椅,椅在桌后曰内场椅),则身体须先向左转,走至椅子前,再向右转,方坐。如系内场椅,则须先往右转,走至桌后,再往左转,再坐。倘都向右转,或都向左转,那提线就拧成绳了。到现在受过传授之演员,仍人人如此,无一或差,此足见戏与提线是有联系的。尤其演员的步法,或武将之抬腿、落足等等,确与提线人子之步法、姿势,都大致相同。[69] 根据陈梦家的研究,傀儡即鬼,方相氏蒙魌头驱傩即傀儡。也就是说“傀儡子”就是上古傩神方相氏,傀儡戏实质上即傩戏之一种。或许可以说,傀儡戏也是从巫术通向成熟戏剧的一个中间环节。 从巫术到戏剧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人们却走了太长的时间。这一步不仅是缓慢的,而且是间接的,难以清晰地辨别其踪迹。正如朱狄所说,要想把人们的非审美动机与审美动机截然区分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非常含糊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事实上它是一个极其缓慢、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70]同时,由于经济、文化、交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巫术向戏剧演进的速度差别极大。在大城市,人们早已习惯于在厅堂、茶楼、会馆、戏院中边品尝香茗边欣赏“角儿”们委婉动听的唱念和美丽婀娜的舞姿,但在偏僻的乡村,师公们仍旧戴着狰狞的面具,歌呼跳跃,驱邪逐鬼。这或许就是王国维与田仲一成的批评者所说“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的来由吧? 中国戏剧起源问题是任何中国戏剧史著作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难题。无论巫觋说、劳动说、歌舞说、外来说、词变说、综合说(多元说),或许都从某一侧面说出了一定的道理。但从戏剧形态学和戏剧发生学的角度看,从已发现的文献、文物和田野资料看,王国维的戏剧起源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一说,其生命力也应当是最长久的。 注释: ①《宋元戏曲史》连载于《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十号、第十一号及第十卷第三、四、五、六、八、九号(1913年4月—1914年3月),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②就笔者所见,1949年以前专论《宋元戏曲史》并对其批评的文章只有一篇,即王玉章的《〈宋元戏曲史〉商榷》,载《文史哲季刊》第3卷第1期,1945年。 ③详参康保成:《五十年的追问:什么是戏剧?什么是中国戏剧史?》,《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 ④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4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⑤《礼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4页。关于“邮表畷”为“界牌神”的说法,可参萧兵:《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3-584页。 ⑥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40-1642页。下文引刘师培此文不另出注。 ⑦参王立兴:《刘师培戏剧起源观论略》,《中国近代文学考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还有人指出,刘师培的“思路和考证方法对王国维《戏曲考原》及《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启发”。(张晓兰:《刘师培戏曲观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⑧施秋香《刘师培与王国维戏曲理论之比较》:“刘师培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某些理论暗合”。(《求索》2010年第11期) ⑨解玉峰:《献疑于另类的中国戏剧史——读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胡忌主编:《戏史辨》第4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后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题目改为《巫风傩影中的迷失——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 ⑩解文发表后,围绕相关问题发表的学术批评论文有:田仲一成:《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解玉峰:《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兼答田仲一成先生》,《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傅谨:《中国戏剧发源于祭祀仪礼说质疑》,《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田仲一成:《再论民间祭祀文化在戏剧起源史上的重要作用——对傅谨教授〈中国戏剧发源于乡村祭祀仪礼说质疑〉一文的回应》,《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傅谨《田仲教授,这次你真的错了》,《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 (11)以上参康保成:《傩戏艺术源流》,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标签:戏剧论文; 王国维论文; 宋元戏曲史论文; 中国戏剧论文; 艺术起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周礼论文; 国语论文; 祭祀论文; 东坡志林论文; 歌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