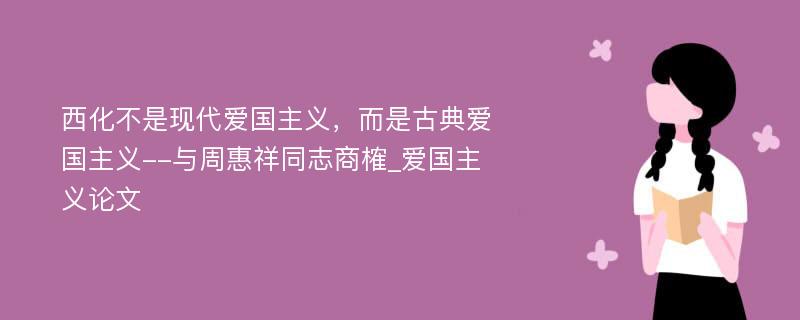
洋务思潮是古典爱国主义而非近代爱国主义辨——兼与周辉湘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洋务论文,思潮论文,而非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大学术问题讨论
前些年,史学界曾就洋务思潮的属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最近,周辉湘同志又在《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上发表《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蕴义》一文,从爱国主义视野对洋务思潮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有益探讨,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洋务思潮界定为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敢苟同。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在近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遇到一些很难解答的题目:明明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行动,似乎又有悖于爱国主义的原则。这当中涉及到爱国与进步、保守的关系问题,很有必要首先逐一剖析,以利于认识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规律。
爱国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反映。在一个时代大转变的前后,亦即古代与近代交替之际,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生,必然有一个与旧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共存的时期,反映在爱国主义领域,就是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共存的重叠现象。对君主的无限忠诚和对传统文化的眷眷深情,使鸦片战争后以“师夷”为时代标志的爱国思想具备了古典与近代的双重性格,更使其后的爱国思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互相重合、同时并存的矛盾现象。在古代向近代转变开始时,古典爱国主义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近代爱国主义只能占次要地位。随着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爱国主义日趋成熟,古典爱国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近代爱国主义。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古典爱国主义不可能立即消失,有一个缓慢的嬗变期。在嬗变没有完成之前,在一定条件下,仍会有非常强烈的表现。
两种爱国主义的交织重合现象,乃是近代史上研讨爱国主义问题时所碰到的一切矛盾之源。在古代,由于爱国标准的单一性,侧重点不同的爱国主义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保君、保国、保族、保教,多元一体。在近代,世殊情移,不同侧重点的爱国主义往往势同冰炭。侧重于保文化和保国家(清朝)的爱国主义常常结合在一起;保民族则以攻击传统文化为肇端,以学习西方为手段,以推翻旧国家、封建君主为目的,表现为保民族与保君、保国、保教的对立。由于爱国途径和标准的不同,人们对爱国行为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曾国藩举办团练,组织湘军,挺身纾难,是标准的古典爱国主义者,但身后却留下了民族罪人的千古骂名;孙中山等革命派以驱逐鞑虏,振兴中华为己任,表现出爱国救亡的高度热情,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推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步运动,但似乎很难说是一场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当然是爱国运动,但还不能说是进步运动。在这杂乱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近代爱国主义的蕴义何在?
诚然,任何历史人物,没有谁是天生的卖国贼;任何历史行为,也没有一开始就以卖国的初衷出现的。这当中就牵涉到人们对爱国途径的理解与选择的具体问题。以此为基点,形成了进步与保守、近代爱国主义与古典爱国主义的历史分野。在近代史上,守旧与革新、封闭与开放的反复较量,不存在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体现着新旧两种爱国观念的激烈抗争。一切守旧者、顽固派,最初都死抱古典爱国主义的传统;他们忠君,也同样有着反侵略的要求;但他们以为传统文化海涵地载,沃日吞天,自来夷变于夏,未有夏变于夷者,所以他们照袭清初老谱,封关禁海,凡是外国的东西都一概排斥,以为只有这样才显出我中华之伟大。其结果,在一次次失败面前,都归于屈辱投降的道路。他们所谓的“爱国”,就与误国卖国的结果纠结在一起。而一切革新派,他们都有着冲破传统的勇气,有着见贤思齐、向西方学习的胸襟胆识,有着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所以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展示了古老爱国传统的时代风采。因此,近代爱国主义都紧紧地与社会进步结合在一起。尽管爱国与进步不是同义,爱国不等于进步,进步也不等于爱国,但两者必须结合一起,要爱国就必须进步,要进步就必须爱国;一切清醒的、有远见的近代爱国主义者,就一定是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进步的统一体的负载者。反对帝国主义,走向民族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走向民主主义,争取国家富强与推动社会进步相辅相成,这就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本质蕴义所在。
二
无可讳言,洋务派作为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情感,并对国家、民族有一种责任感。因此,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付外国的侵略,“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①]。即使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前,其御侮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曾国藩就曾说过,当时太平军在水面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他所担忧的是洋人随时可能“兵端立开”,为避免“临渴掘井”,所以他们“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②]。特别是随着外国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和边防危机日益加剧,洋务派更把精力放在御侮方面,一再强调“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③]。由此可见,洋务派的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倾向。
但是,从主要方面看,洋务运动打出的“学习西方”的旗帜,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性质,就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是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救亡自强运动。他们代表地主阶级和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剿发逆”、“勤远略”,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所谓“御侮”、“示威”,不过是“安内”的附属效果。洋务派强调“内患除则外侮自泥”[④],咸丰皇帝专门发布上谕说:“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曾国藩说这是“安内攘外之至意”[⑤]。因此,他们的爱国情感,充其量不过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延伸,带有浓厚的古典性和局限性。
洋务派打出的旗帜是“自强”、“求富”,它所标榜的是“时务”和“新政”。表面上,他们直接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制器、用人、筹饷等方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洋务派不仅没有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制夷”思想前进一步,反而排除了其爱国精神的内核,代之以抚夷和媚夷。洋务派“自强”的重点,是用帝国主义提供或支持制造的近代化火器装备反革命军队,发展自己的军阀武装,服从加强封建国家、强化地主阶级专政这一根本目标。奕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⑥],道出了所谓“治国之道,在乎自强”的中心环节。在企求地主阶级“自强”的同时,洋务派也标榜争取“民富国强”,提出了“求富”的口号。但是,在实践上,洋务派的军事工业既无补于民生,民用工业也主要是为了封建国家、反动军队筹款筹饷,供应民需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历史表明,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招牌下,办了几十年近代工业,其结果,反而阻滞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富国强”不仅成了一句空话,而且适得其反。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民生凋敝,民穷财尽,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国家利权不断丧失,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到内地。本来就很微弱的民族工业,受到压制与摧残。中华民族被进一步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脉民命不绝如缕,只是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而已。洋务派所醉心的地主阶级的“自强”和封建统治的稳固局面也没有出现,清政府正在向“洋人的朝廷”急剧堕落。历史是无情的。事实彻底戳穿了洋务派鼓噪了几十年的“自强”、“求富”的虚伪性。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淹没了“国富民强”的微弱呼声。曾经一度对洋务派抱有幻想的人们,在“理想”幻灭之后,有的回到了封建保守的老路,有的则进一步去探索救国的途径。
三
随着西方近代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已摆在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正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洋务派面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条原则,也是他们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主张同样反映了洋务派“爱国”思想所处的层次和水平。
“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动,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洋务派亮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叫做“变器不变道”,笼统道出了固守传统文化的立场。当时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主张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种观念准则,几十年中一直是洋务实践的依据。最早喊出“中体西用”口号的是沈寿康,他在1896年4月发表的《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进行了详尽的概括和阐发。按照张之洞的理论,所谓“中学”,是指两千年来在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其基本内容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制度,包括社会生活准则、道德规范。张之洞引用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论述“中学”的“体”,也就是封建道统、纲常名教,这些都是不可移易的,不能动摇的。所谓“西学”,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西学也有“体”和“用”两个方面。西学的“体”,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等,都是不符合封建道统和法统的东西,是不能采用的,用了就等于自我否定,就要根本违背“中学”的“体”。张之洞要用的“西学”,仅采其器物文明的“用”的某些方面,不仅是支离破碎的,也是很皮毛的。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简单的“中西结合”,而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核心,引进西学中可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部分,作为“应世事”的手段。
“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体现了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后国人的普遍反应。在封建主义旧文化充斥的年代,“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它在维护“中体”的名义下采纳西学,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使西学得以在中国旧文化的天地里落户生根。从这一意义上说,“中体西用”论包含着一定的近代爱国主义倾向。但是,就整体而言,它反映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只承认在“器物”上不如西方的阶段,亦即停滞在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水平。它主张引进西方先进工艺,又拒绝先进的政治和文化,并以传统文化的历史成就相炫耀,保留着深厚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李鸿章就觉得,“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洋务派对“中学”之“体”的强调与维护,主要地表现出古典爱国主义的保传统文化的思想特色。它与忠君、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是相互呼应的。
在洋务运动中,“中体西用”论是洋务派与顽固派争论的理论武器,相对顽固派僵化盲目的思想而言,它有着进步、积极的一面。但是,在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的救国方案、将近代爱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层次后,“中体西用”论对传统文化的着恋与卫护,则表现出对近代爱国主义思潮的滞后与反动。
“中体西用”论又是古典与近代两种爱国思潮撞击的产物。一方面,它反映了古典爱国主义忠君保文化的传统在近代仍占有相当广阔的市场。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开始感觉到西方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他们当时对西方文化的具体认识是浅薄的。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到洋务运动兴起之后的一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器物文明的水平。洋务运动初兴时,办洋务的阻力也很大,“动以不谈洋务为高,有讲述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那时候的中国,要在封建旧文化的氛围中容纳外来的器物文化现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洋务派穷于应变而采取的“以制器为先”的策略,打出“中体西用”的旗帜,既基本顺应了中国学术当时趋于务实的潮流,又大体满足了古典爱国主义保文化的普遍心理,从而被洋务运动几十年间的社会思潮所接纳,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曾怀疑它的正确性。这种思潮大大延缓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论本身又蕴含着古典爱国主义的日趋没落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物质变化所必然带来的诸种问题,许多都是物质自身所无法解答的。例如铁舰和洋炮之使用,便带来了军队的编制、军需军务管理、人才培训等一系列问题。因而要求在管理制度、行政体系上相应地改变成法,促使中国文化这个主体本身作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外来之用的要求。这就唤来了近代爱国主义向西方学习的深层迈进。
早在洋务运动开展后不久,作为洋务派上层人物的郭嵩焘,就对洋务派的作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而造船制器之类的事情仅仅是“末中之一节”[⑨]。他批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⑩],主张向西方学习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建立一套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他尤其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认为英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贾阿门(mayor,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此其立国之本也”[(11)]。郭嵩焘的思想既透露出洋务派内部的有识之士对“中体西用”准则的否定,又喻示着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萌生。
四
洋务思潮所代表的古典爱国主义忠君保文化传统在近代的表现颇引人思考。从形式上看,曾国藩等洋务派在清王朝危难之秋,挺身纾难,其对君主、王朝的强烈依附和一片深情,与古代的大忠臣、爱国义士并无二致。但是,古典爱国主义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对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意义,在曾国藩等人身上已荡然无存;相反,古典爱国主义的依附、愚忠、保守的局限性却充分地暴露出来,成为近代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障碍,并且随着斗争的日益深入,其危害性也愈来愈大。步入近代后,尤其是近代爱国主义产生后,古典式的爱国思想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积极、进步的因素,而日益与保守、落后、反动结成不解之缘,甚至与卖国纠结在一起。以曾国藩为例,他对西方侵略者也以名教为价值标准。他吹捧外国侵略者“素重信义”,“颇有君子之行”[(12)]。在他看来,洋人不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推翻清朝统治,又攻打名教的罪人,这才是大者。洋人的侵略行为则属小事。依据曾国藩的价值观念,名教重于主权。因此,他提出对外要实行“礼让为国”的方针,对外国侵略者,不取虞诈之心,不用欺讹之言,要质厚谦恭,服服贴贴;只要他们不危及国体及封建道统,领土主权大可让位于“礼让”。这就是他的投降、卖国滥调。后世多以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看来并没有冤枉他。
为什么像曾国藩这样颇具古典爱国意识的思想家,同时又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卖国贼?简而言之,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阶级本质的反映。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的靠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在对待人民革命运动这一点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谓“共同大局”,决定了地主阶级在其自身统治受到人民革命运动的打击,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候,它宁愿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出卖领土、主权,以保全其反动统治。明乎此,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到,古典爱国主义在近代的反动性与危害性。明乎此,我们更能区分近代史上同时并存的两种爱国思潮的不同性质与功能,而不致将两者混为一谈、不加区别。
注释:
①《洋务运动》(三),第467页。
②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十八,第30页。
③《洋务运动》(四),第10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十二卷。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二十五卷。
⑦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⑧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第一卷。
⑨《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⑩《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
(11)《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12)《复毛寄云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
标签:爱国主义论文; 洋务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曾国藩论文; 中体西用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