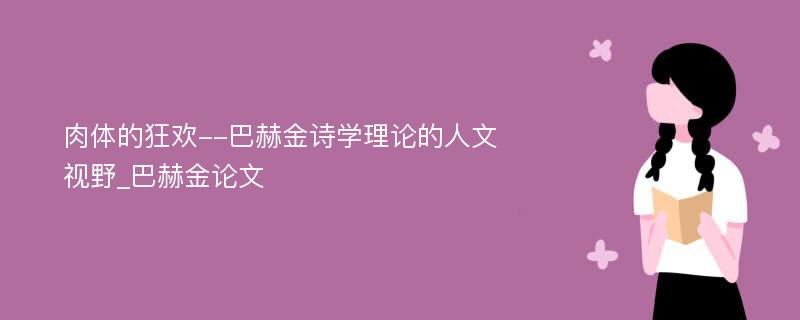
身体的狂欢——巴赫金诗学理论的人学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人学论文,视野论文,身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6-0120-06
一、身体占位:巴赫金诗学理论的现实基点
在尼采之前的西方诗学史上,身体问题曾经受到长期的压抑与遮蔽。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人是信仰的存在;近代的笛卡尔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然而到了尼采,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站在现代人本主义立场上为身体辩护,阐明身体在存在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1],要求人们“以肉体为准绳”衡量人的存在[2]。尼采所说的身体当然不是单纯的肉体,而是人的生命活力,他要以人的生命活力的强弱大小,来判别生命存在的健康与否,并以此来衡量价值的高低与有无。
无独有偶,在尼采之后,巴赫金(Bakhtin)成为西方诗学史上又一位关注身体、思考身体价值与意义的重要思想家,不同在于,后者关注的重点是人的身体行为及其存在占位。在早期的《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从身体作为一种“存在事件”的角度研究“身体”,强调身体存在是人的行为世界、事件世界,认为“身体”是理解“存在”的一个独特视角,认为“我”的思想是由“我”的自觉负责的行为构成的,“我”的生活世界是由“我”的负责行为建构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不过是“我”的一连串负责的行为过程。他批评理论思维、历史认识和审美直觉都不能准确把握存在的事实及含义。理论思维只认识到存在的抽象含义,却失掉了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看到了存在的历史事实,却失掉了存在的个性化独特化含义;审美直觉既把握了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把握了存在的个性化独特化含义,却失掉了人对存在的负责意识。“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把握世界进程的全部,即惟一性的实事、进程、内涵、意义与我们的参与性的统一和相互渗透(因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世界是统一的又是惟一的)”[3](P20)。他认为,这种错误的状况是由现代理性主义哲学造成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合乎逻辑的才是明晰的合理的,然而,理性主义没有想到,明晰合理的逻辑排斥人的负责意识,让存在进入自在状态。一种缺乏具体负责意识的自在存在,是抽象的普遍存在。它即使明晰无比、秩序井然,由于否定和排斥具体又惟一的人的参与,因而抽空了它的所有价值。
巴赫金的生存诗学思想是从人的“身体占位”出发并展开的,“身体”为“我”占据了一个“他人”不能分享的惟一的存在位置。这里所说的“身体位置”既有自然的又有文化的含义。作为自然存在,人的“身体”是一种具有广延性的存在,他的生存占位具有惟一性:“我”此刻在自然中的存在位置,“他人”是无法分享的;“我”此刻拥有的对天地自然的观察视觉,“他人”也不能重复。作为文化存在,人的“身体”又占据一定的文化空间:“我”此刻的文化承载,“他人”无法重复;“我”此刻看待文化的视角,“他人”不可能重叠;“我”此刻从文化中所看到的具体蕴含,“他人”不会完全认同。“我现在身处的这个惟一之点,是任何他人在惟一存在中的惟一时间和惟一空间里所没有置身过的。围绕这个惟一之点,以惟一时间和惟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惟一的存在。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实有存在的惟一性质是绝对无法排除的”[3](P41)。这一论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为“我”的生活和行为找到了坚实的根基。“我”是自身行为的主动发起者,“我”从自己的惟一位置出发进入生活世界,把握行为的方向,评估行为的价值。“我”在整个活动中都能体验到这个惟一的自我,“我”的自我在生活中始终是在场的。因此,“我”必须对自己的惟一性存在承担起责任。二是为“我”的生活世界找到了建构的基石。“对于我的参与性的行动一事来说,这个世界作为建构的整体,分布在我行为发源的惟一中心——我的周围,要知道这个世界是由我发现的,因为我在自己的观照行为、思考行为、事业行为中都是从自身出发的。根据我在世界所处的惟一位置——能动发源的位置,所有思考到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都找到了价值的中心,并围绕这个中心形成某种稳定的具体的建构整体;这样,可能的统一性就变成了实际的统一性”[3](P57)。“我”所生活的世界,是从“我”的惟一位置周围展现给“我”的,也是“我”从自己惟一位置出发建构起来的。“我”是自己生活世界的几何中心,责任中心、价值中心。“他人”和“我”一样,也从自己的惟一位置出发,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创造自己的价值理想,让自己时刻都作为一个负责的主体参与到生活之中,摒弃一切不负责任的旁观意识。如果“我”脱离开自己所处的中心位置,从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变成一个旁观者,对“我”来说,世界的具体惟一性和必然现实性就会解体,变成抽象笼统的统一体。这个抽象的世界由于剥离开“我”的具体建构行为,对“我”来说就不再具有价值,而是一个非价值的系统整体。
巴赫金特别强调,生活从“自我”出发,并不意味着为“自我”生活;行动的方向由“自我”来把握,并不意味着仅为自我实现而行动;“我”以惟一的方式参与生活世界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只有“我”的生活具有正面价值;“我”置身于存在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我”的存在具有崇高价值,别的存在只有从属价值。“我们打算做的,是描述从价值角度对世界进行的体验感受是如何实际而具体地建构起来的;这里重点不是分析性论证,重点在于发掘实际评价、确认、行动等等的真正具体的发源中心(也是时间与空间的中心)”[3](P60-61)。搞清了这个中心,将生活世界与其联系起来,生活世界的具体价值就会得到凸现。因为生活世界中不仅有“我”还有“他人”,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价值中心,责任中心。“我”和“他人”从各自的角度对生活世界进行个性化的建构、对价值世界进行负责任的创造。生活世界因此变得多彩,价值世界因此变得多元,人生因此而变得更加具体独特。具体来说,固定不变的同一个地方,是引发我无限甜蜜和酸楚回忆的故乡,却是我的爱人没有多少特别感触的异乡;我与她面对着共同的世界,世界对我和她却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价值。“没有任何一个意识会被另一个完全吸收。即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怎么紧密,也不能把它们化约为一个统一体,使得所有的个别形式消失于一个专制的,单调的和终极的意识之中。这是因为,它们的性质、意义和基础,每一个形式都有其自主性”[4]。
世界在宏观上是一体的,具体的生存者却是多样的,每个生存者从自身所处的位置出发,以负责的态度参与到存在之中,就会构建出多样化的生活世界,从而使生活世界的价值因其与参与者的关系而不同。也就是说有多少个责任中心,有多少个惟一性的参与主体,就会有多少个不同的价值世界。巴赫金由此得出结论,“固定不变的、普遍使用的公认的价值是没有的,因为被承认的价值的大小,不是受抽象内容决定的,而是要同参与者所占有的惟一位置联系起来看;从这个惟一位置出发,可以确认所有的价值,确认任何的他人及其拥有的全部价值”[3](P49)。
二、身体时空体:巴赫金诗学理论的先验建构
巴赫金在他的“时空体”(хронотп)理论中,将身体占位上升到生存世界观的高度进行研究,认为人的身体是时空的中心和基石,“我”所说的上下、左右、远近、高低,是以“我”的身体位置为中心的;“我”所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以“我”的身体存在为出发点的。“我”的身体位置为“我”感知世界设定了具体的时空模式,时空模式的本意是中性的,不含任何褒贬的。当“我”把它运用到人际关系方面时,身体位置变成一种价值基石,时空模式就衍生出各种褒贬亲疏的含义。然而,无论“我”处于中性时空,还是“我”置身价值时空,身体位置的基石身份一直没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含义。进一步来说,身体位置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具体主体的生活状况、人生遭际以及世界观人生观都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
虽然每个身体占位对于生存者本人来说都具有奠基作用,但是自从人类出现等级以来,生存位置本身也有了宫廷庙堂和山野草舍之分。由于位置决定世界观,这两种不同的身体占位者对于人生就发生了决然有别的理解和认识。宫廷之中庙堂之上的身体占位者,没有衣食之忧,喜欢追求精神的永恒性,追求思想的升华和抽象的进步,排斥作为生存基石的物质肉体因素。在他们的视野中,世界是一个等级构成的空间,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边的成员是天国、灵魂,下面的成员是尘世、身体;上边代表着崇高、纯洁、真实、善良和不朽,下边代表着卑下、污秽、错误、罪恶和短暂;上边是主人、法官、享有主宰权,可以任意实施规训和惩罚;下边是仆人、罪犯,只能服从和承受。不论任何时候,面对任何生存境遇,只要进入宫廷庙堂之中,“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它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5]。宫廷庙堂既是灵魂的天堂又是肉体的地狱。
山野之间草舍之下的身体占位者,为衣食所困,有肉体空乏之忧。在他们的视野里,肉体是存在的中心,世界首先是由一日三餐,昼夜交替,四季变化的时间构成的。他们更看重尘世和肉体,轻视天国和灵魂。他们追求变化、歌颂更新,因为变化和更新伴随着生存的理想和希望。巴赫金称赞山野草舍占位者的独特世界观,认为他们以身体为中心所构建的时空体是“身体时空体”,它的实质,“首先就可以归结为破坏一切习惯的联系,事物间和思想间普通的毗邻关系,归结为建立意想不到的毗邻关系、意想不到的联系,其中包括最难预料的逻辑关系和语言关系”[6](P364)。这种新联系、新意义、新价值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一切崇高的、理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与人的“身体”联系起来,都在人的“身体”中得到体现,都要用“身体”来衡量,“身体”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这一思想与尼采不谋而合,尼采曾说,“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2](P152)。人的身体是宇宙自然最完美的代表,身体上烙印着整个宇宙的运动和生成,整个自然的历史和未来。身体中蕴藏着多种潜能,一方面它向死而生,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孕育着新生。因此,尊重身体,就是尊重宇宙的核心价值,礼赞身体,就是礼赞社会的价值核心。
其次,“身体时空体”强调时间维度,强调了死亡与新生的互生关系,创建了一种活的永恒观。巴赫金的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哲学渊源。早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一切都在流变,只有流动变化是永恒的,“除了生成,我别无所见。不要让你们自己受骗!如果你们相信在生成和消逝之海上看到了某块坚固的陆地,那么,它只是在你们仓促的目光中,而不是在事物的本质中”[7]。人是在时间中生存成长发展变化的,人的生命从来都是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发生过程。在他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时间的三种样态——过去,现在,未来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携带着过去,创造着未来。所以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德勒兹在分析时间时也指出,“流逝的时间倘若不同时是既已过去的,又是即将来临的和此刻的,他将永远不会消逝。倘若此刻不自动消逝,而等待着另外一个此刻的莅临以便令自己成为过去,那么通常意义上的过去永远无法在时间的隧道中形成,而且这一独特的此刻也不会消逝。我们不能等待,一个时刻为了消逝(为了其他时刻而流逝),必须同时是现在和过去,现在和将来。此刻必须同时与过去和将来共存。每一时刻与自身作为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综合性关系奠定了它与其他时刻的关系基础。”[8]。生命在生成变化中创造永恒,同时又在永恒地创造变化着自身。山野草舍的身体占位者用身体时空观重新审视世界,评价生死。认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中的各种现象都处于未完成的变态之中,处于从黑夜向清晨,从冬季向春季,从旧事物向新事物,从死亡到诞生的过渡状态之中”[9](P188)。因此,他们都是一体双身的。以此来看,死亡是生命本身的必然因素,是生命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体的死亡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终结,相反,它是新生命得以诞生的前提,任何存在没有死亡都不会有新生,它只能在死亡中获得新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引用的《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是这种死亡观的最好注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山野草舍的身体占位者没有把死亡看成是个人现象,没有把它放在封闭的个人生命系列中来认识,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类现象,把它放到人类历史的广阔场景中来认识,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个人的死既没有什么开创的意义,也没有了不起的结束的意义。死亡在这里是播种生命,毁灭在这里是孕育新生,他们都变成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的一个部分,被完全纳入到不断向前、永远胜利的生命范围之中了。
再次,“身体时空体”强调时间因素,把世界拉入一个辞旧迎新的永恒过程之中。由于时间中更迭性因素的突出,人的“身体”第一次脱离有限存在而在人类学层面上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人。人的个体生命是要面临死亡威胁的,然而整体的人却会在时间的运动中日臻完善。巴赫金指出,“物质—肉体基础,土地和现实时间正成为世界新图景的相对中心。不是个别人沿着超时间的垂直线登上最高层,而是整个人类沿着历史时间的水平线向前运动成为一切价值评估的主要标准。单个人做完自己的事情以后同肉体一道衰老、死亡,但是由死者所孕育而生的人民和人类的肉体是永远能得到补偿并坚定地沿着历史日臻完美的道路前进的”[9](P469-470)。宫廷庙堂身体占位者把个体生命个体命运等级化严肃化,隔绝了它与整体的密切联系,遮蔽了它的“身体”特征,阉割了它的生机与活力,他们眼中的生命是渺小的、纯粹精神的、缺乏生命力的。在山野草舍身体占位者看来,真正的人是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存在于宇宙中的,他的形象硕大无比,他的命运关联着整个宇宙。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就是这样,不仅在形象上是硕大的,他的价值也是不同寻常的,他同中世纪的纵向发展的世界观完全对立,追求时空规模与价值分量相称的激情。在打破纵向的等级世界后,在水平的和谐世界中快乐地生存着。“身体”时空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破坏宫廷庙堂身体占位者所构建的精神化的世界图景,建立以“身体”和精神浑然一体的人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它把人从封闭的宫庭和庙堂拉出来,让人走向开放的山野和广场。抛开那中性不育的精神,张扬那创生世界拥抱人生的肉身性别。巴赫金认为,山野草舍占位者在狂欢广场上创造的怪诞人体,是这一世界图景的节日展现,拉伯雷小说中的人体则是这种世界图景的文学体现。他说拉伯雷的人物“仿佛成了一个特殊的小说人物。不过这个小说人物,并不是个人不可复现的生命序列里的某一个人的躯体,而是一个无名氏的躯体,是人类的躯体;它降世、生活、以多种方式死去,而后又一次降生;它在被揭示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的结构和自己生活的一切过程”[6](P369)。
三、身体狂欢:巴赫金诗学理论的现世操演
如果说巴赫金的“身体占位”与“身体时空体”理论只是其生存诗学的思想建构的话,那么,“身体狂欢”理论则是其现世的操演方式。在巴赫金看来,狂欢总是身体的狂欢,狂欢总是与节日、广场联系在一起,广场为节日的各种演出提供舞台,为各种自由、粗率、不拘形迹的交往创造条件;节日为广场上进行的各种演出和交往活动创造一种欢乐的氛围,节日的广场和广场的节日,是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生活世界,人们在此过的是一种身体化的欢乐的生活。“非官方的民间文化在中世纪,还有文艺复兴时代,都保留着自己的一块特殊的领土——广场,和一段特殊的时间——节日和计时器。这个节日的广场,正如我们多次谈到的那样,是处于中世纪官方世界之中的第二世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广场式的交往”[9](P174-175)。
节日里广场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各种欢快的吆喝声响成一片,渲染出一种亲昵交往的气氛。“响亮的广场话语,它存在于人群之中,既是人群发出的,又是对人群而发的。说话人与广场上的人群打成一片,它不与大家对抗,不教训,不揭发,不恐吓众人,它与大伙一起发笑。任何一种统一的、哪怕是稍稍有点阴森、严肃、恐惧、虔敬、顺从的音调都未渗透到它的语言中去。这完全是欢快的,无所畏惧的,洒脱不羁和坦率直白的语言,与种种语言的禁忌、限制和客套不同,它自由地唱响在节日的广场上”[9](P190)。这些异常生动、活跃、响亮的吆喝声,为我们描画出了五光十色的人群形象,我们能从中听出人群中的各种社会成分,分辨出他们节日吆喝的个性化特征。狂欢节始终洋溢着愉快的笑声,人们之所以要笑,是因为节日的时空中充满了除旧布新的变化要素,把一切都纳入到了死亡和再生的轨道,让世界充满了生机,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节日广场的时间,就是渗透了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时间,是带有山野草舍占位者的乐观主义的时间,山野草舍占位者在这种世界里寄托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世界像物质—肉体一样,在时间中不断地再生和更新,并且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好。它一直在朝着黄金时代进发,而不是走向末日的审判。因此,我们不必恐惧,而应充满快乐,在快乐中为中世纪的末日论脱冕,并且“在物质—肉体的层面上复活它,使它降之于大地,使它肉体化,把它变成美好的和欢乐的时间”[9](P274)。
狂欢节广场一个重要的演出节目,就是给国王加冕和脱冕。狂欢节的国王是由小丑打扮成的,当他的统治期结束之后,人们又给他换装,把他滑稽改变成小丑模样,对他进行嘲笑、辱骂和殴打,辱骂和殴打是对皇帝脱冕。整个过程是一出欢乐自由的游戏,它的起点就是用掷骰子的方式来选国王和王后,把所谓最吉利的一掷称为王点。这个游戏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它的加冕—脱冕游戏形象,似乎浓缩着人生的上升—下落、获得—失去、幸福—不幸。“在这个游戏中,既有主角,也有欢笑的合唱团。主角就是旧世界的代表,然而这又是一个孕育并生育着的世界。人们殴打和辱骂它,然而这殴打是创造性的,因为这些殴打有助于新世界的诞生。因此殴打就成为欢乐的、悦耳的、节日般的了。辱骂也具有同样创造的和欢乐的性质。”[9](P237)
狂欢节是关怀身体,放纵身体,愉悦身体的节日。节日的参与者全是“身体”化的人,他们创造出各种怪诞肉体形象,在广场里游行,比如驮着巴比伦淫妇人的怪物,长着硕大身体的巨人,跳着性感舞蹈的年轻人等。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身体”特性,强调“身体”的凸出部凹陷部,强调不同“身体”亲密结合的可能性,强调结合的愉快以及再生产的价值。于是,生命现象中原来被视为决然对立的因素,现在走到了一起,游戏般地交替着。世界历史也似乎成了时间的游戏,但这游戏不是末日审判前的绝望的放纵,而是节日庆祝者欢乐情感的自然流露。它向我们宣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那就是带着欢笑看世界,带着愉悦享受人生。它与日常的生活世界大不相同,那个由宫廷庙堂占位者主宰的世界,要求人们皱着眉头看世界,憋足劲儿担负人生。狂欢节是山野草舍占位者自己创造的节日,山野草舍占位者自己就是狂欢广场的主人,他这时摆脱了平日被压抑的不爽,受排挤的郁闷,抛开了平时令人不快的一切严肃、庄重的东西,尽情地享受快乐。
广场里的人赞美充满生机、具有生育能力的人体及其部位,因为它给人类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希望;否定那些衰老的“身体”,嘲笑那些不育的精神,因为他们断绝人类再生的可能性。拉伯雷小说中巴奴日的话很有代表性:“其实丢掉脑袋,不过死一个人,可是丢掉那玩意儿,等于死了全人类”[9](P364)。“身体”下部与人类整体的创生紧密相连,因此在广场受到特别的重视,给予加倍的放大,达到严重超出正常人体比例的程度,头颅因为与人类的生育乃至再生没有直接关系,则被无限缩小甚至忽略,从而成为一种怪诞人体。怪诞人体的中心不是头颅,不在人的上半部,而是人的生殖器官,是人体的下半部。拉伯雷小说中描写“身体”,总是把中心集中在人体凸出和凹陷的部位——肚子、性器官、嘴巴和臀部。因为,这些部位显示的人体总是形成中的人体,是未完成的,它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打开边界对外开放,与他人他物始终处于越界的交流状态,一方面向世界输出自我,一方面从世界中吸纳非我,让人永远处于生生不息的更新之中。用巴赫金的话说,“它永远都不会准备就绪、业已完结;它永远都处在建构中、形成中,并且总是在建构着和形成着别的人体。除此之外,这一人体总是在吞食着世界,同时自己也被世界所吞食。因此,在怪诞人体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生长业已超出自身、业已超越自身界限,新的个体开始发端的那些部分和部位,即肚子和男根。在怪诞人体形象中,它们起着主导作用”[9](P368)。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凸起部位和孔洞的特点在于,正是在它们身上,两个个体间、以及人体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它们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换和双向交流。因此,怪诞人体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人体戏剧的各幕:如饮食、饮料、粪便、交媾、怀孕、分娩、发育、衰老、疾病、死亡、折磨、肢解,被其他人体吞食,都是在人体和世界、或新旧人体的交界处进行的”[9](P368)。“身体”的凸出和凹陷的部位,似乎显示出“身体”力求挣脱个体范围而与其他“身体”、或非“身体”世界联系起来的愿望,这是处于临界点的怪诞“身体”,它生长着、与其他的“身体”结合着、死亡并孕育着,它是人类整个的“身体”,是宇宙自然的象征。处于临界点的怪诞身体,在与其他身体的自由交往中,展示自身的生机与活力、表演各种亲密交往,越界融合的戏剧,享受人生在节日广场演出中获得的巨大乐趣,它一旦成为宇宙自然的象征,也就意味着向严肃古板的世界,为我们展示出它调皮好玩的一面,让我们也轻松快乐一把。原本沉重难忍的人生,因为有了这种轻松和快乐,变得特别值得一过。
当今,随着科技理性霸权地位的日益扩张,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生活变得日益严肃,乡野的地盘日渐萎缩,山野草舍占位者用身体在广场进行狂欢的场面几近绝迹,要想感受节日广场的热烈氛围,体验广场节日的欢乐情怀,只能去阅读狂欢化的文学作品了。因为,“在文学发展的所有时代,狂欢节,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却是潜藏着的、简洁的、难以把握的,只有在文艺复兴时代它才不仅格外强烈,甚至直接而清晰地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文艺复兴,可以说,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9](P317)。这既让人感伤,又让人欣慰。感伤的是人类自己用身体创造由亲身感受的狂欢节,在今天离我们的身体距离越来越远;欣慰的是毕竟以拉伯雷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用生花的妙笔创造了狂欢化的文学作品,使我们有机会通过文学来体验本该属于我们的身体的狂欢。
收稿日期:2009-09-01
标签:巴赫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