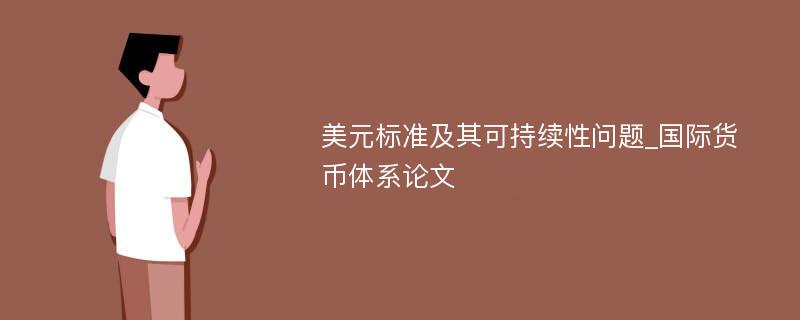
美元本位制的问题及其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持续性论文,美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金融动荡。这些变化在相当程度上都根源于美元本位制。换言之,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贸易格局以及金融运行规则;美国凭借美元支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资源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经济金融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全球各国寻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应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际,深入研究美元本位制与全球经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元本位制与全球经济失衡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由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失衡构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国内外学术界已经作了深入的探索。但笔者认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本位制这一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第一,美元本位制下“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产生。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可以对称性地保持本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并内生地决定本国的价格水平,而不需要哪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扮演名义锚的角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逐渐形成。该体系以盯住黄金的美元作为计价标准,将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在官方平价上,从而使美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而其他国家则处于该体系的外围。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本位制下,这一“中心与外围”的格局并未改变,即处于该体系中心的美国成为掌握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而其他外围国家则成为“贸易国家”。①具体来说,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而只是依托美国强大的政治、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扩张开始从贸易和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与“金融国家”的地位。而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贸易国家”则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强化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即通过不断投资扩大生产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并通过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吸收过剩的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即美国主要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与金融产品,从货币金融资产的不断交易与周转中获益;而“贸易国家”则主要提供制造业产品,从而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演变为“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这一格局。
第二,美元本位制下“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经济关系的失衡以及自我强化。由美元本位制所导致的“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这一格局必然引发全球经济失衡。这是因为,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以在无需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从“贸易国家”获取所需的商品,而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国内投资,实现低储蓄高消费,进一步增加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了国内一部分制造业的衰退或向国外转移而第三产业则迅速发展,从而需要大量进口弥补需求缺口;而美国服务业的产品多为非贸易品,其优势不能弥补制造业的劣势,进而导致其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在1973-2007年这一期间,除了1974年、1975年、1976年、1980年、1981年以及1991年这6年之外,其余29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都处于逆差状态)。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增速加快,在2007年达到7312.14亿美元(占其GDP的5.29%),这意味着美国吸收了全球75%左右的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贸易国家”的经济资源则更多地配置在本国的出口部门,导致国内的非制造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使商品贸易自由化迅速发展与金融发展水平滞后的矛盾不断加剧。因此,“贸易国家”的高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与消费,而主要依靠大规模引进FDI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通过汇率长期盯住美元使其劳动密集型和低端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获得出口竞争力,从而造成经常项目的顺差。19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经济关系失衡的突出表现。②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在2000年达到838.1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0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562.7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31.4%。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是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因为中国处于东亚产业分工链的末端,许多技术与中间产品都来源于本地区。
值得关注的是,美元本位制下“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经济关系的失衡存在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即美国通过对“贸易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不断扩大商品进口输出大量的美元,“贸易国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贸易国家”只能把所积累的美元重新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国债即形成对美国的资本回流。美国与“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与金融失衡由此得以持续并不断扩大。这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以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最为典型。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6月,中国(仅指中国大陆地区)对美国的证券投资达到9220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60%),而美国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仅为970亿美元。长期稳定的美元回流不仅帮助美国维持了低储蓄率、高消费、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与高经济增长率的并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成为美元的“人质”。根据美国经济学家Brad Setser的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8月~10月这一期间增持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达到7500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过日本(595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之所以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仍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主要是为了减少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换言之,如果中国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为了推销新发国债,必然会大幅提高新发国债的收益率,从而导致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进一步缩水。③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元本位制内在的特殊的融资机制,调整“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经济关系失衡的传统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通过“金融国家”的货币贬值来调节这两类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失衡,会由于“贸易国家”不断买入美元以避免美元资产损失的逆向操作而失效;而通过“贸易国家”货币的升值来调节这两类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失衡也未必有效。如“广场协议”以后的日元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状况;至于2005年7月21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不但没有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④
二、美元本位制与全球流动性过剩
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性过剩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⑤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全球的流动性自1996年以来迅速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其中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广义货币存量与其名义GDP之比在1996-2006年这一期间上升大约1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存量与名义GDP之比上升约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01-2003年这一期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全球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迅速提高(最高分别达到8.9%和13%),最终导致全球经济面临流动性过剩。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传导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美元本位制是引发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美元本位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必须承诺依照固定价格允许成员国中央银行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成为其货币发行的硬约束;而在美元本位制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不受任何实物约束,即美元的发行没有黄金约束,美国国债的发行也没有国内储蓄的约束(邓肯,2007)。因此,美元本位制下全球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流动性状况。自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2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并将这一超低利率保持到2004年6月。因此,从2001年起,美国狭义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幅上升。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2-2006年,美国的股票市场价格涨幅达到75.5%。同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从2003年开始出现快速上升,到2006年翻了一番左右。资产价格的上涨造成家庭财富价值上升,进而导致许多居民进行举债消费。与此同时,流动性过剩促使美元不断贬值,一方面造成全球能源及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助长了能源与初级产品交易中的投机行为,出现了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推动现货市场价格上涨的倒逼现象,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从2006年开始,全球各国的一般价格水平不断上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5月,发达国家广义通货膨胀率和核心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3.5%和1.8%(其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和核心通胀率分别达到8.6%和4.2%(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7.7%)。
第二,美元本位制下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使流动性过剩不断向“贸易国家”蔓延。首先,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使那些寻求高收益的资金大量流向“贸易国家”,与巨额贸易逆差一起造成美国直接输出大量的美元;另一方面,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导致国内储蓄率不断下降以及政府投资与私人消费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经常项目逆差,成为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元从而引发美元泛滥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元本位制是浮动汇率制,即美元与主要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美国没有保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因此,为了应付汇率波动、干预外汇市场从而获得稳定的金融环境,“贸易国家”通常需要主动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贸易国家”又因为担心减持美元会促使美元贬值,导致本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缩水,从而不断被动地买入美元使其外汇储备陷入被动增长。⑥其结果是,一方面,美元储备货币的积累造成央行货币投放增加,并通过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使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不断膨胀;另一方面,输入的资金通常具有较高的活跃度,从而使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货币流量的增加和流通速度的加快推动了价格(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和交易量(GDP和资产交易)的膨胀(殷剑峰,2008)。最后,由于“贸易国家”普遍采取有限灵活的汇率制度,⑦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金融国家”的流动性过剩进一步诱发“贸易国家”的流动性过剩。
第三,美元本位制下美国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也是促使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向全球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7年,包括以利率、外汇、股权、商品以及信贷为基础的远期、互换和期权等产品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超过500万亿美元。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创造信用的能力显著提高,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同时,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背离。据统计,目前全球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165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3.7倍(两者的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还大体相当)。⑧因此,随之增加的美元供给成为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在金融创新中,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原本无法参与金融交易(或交易成本非常高昂)的资产变成金融资产,成为抵押贷款或其他融资手段,从而导致流动性资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三、美元本位制与全球金融动荡
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美元本位制以来,制度约束明显弱化,成为“无体系的体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提供全球性汇率稳定机制等全球性公共产品与明确的国际金融规则,其“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也在无形中受到削弱;全球范围内也不再存在以往的那种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非正规化的汇率政策协调。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元本位制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
第一,美元本位制加剧了长期利率波动。麦金农(2006)通过对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本位制下长期利率的波动情况的对比,指出全球长期利率水平在美元本位制时期更具波动性。最为明显的是1973-1990年美国长期利率的平均变动率达到111%,远远高于金本位制时期的14%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29%。长期利率的大幅波动意味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全球经济面临诸多的风险。而导致长期利率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本位制下各国货币汇率可自由浮动。具体来说,由于汇率可自由浮动,投资者面临的实际汇率风险不能被完全对冲,导致不同的风险溢价,进而增加了利率水平的波动性。此外,利率水平的差异会进一步导致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平变化不一致,这种相对价格风险通过国际投资者不断变换其以不同货币计价的资产组合也会引发利率水平的剧烈波动。因此,虽然浮动汇率使一国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同时面临贬值与升值压力的美元汇率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长期利率水平的无序波动。
第二,美元本位制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在美元本位制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也不断加快。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远远高于全球GDP的年均增长速度(3.8%)和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7%)。其中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流动的资本规模持续扩大,在2006年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8%。与此同时,国际证券投资的规模超过直接投资,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主要形式。1990-2002年,国际债券发行总额和国际股权发行总额分别增长了约480%和600%。2006年流入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欧元区的国际证券投资分别为10174亿美元、1986亿美元、2944亿美元和10177亿美元,均大于流入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额。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证券投资也呈快速增长之势,在2006年达到2119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23.5%。⑨其中不乏大规模的投机热钱。如2003-2008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总额为1.2万亿美元,热钱利润为5500亿美元,二者之和相当于2008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⑩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元本位制下无约束的美元信用创造出过剩的流动性。随着各国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过剩的流动性逐渐形成大规模和快速的国际资本流动,进而成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会加剧流动性过剩,推动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迅速流出,会促使一国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并通过负的财富效应影响其实体经济。
第三,美元本位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扩散。自美元本位制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的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并多次爆发货币金融危机。据统计,在过去的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2002)。虽然每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动因不同,但大多数金融危机在本质上都与美元汇率以及利率的调整有着紧密联系。美国作为处于美元本位制中心的“金融国家”,其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无论美国实行弱势美元政策还是强势美元政策,由此导致的其他国家的流动性的迅速膨胀和收缩都可能触发金融危机(典型的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当美国经济金融运行的某一环节或某一领域由于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出现问题时,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也都有可能出现动荡或危机(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此外,由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国与“贸易国家”的地位不对称,“贸易国家”的金融风险大多在同类国家之间传递,很难影响到美国;而美国的金融风险则很容易蔓延到全球。另外,金融危机的传递途径也不同。如果“贸易国家”的金融危机没有触及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则只会形成在“贸易国家”之间传导的区域性危机,而不会形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反之,如果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则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贸易国家”,从而形成全球金融动荡。如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不足与信贷紧缩导致了全球股市大幅下跌,从而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而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主动采取美元贬值的做法,则推动了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由此可见,美元本位制决定了“金融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更容易全球化。
四、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续性
由于美元本位制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本位制是否可持续,因此,美元本位制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回顾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不难发现,国际货币本位在初期都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稳定国际价格体系,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本位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导致严重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进而使该货币本位不可持续。具体来说,在金本位制初期,黄金可自由兑换使汇率最终必须恢复到铸币平价水平,从而保证了汇率的长期稳定。(11)此外,各国保持本币对黄金的固定比价,稳定了各国国内的价格水平。因此,在金本位制初期,国际贸易与投资显著增长。随着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黄金逐渐向英国集中,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然而,由于黄金的稀缺性,全球流动性容易突然紧缩并在短期内加剧各国价格水平的波动。(12)同时,有限的储备资产约束了国内信贷的增长,汇率稳定与通货紧缩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金本位制崩溃,英镑也丧失了霸权地位。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一种“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体系确立的初期,良好的美元信用与汇率和价格的锚定作用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促进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缓解了通货膨胀并降低了失业率。然而,各国迅速积累的美元债权与美国有限的黄金储备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特里芬两难”等问题最终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美元本位制时代。美元不再维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其价值以美国的信用为基础;各国不必维持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汇率安排也更加多样化。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证明,当单一的主权国家货币充当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时,该主权货币本位制存续的条件主要包括:第一,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充足;第二,该主权国家的货币价值稳定;第三,该货币的发行国应维持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对称的经济、金融实力。美元本位制自确立以来基本上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具体看来,首先,在美元本位制下,由于美元已经完全与黄金脱钩,美元的供给量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换言之,美国在理论上拥有近乎无限的以本币计值的国际信用,可以通过不断发行美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流动性需求。其次,在美元本位制下,由于美国不再承诺美元与黄金可自由兑换,因此贸易顺差国只能被动地将其积累的美元投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从而使美国可以在国际收支失衡的条件下保持美元价值的稳定。再次,在美元本位制下,“贸易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贸易国家”)在汇率安排上对美元的依赖性较为明显,从而不得不维护美元本位制。“东亚国家越是希望保证对美国的出口,就越要维持汇率安排上对美元的依赖;而越是维持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就越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美元外汇储备。”(13)由于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贸易国家”害怕美元贬值使其储备资产价值缩水,从而继续购买美元资产以稳定美元汇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贸易国家”都已被美元“绑架”。最后,美国在经济、科技以及金融等领域的综合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元依托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基础,成为国际核心储备货币。此外,在美元本位制下,“贸易国家”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方式持有美元储备,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其结果是美国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国内的“储蓄—投资”转化率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强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
从短期来看,由于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等问题的积累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美元本位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具体表现为:美元价值不断下降以及全球价格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动荡不断加剧;至于美联储所采取的降低利率和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应对次贷危机的做法,则使全球流动性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不断扩大。此外,随着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等主要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这一方面将动摇美元本位制所依赖的经济、金融基础,另一方面打击了各国长期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笔者认为,尽管这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元本位制,但美元本位制短期内仍将持续。首先,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欧洲和亚洲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但美元资产在短期内仍然是最主要的避险工具。(14)其次,短期内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能够完全替代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结算的比重接近90%;美元储备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中占63%(而欧元仅占26.8%)。美元依然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与计价支付手段。最后,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与美国拥有的强大否决权决定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不仅可以获得大量铸币税收入,而且掌握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从而能够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的资源财富。因此,美国很难放弃发行国际核心货币带来的霸权收益(Shelton,2008),即美国在积极维护美元本位制的同时,会抑制其他强势货币的崛起。
然而,从长期来看,美元本位制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而难以为继。首先,由于美元的发行不受约束,当美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时,美国可以在不实行紧缩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大量发行美元以满足对外支付的需要。其结果是,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与对外债务不断累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被严重削弱,美元本位制将面临美元储备资产供给充足与美元价值稳定难以同时实现的“新特里芬两难”。其次,在美元本位制下,“贸易国家”无法以本币提供国际信贷,这必然引发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从而使其对外资产面临由于美元贬值而损失的风险。因此,“贸易国家”仅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维护美元本位制,即当稳定且低估的汇率带来的收益超过其外汇储备增长带来的成本时,“贸易国家”为了维持其美元储备资产的价值才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购买;而当“贸易国家”面临美元的大幅贬值与本国外汇储备资产严重缩水时,则可能采取以邻为壑竞相减持美元资产的政策。此时,美元本位制将难以持续。正如Eichengreen(2004)所指出的,外围国家不存在强有力的行动集团,当单个国家的利益与所有外围国家的整体利益产生冲突时,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可能会竞相抛售美元从而导致美元本位制难以为继。再次,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的净对外债务由于“贸易国家”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不断上升,同时促使美国在低利率水平下形成了低储蓄、高消费的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然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证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贸易国家”长期坚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其承担了各种福利损失并面临诸多政策困境,(15)因此这些国家在长期内将逐渐调整或转变其经济增长模式,进而改变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国际金融格局。这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或转变都会对美元本位制形成冲击。最后,欧元区经济、金融的迅速发展使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日益提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欧元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比重已经从1999年的17.9%增长到2008年的26.8%。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不断加强,人民币的区域化程度也日益加深。这些趋势在长期内都将会削弱美元在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对美元本位制形成挑战。
综上所述,由于美元本位制在很大程度上将“贸易国家”与美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贸易国家”的“去美元化”成本很高。因此,“贸易国家”在短期内不得不与美国共同承担维持美元稳定的责任。但在长期内,美元本位制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存在较大争议。(16)笔者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全球各国通过协商确立一种能够有效地限制和约束美元霸权的制度安排,逐步打破单一主权国家的货币本位制,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当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改革最终将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三极鼎立将是这种博弈的结果。
注释:
①所谓“贸易国家”,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因而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金融国家”是指掌握“金融霸权”的国家(李晓、丁一兵,2006)。
②因为美国和中国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在所难免(华民,2007)。
③张明.为何中国央行仍在增持美国国债[R].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08076,2008.
④据美国商务部报告,2008年9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8月份的253.3亿美元扩大至277.7亿美元。引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http://chinese.wsj.com/gb/20081113/BUS007985.asp?source=NewSearch.
⑤需要指出的是,在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各国普遍面临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全球流动性日趋紧缩,本文所研究的正是此前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
⑥据统计,1999年底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仅约为1.05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59%),2007年底上升至4.9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77%),增长了3.7倍。其中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最为迅速。199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0.16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9%),2007年底上升至1.53万亿美元(占全球规模的24%),增长了8.6倍。数据引自张明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现状及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08057,2008)。
⑦麦金农等学者在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之外)的汇率波动性时,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都高频地盯住美元,美元在亚洲国家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McKinnon and Schnabl,2004)。
⑧Martin Wolf.The New Capitalism[J].Financial Times,2007(7).
⑨IMF.Containing Systemic Risks and Restoring Financial Soundness[R].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April,2008.
⑩张明,徐以升.全口径测算中国当前的热钱规模[R].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0814,2008.
(11)Michael Bordo.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Some Lessons for Today[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May 1984.
(12)Richard N Cooper.The Gold Standard:Historical Facts and Future Prospects[R].Brookings Pap.Econ.Act.,1982(1).
(13)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7.
(14)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在继续加深,但全球各地的企业和银行纷纷增持美元,这或是因为它们需要美元来做生意和偿还贷款,或是因为它们将美元视为避风港。参见《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http://chinese.wsj.com/gb/20081117/hrd104921.asp?source=New Search,2008年11月17日。
(15)项卫星,刘晓鑫.中美金融关系的动态演进[J].当代亚太,2007(11).
(16)向松祚(2008)较为详细地论述和总结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相关问题,包括改革的方向与可能的实施方案。参见向松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前景和可能方案[EB/OL].清华环球财经高级论坛,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43867.html,2008年12月21日。
标签: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流动性过剩论文; 外汇储备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国际黄金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货币流动性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金融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黄金美元论文; 银行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次贷危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