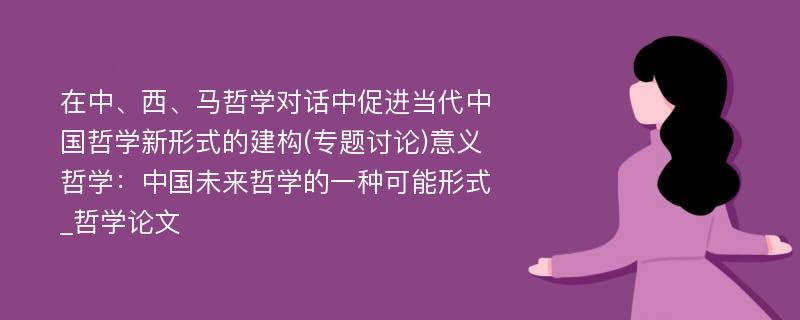
在中、西、马哲学对话中推进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专题讨论)——3.意义哲学: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在中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讨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方互动,不仅是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其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风云际会为这种互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正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在中国相遇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传统由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三者的对话互动中推进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设显然是一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大课题。限于学力与篇幅,这里只想在三方互动的框架下、从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开展的角度,对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的形态作一探讨。我的基本看法是:体现了现代实践哲学要求、涵容了科学理性精神、以人生价值安顿问题为思想主题的“意义哲学”①,将是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对民族哲学传统的承继指向了“意义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中心展开思想形态,是中国哲学传统的重要特色。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厘清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得到较多认同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关注的中心是人生问题特别是生命价值的安顿问题。张岱年不仅把人生论与宇宙论、致知论一起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干”②,而且把“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看作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之③。在此基础上,他还明确指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④,“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论即人生理想论”⑤。作为港台地区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两个重要代表,劳思光与牟宗三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劳思光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间作出了“认知性的哲学”与“引导性的哲学”的区分,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道各家)皆重视自我之转化,因此强调体验、境界与直悟,对于思辨本不重视”⑥。牟宗三则用“生命”与“自然”来标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领导观念”。他指出:“由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就可把握中西哲学发展之主要纲领的差异何在。……我们可说两个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一个是生命,另一个是自然。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对象’,这是领导线索。”⑦而“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生物学研究的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实践中的生命”⑧。由此,中国哲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就区别于西方哲学:“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⑨成中英则用“知识”与“价值”来判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他看来,相对于知识形态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处处紧扣人生的中心价值来思考问题,它“本质上是价值哲学,是对宇宙价值、人生价值、人类价值、社会价值深沉的肯定与体证”⑩。
中国哲学的上述基本特质在20世纪作为现代学科而确立起来的“中国哲学”中亦得到了清楚的表现。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在相当程度上规约了国人对哲学的认知。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一种以客观认知自然、社会等外在对象为指归、以求“真”逐“实”为标的的知识论系统,人生问题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们在对哲学予以界定时,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到了人生问题。在胡适看来,“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1)。尽管他后来觉得“根本”两字意义欠明,因而重新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但依然强调了哲学与“人生切要问题”的内在关联:“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使用的意义。”(12)同样,冯友兰不仅认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引者按:指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13),而且明确地以如下话语论说哲学:“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14)其次,注重人生问题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正如有论者已注意到的,中国现代学界对哲学的基本理解,是将之看作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这种理解的精神实质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15)这显然与西方学术图景中的哲学有着相当的间距而与中国哲学的自身传统在深层次上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
顾名思义,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理当具有“中国”特色。由于思想自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因而这种特色又应当是与中国哲学传统有着直接关联的。人类理解活动的本性决定了即使是国人在充分自觉的状态下力图全盘照搬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依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其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具有正向联系的精神特质。这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已得到了清楚的证明。同样,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也不可能在思想主题等方面彻底褪掉与自身民族传统具有正向联系的“底色”。因此,体现时代特点、以人生问题为思想主题的“意义哲学”,应当可以看作是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
第二,中国哲学的“大综合”呼唤体现了现代实践哲学要求、涵容了科学理性精神的“意义哲学”。早在1937年,沈有鼎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三期说,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已完成了先秦与宋明两次大的综合,当下的时代是一个继此之后走向新的大综合的时代。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处于这个大综合的时代中。在这个意义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间的对话互动,走向当代中国哲学中上述鼎足而三的主流形态间的融合会通,堪称是中国文化完成大综合之时代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就包含了中国哲学借鉴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内在要求。从回省的眼光看,中国哲学传统之所以在进入近代以来逐渐走向衰微,与下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是在思想内容上,由于中国哲学传统专注于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而对“理性精神”(16)的显发缺乏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能够发展出以科学、民族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形态。二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更为注重以内在化的进路做修心养性的功夫,因而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缺乏一种客观的物质性力量,不能有效地发挥影响乃至转化社会的实践性作用与功能。耐人寻味的是,上述两方面也正好分别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颇见精彩之处。现代理性精神不仅首先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表现出成熟形态,而且成为作为西方现代化运动之精神结晶的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正是理性精神的凸显,才显发了人所具有的认识与征服外在世界的能力,从而不仅成为自然的主人,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亦获得了自我做主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更是十分鲜明的。早在葛兰西那里,就以“实践哲学”来称谓马克思主义,以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性力量。进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视野中,在明确强调理论活动的有限性、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根本性存在方式的意义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者的马克思,正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开创者。(17)
因此,如何在上述两个方面借鉴与学习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中国哲学通过三足鼎立的互动对话以更为充分地体现时代要求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生活实体,中国哲学要想对现代人生与社会发挥现实的影响作用,就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客观知识问题这一“历史考验”。所以,如何在注重价值问题的中国哲学中凸显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性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就成为中国哲学之现代开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它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价值系统的根本改变”(18),因而尽管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时至今日依然还是一个尚待完成的时代任务。而要突破中国哲学现代开展的这一瓶颈,继续向西方哲学学习的历史进程无疑是必要的。同样,无论是在通过实践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影响乃至转化社会的现实作用方面,还是在根据时代要求实现从古典形态的“实践哲学”向现代实践哲学的转化方面,中国哲学都应当借鉴乃至师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互动,或许是一条在现代实践哲学的平台上“重兴”中国哲学之实践智慧的可能道路。可以认为,中国哲学大综合的时代要求呼唤着体现了现代实践哲学要求、涵容了科学理性精神的“意义哲学”。
第三,全球性的文明对话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省、批判乃至明确倡言要“抛弃现代性”(19),鲜明地表征了西方文化在当今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局限。因此,尽管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生命活力、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现代人类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进步是不容否认的,但在今天,西方文化已难以独立地承担起为人类的未来指引光明前途的历史任务。由此,当代人类文化建设的基本取向已不再是“非西方文化如何按照西方式的现代性彻底改造自己”,而是“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解决地球村所面临的共同困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意义哲学”将有可能参与到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之中去。“意义哲学”的思想主题是生命价值的安顿问题。立足于自身独异的精神特质,中国哲学成就了一套与西方具有相当差异的价值系统。这在各自的终极关怀即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形态中得到了集中表现。中国哲学所成就的,是一个归根结底依靠人类自身就足以安身立命的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而西方则是以上帝为最终依归的。就理论逻辑的彻底性而言,人类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只有两种基本形态:要么人类“自我做主”,要么依归于外在于人类的“绝对实在”(如上帝)。因此,上述两种形态堪称是构成了人类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两种基本形态。进入现代以来,上述两种终极关怀形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西方式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而言,正如丹尼东·贝尔所指出的,“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20)。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缘由在于:在文艺复兴以来上帝遭到放逐的同时,“人”却至今尚未真正摆脱“原罪”的束缚,还不具备吾性自足、自己赋予自己的生命以终极性意义的完备性,依然是一种归根结底不能自我做主的存在者。在这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哲学”或可为西方文明提供某种借鉴,从而为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它应当可以看作是未来中国哲学的一种可能形态。
注释:
①刘述先教授曾以“意义哲学”称谓其相关主张(刘述先:《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本文“意义哲学”的提出与受刘述先教授启发有关,但与其具体含义不尽相同。
②③④⑤《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3、8、194、61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⑥吴有能:《百家出入心无碍——劳思光教授》,第56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⑦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⑧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⑩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30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2)胡适:《哲学与人生》,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期,1923。
(13)(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载《学术季刊》,2000(4)。
(16)需要指出的是,“理性”是一个含义颇为丰富的概念。在广义上,它可以指与迷信、愚昧无知相对立的人之健全的理智、思想和知识。这里所谓“理性”,是指以人类健全的理智为基础的、首先在西方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文化传统之中表现出其成熟形态的、以现代科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人类精神机能。
(17)王南湜:《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问题》,载《光明日报》,2004-08-31。
(18)余英时:《历史与思想》,第16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19)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20)丹尼东·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4页,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实践哲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