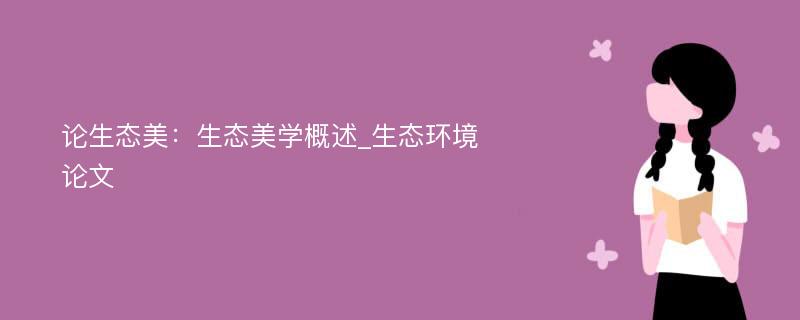
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美学论文,美放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当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便相继踏上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道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便是工业文明高奏凯歌、达至辉煌的时代。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向大自然进军,创造出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当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大干预超过了自然界的自身调节能力时,人类便陷入了生态危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由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便成了当代的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整个人类的面前。众所周知,人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首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人又要依靠自然界而生存,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人生存的前提。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贯穿着整个人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曾经把人的产生看作是人自己劳动的成果,马克思非常赞赏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和合理性。恩格斯则进一步抓住劳动的本质,对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劳动中的演进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双重过程。人的进化正是生物进化和社会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具有理智的头脑和能劳动的双手。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却能主动地改变环境。
人类通过对土地的耕种和动物的驯养开创了农业文明。由此在生命水平上实现了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主宰,也确立了人类在物种世界中的主导地位。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创造了有文字记载的灿烂历史。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人们的泛生命意识,农业文明则开始了人们定居的生活,由此使人产生出田园牧歌的家园感受。但是,自然经济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它使人受制于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种文明不可能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的束缚,人类也无力与大自然相抗衡。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在短短的二百多年时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农业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这是一个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企图“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时代。虽然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了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3页)但是,这位哲人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当自然界对人的报复和惩罚一再地、大规模地出现时,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就不得不认真加以审视和思考了。
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已经确认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及《21世纪议程》,由此揭开了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序幕。
人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败。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可持续发展方针的确立,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而在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中,生态审美意识和生态美学观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审美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人类文化生存方式和精神境界,它是人的生命活动向精神领域的拓展和延伸。美作为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和丰富性,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
二
生态美学的研究,是以当代生态文化观念对相应审美现象的再认识,它把人类历史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审美观,提高到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形成生态美这一特定的审美范畴。生态美首先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它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
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为我们指出,自然界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人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员,生活在地球这一生态系统之中。阳光、大气、水体、土壤等非生物环境作为生物生存的场所和物质成分,构成了生命的支持系统。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关系,没有自然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也就不会有自然的生态平衡。因此,生物物种的消失、森林和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等都会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失调和破坏。
当然,人类的生态过程不同于生物的生态过程,因为人的生态系统涉及人的种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的种群构成了社会关系,它以一定的文化形态存在着。因此,人的生存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就使人的生态结构具有了多层次性的特点,除了自然生态,还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甚至精神生态的内容。但是,在这里自然生态具有生命存在的基础性质,而各个生态层次之间则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为中介的,这说明人类生态过程的特殊复杂性。
美是一种价值存在。审美价值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一种价值属性。也就是说,人是衡量美丑的尺度。美具有直观的形象性,它可以为人所感知并唤起人的愉悦的情感体验。但这绝不是说,美只是审美对象自身的物质属性,或者是审美主体的情感在外部事物上的投射或移情。价值关系体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
审美需要源于人在创造性劳动中所体验到的生命活动的自由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125页、126页)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超越, 人的社会实践把自然的规律纳入了人的目的的轨道,从而体现了人的创造的自由。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自我意识功能,是对人在对象世界中活动自由的自我确证和自我观照。
生态审美是人把自己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作为审美对象而产生的审美观照,它不仅是对人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它把审视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生态效应上。所以,生态美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生命共感。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在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展开的,它是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之上的。
人对生态美的体验,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它体现了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生态美只有内在于生态系统才能感受到,也只有人通过自身生态过程才能感受到。在这里,不能把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判然分离开来,它真正体现了审美境界的主客同一和物我交融。“河流、雨林、旷野、冰川和所有生命种群,都是作为体验者的我的一部分,我与生物圈的整个生命相连,我与所有的生命浩然同流,我沉浸于自然之中并充实着振奋的生命力,欣然享受生命创造之美的无穷喜乐。”(佘正荣:《生态智慧论》,2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这种主体的参与性是一种对生态系统的融入感,是产生生命共感的基础。
早在18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席勒(J.C.F.Schiller,1759—1805)便指出:“美是形式,我们可以观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总之,美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作为。”(席勒:《美育书简》,130~13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这就是说,人的审美感受既来自对于审美对象的形象观照,也来自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状态的体认。同样,生态美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展开也构成了一种意境美和节律美。
三
生态美首先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的展示和体验中。人生是一个过程。人的生命之美应该是一种过程之美,美存在于生命的过程之中。对于人的审美体验,过程本身重于结局,即使是成功的结局。过程之美,就是人们在生命的搏击中留下的足迹,它们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印证。生态美作为生命过程的展示,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同一。当人把审美的目光转向自身的生态过程,便可在时间的流转中获得一种人与自然交融的生命体验。《周易·系辞传上》曰:“生生之谓易。”生命在新陈代谢中不断获得新生,又在文化创造中不断丰富它的意义蕴涵。生态美作为人的生命的动态过程,无不跳跃着生命的搏击和律动。
生态美所展现的人的动态生命律动,存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流程中。现代生活方式为人们在生活形式上提供了众多的选择,它反映出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个性发展的多样性。生活形式的千姿百态、生活风格的异彩纷呈与生活方式在价值取向上的统一,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社会生态景观。生态消费观确定了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点,把中和适度作为新的黄金比例;劳作与休闲的变奏使生活节奏化和富有韵律感,它们既为人提供了生活情趣,也提供了生命感悟。
生态美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道德境界,一种是宗教境界,另一种是审美境界。道德境界追求的是一种无条件服从于群体利益和意志的状态,它具有一种外在的伦理制约和行为规范。宗教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皈依上帝和遁世态度,它的思想基础是人对神灵的绝对依赖感。而审美境界追求的是主体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相结合的主客同一的境界,它的和谐是非伦理而又超道德的自由。
在审美过程中,人突破了日常的感觉方式,专注于对世界的观照和体验,形成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把握。审美体验是以自身的真情实感为基础的,它不仅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也是对于对象意蕴的领悟过程。审美体验中的想象是指向意义、创造意义世界的想象,由此使人进入情感世界。审美超越所追求的是人与现实、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人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和谐统一。所以,审美使人的心灵在形式感受、意义领悟和价值体验中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自古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审美文化成果,丰富着人的审美经验,有助于促进人的理想、情操和人格的完善,从而发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大自然本身就是富有秩序的,秩序感使人的生活有序化。建立在生态平衡基础上的生态环境,会以其自身的生活秩序给人以美的感受。人生活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某些人为建立的秩序关系,如果与自然规律以及人的生理、心理规律相背离,就会干扰人的活动,使人产生不愉快的感受。从居室和劳动环境到整个城市景观,都是人的现实生态环境,它们可以给人提供生态和谐的秩序感、生机盎然的环境氛围和生命蕴涵的意境。
生态审美不止于对对象形象的观照和玩味,而是一种意境的动态审美。审美形象是产生意境的基础,形象的触发唤起人的丰富联想,使人的意象超越特定形象的直接性和有限性,从而产生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效果,进一步达到对人生意味的体认。意境创造是我国艺术和园林创作的一贯传统。生态美的意境审美,可以进一步唤起人对生态观念的认同和生命真谛的感悟,“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
四
生态美范畴的确立,把人们的生态意识植根于人的情感生活之中,又把自发萌生的生态审美经验上升到美学理论的层次。这不论对于美学研究,还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深刻的意义。生态美这一范畴成为生态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生态美学,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取向对审美现象和规律的再认识,又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为对象的美学研究。它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为轴线而展开,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
生态美学不同于所谓的生命美学,它不是孤立地从人的生命现象本身去寻求人生况味和体验,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背景中围绕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去探索。生态审美也不同于自然审美,因为它把审美的目光始终凝聚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相互关系上。
生态美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功能。
其一,把主客体有机统一的观念带入了美学理论中,对于现代美学理论的变革提供了启示。生态美学克服了主客两分的思维模式,明确肯定了主体与环境客体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建立了人与环境的整体观。它反映在人的精神生活和审美活动中,便是人的心态与生态的直接关联性。没有心态的平衡也就没有人的生态的平衡。
其二,生态美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人的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和确立健康的生存价值观。21世纪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有相关理论的支撑。生态审美观不仅可以巩固生态价值观,而且可以推动人的需求和情趣向生态和谐方面转化。生态文明涵盖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关系到未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从生产活动过程和环境到生产成果的产品,从生活空间到生活消费,无一不涉及生态审美问题。
其三,生态美的研究为克服技术的生态异化指出了解决的途径。技术是调节和变革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力量,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直接参与对人工自然的构造。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中,由于急功近利的倾向和机械论科学技术观的影响,可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这便是技术的生态异化。生态美学研究可以从人的感性适应性和精神需要出发,提供生态审美的价值规范,有助于技术生态异化的解决。
其四,生态美学理论有助于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美学将从树立生态审美理想、提升人生境界的角度为切入点,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取向的思考。它将促进全球绿色运动的发展,变革那些使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不适应的体制,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此外,生态美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思路和方法。生态美以其巨大的形象感染力,成为激发人们建设未来的无限推动力。
首先,生态美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直观的尺度和导向。人们可以从生态美的环境体验中感悟到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的价值体验往往是在失而复得之后才有更深切的感受。对于自然价值的认识也必然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类正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误中,从当今不断恶化的生态危机中,从地球生态系统自身的整体性中才能真正认识自然的价值。
其次,对于生态美的观照,直接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例如:生态农业和林业利用生物群落中生物链相互支持和制约的原理,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污染,改善了景观。由此形成观光农业和林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绿色食品,而且提供了休闲旅游的场所。这就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层次上,实现了对田园牧歌的回归。同样,生态工业和科学考察也可以逐步与生态观光相结合,使人们在生态美的观照中培育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去不断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再次,生态美的开发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进生活方式向科学、健康和文明的方向发展提供了途径。具备生态美的环境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迪和审美教育,可以发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总之,生态美学研究涉及对人类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它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命运息息相关。尽管对人生的关切具有无限开放的价值取向,然而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人类幸福的前提和保障。生态美的观照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勃勃生机和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