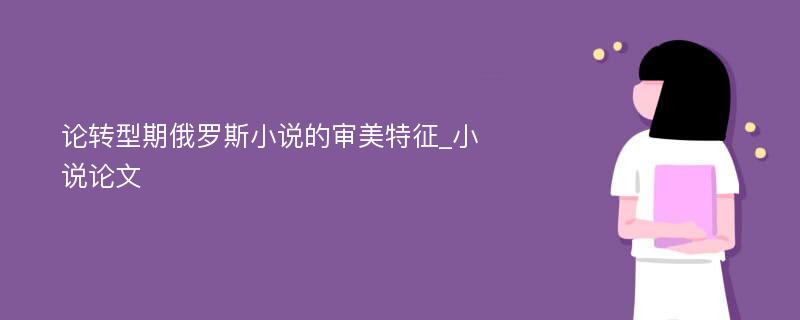
论俄罗斯小说转型期的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俄罗斯论文,美学论文,特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1989年俄国评论家丘普里宁在《文学报》上第一次提出“异样文学”这一概念以来,又有许多新的文艺学名词在评论界出现,如“新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先锋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概念是否科学暂且不论,但却明白无误地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文学与80年代前期及以前的文学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作家在内的每一个俄罗斯人现在都直接地面对着从未遇到过的错综复杂、汹涌澎湃的生活潮流,面对着处于裂变中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道德规范,都体验到了市场经济对于个人生活的重大影响。所有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观念,也改变了他们的审美习惯,并给文学原有的结构形态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小说创作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同处于转轨期的俄国经济一样,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俄国小说正经历着它的转型期。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考察处于这一转型期的俄罗斯小说创作的变化。笔者无意对小说的这些变化作全面的论述,仅想就转型期俄罗斯小说的几个重要的美学特征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
作家的审美意识明显地由作家反映社会生活,反映历史变迁向表现作家对社会生活,对历史人生的感受转变,由“干预生活”向表现自我对外部生活的感受转变。这是近年小说作品的重要美学特征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苏联小说家的创作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无疑是一种反映意识,即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反映外部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或人的命运。这一类小说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图景,再现了在苏联这块土地上的社会、历史、自然和人。80年代的小说以及中期兴起的文学回归潮中的小说体现出了这一反映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不能低估这些作品对新时期俄罗斯民族意识演进的先锋作用,它们逐渐把人们的思考中心由《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新的任命》、《穿白衣的人们》等暴露文学所展示的人间悲剧,引申到对“人生与命运”悲剧之根源何在的思考,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回归文学是如何辉煌。恰恰相反,它的思想命题今天看来,其历时性意义远远大于其共时性的意义,其伦理色彩远远浓于其对历史、对心灵的拷问。小说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的碰撞所产生的一些富有社会意义的事件,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回归”其实并未真正深入到历史哲学的深层。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映意识的庸俗化会导致把小说作为图解政策的工具,要求作家们全身心地“干预生活”,急功近利地为政治服务。
在渐趋平静的“回归”之后,当今的俄罗斯小说家越来越多地开始追求一种表现意识。他们在作品中或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知内容,或强调直觉,或强调体验,或注重发掘潜意识,但就其创作的基本特征来说,都以表现为小说的基本指归。无论作家所注目的题材如何,无论他们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有多么不同,都对小说的表现功能情有独钟,并且纷纷付诸于艺术实践。具体到每一个作家,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接受态度,其表现意识所形之于小说的特点亦有不同。
以表现城市生活见长的著名小说家马卡宁,就其多数作品来说,没有超出写实文学的传统,但近年来的创作,其基本内容则在于表现自己对俄罗斯各个阶层的城市居民的当代命运及其社会历史根源与精神心理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及至《盖着呢子、中间放着玻璃瓶的桌子》(1993)和《昌牌货》(1993)几乎只是以市民生活为载体,表现自己直觉到的,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人生状态。托尔斯泰娅的作品始终坚持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感知内容,只是扑朔迷离的风格带有更多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以冷峻的讽刺为特色的皮耶楚赫,从写《彩票》(1987)、《发水记》(1987)到《7号病房》(1992),越来越显露出对当前混乱世风的荒诞感觉。对于这一批相对年轻的作家来说,表现意识更适应他们表达主观的浪漫主义情愫的需要。俄罗斯目前最活跃,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中青年作家,象上面已经提到的,还有叶·波波夫,纳尔比科娃,叶罗菲耶夫,果连施泰因,叶尔马科夫,别列文,奥加诺夫等等,都多多少少是在浪漫主义前提下表现自己对世界人生的认知、感觉、理想与愿望,从而铸造出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至于其艺术世界与外部具象世界的关系,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色。但就其基本的审美意识来说,都可以说属于表现类的。
这一表现型特征在相当一部分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展现得尤为典型,比如,哈里托诺夫的《生命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1992),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1992)。在这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历史小说里,历史不过是作家自我体验的历史,作家沉入历史,是为了抒发他们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慨,是为了达到作家对现实、传统进行批判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历史小说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在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中,作者常常让古今的场景互相变换,甚至加进当代的人物,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读者进入历史而忘了现实。这种以表现现实为特点的历史题材小说的“现代性”是对传统历史题材小说的冲击,也正是为了表现作家自己的历史意识。而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思想倾向,其实也是与表现这一美学特征有着一定联系的。把现实看作是荒谬的,把历史认作完全是由偶然性支配的,到生活的彼岸世界去漫游,寻找精神苦痛的解脱,觅求民族精神的根基,实质上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独特的自我感受。弥漫着宗教情绪的各种小说所表现的现实,无疑亦是一种经过作家心灵“温暖过的”现实。
以表现为主体的审美意识至少丰富了单一的反映意识。由于出现的避免纯教化的审美倾向,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对多层面审美情感的追求。转型期小说在不同的艺术层面上更新了文学传统的艺术面貌。文学作品必有教化功能的框框已经真正地被打破。加尔科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没有尽头的死胡同》(1992)、科罗廖夫的长篇小说《果戈理的头颅》几乎都没有明显的教育功能,对读者展示出的是文化人无序而又充满苦难的心灵历程,却有着更深刻、更积极的认识意义。皮耶楚赫的中篇小说《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展示了对人性恶的新发现,托尔斯泰娅的短篇小说《索尼娅》(1987)寄寓着对一位憨厚善良纯真的女子不幸命运的无奈与同情,马卡宁的中篇小说《盖着呢子、中间放着玻璃瓶的桌子》是作家对充满了偶然性的世界人生状态的一种代言,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通向爱神之路》、《我爱你》(1992)则写出了女人和男人感情生活中的一个个真实的片断。这种发现、同情、代言和真实的片断,都不是“教育功能”所能涵盖的,它们充分显示了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艺术表现上,由于避免了那种单一外向的止于生活场景描绘和直抒胸臆的实象形态,追求更为复杂的内潜的艺术表现手段,使作家的艺术创造更具个性特色。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表现自我对外部生活感受的美学追求伴随着一种作家创作的自我中心状态。所谓自我中心状态,是说作家在创作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心理状态,即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去体验世界时,都多少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不是让“我”去适应世界的秩序,而是让世界来迎合“我”的思考。这种自我中心状态有时会使作品具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那种后现代主义的以揭示个人内心世界为特点的作品。加尔科夫斯基的《没有尽头的死胡同》就是这样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长篇小说揭示的是一种人生烦恼,一种被作家视为人生基本内容的,以曲折、迷惘、受损害、多变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意识活动。作家较多地沉溺在自我的感情与意识之中,让读者十分真实地体验了人在独特的心理状态下所表现出的异常的意识活动。他追求的主要不是人物、故事、情感的真实,而是形成心理状态的各个因素之间的真实,从而提供了一幅在先前的苏联文学中很少看到的,人在特殊状态中的意识活动图。在马卡宁的《平常化话题和情节》(1992)这部小说中,俄罗斯人自普希金死后的150年的变化,得到了很精彩的展示。两部小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心灵意识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人生的不确定性,这正符合俄罗斯人对历史灾难客观存在的深切记忆。但自我中心状态亦有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当作家沉溺在自我的情感中时,往往难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与历史对话、交流,开阔地俯视历史与人生。故而,上面的两部作品在充满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叙述中,流露出比较明显的人生命运的神秘感。
二
与审美意识转移密切相关的另一特征是审美对象的变更。在冲决传统写实主义的基础上,小说家从社会思索转入个体生命体验。他们的表现对象已经越来越集中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生命意识。这里说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是指个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存在的具体形式。生命被作为独立的个体加以强调,其社会性角色被淡化,生命自身存在的焦灼、苦闷、烦躁等情绪被作家所体验,生与死,爱与恨,自然与本性等成为小说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基本内容。这种审美观照比较真切地道出了当代俄罗斯社会在转型期的一种尴尬与挣扎。
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通向爱神之路》对我们认识现代人的本体存在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小说的故事脉络应该说是很清晰的。它描写了一位名叫普尔海丽雅的中年妇女几近梦幻的未果的单恋。她的丈夫有了新欢,女儿又有了儿子而无暇他顾,于是忠贞不贰的她在情感的孤独和精神的寂寞中,固守家室,几乎两点一线地往来于单位和家中。在一次应邀参加同事家的晚宴后,她迈上了通向爱神之路。“所有的人内里还都是动物,不用说话就能感觉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小说的这一题旨表现了“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的、构成人生命存在的原生欲求──爱的欲求以及为了这欲求而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量。然而,这种爱是虚幻的,不仅是因为她所钟情的男子恰恰是女主人的丈夫,而且是个精神不太健全的人,更重要的是俩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对方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女主人公不可避免地要从幻想走向严峻的现实。作品也正是经由这一轨迹展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全部艰难性:传统心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人性中真假、善恶、美丑的对立及不可调和的永恒的搏斗……。当人发现了自已感知的错觉和追求的幻灭也就可能陷入极度的苦痛之中。人为了完善自己,为了保证世界的和谐与平衡,必须不断唤醒承担苦痛折磨的自信心,这样世界才能不陷入黑暗的混乱中。作家在描写中,没有完全放弃活生生社会内容的融入,假如我们能顾及当代整个俄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我们就能从女主人公的生存苦痛中发现现实俄罗斯社会的尴尬,但生活的力量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具有制约它的作用。在这里,人的生存状态不仅是作为小说的课题,而且是作为哲学的命题,叩击着作家的感知和思维的门环。《我爱你》、《孩子》、《犹太姑娘薇罗奇卡》、《生活的阴影》、《海神波塞冬》、《两个王国》与《通向受神之路》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都被收于《在充满机遇的园地里》的总标题下。这一组短小的作品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们所揭示的人生存状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生命现象的哲理思考,几乎是这些短篇共通的主题意向。
其实,不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小说如此,象叶·波波夫、托尔斯泰娅等人的部分小说也表现出了这一意向。有趣的是,他们都敏锐而独到地将视角定格在市民的日常生活圈里。市民在俄罗斯文学中历来不处于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市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更低。在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小说中,市民主人公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作家本身就生活在都市里。而且这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在喧哗热闹的都市拥挤着过多的各式文化的代表。市民在这里已经超越了题材意义的范畴,而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的载体,成为对人生存意识进行文化思考和价值判断的广阔的空间。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的全部“原汁原味”,摆脱了种种先验观念的干扰以一种自然真实的审美形态出现在这类小说中。作家追求不加雕琢的人的原生形态。作家怀抱着人是人的最高价值尺度这一信念,以冷峻的眼光凝视着一个个有生命的动态结构,记述着他们生命的律动。在一个具体的有生命的个人身上,自然性和社会性、肉体和精神是难分难解的复杂的混合体,作家仿佛从动物性的生命存在中发现人性的美,发现人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这种对表现普通人生存真实的艺术努力,在创作心理上动摇了对小说中人物理想化的认知模式。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彻底告别了正面人物、理想人物,告别了传统“英雄”,而趋向“非英雄”。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的这种“非英雄”趋向既是50-60年代文化非英雄化趋势在新时期的延续,又与其有着许多重大的区别。就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而言,几乎都是平凡的“小人物”,甚至是庸人俗物。从创作的目的来看,不是为了暴露、批判,而是为了展示。从形象来看,多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典型论”的原则塑造出来的。小说中的人物活动在其生命存在的任何一个时空,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代表性。他们或是比较有血肉的凡夫俗子,如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笔下的人物,或者是某种观点的产物,如马卡宁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有些干脆与传统的“典型”绝缘,如托尔斯泰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有些小说中的人物。而在叶罗菲耶夫、纳尔比科娃等人的一些作品中,卑微、猥琐、低贱的俗物几乎有些象象征性的符号。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有两大精神特征:内向性和复杂性。前者表现为人物内心世界的闭锁,后者则表现为人物是多重性格的组合体。在同一个人物身上,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残忍的一面;既有聪明过人的一面,又有浑浑噩噩的一面。波波夫的《穆霞婶婶和廖瓦叔叔》中的大学生,纳尔比科娃的《白天和夜晚的星光的平衡》中的女主人公。
汹涌的商品潮,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作家对社会现实人生中苦恼、不幸、焦虑的无比关注。但作家在表现都市人生存困境的同时,却缺少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对人和社会现实的人文精神的观照,少了些对人的富有理想之光的“终极关怀”。这不能不看作是这类作品的一种不足。作家一方面直面现实的人生,另一方面又潜入人的意识深处,从而表现出生存状态对精神追求挤压的趋势。人文精神衰退使作品缺少了诗意,使作家的创作心态有点“游戏化”的味道。于是,作品中对人生意义的深刻见解,超然物外的形而上的思考,对人生真理的天真向往,对真善美精神的由衷爱悦变得难能寻到。作家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虽然也洋溢着人生的温馨,但却无助于解除困惑和人文精神的重建。托尔斯泰娅多少有些满足于玩赏日常琐屑的生活经验之嫌,她将自己整个地淹没于现世生活的浊流之中,而放逐了文学的精神使命。要说出在哈里托诺夫、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某些小说里,究竟描写了一个怎样的世界,有时的确很难。看他们的作品,会有一种梦魇的感觉:情节琐碎而互不关联,没有逻辑的语言一句句不着边际地跳出来,人物多没有确切的位置,人物相互依赖,又相互窥视、妨碍,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此外,在相当多的一些作品中,作家格外倾心的是生命中灰暗的、疲惫的方面。作品成了人的原生状态的情绪、潜意识、幻觉的排列。作家有意放弃了生命中更为坚实有力的理智、健康、远大精神目标这些俄罗斯文学固有的文学素质。小说在表现人的生命内涵时,往往离开现实多种社会关系的缠绕而显得有些抽象、玄虚。他们以牺牲完整、丰富的生命为代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读者通向他们的道路。
三
作家审美判断的不确定性是小说创作观念的另一种变化。由于文学失去了“热点”,因此没有了“轰动”;由于没有了强大的精神意识的支持,因此也没有了追求的激情。面对新的生活态势,作家尚未形成确定的价值判断体系。使命意识的淡化,再加上作家对原有的问题采取了新的态度和眼光,所以,在小说创作中多表现出一种复杂的、价值模糊的审美判断。作家本人对于所描绘的事件或人物采取的态度已由热情转向冷静,由主观趋向客观,由作者给自己叙述的对象下结论,而转向客观地将真实告诉读者,由显性的、较为确定的历时性价值判断,转向隐性的、比较迷离的共时性价值判断。
这种观念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作者的叙述地位从一种启蒙者式的“全知全能”中隐退,把叙述的职能赋予了作品中的人物或主人公,特别是文化叙事人,作者无意于主观的价值判断,而把审美判断的主体转移到了叙事人身上。果连施泰因的《伏尔加河上的最后一个夏天》(1992)的叙述任务是由一个作家来担当的。他是以一个叔本华思想的崇拜者、一位睿智的哲人的眼光来看伏尔加河及至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这种形而上的俯视角度与常人从平视角度看见的世界是异样的。此外,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夜间》(1992)中的叙事人是一位女诗人,安得列耶夫的《一个新女民粹主义者》(1990)里的叙事人是一个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从这些小说中很难发现比较直接的表现政治态度的功利性倾向,也不易察觉明显的拥有善恶对立的道德评价。作家重在通过叙事人对人生行为的选择来表现有关民族生存状态、民族心理、生活方式、思维情感的思考。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人生态度,其中隐含着对社会制度、道德现状等的一定的情感倾向。小说中的这种文化学态度体现了作家在表现生活时,努力避免一种政治性的价值判断,而追求一种普遍的、共时性的价值取向。
与作者叙事地位的转变互为依存、联系的是小说由虚构向纪实的转移。审美判断的模糊正为我们探寻近年来小说纪实趋势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作者在将叙述职能交给叙事人的同时,越来越多地直接让事实说话。小说家越来越注意隐去“自我”,以超然而又冷静的目光审视现实和历史,力求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这种趋势与渲泄自我、表现个体的精神相辅相成,成为转型期小说表现真实的两种不同形式。应该说,70、80年代的苏联小说已经显露出一定的纪实倾向,但在总体上那一时期的纪实小说仍未脱离旧的思维模式,无论是战争题材小说,还是道德题材小说,纪实的运用都还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的、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只是那时的是非、善恶的标尺与先前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然而,新时期的纪实性小说却突破了这一较为偏狭的思维模式。作家都把人物、事件置于深广的历史与现实、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之中,对发生在俄罗斯的社会灾难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变革与动荡,进行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心理的多维度的思考。小说家没有拘囿于情节、人物等小说要素以及写人、写事的题材窠臼,没有受传统小说创作模式的影响,不以塑造人物或纪录典型事件为目的,而是通过大量的历史纪实、回忆,甚至社会新闻等手段,着力开掘普通人的社会心理、文化心态,从更宽广、更深入的社会人生的视角观照时代,揭示生活和社会的本来面目,忠实地记录时代的变迁,勾画一幅全景式的、立体的社会画卷。
探讨小说的这一特点不能不提到叶甫图申科的《不要在死期到来前死去》(1993)和季诺维耶夫的《混乱人世》(1993)这两部小说。前者不仅揭示了1991年8月事件的政治内幕和起因,苏联将军的秘密情事,包括叶利钦本人在内的上层人士的私生活,还叙述了年轻的侦察员帕尔奇科夫坎坷、不幸的人生遭遇,描写了俄罗斯杰出的足球运动员与女攀岩运动员之间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作家本人的婚变历史以及受雇克格勃的经历……《混乱人世》从俄罗斯的“改革与犯罪”切入,以纪实为主体,用虚构和纪实相结合的手法,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十分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作品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新时期的《悲伤的侦探》”。两位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了构成社会的细胞之中,于是,包裹在家庭、婚姻、性爱外面的帏幕被揭开了;作家的笔触波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于是,教育、体育、卫生、交通、安全等部门的从业人员的酸甜苦辣得以倾吐;作家的笔触涉猎社会各个阶层,于是,工人、运动员、演员、大学生、医生、妓女、罪犯等的人生悲欢得以渲泄。这些作品把过去封闭着的,或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的世界、新的冲突一个个展开,人们既从中获得认知的满足,又获得渲泄情感、寻求理解、平衡心理的愉悦。由于小说揭示了许多外界所不知的内幕新闻和名人的秘密,加上情节曲折起伏,充满了悲欢离合、人情冷暧,作者现身说法,讲得娓娓动听,使读者读得津津有味。与此同时,作家在评论生活和人的标尺时,已经从单一的政治角度扩大为社会、历史、文化等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尺度。使读者从中得到的启示不仅仅限于表层的社会的发展运动,而且还有更恒久、更深刻的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在作品中作家将小说与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等结合起来,将文学手段与政论、随笔等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带有浓郁的通俗文学风格的“不似小说胜似小说”的反小说,开拓了小说的新领域。
在“表现型”小说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在“生存”小说愈益受到作家的重视,在纪实性和回忆录式小说不断地走向读者时,我们会发现,小说的表达形式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描述之外的大段议论,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科技专业的等等已成为小说司空见惯的内容。兴许这是作者为了突破传统的情感表达方式,想用理性化了的情感来激活人们深层的审美愉悦,使小说更具心理和情绪的特点。伴随着目前众多的作家对各种艺术样式的探索,艺术形式的大幅度变化所带来的审美效果,也出现了一些孱弱的现象,叙述学、结构功能、假定性手段、语言的变构等,被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而这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从“美文”的标尺出发的。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之嫌。因为真实的生命状态永远是构成艺术最重要的东西。它既是内容,又是赋予内容以完整意义的形式。普希金笔下的阿乐哥、莱蒙托夫诗中的童僧、艾特玛托夫小说中憧憬白轮船的小孩,他们可以远离喧嚣的尘世,甚至可以展示人与自然的种种斗争和契合关系,但是根本上作者展示的是一种生命状态,是为真实的生命而斗争的基本文学母题。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品得以流芳百世的关键还不在于表层意义的形式和语言效果。任何时代真正称得起是创作的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生存状态的展现,是独特的生命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创作手法无“过时”和“时髦”之分。肖洛霍夫与布尔加科夫都是传世的。
我们提出俄罗斯小说转型期具有新的美学特征的目的在于:面对着俄罗斯新的小说创作实践,我们的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以期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然后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研究。固然,新的东西不可能脱离旧的观念的形式,但又必然会与它们产生距离。如果总是站在旧有的理论框架上,完全以传统的批评视角去看变动着的俄罗斯文学,我们注定要落入歌德预言过的悲剧: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绿树常青。这也许就是我们在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时所应遵循的一个理论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