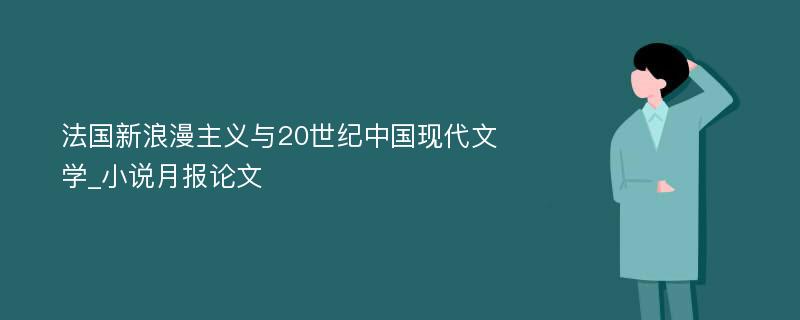
20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法国文学流派纷呈,思潮迭起,“它的独特、丰富与辉煌,似乎并不亚于一直被视为难以企及之高峰的19世纪文学,它作为不止一个新思潮、新流派之摇篮的世界性影响,更是人所共见的明显事实。”(注:柳鸣九:《〈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总序》,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中国人引进借鉴这些法国文学的新思潮、新流派,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年代中国新文学创始阶段,二是70-9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阶段。20世纪法国文学思潮的东进几乎与其在本土的崛起是同步进行的(注:譬如,诞生于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30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来了,而诞生在40年代的存在主义,差不多同时被引进到中国。),其两次东渐涌入华土,正处于中国文学的两次转型期,五四时期是旧文学向新文学转换,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性转换。法国文学新思潮与中国文学碰撞交融,呈现出两次高潮,推动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五四”中国新文学初始阶段,是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进中国的时期,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无不以绍介西方文学思潮、改革旧文学、创建新文学为己任。在中国新文学开拓者中,茅盾是特别注重“源流与变迁”、自觉系统地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的作家。早在1920年1月,他就对西方文学源流与变迁的“进化次序”作过具体的描述:“西洋古典主义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特林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注:茅盾:《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见《茅盾全集》第18集,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在茅盾看来,西洋文学的这种流变与发展在法国表现得最为充分:“近代西洋文学思潮,几乎统统受着法国的影响;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都是从法国发源的,法国文学之重要,无论谁不能不承认的。”(注:《〈法国文学研究专集〉征文启事》,《小说月报》第3卷第8号,1922年8月。)步入文坛伊始,茅盾就把目光投向法国文学,致力于法国文学思潮的介绍。
茅盾仔细考察了“一部西洋文学思潮史”,认为,若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这一世界近代“文艺进化的大路线”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发展“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大大落后于西欧文学。”中国文学要现代化,自然也要受这个路线制约,“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一过之必要”。(注:茅盾:《最后一页》,《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按茅盾最初的认识,西方后出的“新浪漫主义”最为理想,他曾经明确指出:“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能引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但当时的中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中国文学尚未受过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洗礼,而未经自然主义的洗礼,就侈谈“新浪漫主义”,在茅盾看来,“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注:茅盾:《文学作品有主义与无主义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因此,20年代初,茅盾在大力介绍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同时,也开始倡导新浪漫主义。
什么是新浪漫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的茅盾,何以能在大力推广写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同时,又积极倡导这种新浪漫主义文学呢?这是需要弄清的问题。在茅盾那里,新浪漫主义内容极其庞杂,包含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新理想主义等,他在50年代《夜读偶记》中曾一言以蔽之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主义’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在茅盾的文学观念中,“新浪漫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而是一个富有动态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接受者的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转变而变化。“新浪漫主义”或“新浪漫派”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茅盾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虽然当时的茅盾重点尚在于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思潮,但却已简要地道出了新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从写实主义的“客观变回主观”,而又不同于旧浪漫主义“从前的客观”;它以象征主义为前导,“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1920年上半年,茅盾翻译介绍新浪漫派文学渐多,仅一月至八月间,便连续介绍了比利时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俄国神秘而带有颓废色彩的作家安特列夫、英国象征主义作家叶芝、瑞典表现主义作家斯特林堡以及法国作家巴比塞等,特别是对后者的介绍值得重视。因为茅盾通过论及巴比塞的《非杀论的文学家》,第一次将“新理想主义”概念引入了新浪漫主义范畴。如果说,在一个阶段中,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态度,尚处于矛盾与困惑中,(注:西洋文学演进的先例,旧写实主义“精神上太无调剂”的缺点,都促使茅盾把希望寄予新浪漫主义。但‘为人生’的强烈责任感,又要求他以“合于我们社会与否”为尺度,量出新浪漫主义文学诸多流派的弊端。因此,介绍叶芝,茅盾谨慎说明是为了“增加中国人对于西洋文学研究的资料和常识,当然不是鼓吹夏脱(今译叶芝——引者)主义”《沙漏》译者前记);对于安特列夫的作品,也担心“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致周作人信》)。他对于新浪漫主义暂先介绍而不提倡的主张,除了源于我国文学“还是仪在写实以前”的估计,以及文学发展只能依次进化的观点,似乎也是一种矛盾心理的反映。)那么,当“新理想主义”进入了茅盾的接受视野并被纳入新浪漫主义范畴时,他的这种困惑和犹豫便得到了消除,这就是为什么1920年9月,他要为新文学研究者进这样一解:“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此时的茅盾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运动,初期始于心理派小说家和象征诗人从艺术上对自然主义的反拨,渐次发展,终于以罗曼·罗兰、巴比塞等新理想主义为“主要的趋势”。(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着眼于新浪漫主义诸多流派的同中之异,推重新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正是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理解与汲取的独特性。因此,茅盾二十年代前半期推崇与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实际上主要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法国文坛的,以法朗士为前驱、以罗曼·罗兰为旗手、以巴比塞为干将的新理想主义文学流派。茅盾认为法朗士“重理想理智”,“合写实主义与感情主义为一”,“可以称是新浪漫派的前驱”。(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而“新浪漫主义现在主要的趋势光景可以拿罗曼·罗兰为代表”(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最能为新浪漫主义之代表之作品,实推法人之'Jean Christophe'”(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引者),“其次则如巴比塞之《光明》”,巴比塞的小说“可说是新理想派”(注:《为母的》译者前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之作品。发展“到今日已经有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立起新浪漫派来了”(注:《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可以说,二十年代的茅盾是以法国的新理想主义文学作为新浪漫主义的主要内涵来加于介绍的。这样,茅盾在大力引进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同时,又积极倡导以20世纪法国新理想主义为重心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从文学与时代人生关系看,茅盾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又“束紧了一步”。一如茅盾接受自然主义文学有其独特的角度,茅盾在接受新浪漫主义时也有自己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的观察点与立足点。在他看来,西洋文学“由古典文学—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不是渐次使文学飞升人唯美主义象牙之塔,而是每前进一步“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新浪漫主义文学不但不与人生远离,而且还能补救以往文学的不足而“综合”地表现人生,“能引我们到真确的人生观”,在这一点上,它比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前进了一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浪漫主义是中国新文学“免不得要经过的一步。”茅盾认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依照这一标尺,茅盾指出“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注:《为母的》译者前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因此他拒绝把“目的只在美,而不言有新理想”的唯美主义划归新浪漫主义范畴,而把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奉为新浪漫主义的圭皋,因为从艺术上来说,罗曼·罗兰的作品也属于“为人生”派。
其次,从艺术上来看,新浪漫主义可以使“自然主义在文学上的价值抬得更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茅盾看到,与“新浪漫主义之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之于古典主义”“纯乎其反动”不同,二者间“非反动而为进化”(注:《〈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东方杂志》第17卷18号。),或者说,新浪漫主义“在表面上似乎是自然主义的反动,其实却是自然主义的帮手”;不经自然主义洗礼,新浪漫主义无法产生;而“经了新浪漫主义作家的努力,自然主义在文学上的价值更抬高了”(注:《霍普特曼传》,《小说月报》第13卷第14号,1922年4月。)。而且,文学上每一种新主义的出现,总是“把前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进一步。”(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14号,1922年4月。)因此,茅盾认为:介绍与提倡新浪漫主义,目的不在取代或反拨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而在于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予以“补救”(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这种补救主要是下列几端:
(1)“为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自然主义作家只重观察而轻视想象。客观的观察固然是文学创作之本,但自然主义将其推向极端,“其弊在枯涩而乏轻灵活泼之致”。(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则偏重于主观想象,张扬个人自觉的思想和创造自由,茅盾把它称作是一种“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思想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进步有生气。”(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因此,新浪漫主义作为对自然主义的补充,常常使客观与主观,也就是客观与想象相辅为用,犹如车之两轮,从而达到“兼观察与想象而能谐和”的“艺术之至高格”。(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2)“为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自然主义“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因看不到前途而“感觉沉闷烦忧的痛苦,终至失望”。茅盾认为:“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14号,1922年4月。)必须“含有新理想”,这样才能起到指导人生的作用。作为新理想主义的旗手的罗曼·罗兰,以他辉煌的大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过去,表现现在,并开示将来给我们看”。(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而巴比塞的小说“大概都含有一种新人生观在文字夹行中。”(注:《为母的》译者前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因此,他们的小说,“不是绝望的文学,乃是希望的文学,得救的文学,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文学”。这种将“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的新理想主义正是自然主义和当时中国文学所极为缺乏的。
(3)“为补救写实主义不见恶中有善”。自然主义认为现实人生中所有的只是丑恶,因此专注于世间丑恶的一面,其结果“使人失望,悲闷”。(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新浪漫主义则强调“兼观察与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以为生活中除了丑恶,更多的却是真善美。“他们暴露了现实的丑恶,同时也发现了在现实的根底,原来还藏得有美善的生活力”。(注:《欧洲最近文艺思潮》。)茅盾认为只有这种既能揭露假丑恶,又能展现真善美的文学,才真正符合艺术的最高目的。
总之,新浪漫主义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补救”,不外包括理想、情感、想象、象征等内容。但茅盾从现实主义立足点出发,要求这些因素不能越出现实主义轨道独立膨胀。因此,增强理想成份与感情色彩,却不是要作家对社会人生“装作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文学旬刊》1922年8月。)而要求在揭示“下流社会之生活”严酷的同时,又不流于旧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偏在恶的一面”,展现出善的力量和理想的晖色。同样,重视艺术想象,也要加以限制:要兼观察与想象。就这样,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文学特征的阐释,融进了自己的“改造”性见解,一如他对自然主义的借助与改造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取向。茅盾推崇新浪漫主义,追求的“新”其实只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风貌的现实主义,所谓“兼有浪漫和写实的精神”,(注:《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徽支》。)“合写实与浪漫为一”,追求客观描写和主观见解的结合,追求观察与想象的结合、反映现实和展现理想的结合。可见,他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初衷并不在掀起一个西方本来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艺潮流,而在探求和营构一种更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它将以揭破现实黑暗而又能启示未来光明,并于“外面真实”的细微刻画兼有“内面真实”的深入发掘而超越批判现实主义。这样,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借鉴择取,明显拓宽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空间,改善了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人生的功能结构,并使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建构之初就呈现出开放的态势。
茅盾在20年代所张扬的法国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和巴比塞等人,是20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代表,他们是法国新一代“行动着”的作家,都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而著称的进步作家。他们崇尚正义,向往光明,充满理想,积极参与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他们的作品便是参与政治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还是揭露生活中丑恶现实,他们总是运用自己手中的犀利的笔发出进步的正义的声音,尤其在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下的“反战文学”曾在人类进步历程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赢得了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信赖和爱戴,并被广泛接受。在这里,作家的进步行动和人文精神似乎比作品本身更吸引中国人,中国接受者与其把他们看作“为文”的榜样,毋宁视为“行动”的模范。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开拓者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沿着这种择取方向,投向这群新理想主义作家。比如,鲁迅就曾经称颂过法朗士、罗曼·罗兰和巴比塞等是法国新一代“富有实行质素”的作家,推崇他们的人文精神和为真理、正义而抗争的战斗传统:“法国的文艺家这样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浮斯打不平,法朗士当左拉改葬之时讲演;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对法国作家的这种伸张正义的精神传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国新文学作者和翻译家要向中国人介绍他们的作品。在他看来,法朗士之作“有历史气”(《政江绍原》1927年11月20日),且“精博锋利”(《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表明这位作家“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而中国人向不注意,实为憾事;罗曼·罗兰是个“大作家”,其作品于“读者有益”(《致曹白》1936年5月8日);而巴比塞的作品最少“享乐气息”,虽然“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但是鲁迅认为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来“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不仅对读者有益,而且对“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示范”(注: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推重这些作家的进步行为与创作,把他们视为“行动”的楷模而加以亲近,并非是政治的选择,而是精神层面的吸收,这与茅盾是不相同的。茅盾推崇罗曼·罗兰、巴比塞,主要偏重于其进步的政治导向,偏重于一种政治层面的选择,而注重政治倾向的变化,也是促成茅盾文学思想转变的一个内在驱力,就是说,“以社会政治观变异为先导,牵引文学观诸因素组合序列的迁移和消长。”(注:王中忱:《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茅盾对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的推重与克服及由此产生的“新浪漫主义”内涵的变化和接受序列的“迁移”也往往是由这些作家的社会政治倾向而引发的。例如,罗曼·罗兰在一战期间写的“反战文学”固然在当时的西方和东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茅盾看来,作者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力倡“非战论”,不免空洞软弱,他赞赏巴比塞的《火线下》,因为巴比塞在这部“奇书”里,不仅“满现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赞同国内的阶级革命”,而且还以强有力的声音喊出:“唯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终止帝国主义的战争而确立人类间友爱关系之唯一的大路。”茅盾指出:“我以为这是《火线下》所以巍然独立,不同于汗牛充栋的其他的许多言兵凶战危的小说之处。”也就从这一观察点上,茅盾看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与巴比塞阶级论的区别,并由此出发,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表示了对罗兰所谓“民众艺术”的否定。罗曼·罗兰与巴比塞在茅盾接受视界中位置次序的更换,标志着他对法国新理想主义文学思潮接受方向的又一次调整。不过,茅盾此时不再把巴比塞视为“新理想主义”作家,一九二九年,他在《西洋文学通论》里,把巴比塞划归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行列。在这部著作里,茅盾否定了西洋文学从古典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公式必定在中国演进一回的观点,否定了新浪漫主义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的认识,他考察了欧洲自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新俄文学的发展嬗变历史之后,终于找到了中国新文学真正的发展方向,那就是高尔基为代表的“清新雄健”的革命现实主义。(注:茅盾说:“将来的世界文坛多半是要由这个受难过的新面目的写实主义发皇光大,或者这也不能算是太胆大的论断吗?”)与茅盾不同,鲁迅看重的是罗兰等人主观“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即鲁迅称之为的“真勇主义”,注重于法国新理想主义作家的人格意志和精神层面的吸收。早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就亲自翻译发表了日本作家写的《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率先向国人介绍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作家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表达了他由衷的钦佩之情,并由此而开始了他与罗曼·罗兰的高层次的精神交流(注:详见拙著《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24页。)。他高度评价了罗曼·罗兰反战的英雄行为及其所表现的精神品格,同时又依据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自身的斗争经验,对罗曼·罗兰的反战思想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乃至诤友式的补正,表现了东方思想家对西方勇士独特的深刻的理解与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鲁迅和罗兰之间的这种理解和沟通,不仅表明了20世纪中法这两位伟大作家内在气质的某种相通,而且也表明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法国新理想主义作家的英雄精神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内在契合。我们知道,罗曼·罗兰这一代作家的英雄主义深深扎根于对人类和人类正义事业的挚爱与必胜信念里,扎根在探求真理,追求人生和人性至善至美的搏击精神中。因此,这种英雄主义的内核,便是直面人生的“大勇者”的精神与信念,是建立在这种精神和信念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是直面理想生发出的“大勇主义”、“努力主义”、“忍苦主义”(注:白晔:《克利斯朵夫与悲多汾》,载《黄钟》1卷。)。借助罗曼·罗兰的这种英雄主义,不仅可以陶冶人性,提高人生境界,也能疗治国魂,振奋民族精神,这便是鲁迅为什么特别看重它的原因。对于执着于现实的艺术家来说,直视人生的“大勇者”战斗精神,其实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所以,罗兰的英雄主义便自然地令人想到鲁迅那种韧性的战斗风格与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两者存在内在契合。这就是鲁迅与罗兰从未谋面,而能心息相通,倾心交流的根由;后来的中国新文学作者总是把鲁迅所开拓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罗兰的英雄主义联系起来观照,其理由也在于两者的内在契合与一致。1945年萧军在一篇纪念罗兰的文章里(注:萧军:《大勇者的精神》,载《解放日报》1945年1月29日。),首次将罗兰的“大勇者的精神”与鲁迅的那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打”,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并论,他是把握到了罗兰的英雄主义与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在中国新文学的作者中,真正把握到法国新理想主义作家罗兰等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理论上加以开发的是胡风,在创作上加以实践、加以拓展的是路翎和巴金。胡风迷恋罗兰的英雄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卓具个性的理论家,他那渗透着“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风格,投射着罗兰式的“征服苦难,追求光明”的英雄气质,具有罗兰式的由“痛苦的热情凝晶成”的,“带着宗教热的色彩”的“理想主义”(注:胡风:《罗曼·罗兰》,新新出版社,1941年。)的投影。胡风认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罗曼·罗兰同样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在胡风那里是互为一体的,但“他的现实主义是为他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服务的”,而“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伟大激情”使他的英雄人物,“通过苦难的欢乐”的艰苦斗争的道路,“达到了精神斗争的最高度”(注: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见《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具有动人的现实主义力量和理想主义光彩。胡风赞叹罗兰创造出“那为善而受着痛苦的灵魂”,以此来“救援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样在孤独和寂寞中间作战的痛苦的兄弟们”,来“照亮他自己身受的腐朽的世界和困乏的人生”(注: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见《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1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由此,胡风通向他那写出真实人生,写出人生真血肉的“灵魂现实主义”的思考,而这种“灵魂现实主义”的思考是由鲁迅所开拓,与罗兰理想主义的真髓相沟通的。胡风看到,罗兰笔下的一些受难的灵魂之所以具有一种魔力,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就在于真实,“真实就是生命,历史的真实只有溶进战士底伟大的性格而被发现出来以后,才能够成为精神的力量。”(注:胡风:《向罗曼—罗兰致敬》,载《新华日报》,1945年1月25日。)罗兰创造的这些“伟大的性格”和真实的、“受着痛苦的灵魂”正是罗兰的英雄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胡风明确地指出,罗兰的英雄主义通过中国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俯向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燃烧在克服苦难、争取自由的人民里面”(注:胡风:《向罗曼—罗兰致敬》,载《新华日报》,1945年1月25日。),他清楚地看到了罗兰的英雄精神在中国滋养民心,滋养文心、振奋民气的重要作用,因而更深刻地理解到了鲁迅与罗兰内在精神的相通,更深刻地发掘出罗兰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鲁迅现实主义精神内脉的一致性。
如果说,令胡风迷恋的是在“痛苦的热情里生长起来”的罗兰,是罗兰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黑暗作战和痛苦作战”(注:胡风:《向罗曼—罗兰致敬》,载《新华日报》,1945年1月25日。)的英雄气质和精神力量,并由此溶进自己的血肉,促成了他那令人瞩目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理论个性,那么,令路翎倾心的是在“崇高而热烈”的“观念里生活”的罗兰,是“由罗兰的强烈精神渴望所产生的”那个英雄世界,并从而找到了中国的“克利斯朵夫”,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项“未完成的探索”(注:参见赵园:《路翎:未完成的探索》,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路翎曾明确地说过:“我在当时,是很欣赏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内容是当代的人生追求和当代的人生现实之间的斗争内容。我在写《财主底儿女们》的时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伴我走过这段行程。”(注:李辉:《路翎与外国文学》,载《外国文学》1985年第8期。)出于对罗兰英雄主义的感召,路翎在他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克利斯朵夫——蒋纯祖。在这个财主的儿子、青年知识者身上,我们确实见到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他们都具有不寻常的“雄心和梦想”,幻想建立奇功伟业,都企图跨过“混沌的生活”,追求阔大、自由的人生,都是“漂泊者”,都骄傲于“漂泊者”的那份“孤独”,对于同类怀着“轻蔑”,以致“骄狂的憎恶”,都有着“内省”的狂热癖好,都不乏“光荣的、高贵的”自我意识,都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这些相似都深深地打上了罗兰英雄主义的印记,表明《财主底儿女们》是罗兰的新理想主义思潮催生下的果实。
将罗兰的英雄主义和战斗品格升华为生命意识和创作的主体精神,并由此开创了人品与文品谐和一致的中国新文学一代风范的,是巴金。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正以此通向罗曼·罗兰和20世纪法国新理想主义作家的。在提及外来文学滋养时,巴金从未回避罗兰给予他的这种特殊的影响。他在40年代给法国汉学家明兴礼博士的一封信中曾这样明确地说过:“我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比方他所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三部传记、大革命戏剧。他的英雄主义给了我很大影响:当我苦闷的时候,在他的书中我常常可以寻找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地明了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欢乐。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害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模范和典型。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注:明兴礼(Dr.J.Monsterleet):《巴金的生活合著作》(王继文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第57-58页。)在这里,巴金显然是把罗兰视为人的“楷模”加以接受的。他也像大多数中国读者一样,很少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接近罗兰,但他对罗兰的择取又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选择,而是做人的选择,这种人的自觉意识的投入,对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作家来说,又不能不通向“文学—人学”的选择,并使这种选择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主体精神。正像罗兰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往往不可分割一样,集作家、战士于一身的巴金,为文的原则和为人的原则也是二而一体的。当他从罗兰那里学到了“爱真、爱美、爱生命”的品质时,事实上他也获得了一种为文的准则,巴金的全部作品可以说都是这“爱真、爱美、爱生命”的颂歌。它既是巴金受惠于罗兰人品的结果,也是巴金受惠于罗兰文品的结果,既构成了巴金的生命意识,也构成了巴金的创造意识。巴金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走向罗兰的。
从上面简略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新文学作者对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法国20世纪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的倡导与接纳,旨在寻求和营构一种更理想、更符合本土文化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以便推进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近并接受了法国新浪漫主义、新理想主义思潮,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合乎各自个性的文学选择:或致力于精神层面的提取,或助成了理论探索的契机,或学到了为人、为文的榜样,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对罗兰英雄主义的亲近与认同,不仅是这位中国新文学奠基者致力于人的精神现代化的探寻的一种深化,是他那独特的严峻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而且也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作家注重于施与者英雄气概和人格力量的追寻,即从精神层面汲取法国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巴金、胡风、路翎等中国新文学第二代作者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这就助成了继鲁迅之后一代求索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人格的建构,无疑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标签:小说月报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约翰·克利斯朵夫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自然主义文学论文; 胡风论文; 鲁迅论文; 茅盾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巴比论文; 写实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