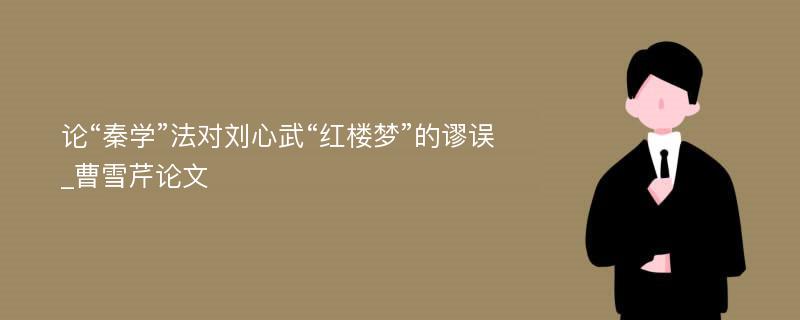
“秦学”方法谬误论——平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谬误论文,刘心武论文,方法论文,平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11-26
中图分类号:H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0X(2009)01-0040-05
随着“秦学”风波逐流而去,“红学”似乎又已翻过一页。然而物循常理而事有意外,“秦学”论战硝烟尽散,“揭秘”红楼却是涛声依旧。谓予不信,诸君请看,时至今日,“秦学”主讲不是还在央视频频出镜继续兜售,“揭秘”文稿不是又有多部出炉,四海畅销!
坚持“红学”的学术方向,排除“秦学”的社会影响,决非一蹴而能奏其效,一役而能毕其功。有鉴于此,红学界正在多方努力。也正因此,本文试就“秦学”的方法再作一些考辨评说。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曾在正文之前为“秦学”作出辩解,刘先生说:“我的秦学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诸如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的原型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1]4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误解。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刘先生的“揭秘”的确打开了一扇最能看清政治权争景象的窗户,迈过了一道最能通向清朝宫廷深处的门槛,掌握了一把最能开启大内档案橱柜巨锁的钥匙,引领我们进入“秦学”海市蜃楼一般的宫殿,欣赏到红楼背面的奇异景观,领悟到索隐新说的无穷奥妙。同时我们也看得明明白白,刘先生所以如此曲解《红楼梦》,原因就在于他的研究方法。“秦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他这里申明的“探佚”、“原型研究”,还是他曾经谈论的“考证”、“接受美学”,其实无一不存在谬误。
1 关于“秦学”探佚
探佚学对于《红楼梦》是一种特殊的研究范式。探佚学探索的依据,一是脂批,二是前八十回文本中的隐喻、暗示、伏笔及其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探佚学探索的指向,是八十回以后所佚原稿关于人物命运的描写,或者是曹雪芹最初拟定却又没有写出的某些情节。研究者着手探佚之际理应保持清醒认识:作为特殊研究范式,探佚必须注意有个界限。正如郑铁生先生所说:“在界限之内,是探索曹雪芹创作思想的研究;超越这一界限,就容易滑入索隐的泥坑。”[2]
刘先生说,“秦学”探佚有四个层次:第一是《红楼梦》的文本;第二是曹雪芹的构思;第三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第四是曹雪芹创作的人文环境。简要的标题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具体阐述之中,特别是后面两个层次的阐述。关于第三层次,刘先生说,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及其后果,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的创作心理,便很有必要,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关于第四层次,他又说:“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因此秦学的空间,也便必须延伸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间,当然也就大大地展拓开来。”[3]16如此策划、照此实施的“秦学”探佚于是体现出两大特征。
1.1 执意指向既定目标 “大的方向我们老早就确定了……《红楼梦》应该写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写的是在那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事。”[1]205既然早已认定《红楼梦》文本掩盖的实际内容就是清代三朝的政治时局,所以探佚的任务自然就是“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由此推进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可见,秦学的探佚完全是一个“逆行模式”:不是利用可靠可信的证据去探索文本所佚情节内容,而是服从预定或既定的结论去寻取似是而非的证据。“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都是这种“逆行模式”的产物,正是这种“逆行模式”决定了秦可卿必须出身高贵,贾元春必须相机告密!这样的探佚势必超逸于《红楼梦》整体叙事结构的制约,而为读者提供一部不同于原作的“故事新编”。
1.2 任意拓展探佚空间 正当的探佚可以凭借文本与脂评双向观照、互为补充,在特定界限之内探索某些可能。秦学探佚根本无视任何“界限”,不仅理所当然地“跨入了‘曹学’的空间”,随心所欲地以贾证曹、以曹证贾,而且强调“必须延伸到”清代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大大地拓展”“探佚的空间”。刘先生再三说过:“探佚学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前八十回的文本的理解,根据脂砚斋批语,以及根据我们自己的善察能悟,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探索《红楼梦》或者说《石头记》在流传过程当中丢掉的是什么,我们争取把丢掉的找回来,这本身就是阅读当中的乐趣。”[1]26依照刘先生的意思,“空间”既然“广阔”无限,“根据”又都在于“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丢掉的找回来”——如此探佚固然不乏阅读“乐趣”,只是不知“学术”二字从何谈起!
2 关于“原型研究”
刘先生说:“我的研究方法,说了好多次,主要是原型研究,原型也不仅是人物原型,还涉及事件原型、细节原型、话语原型、等等方面,那么空间原型、场景原型、物件原型也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通过这样的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曹雪芹他写这部书不是凭空虚构,这部书具有自叙性、自传性、家族史的性质。”[1]203这段话颠倒了一个事实,事实是他先行确立“基本看法”而后进行“原型研究”,并非“通过这样的研究”然后才有这“基本看法”。他的“揭秘”第一讲,即着意将鲁迅先生“正因写实,转成新鲜”[4]205八字作了引申:“我理解的鲁迅先生的意思,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他是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根据自己家族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里面的盛衰荣辱、惊心动魄的大变化、大跌宕来写这个作品的。所以它是带有自传性的,是自叙性的。”[1]9整个“揭秘”反复强调“《红楼梦》它是一部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家族史特色的小说”[1]242,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刘先生致力于所谓“原型研究”。
刘先生自命的“原型研究”,其实与人类学、神话学以及原型批评等毫无关系,充其量只是寻求文学创作所依据的人物模特和生活素材,如他所说:“我的整个研究都是在探究《红楼梦》当中的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1]144。探讨生活原型与艺术形象两者关系的原型研究,至少应该具备两条:一是必要的条件,二是明确的目的。首先它的条件是,必须有着可靠的依据证明小说确有原型,就像高尔基笔下笃定无疑的自传类小说,而且作者生平经历与自传性质小说都有大量材料可以相互印证。蔡义江先生说:“凡人物形象有原型的小说,不论其原型为作者自己或他人,都有可靠的依据。或作者曾有自述,或彼此可一一印证,非捕风捉影所能求得的。”[5]80其次它的目的是,探讨原型人物的生活经历及其创作依据的生活素材对艺术形象塑造发挥的作用,探讨生活原型及其要素在作品构成中体现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寻找生活原型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更不能像刘先生这样颠倒过来,利用艺术形象来“还原”生活原型,编造文学文本背后的历史事件。
2.1 原型研究问题——前提在于印证材料的缺乏
虽经无数学者努力,我们对曹雪芹及其家族的了解,还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何况刘先生依仗“自传说”而寻出秦可卿、贾元春等“生活原型”,又是子虚乌有查无其人。但是刘先生却无视材料与依据的要求,全凭一己的主观猜想,强行索求艺术形象背后的生活原型。他说:“《红楼梦》里的许多人物和曹雪芹自己家族的某些人物惊人地相似。”“我越细读,就越相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1]38凭借一己感觉、主观意愿的原型索求,能够称为原型研究么?
2.2 原型研究问题——关键在于探索意图的偏差
刘先生认为清代三朝的政治斗争与作者家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所以作者“似若有所指,又不敢造次”,以致文本既作“暗示”又有“隐藏”,成为一种神秘的作品。在他眼里,秦可卿“这位神秘人物是破解《红楼梦》秘密的总钥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红楼梦》的巨大秘密。”[1]30于是他由秦可卿的形象着手,逆向索求人物原型,进而启动整个“揭秘”工程。可见他的原型研究,正是一种利用文学形象“还原”历史事件的倒行逆施,目的在于实现其主观意图,亦即揭示《红楼梦》背后的“巨大秘密”[1]30。
2.3 原型研究问题——要害在于文史关系的混淆
混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也就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也就不再是用文学眼光去作文学研究,而是在小说中从事索隐。姑且不论《红楼梦》人物是否都能找到生活原型,即便是都有生活原型,但是一旦进入文学创作之后,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还是一回事么?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即使有其原型也多有综合,岂能将文学形象再去坐实某个原型?鲁迅先生关于典型创造的那段无人不知的经典论述,把文学形象与生活原型的关系揭示得何等透彻!王国维先生也有一段精辟论述,他说:“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6]
3 关于“秦学”考证
刘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1]204
考证是中国学者比较可靠、比较有效的治学方法。明清之际顾炎武开创考证之学,乾嘉时期考证之学成为一代学术主流,在古籍的辨伪、整理、训诂、等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所谓考证,就是利用一定的文献资料作为“证”、作为“据”,通过梳理、辨析、推理、判断,来考核、证实、说明和揭示文献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考证的条件是证据充分、事实确凿,考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考证的结论应如考证大师戴震所说的是“十分之见”、“不留余议”[7]372。戴震强调:“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7]372这也如同擅长考证的胡适先生所设的比喻:“把一个不倒翁掷到地上”而“有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8]
针对“秦学”,我们只须强调两点:一是考证必须具有确凿证据,否则即为虚妄之论;二是考证必须注意适用范围,否则即为无谓之举。以此审视“秦学”考证就会看出问题所在。
“秦学”立论既然牵涉清代史实,严谨的历史考证就不可或缺。“秦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只凭主观臆想、穿凿比附提出一个又一个的“谜”,然后煞有介事地借助想像和猜测去一个接一个地破解。要说“考证”,“秦学”除了牵强地利用周汝昌先生某些并不完全可靠的考证结果或探佚所获,此外并未提供任何像样的资料证据。刘先生偶尔也曾提出自己的发现,结果却更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为了证明曹家与胤礽的关系,他别出心裁地硬把两幅原本无关的对联捏合到一起,他说:“我现在让你把林黛玉在荣国府所看到的那幅楹联和真实生活当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时候写的对联加以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两幅对联是有血缘关系的,它们之间是有一个从生活真实升华到艺术真实的过程。”[1]110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出两联之间有何“血缘关系”,所谓“血缘关系”恐怕只是刘先生心存所望而目生其幻耳。况且已有专家指明,他所说的“太子名对”[1]111实乃唐人诗句。我们在此实话实说,刘先生的两联关系之论是无中生有,刘先生的名对归属之见是张冠李戴——“秦学”考证于此可见一斑!
“秦学”的考证之所以处在失“考”无“证”的尴尬境地,根本原因在于盲目迷恋考证而应用范围不当。关于红学考证的范围,胡适早就有言在先,他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9]189-190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此间所谓‘证据’,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并不是那些‘红学家’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9]305李希凡先生最近也重申:“我们要考证,是考证作者,不是考证小说里的人物的史实背景……我希望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要靠近《红楼梦》,靠近曹雪芹真正的家世,而不是靠近作品里的人物所谓的家世。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作者家世靠近作品里的人物去研究,这样做终将失败,因为什么证据也找不到,还会把大家的思想搞乱。”[10]
4 关于“接受美学”
为了支持自己关于探佚空间无限广阔、人人可以自由探佚的高论,刘先生又信口谈起“接受美学”。他说:“西方后来有一种审美的观点,叫做接受美学,就是读一本书,不是说被动地去接受作者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参与作者的创作,他虽然已经写完了,我阅读当中把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想象参加进去,最后我们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精神之旅。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可以挪到我们的探佚学里面来,我们可以搞探佚。”[1]26
不错,西方的接受美学的确认为,作品是在接受过程中由读者与作者共同完成,甚至主张“杀死作者”而由读者独立阅读、自主接受;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观点只是着眼于创作的广义延伸,关注读者阅读之中的能动作用,根本就不可能意味着读者可以无视作品本身的客观存在、客观性质,可以肆意曲解原作,甚至任意颠覆原作。
刘先生谈论探佚空间已经三番强调“自己”,这里谈论接受美学又两次推出“自己”,竭力主张阅读当中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像”参加进去——如此强化“自己”的意识,也就难免漠视异己的原作。正因如此,在刘先生的接受过程中,文本写明出身寒微的秦可卿,能够血统一变而贵为公主。也正因如此,在刘先生的接受过程中,《红楼梦》存在两个不同的文本,一个是作者明确写出的文字,叫做“显文本”;一个是未能充分展示的构思,称为“隐文本”。刘先生所谓“揭秘”,其意不在于阅读“显文本”,而在于索求“隐文本”。
我们在“接受”刘先生“揭秘”的过程中,倒是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揭示的巨大秘密、索获的全新文本尽管很有趣味,但是却都属于他自己的虚拟与杜撰,与《红楼梦》原作毫不相干。依据“秦学”的“揭秘”情况而言,刘先生的“接受”美学还是称作“新编”美学更为名符其实。
5 关于“秦学”新索隐
经过以上多方考辨可知,所谓“秦学”不是什么值得肯定、值得推广的学术研究范式;“秦学”只是一种索隐,一种新的索隐。我们因此明白,何以刘先生早早就有一个说法:“索隐派你也应该尊重,不能一提索隐派就嗤之以鼻。”[3]175
“秦学”本身充分表明:没有索隐便没有“秦学”。历来索隐派惯用的手法,诸如随意联想、过度诠释、图形暗示、谐音寓意、拆文破句、拆字测字、猜测、影射、比附、诂诗、抉微、分身、合写、等等,“秦学”也都招招取用、不舍不弃,得心应手、操之若习。在一无系统理论基础、二无可靠文献支持的情况下,刘先生就是依仗“自己的善察能悟”[1]26,利用索隐的种种手法,拼凑出大量材料,搭建起“秦学”体系。
关于“秦学”索隐,论者多有剖析。下面仅举两例,权当“立此存照”。
例一:小说所写贾府一副对联的落款“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11]32,在刘先生看来,“这些字眼里其实也都埋伏着意思,都是在暗示太子”[1]111。何谓“同乡世教弟”?“东安郡王”何意?“穆莳”又作何解?他都有诠释。他说:“曹寅跟康熙是一辈的,他转化到小说里,就是贾代善;而曹颙和曹頫跟太子是一辈的,他们转化到小说里,就是贾政这一辈。因此,写对联的人就称自己跟贾政是同辈的,他们祖上虽然是主奴关系,但是起初都在关外生活,又一起打进关内,因此谦称是‘同乡世教弟’。”[1]111又说:“曹雪芹在对联落款上写出‘东安郡王’,是别有用意,是在影射‘东宫’,写对联的时候还安好,但是到后来,可能就坏了事,就消失了。”[1]111至于“穆莳”一解,更见索隐本色:“穆,古汉语里通‘密’,胤礽死了以后谥号就是密;莳,是将植物移栽的意思,胤礽一生两立两废,两次从当太子的毓庆宫移往咸安宫被圈禁起来”。[1]111总之,他说:“这么一想,曹雪芹用这些字眼来写,确实都是影射废太子胤礽,否则,哪有这么多的巧合?”[1]111刘先生末了这一问,倒是“逗漏”出一个重要消息:所以有“这么多的巧合”,不正在于他的“这么一想”吗?
例二:小说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写到一个医生张友士,刘先生凭借“谐音、暗喻”的索隐之法,轻易识破其名“友士”谐喻“有事”,进而揭穿他的身份伪装:“他哪里是个什么业余医生,即便是,那也是个障眼的身份,他分明是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间谍,为秦氏家族背景所派,因而,他那诊病的过程,我以为其实是黑话连篇,”[1]171在小说中,张友士说,“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痊愈了。”[11]126刘先生说:“这都是一些黑话啊,是不是啊?……这个话不是正常医生的话,实际上他所传递的,是某种非医疗诊断的信息。”[1]171针对张友士开的药方,刘先生说:“实际上这个药方,应该是秦可卿真实的背景家族,跟她跟宁国府进行秘密联络时,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1]171接着他说:“下面我把第三味药的两个字拆开,与前后两味药连成句子,那意思就很直白了,它是这样的: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意思就是她的父母说……也即命令她,在关键时刻,在她生长的熟悉的地方,结束她的生命。”[1]172人参、白术竟然代表着父母、兄长,真亏他想得到也绕得到,只怕《红楼梦》作者却始料未及。
然而,红学的历史昭示着:刘先生运用的这些技法,都是毫不新鲜的索隐老套!当然,“秦学”索隐所以称为新索隐,是因为其基本表现与以往索隐有所不同。
不同之一:老索隐只是不顾小说实际,新索隐则不仅不顾小说实际,而且不顾历史实际。老索隐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正确,但是索隐出来的人、事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不过是与《红楼梦》毫无关系。比如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当然背离了作品实际,但是所指顺治皇帝、董小宛毕竟都实有其人。新索隐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凭借主观臆测。“秦学”所谓牵动贾府两翼的人物,一个是秦可卿的原型即胤礽之女、弘皙之妹,一个是贾元春的原型即曹雪芹的一位姐姐,全是凭空捏造的历史人物。
不同之二:老索隐具有较好的学问功底,新索隐学问素养不佳,但却具有文学创作专长。以老索隐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先生为例,尽管他在胡适新红学的批判中首当其冲,但是平心而论,无论是他的专著《石头记索隐》,还是他与胡适进行的论争,都曾显示出令人敬佩的学者风范和学问功底。这一方面,新索隐则难以望其项背。刘先生在“揭秘”中确实暴露了学养的严重不足,学者已经对他讲座的错误多有指摘。他的长处显然就是作家所具备的丰富的想像和艺术的技巧,所以“秦学”索隐更加富有故事性、传奇性以及由此而生的诱惑性、欺骗性。
不同的表现决定于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基础,因此新老索隐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一是新索隐产生的时期不同于老索隐,他们持有不同于老索隐的价值取向。历来索隐者的本意应该说都比较严肃,然而确如有人所指出,“在商品大潮冲击、宏观管理乏善、社会转型期浮躁风盛行的情况下”[5]144,以“揭秘”形式问世的新索隐,“凸显和折射了学术泡沫化、学术浮躁化、媒体商业化、学术庸俗化现象。”[5]144二是新索隐产生的基础不同于老索隐,他们拥有不同于老索隐的学术前提。众多专家业已指出,新索隐都是建立在“自传说”基础之上,是用索隐的手法弹奏着“自传说”的老调。“秦学”立论的前提就是认定“《红楼梦》具有自叙性、自传性、家族史的性质”,“秦学”也已在实际上将坚持极端发展的“自传”论者引以为后盾。考察一下刘心武索隐与周汝昌考证的关系,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