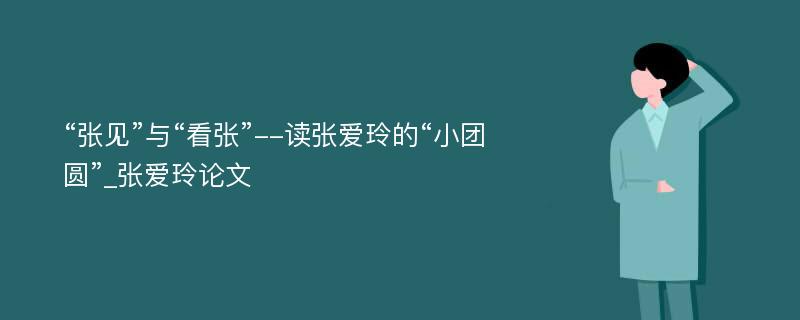
“张看”与“看张”——读张爱玲《小团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圆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张爱玲悄然辞世14年之后,她的遗作《小团圆》果如她的朋友邝文美在1976年所预料的那样——“在万众瞩目的情形下隆重登场”①。应该说,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相比,出版方的“炒作”倒是更为“成功”。其实,无论是出版方还是读者心里都非常明白,《小团圆》之所以能成为热点,“被全球3000万张迷翘首企盼”,并不真的因为它是“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之作”,而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几乎事事物物皆可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相对照并且落实。它浓重的自传色彩,第一次让人看到了张爱玲——那个下笔从来“不沾身”的作家——呈现出来的自己。或者可以说,《小团圆》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让人在读了那么多“张看”的作品之后,终于有机会满足一次“看张”的愿望。
张爱玲的“看”,是一个引起过研究者关注的话题。1976年,当她的散文集《张看》在香港出版时,这个新异有趣且涵义丰富的标题立刻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同和理解,并被看作是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准确概括。这个看似文字游戏的说法具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指作家有意回避主观介入的“张望”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因作者姓氏的巧合,表明了这是一个张姓作家的带有鲜明个人视角和主观色彩的写作。这个双关的说法,正是张爱玲所要表明的复杂的写作立场和姿态。也就是说,张爱玲的“看”,既是一种对世人世情的冷眼旁观,同时又渗透了作家本人对人性、人生、社会、时代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这个“看”的背后,有“思”也有“叹”,有体谅与悲悯,也有刻薄的嘲讽。这应该就是“张看”的特殊风格所在,即:置身事外的观察、精明的世事剖析与苍凉的人生喟叹的三者结合。
事实上,早在张爱玲的成名作《传奇》出版的1943年,这样一个“张看”的姿态就已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多年来为读者津津乐道的《传奇》的封面就是最好的证明。张爱玲自己解释说: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型,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②
炎樱笔下窗外那个窥视着的“现代人”,显然带有张爱玲的外貌特征,这个面孔没有五官和表情,但肢体的动作表现出明显的“好奇”与“孜孜”的姿态。在《传奇》的扉页上,张爱玲写下这句著名的话:“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可以说,对普通人生的窥视,以及从普通人生里窥视到普遍而深刻的人性,是张爱玲小说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她的最高追求。
因此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平凡男女演出的都是时代故事。即如她自己所说的:“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③“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④也无怪乎夏志清对她有这样的评价:“《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他们大多是她同时代的人;……他们的背景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广言之,是一个衰颓中的文化。”⑤应该承认,张爱玲与很多大作家一样,在自己的写作中是有这样一种写出人性之“常”与时代之“变”的抱负的。
张爱玲反复申明自己使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并强调“它是较近事实的”⑥。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为,“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⑦也就是说,她所谓“参差的对照的”的手法是对立于极端的、整齐划一的方式而言的。在她看来,大事件、大人物、大彻悟,都是极端的、不尽真实的。张爱玲的“分寸”,使得她的故事都是小人物的小悲喜。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张爱玲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写不出“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也淡化了战争、回避了革命等题材。她只关注那些乱世中的普通人,关注于他们的恋爱,尤为重要的是,她要写出他们在恋爱之类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素朴”和“放恣”。因为在她看来,这才是人生的真相。
显然,这就是“张看”所采用的“看法”。它带有作家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独特的视角,它决定了张爱玲的写作方式——既写出自己眼中的时代故事,但又不过多掺杂个人感情。事实上,张爱玲的确从不动情。无论是悲悯还是嘲讽,她都不会替小说中的人物多愁善感,更不为他们设身处地。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超然的,即如炎樱的画中所表现的:她站在窗外,面无表情,只有旁观者的好奇,没有介入者的悲喜。但是,情感的疏离并不等于观念的抽空。事实上,张氏故事中处处表达着张爱玲的人生感悟。即如作家王安忆所说:“张腔张调”“不在技巧,亦不在风格,而是直指人世观念,苍茫的空间和时间里,有情人均是一瞬间地擦肩而过。就是这,无疑是张爱玲所作。”就是说,张爱玲是借他人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观念。正是这种“人世观念”,决定了张爱玲只写她自己相信的东西。或者说,她对小说中人物和情节的处理,都会最终归于她观念深处的“真实”与“真相”。比如她在谈及《倾城之恋》的结局时说: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这个结局的设置,典型体现了张爱玲的人世观念。她只相信这一种结局的真实性,否定了其它结局的可能性。她时刻把握着的现实和人性的这一“分寸”,正是在她“张看”的冷眼背后所依赖的思想立场。
因此可以说,“张看”的看法决定了张爱玲小说的风格和深度。在题材上,她专注于乱世中的男女故事;在手法上,她采取“参差的对照的”方式,写“普通人的传奇”、市井人物的悲喜;在主旨上,她是在力求揭示出时代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真实。
“张看”的成功,也让作品背后的张爱玲显得更加神秘起来。多年来,张爱玲以“张看”的姿态行世,虽然在她众多小说的人物形象中,不无自己生活的只言片影,但是,正如那幅封面所呈现的,观看者与被看者之间明显地“比例不对”,观看者的强势无疑使得读者只能随她一同去“看”,去体味“张看”所看到的东西,而对于观看者本身,却多少有些无从认识。直到《小团圆》,才终于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看张”的机会。
事实上,《小团圆》之所以能形成热潮,纯粹就是因为那是张爱玲写出了她自己。虽然无论是张爱玲自己还是他的好友宋淇,都对于读者“喜欢将小说与真实混为一谈”表示了清醒的忧虑,对于“尤其中国读者绝不理什么是fiction,什么是自传那一套”,更是“牢记在心”。但是,与宋淇的忧心忡忡相比,张爱玲的表现显得更加无所谓。说得委婉些,张爱玲是故意要写出自己“最深知的材料”,说得直接些,她那时已经决心要写出一个自己的张爱玲,送给人看,任由人品评。所以她并不真的担心读者“将小说与真实混为一谈”。这样做的原因,也许出于对胡兰成文章中的虚饰之词的不满,意图暴露真相加以报复;又或许是人之将老,真会产生一种任性与冲动,想对历史做一个交代;抑或,是多年的情感和记忆真的压迫着她,令她不吐不快……所有这一切,他人当然无从知晓,包括她最亲密的朋友。
事实是,张爱玲是有意识地写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浓”到人物虽为虚构但事件几乎全部真实。任何一个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很容易把小说人物与现实故事一一对应起来。对此,张爱玲有足够的清醒,因此她会对宋淇说,即便是“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因为“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2页)事实上,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已经委婉地说明了写自传的用意:
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⑧
这样看来,如果说宋淇是希望张爱玲把《小团圆》改写成一篇小说,尽量加入虚构的成分,而张爱玲却迟迟没有依照建议改好的话,倒不如认为,张爱玲从内心并不真的希望把小团圆当一本小说来写,或者,她并不真的希望读者把它当成小说来读。事实上,在写尽人间传奇之后,晚年的张爱玲可能就是想写一本自己的故事。那些她自己“深知的材料”,同样为读者所“深知”,当胡兰成把他们的爱情、把他本人和张爱玲都传奇化了之后,任性的、信仰“真相”的张爱玲,有这样一个还原自己、表达自己的冲动,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说这些似乎都是在妄测作者的动机,其实我想说的是,作为读者,尤其作为深知张爱玲一生经历和故事、熟悉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的读者,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小团圆》当小说来读的。索性抱着一种“看张”的心态,倒也许是读解《小团圆》的最适合的方式。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对于这样一次“被看”的明确意识,是从全书的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中就表现出来了的: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张爱玲一向以用语讲究著称,其比喻之贴切巧妙也一直是无人可及的。她的很多小说都是在全书第一段就奠定了基调,比如《金锁记》开篇那一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的“三十年前的月亮”,就“不免带点凄凉”。因此,作为熟悉张爱玲的读者,对于《小团圆》开篇这一笔,是断不可轻易放过的。
与《金锁记》的月亮相比,《小团圆》的基调可谓更加“惨淡”,更加阴冷沉郁。一向善用比喻的张爱玲,以“军队作战前的黎明”来比喻“大考的早晨”的惨淡,而且称之为“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问,这个比喻是否“言重”了?但是我想,张爱玲是有意为之的。为什么惨淡?为什么恐怖?张爱玲的回答是:“因为完全是等待。”
现实意义上的“大考”,再残酷也未见得能及于战争,或是给人带来惨淡而恐怖的感觉。固然她在后面的一章中详尽甚至是啰嗦地描写了九莉在香港的大学里经历的真实的大考。但与后面具体的描写相对照很容易发现,那实在谈不到惨淡和恐怖,只是普通的紧张和惴惴不安而已。所以,开篇的“大考”,是要在隐喻的层面上才能被理解的。在我看来,这场“大考”,就是张爱玲自己意识里对于《小团圆》有朝一日终将被公开、被“看”、被评说的一种“等待”。
更有趣的是,这样一种对大考的恐惧,又出现在了全书的结尾。当九莉在一场与之雍相遇相爱的美梦破灭之后,接下来是这样一句话:“这样的梦只做过一次,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随后,作者一字不差地复制了全书开篇的一段。形成了在张爱玲小说中难得一见的“首尾相应”的俗套。不消说,这个俗套的写作是非常刻意的。
这个回环往复的俗套,无疑是在加强对“大考”的噩梦体验的强调。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动笔之初,还是在最后收笔之际,张爱玲都深深地知道:《小团圆》这种自传式的写作方式,以及书中无法辨清虚实的“最深知的材料”,正是她将要被人“看”到的人生秘密。《小团圆》记录的是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的一段普通的男女情爱体验,但同时,又因她和胡兰成等人的特殊身份和历史地位,这也便成为了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记忆。这正应了她自己那句关于“传奇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人的传奇”的话。毫无疑问,《小团圆》是张爱玲为自己的人生交出的一张最终的答卷,所以,在交卷之前,她被噩梦一样恐怖而惨淡的“等待”所煎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她不断地进行思想斗争,对是否修改和是否交付出版都举棋不定,在冲动与放弃中反反复复,甚至不无矫情地要朋友代为销毁原稿等等,这无非都是在“等待”过程中的所表现出来的“人之常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团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部。虽然它在艺术方面成绩平平,在意识形态上问题重重。但用“看张”的角度来看,倒是可以忽视那些粗陋和问题的。《小团圆》应有的位置,不是艺术的顶峰,而是作家晚年写作的一个镜像。具体到张爱玲来说,就是一段——甚至一生——“传奇”的“收场”。多年前,傅雷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位旅华数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⑨到《小团圆》为止,传奇真要收场了。与整整一生的传奇相比,这个收场必然是一次示弱,但它或许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对“真相”的坦白:张爱玲,终究是一个有着寻常苦乐的寻常女子。
事实上,“张看”与“看张”并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是有意识地写自传性小说,所以《小团圆》应该算是一次“张看”和“看张”的结合,也就是说,读者通过《小团圆》所看到的“张”,也是张爱玲自己所看的那个自己。打个比方说,这就像是张爱玲照镜子,而我们看到的是她自己在镜子中看到的那个自己。这同时既是看也是被看,这个镜像本身成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
在张爱玲的名篇《金锁记》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片段: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在以往的研究,这一段手法多次被提及并被称赞。主要是因为她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一个画面的淡出和溶入,巧妙地连缀了十年的时间跨度。也有研究者认为,“镜子”是张爱玲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意象之一,在不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镜子,已经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同样具有结构意义的道具。⑩但是除此以外,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一个在隐喻意义上的“镜子”。那就是张爱玲通过小说艺术的方式,对自我内心与生活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观和反省。这种反观,在《小团圆》中,成为了全部的、最重要的主题。
由此把“七巧”置换一下,简直可以说,是张爱玲“双手按住了镜子”,望了很久,在一阵记忆带来的晕眩中发现,镜子里的人也老了三十年。
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看张”中,人们看到了什么?或者说,在《小团圆》这面镜子里,张爱玲照见了什么?
张爱玲自己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当然算是一句较为老实的自陈,但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另外一处则更为坦白直接,那就是说九莉的那句话:“她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事实是只有她母亲与之雍给她受过罪。”
可以说,《小团圆》中除九莉外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两个“给她受过罪”的人。他们与九莉的故事合在一处,就成为张爱玲的镜子中看到的全部故事——童年与青春的悲喜剧。在九莉的童年里有一个母亲;在她的青春里有一个男人,这个人在小说里名叫邵之雍。这两个人都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她的生活,也相继带来了巨大的失望和幻灭。他们是她最亲爱最亲近的人,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分开,他们爱过她也折磨过她,这一切,造就了三十年后那个惨淡而恐惧地等待人生“大考”的她。
写童年、写青春,注定《小团圆》是一本回忆之书。正如张爱玲早年说过的:“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如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11)《小团圆》所做的,也是“证明自己的存在,抓住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同时,这也就是她自己说的“完全幻灭了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的证明。
当张爱玲晚年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她追溯到了自己的童年。宋淇曾经非常准确地指出:
我知道你在写作时想把九莉写成一个unconventional的女人,这点并没有成功。只有少数读者也许会说她的不快乐的童年使她有这种行为和心理,可是大多数读者不会对她同情的,总之是一个unsympathetic的人物。(12)
这句批评里面带有相当的理解,就是知道张爱玲对于“不快乐的童年”所抱有的耿耿于怀的心理。在她的反省中,这“不快乐的童年”是后来一切故事的根苗。九莉长大成人之后,所遇到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她的爱憎好恶、她的欣喜忧惧,归根结底都由她的童年所带来。而这“不快乐的童年”的来源,当然要追溯至她与生母之间的特殊关系与感情。
九莉的身世和张爱玲本人的完全一致:父母离异,从小被过继给亲戚,遂与亲生父母以叔婶侄女相称。虽然少女九莉最终选择母亲而疏远了娶了继母的父亲,但事实上,真正亲近她照顾她的还是那个一直未嫁的姑姑。可以说,在九莉(或说张爱玲)的生活里,母亲这个角色是完全缺失的。有着特殊友情的姑姑与生母——名义上的“二婶”——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奇怪的“母亲”角色。这个“母亲”,模糊在血缘的有无之间,摇摆于关系的亲疏之间,常常在具体事件中提供母爱,却也时刻提醒着她的母爱的缺失。应该说,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母亲的角色至关重要,人生所有功课的启蒙都来自于母亲。在九莉未成年之前,她显然没有得到这样一种来自母亲的慈爱。而到她成年以后,面对那个漂亮的、时髦的、风流的蕊秋,九莉更感受到一种女性间的竞争和压迫。当蕊秋以母亲身份出现时,她是霸道的,纠正九莉的一举一动,还时时刻薄讥讽;当她以一个世故女子身份出现时,她处处优越,使得女儿在美丽高尚的母亲面前,总感到强烈的自卑。仿佛天鹅生下的丑小鸭,而且用九莉的话说:“她这丑小鸭已经不小了,而且丑小鸭没这么高的,丑小鹭鸶就光是丑了。”容貌丑、没有男朋友,是最让九莉自卑的地方,而这足以反映出成年九莉与蕊秋已经完全成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再带有母女之情。
这样的母女关系,决定了九莉的性格和人生。这也就是宋淇所说的“她的不快乐的童年使她有这种行为和心理”。张爱玲确乎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达这一层意思。她不顾读者要小说“好看”的心理,顽强地从头写起,致使宋淇都认为前三章太过琐碎,几乎是人物列表。一向照顾阅读心理的小说家张爱玲这次是任性的,强迫大家读她冗长而琐碎的爱情前史,就是为了交代出九莉成长的心理过程。当九莉真的遇到邵之雍并爱上他的时候,她才会发现,她的人生中原来一直没有上过一堂有关爱情和婚姻的课。因此,即便她拼尽全力去爱邵之雍,但仍要失去他。因为在她的生命里,对于爱情,她是一个天生的残疾儿。
由此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张爱玲其它众多作品中的“母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花凋》里的郑太太,等等,她们都是情感残疾的母亲。她们对于她们女儿的情感悲剧,无一不负有很大的责任。没有“好母亲”,女儿们无从继承和学习“爱”的能力,这就在她们的童年里早已埋下了一个悲剧的种子,只能经历一场悲剧性的青春。这是张爱玲个人的体验,也是她所看到的人生的真相。
然而,在无爱的情感悲剧上又来雪上加霜的,是金钱的罪恶。在《小团圆》中,蕊秋和九莉母女关系的真正破裂源于金钱。特别是在母亲将老师资助女儿学习的八百元打牌输掉之后,母女关系真正破裂了。女儿在心里几次想到“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作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在我看来,张爱玲之所以把小说从她在香港大学读书写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写到这次决裂。而这,正是九莉真正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女人”,而不再是一个女儿或女孩的标志。
在张爱玲的故事里,性别与金钱是在普通人生活中导致“战争”的两个元凶。同时,金钱也是谋杀温情的最利武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锁记》里七巧和季泽决裂的那一段描写:当“命中注定要和季泽相爱”这样的浪漫幻想,遭遇到“他想她的钱”的想法时,一切温情和浪漫都被毁灭了,“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七巧终于变成了一只挣扎的、愤怒的野兽。十年的情感终于抵不过一刹那对金钱的看重。正如七巧立刻明白的那样:“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也许算得上是张爱玲对人性最深入和独到的观察。这观察源自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可以说,张爱玲在写作早期作品时,虽然自己尚未经历恋爱,也并未受到来自异性的伤害,但由于从小在大家庭内部的所见所闻,她还是过早地接触了世事,懂得了金钱对情感的杀伤力。这一点,只要看《小团圆》的前三章中不断出现的各种亲戚家的家务事——尤其是有关离婚与财产争夺的方面——就完全能够明白了。
由于很早就有了对人生的苍凉体认,使得张爱玲笔下各式各样的女性悲剧,表现出相当的共性,即:情感经历的残疾加上金钱关系的腐蚀,撕去了女性所有的浪漫幻想。这是年轻的张爱玲从小看到的“真相”和感受到的“苍凉”,也是她笔下一切悲剧的起点。《小团圆》告诉读者,这个悲剧的种子,是在张爱玲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孕育萌发的。她通过自己的生活,选择了这种特殊的人世观念,并通过写作,反复印证着这一“真相”。可以说,《小团圆》的逻辑,正是“张看”的逻辑;《小团圆》表达的思想,正是“张看”的核心思想内容。
与来自母亲的爱与怨相比,来自邵之雍的一场痛苦而又不无美好的爱情,对九莉来说,可能更加刻骨铭心。那是一场更加身不由己的战争。《小团圆》之引人好奇之处,恐怕也主要集中在这里。与胡兰成的《民国女子》一文相比,张爱玲还原了一对乱世中的普通男女的感情与欲望的故事。张爱玲未必是要故意揭掉胡兰成给这份情感上笼罩的那一层传奇浪漫的面纱,但的确在客观上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这让人想到《小团圆》中的两句对白:
“你脸上有神的光,”他突然有点纳罕的轻声说。
“我的皮肤油,”她笑着解释。
九莉的回答看起来有失浪漫,甚至非常让人扫兴,但确乎是真实的。张爱玲信仰的正是这种“真实”。《小团圆》从整体上就是在消解胡兰成文字中那层浪漫的虚饰。这看起来是让人扫兴的,但细究起来,却非常符合张爱玲的人世观念。宋淇曾对张爱玲说:“这些事积在心中多少年来,总想一吐为快,……好了,现在你已经写出来了,这点也已做到了。”我想,积在她心中多年的,不仅仅是对胡兰成及这段感情的幽怨和回忆,更多的,是通过这段往事,再次让她看到的人生的真实。这真实,是连她这样一个本已看透人生的聪明人也无法逃脱的。如果说,“张看”是张爱玲对“普通人的传奇”的书写,那么,《小团圆》则是她在个人传奇中向普通人的回归。与其称之为“巅峰之作”,不如说是“回归之作”或“真实之作”更加贴切。
从“张看”到“看张”,阅尽苍凉人世的张爱玲最后写到自己,这几乎是一种象征。就像她说九莉的那样,“她最大的本事是能够永远存为悬案。也许要到老才会触机顿悟。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因为是自己体验到的,不是人云亦云。先搁在那里,乱就乱点,整理出来的体系未必可靠。”换句话说,张爱玲是在用交出一个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她的信念,“她相信只有那样的信念才靠得住”,而且,她也相信自己已经到了“到老才会触机顿悟”的时候了。
晚年张爱玲写出了一部琐碎的自传体小说,用家事和情事来应付人生最后一场“大考”,这看起来也许是个有点“小家子气”的选择。但张爱玲有理由这样做,她借小说人物之口这样说:“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或者说,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取向与人生信仰。假如真有“晚年写作”这个概念的话,张爱玲的《小团圆》大概算是最典型的文本。它浓重的自传性、意识流的手法等等,都体现着晚年写作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她写出了一个人即将走完一生时最深切的感悟。张爱玲由此带领读者重走了一遍她人生中重要阶段的道路,她在回忆中顿悟,也让读者由此看到了她文学中最苍凉、最真实的底色。
注释:
①⑧(12)宋以朗:《前言》,《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页,第4页,第10页。
②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倾城之恋》45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③④(1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⑤夏志清:《论张爱玲》,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第26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
⑥⑦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倾城之恋》第462页。
⑨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第70页。
⑩参见水晶:《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