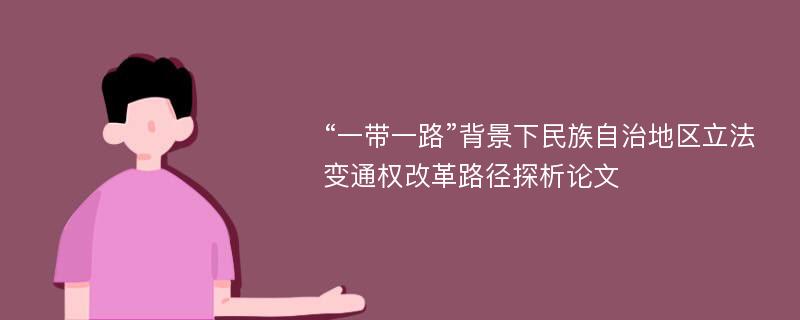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改革路径探析
阳娇娆 黎 群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最终需要沿线国家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配合。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宪法以及相关法律中规定的民族自治地区能够在综合考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对一些特定法律规定进行立法变通的权力。对于民族自治地区而言,立法变通权是宪法所赋予的一种特殊权力,该权力的赋予为民族区域实现自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支撑。当下民族自治地方法规的形式和实质分离、可操作性缺失、公民参与度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评估机制落后是立法变通权改革最紧迫的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族自治地方,在新时代必须自觉地改革已有的不合时宜的法规,提升投资、贸易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 “一带一路”;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改革;效力层级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倡议是国家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变化、立足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目前我国国际法学者从区域一体化国际法和双边国际贸易与投资法的角度开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起到了切实的智库作用。但是,“一带一路”涉及沿线国家的国内法,例如,外贸法、外商投资法、税法、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环保法、知识产权法、民法、物权法、债权法和土地征用规定等。而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根据立法法和全国通行的单行法的授权,可以进行变通规定,本文称之为立法变通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落地实施、深耕细作的阶段,具体到法治建设的层面,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其一,全国性投资法和贸易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必须根据“一带一路”倡议所对接的相关国家进行变通规定,例如,民族特色商品的运输和销售,需要因地制宜地作出变通处理;其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而谋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必然引起自然人跨越国界进行更加频繁的自由流动,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居民与外国人缔结婚姻、生育后代建立国际化家庭的现象增多是必然趋势,于是,根据外国婚姻法所授权的立法变通权,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完善相关立法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了;第三,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民族地方法治的系统性构建,并提出了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实践的迫切需求。我国宪法学者们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也为“一带一路”新形势下探索改革立法变通权的路径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民族法治建设的要求
民族自治地方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是发掘国际经济合作增长结合点的必然要求。例如,广西属于西部沿海的自治区域,面积大,人口多,涉及众多的海洋经济产业,具备连接“一带一路”的海洋合作通道。广西正在大力建设的“南向通道”,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升级换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远洋渔业具备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竞争的优势。东南亚沿线国家大多被海“环抱”,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久远的贸易往来关系,资源丰富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沿线国家的短板正是广西对外开展海洋科技合作的潜在比较优势。广西靠海,具备天然港口的条件,拥有“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输出民族地方特色产品的海上通道。广西作为民族自治区域,这种填空式的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若得不到国家和地方法治的保障,广西企业与沿线国家的企业建立起来的贸易投资关系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目前民族自治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难以实现对接,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立法调整的缺位性和单向性。“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欧亚非洲大陆上和海洋上建立起连接不同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众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纽带,是经济全球化面临困境之际的新举措,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性工程。“一带一路”必定是法治的,否则是不可持续的。在没有先例或可以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在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带给的贸易、投资机遇之前就要清理过时的地方法规,特别是要积极调研,推动构建新的符合一带一路精神的地方性立法,避免法律的缺失。同时,考虑到国际承诺属于国家之间的义务承担,而要实现地方层面的法律义务与权利的转换,需要经过层层的立法授权,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自治地方立法的单向性以后肯定要发生改变,实现双向的调整,更加注重对内对外的权利义务的均衡化处理。二是地方政策制度调整的原则性和随意性。[1]政策的调整空间是允许存在的,但是,多大的政策空间较为合适,是无法划一规定的。例如,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PPP项目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不可随意,也不能过于原则。民族自治地方,PPP项目可能涉及任何社会或经济基础设施,例如,港口、机场、路桥,能源领域的电站,民生领域的公共建筑、体育设施、商业住宅、污水处理等,具体哪些领域允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参与竞争,哪些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政策调整范围之内的事项,需要仔细区分甄别。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必须及时修改或创制符合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地方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区域法治需要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构建。
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使得物流运输需求量不断增加,集装箱作为现代物流的重要载体,极大的提高了物流效率,但是由于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时空跨度大、环境复杂、难以监管,导致货物失窃、产品变质、货物损坏等各类事故频发,甚至出现集装箱被不法分子劫持进行危险品走私和恐怖袭击的事故[1-2],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对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进行信息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举办的2018中国西南(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共开设8个展馆,现场汇聚国内外102个知名汽车品牌,参展车辆1023多台,新车发布会33场;同时举办的“魅力丝路·时尚昆明”汽车模特选拔大赛吸引了400位名佳丽参赛,开展演艺活动100多场,车展规模再创新高、展会品质全面升级。
二、“一带一路”条件下民族自治地区立法变通权改革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改革的巨大动力之源,区域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也在淘汰法治不健全的地方经济体,“法律竞争”的结果是投资主体和贸易主体做出缔约决定的重要考量。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改革的法律基础而言,第一,就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在民族自治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区域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物权法律关系需要协调;第二,就同一民族区域之内,自然人、法人之间,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约束;第三,就同一民族自治区域之内,实体经济的布局和发展,要求地方立法照顾极端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需要。[2]
从微观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有参与合作发展的意愿也是由于经济基础上国家及其内部地方有值得互通有无的地方,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就要具备地方特色,使之能够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动提供根本保障。[8]67民族自治区域所进行的变通立法,当然不得违背上位法的精神,更要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新情况。“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在贸易、投资、劳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方面要抓紧立法,使之符合“一带一路”双边协定下有关市场准入、外汇管理、融资、土地政策、并购、竞争管制、税收政策等的国际承诺的基本要求,但是,这些新情况决定了民族自治地区的法规要做出变通性调整,要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完全反映特定民族自治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地域特色。
综上,回归结果支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变动会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率,然而这种影响呈倒U型,其最终作用结果与一国发展状态(尤其是低收入国家阶段)密切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能存在一个“经济增长最大化的金融最优开放程度”
展会分为宣传水利建设综合展区、施工设备展区、水利机械展区、市政建设及水处理展区、专用车辆展区等。展出的水利机械设备包括汽轮机、水轮发电机、闸门、启闭机等,除了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的龙头企业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恒天九五外,国内外领先工程机械企业如华德液压、福田雷沃、厦门正鸿昌等,国内一流的水利机械企业如葛洲坝船舶、三门峡水工、福建水工等也纷纷亮相水工展。
在“一带一路”落地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国内的民族自治区域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在市场失灵时有政府的适度干预,但是如果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就必须依靠法治的力量。也就是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失灵”最终导致了民族自治地方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就民族自治地方而言,所谓“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民族区域经济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市场失灵的核心因素。
从实际需要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改革的地方文化基础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第一,不同社会法治文化的协调。“一带一路”涉及不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国家,相对于外国而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则是属于一国之内的地方区域,更加增加多样性,需要协调的法律问题更多、更复杂。第二,民族地方法治是利益需要的产物或者说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生成于利益驱动。“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展开,但具体的落地实施是需要一国之内的企业、自然人参与的,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基于民族的特性而设立的,是基于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空间自治,进而形成法律制度的区别化处理。在全国统一的法律之外,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可以基于地方情况的不同而制定出不同于全国的法律。法律的差异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均衡的问题。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涵盖贸易、投资、劳动力输出,甚至涉外婚姻,沿线国家的自然人、法人与民族自治区域内的自然人、法人必定会缔约,双边往来会扩大,那么,“无规则、无经济往来”的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民族法治需要及时变革。第四,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在改革开放40年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缺位,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是史无前例的大战略,是崭新的命题,既有国际的法律竞争也有国内的法律竞争,法律制度的立、改、废是势之必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民族自治的地方性规范要结合具体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使法规条款能够落地实施。为了便于实施到位,具体规范制定之前要注意条文的设计和选择,避免流于空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规范公共权力。在“一带一路”项目承揽、货物进出口审批、进出口企业合同的缔结与监督等环节,都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截至目前参加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数十个,社会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必定影响到各国对法治本身的理解。具体到我国民族自治区域的情况而言,民族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参差不齐,需要我们准确判断法治的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我们知道真正的法治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情形下才能产生,我们不能寄望于人类伟大的想象力,凭空想象出极其完美的适用于任何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民,因此,适合特定民族区域的法治必定是要有丰厚的价值内涵的,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实体的价值。在“一带一路”条件下,我国自治地方立法机构不得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要全盘考虑到诸多外国因素,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人、企业来投资、贸易和参与当地环境生态保护事业,从而,要求对既有的地方法规中排斥外国资本的条款予以修订,使之符合平等竞争的形式价值的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即使国家人口有多寡、实力有大小之分,但是基于司法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法原则,各国的合同法、电子商务法、海关行政法,经济贸易纠纷解决的仲裁或司法制度各有不同,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必须注重立法形式与实体价值的统一,不得出现两张皮的现象。[7]103
从文义解释来看,民族自治地方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立法的,应该就“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立法。[6]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立法变通权改革的路径
(一)立法变通权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化思路
从实证的角度,就我国而言,《立法法》第64条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可以作出规定的事项,民族自治地方据此享有变通立法权:第一,为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这是执行性质的立法变通权。第二,对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可以作出变通规定,这属于自主性立法变通权。[4]第三,在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5]这属于特殊情形下的立法变通权,目前使用的较少。
从宏观来看,“一带一路”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区域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和力度,与之同步的必然是进一步整理和完善那些相对保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活动的过程中确实需要进行变通立法时,必须遵守其允许变通立法的界限,不可逾越但可以适度超前制定地方性法规。我们知道,全国性的法律的触角几乎遍布全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这样说,在每一部地方立法里都可以找到中央立法的痕迹,但是,地方立法是必要的,很多事项的立法必须地方化,且无需中央的特殊授权。这是“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落实之后我们必然看到的立法现象,也是体现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方面。尽管不同层级立法机构之间立法事项有太多的重合部分,出现了“职责同构”,但是,民族自治地方不可以越位立法是自始至终要遵循的原则。“一带一路”是巨大的创新之路,不同于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多边主义,因此,在沿线国家相互签订双边投资或贸易协定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作为协定缔结国的领土之一部分,在对接对外贸易、投资、劳动力输出的快车道的时候,创新清理、完善地方性法规的自觉性、主动性也就更加强烈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清理那些不够适应“一带一路”沿线经贸竞争需要的过时的法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扩大对外开放是民族自治地方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利好机遇,也有修订过时立法的迫切需要。在传统的立法分权的角色中,民族自治地方作为中央的下属机构,是在地方的代理人,民族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精神当然要保持一致。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民族自治区域是作为特定区域的管理者而设置的,有着本区域的利益要求,代表着自身利益,同时对该利益负有管理的责任,并且要负责实现到位,因此,在地方法规的修订工作中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在平行并列的若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要实行国际法治,就必须寄望于塑造有序化的经贸合作模式。所以,从形式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法治。就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参与“一带一路”的实践而言,国内民族法治的结构要合理,法律条文之间不能出现前后矛盾,也不得朝令夕改。由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至今尚未定论,也没有统一的国际法可以参考,因此,相对于国际法而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法规体系、结构与规范、方式和程序及其调整社会关系的效果等方面,应当具备本身的要素与特质。形式价值要求民族自治地方要有完备的法规和规章体系,而实体价值则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法治对公权力予以规范,对私权力加以保障。在“一带一路”条件下改革民族地方立法的总目标是要将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在法治建设中统一化于法治的运行与成效、结构与功能、进路与目标。
1.认真学习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法规,加强行业自律,要时刻保持对政府采购工作的“敬畏”之心。之所以要“敬”,是因为政府采购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不能敷衍了事。同时,对招标代理机构而言,虽然不是权威机构,但招标代理所产生的结果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必须无任何水分地执行的。之所以要“畏”,是因为政府采购这项工作时刻充满诱惑,稍有不慎就会触碰到法律红线。
(二)立法变通权要被精细化运用的策略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改革的经济基础,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需要:第一,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我国是多民族聚居的统一的国家,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诸多民族矛盾,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宗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改革也就从“应然”走向“实然”;[3]第二,基于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求,在民族区域内还有部分极端贫困人口,需要立法的支持和关照;第三,基于解决民族区域之间社会矛盾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实施是法律规范的竞争,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其解决不得不依赖创新性民族地方法治。
所谓“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一是民族区域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信息不完全,经济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不够,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备;二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在对接“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产能输出和技术合作的过程中不能尽其所能地予以政策配套;三是民族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充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尚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四是区域经济管理部门的寻租行为,凭借政府保护进行财富的转移而造成资源的浪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个前提就是沿线国家的企业、自然人必须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合法的利润,坚决打击寻租等违法犯罪活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都颁布了“反商业贿赂法”,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摆脱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究其实质是法律竞争的结果,企业、法人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后产生经济效果的主要参与者。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企业、自然人在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应当被激励参与法制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发展,沿线国家立法技术的交流也将趋于频繁,众所周知,立法听证,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程序。就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立法权的运用而言,作出变通规定之前的听证程序可以切实地提供程序性的保障。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程序中,公民参与的过程要有明确的规则,例如,代表的资格审查、发表意见的次数、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民众意见的收集和整理,都需要落实。
在“一带一路”的双边合作过程中,透明度原则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对产品来源地标志、税务处理程序、检验检疫标准等法规,必须预先公开,这是国际贸易领域通行的规范。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公民参与本区域经贸法治建设,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法人代表的身份,都需要获得对称的信息。信息披露的条件、程序、细则,是立法信息披露的前提和保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达,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振兴民族地方经济的推动力量,数字经济的法律调整也将提上日程。在数字贸易与地方特色文化价值的冲突、数字贸易与个人隐私权保障的冲突加剧的条件下,要实现信息披露的要求,是需要地方立法机构进行慎重权衡的,此是立法变通权改革的难点。
即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前,我国民族自治区域进行变通立法之后也是需要配置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的。民族地方的变通规定,其效果和质量如何、谁来评价、评估标准是什么,至今仍然有待解决。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来看,多半偏重于自我评价或上级主管部门评价,目的也只是对法治工作的落实和绩效的推进。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立法评估机制,侧重于变通立法后的法律实施实际效果的评估。
(三)立法变通权要更多地在新的经济法律领域运用
在“一带一路”落地实施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反思和改革民族自治区域实体法制建设的效力层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客观的,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区域经济体的身份参与到对外经济贸易投资活动的潮流中必定引起地方经济法律的竞争。民族自治区域发展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必定催动民族自治区域经济法律之间的竞争,且趋于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加强对经济领域立法变通权的改革。
首先,要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变通。经济学理论表明,法律对于经济的运行不仅仅作用于外部,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引发经济变革的重要因素。[9]从这一理论不难判断,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合理变通和运用,能够更好地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不过,毕竟“一带一路”倡议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当前国内的地方法律接轨和变通的情况来看,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法规的变通权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经济方面变通的法规数量较少,质量也相对较低,由于大量涉及自然资源以及经济管理权限。[10]因此,在地方经济法律领域进行变通非一日之功。
(3)在相同质量流率和相同热流密度条件下,均是微通道分支数越多,热沉最大热应力和最大形变越小,研究表明,微通道分支数为8时可以获得最小的最大热应力和最小的最大形变,但微通道分支数由6增大到8对最大形变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经济活动方式更加需要立法变通。电子商务法等规制新经济活动的地方性法规的变通规定有利于民族区域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和贸易发展。在互联网成为链接地球各个城市、村落的重要工具的当今时代,我国民族自治区域也实现了网络化,取得了数字化普遍率攀升的效果,为此,数字贸易的地方立法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要抓住法律创新的机会,可以考虑在民族地方变通权的运用中开辟出新的实验区,构建统一适用的数字贸易法。
参考文献:
[1]徐亚文,邵敏.论新《立法法》修订后的市级立法权[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2]唐杏湘.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权的完善[J].广西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0(4).
[3]苗连营,张砥.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规范分析与逻辑求证[J].地方立法研究,2017(1).
[4]刘琳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探析[J].社科纵横,2010(2).
[5]敖俊德.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两种变通权之间的联系和区别[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6]石东坡.立法需求的生成与确立问题探究——析《立法法》第72条第4款[J].法学论坛,2016(1).
[7]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8][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9]苏鹏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角度[J].青年与社会,2013(6).
[10]徐合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解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
THE REFORM PATH OF LEGISLATIVE ACCOMMODATION POWER IN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ang Jiaoyao,Li Qun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The legislative accommodation power in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is the right to adjust some speci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ccom⁃modate the special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ethnic autonomous areas,which is stipula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relevant laws.For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it is a special power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which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ethnic autonomy.At present,the legislative accommodation power in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suffer from face problem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its form and substance,lack of operability,low participation,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and backward evaluation mechanism,all of which are in urgent need of reforming.In the new era,the ethnic autonomous areas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voluntarily reform their existing outd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thnic autonomous areas;legislative accommodation power reform;effectiveness hierarchy
【作 者】 阳娇娆,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法学硕士;黎群,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师,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在站)。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 DF28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19)04-0038-006
〔责任编辑:罗柳宁〕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民族自治地区论文; 立法变通权改革论文; 效力层级论文; 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