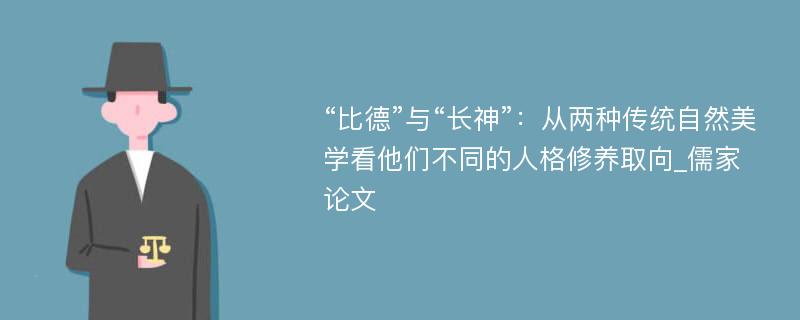
“比德”与“畅神”——从两种传统的自然审美观看其不同的人格修养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审美观论文,取向论文,修养论文,人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基于不同的人生意义和宇宙观点,形成“比德”与“畅神”两种自然审美观。他们从人与宇宙自然的交相感应之中,领悟到两种不同的人格完善的真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精神修养取向。这两种自然审美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后世人际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伦理教化与神与物游
“比德”作为儒家自然审美观,必然与其强调人际伦理,重视仁、义、礼、智、信紧紧相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在于“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只有“礼”才是理顺君臣父子、夫妇、亲朋之间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上下等级之间只有各明其分,才可大顺而治,否则,逆之则乱。“大逆不道”历来为儒家所耻,因此,各种人伦规范也纷纷因礼而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而以礼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规范要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推广,就必须要求每个社会个体加强内在精神上的修炼,以严格的道德自律使外在的社会理性纳入个体内心,内化为一种伦理人格。而“比德”就是这种伦理人格精神在自然审美方面的表露。
孔子及其后继者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把握中,以自然山水的某些形态特征与人际的伦理品格之间的相通作为契合点,把二者相比拟,为理性的社会内容强化为人的内在人格找到了感性依托,借自然的感性审美力量,进一步强化人格中的理性内容。
最早提出“比德”这一概念的是荀子,他在《法行》篇中说: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粟而理,知也;坚刚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
这里对于玉的欣赏不再停留在玉本身,而是把玉的光滑、润泽、纹理细腻、坚刚不屈等特点与儒家个人修养中的仁、知、义、勇等品质相类比,在玉与人的品质之间找到了契合点。玉在古代常常为士大夫阶层所贵重并获得较高的审美意义,也正在于此。
从玉与人的品质的这种比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比德”这一自然审美方式的根本特点,那就是尽量寻找自然审美对象与人的品质之间的相通相似,以自然物审美特点为人格修养的标准。
对这种审美方式加以追溯,便找到孔子。《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的很多这类言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面对碧水之浩荡奔流,高山之奇伟峭拔,松柏之肃然威严,领略的重心不在于自然山水本身的美,而在于它与人的精神品质的相通类似,自然景物作为人的精神品质的象征而存在。
最能集中体现儒家这种自然审美方式的要算他们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思想的阐发解释。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有载:
“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下之,其似有礼者。……不清以入,鲜活而出,其似善化者。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者所以乐水也。”
可以看出,刘向把活泼灵动的水的自然之态与人的品格修养作了绝好的类比,从儒家的思想出发,对知者所以乐水的原因作了最充分的阐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刘向对水的审美体验是不完全的,即他并不能完全地沉醉于自然山水之中,做忘情的美的享受,儒家的“德”、“圣”、“善化”这类理性的内容始终不能使他实现自身与自然的完全的融合,因此,这就严重影响了对自然的审美向更高境界的发展。
与儒家不同,道家讲究的不是理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而是人对宇宙天地、自然大化生生无穷、运作不息的大道的感悟。这种玄妙无比的“道”被看成是宇宙之终极,天地之本源,同时,又是其运作变化之动力。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又是先天先地无始无终的“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种幽微玄妙的道涵纳于一切事物之中,又超越于一切事物,道家所提倡的就是对这种宇宙大道的感悟,通过感悟大道从而实现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感受大的自由。因此,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非常鄙视斤斤于是非、利害、得失的儒墨之学,而崇尚生命的丰富自足,精神的自由解放。他告诫人们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超越是非、物我、生死,在天地大化中寻求自由与永恒,与道为一,与天为徒,与天同乐。
道家的“畅神”自然审美观与这种悟道思想相一致,表现为内在精神上的领悟,人的内在精神完全浸润于自然之美中,与自然天地相融注,“神与物游”合于大道,人在其中感受到自身与自然的内在交融,获得直抵生命本源的周流六虚、上天入地的生命体验,或者大智若愚、返朴归真的澄明境界,这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和解放。
对老庄这种自然天道观作进一步发挥的是其后学——魏晋玄学。魏晋时的隐士浪子把人的视野从注意社会伦理规范的汉代儒家独尊而引向纵情于自然山水,从自然美中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从而摆脱樊笼似的人事羁縻。此时,人们开始以真正审美的眼光来欣赏自然。自然山水不再只是道德的比附物,而是亲切的,充满生机与活力。对此,我们可以从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及顾恺之的画中清晰地看到。人们至此才真正发现了自然美,一方面使其脱离了沉重的道德比附而独立出来,同时又承接老庄思想并把他们所宣扬的本体意义的“道”世俗化,推向广大的凡世人间。
晋宋时期著名的绘画理论家宗炳最早在他的绘画理论中提出山水画的目的是“畅神”。“峰岫峣岩,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注:《历代论画名著条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岩岩山林、流泉飞瀑、茂林修竹、云光霞影在人的审美心理上唤起的已绝不只是取譬象征的比德,人类此时才真正成为审美的主体,在自然山水的忘情游乐之中,获得生命的激情和超然心境,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到与人的内在心灵性情相通相融的精髓所在,使心灵在自然山水中获得完全的舒展自由。
人类这种对自然美的自觉是与魏晋这一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同步的,从曹氏父子到竹林七贤,再到陶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的发展规迹。而溯其源头,我们不能不看到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道家是重视生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人与自然大化的和谐之中寻求一种无限与永恒,实现心灵的超越与自由。道家的这种影响非常广泛,不仅成为中国古典艺术与审美的重要特色,而且使这种对自然美的追求成为民族性格中充满浪漫色彩的重要特点。
二、理性精神与浪漫情怀
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比德”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其中自然的价值在于它的一些形态特征与人的品格的相通,从而成为人格美的隐喻或象征。从审美角度来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地,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成完全的审美对象进行把玩、鉴赏,就更不必说超越自身,游心于物,体验神与物游的畅适、美妙。因为儒家过于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来接受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体改造为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因此,无论在艺术中还是身处自然山水中完全地放纵个人感情都被认为是不可取的,都有损于人伦教化的完成。孔子所谓“乐不至淫,哀不至伤”、“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样就限制了个体丰富的感性直觉在自然山水中的自由舒展,严重阻碍了人对自然的审美向更高境界的迈进。这就好比是系上黄金的鸟,永远不能像大鹏那样扶摇直上青天,在宇宙天地间作自由翱翔。另外,在自然美的特征与人伦精神之间所做的比拟,往往显得生硬牵强。刘向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作的阐释显然是有意比附。而汉代《诗大序》中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成是“后翼之德”,就更显得荒诞了。
“畅神”自然审美观抛开了对于现实利害得失的计较,也不存在要把身外理性的内容纳入自身,而是完全使人浸润于宇宙自然之中,感受与物俱化,神与物游的境界。
庄子在他的寓言故事中用奇伟瑰丽的言辞尽情泼洒,表现他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他赞美怒而奋飞的大鹏,其翼若陲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扶摇而直上者九万里,尽情渲染宇宙天地的壮阔豪迈,显示一种生命的力量和激情,使人感受到其中的浪漫与自由,这就是庄子所谓“天地之大美”。对于大而无用的曲栎树,庄子说“何不立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对于盛水不能自举,剖之无所用的瓠,庄子又建议“虚以为樽,而浮游乎江海之上”(《庄子·逍遥游》)。可见,庄子与儒墨之学完全不同,他不仅超越了物性实用目的,还超越了社会伦理道德,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超然的态度,所求的也完全是精神上的逍遥自适。
“姑射神人”是庄子心中理想的人生境界。他这样描述:“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这种人生的精纯美妙是一种超越了人世之累,生死之苦的沉静恬淡。这种淡远辽阔、高明澄澈的境界是审美之至境,也是人生之至境。
达到此种境界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静思默察的方式,由感悟来实现的。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十六章》)只有保持静虚状态,才能观照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庄子则在此基础上把这种心灵的内修发展为“心斋”、“坐忘”和“朝彻”,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如此,人进入一种空明之境,俯仰天地,心与物游,“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想象力自由伸展,生命回归灵魂之乡。
三、伦理人格与审美的价值取向
儒家“比德”自然审美观强调的是“德”,因此,成就“德”成为所有的中心,也就是要塑造一种儒家伦理人格来适应社会的要求。千百年来,众多的贤士儒生往往把自然物的美好特性悬为自己的理想,磨练自己的意志,修养性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论语·子罕》)“出污泥而不染,浊清濂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把个人刻苦的自我修养与治国、平天下伟大的历史使命相结合,成就一种具有光辉色彩的崇高的儒家伦理人格,这就是自然在儒家个人修养中的重要意义,像梅、兰、竹、菊、剑以及前面曾提到的玉都具有这种意义。豪侠之士,仗剑远游,以剑自喻,宁折勿弯;儒雅书生,植竹种兰,修身养性,以图来日有成,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畅神”作为道家的自然审美观,从自然中感受到的是精神的欢娱自适,完全是形骸与灵魂的双重放松,人从自然中感受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美好,那是一种人性的自由舒展。“畅神”自然审美观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审美,它所孕育出的是一种审美情调,培养出的是人的审美人格,其主要影响表现在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方面。
首先,对自然的热爱与赞美是艺术永恒的主题。在美好的自然中,人类不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抚慰心底那股永远的乡愁。宋人张于湖在其诗作中曾有精妙之语。他的《念奴娇·过洞庭》曾有这样一段:“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这里作者表达的是一种神融于自然,表里澄澈清明的境界,这种“意境高超莹洁,而又具有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的境界”(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就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正是借自然之美妙意蕴才把内含于生命底层的激情倾吐宣泄。
其次,我国古代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讲求意境、神韵,提倡清水芙蓉式的素朴恬淡、不事雕琢的自然美,就是继承了道家“无以人灭天”的思想,把朴素无华、自然天成看成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审美感受、艺术欣赏中讲求领悟,灵犀感应相通,在艺术创作中讲风骨、重传神,也与庄子的“心斋”、“坐忘”思想相承。
最后,“比德”与“畅神”两种自然审美观并不是对立的,界限分明的。虽然“比德”观念从产生后一直沿传至今,但从它产生的历史阶段来看,是人与自然建立审美关系的初级阶段,而对自然进行完全的审美观照的“畅神”观念,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未尝不是以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更高一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不仅需要有社会理性的规范,同时也需要在自然与艺术中放松形骸,提升精神。如此,两种自然审美观在具体的与人融合的存在样态中不仅不对立,往往还能够相互补充。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就是集二者于一体的,像李白、苏轼、郑板桥等等,都是如此。郑板桥曾有过这样一段表述:“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闭中闷中有伴。非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注:转引自叶朗:《儒家美学对当代的启示》,《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这里,郑与竹石之间结为一体,息息相通, 充满了不可言说的诗意,而另一方面,竹石又何尝不是他人格品质的象征呢!
收稿日期:1997—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