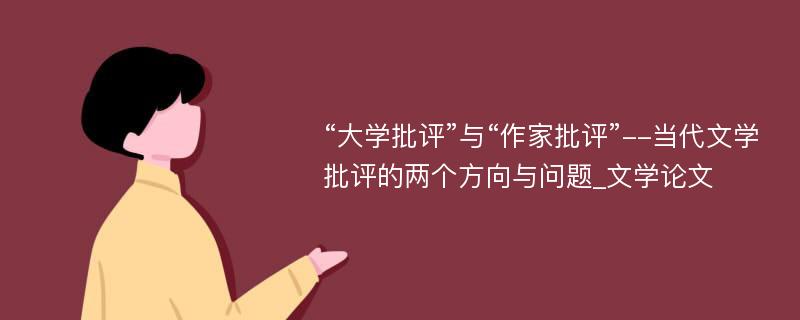
“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两种论文,当代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向”或者说“模式”:一种是学者批评,我称之为“学院批评”,这类批评更关注文学理论问题,它虽然也涉及到当下的文学现实,但这些当代文学现象多表现为理论的材料,即是为理论服务的,其最终结果表现为理论形态而不是批评形态,具有中国古代“八股文”的倾向和特点。另一种是作家或准作家批评,或者是具有作家倾向的批评,我笼统地称之为“作家批评”,这类批评多关注文学的创作实际,多从写作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其最后的结论多是为其他的作家写作或现实文学问题“献计献策”,具有中国古代“策论”的倾向和特点。
当然,我这里所谓“策论”和“八股文”都是比拟意义上的。事实上,在内涵上,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批评”与“八股文”写作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作家批评”也与“策论”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在写作特征和写作取向上,以及二者各自的优缺点上,“学院批评”与“八股文”写作具有惊人的相似,“作家批评”与“策论”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八股文”在写作上循规蹈矩、引经据典乃至于墨守成规,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批评”也是重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历史上的理论问题,也是旁征博引,理论上一套一套,但却脱离文学现实,缺乏实际意义。“策论”在科举考试中与“经义”相对,主要是议论时事,所以本质上是“时论”。而“作家批评”也是关注文学中的时事,包括创作经验和体会,具体作品的创作得失,文学发展的价值取向、政策措施等。所以,本质上,“作家批评”属于实用批评,而“学院批评”则具有纯粹的学术研究性。
其实,“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的分野并不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现象。英国哲学家、美学家科林伍德曾把对艺术哲学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哲学素养的艺术家”,另一类是“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艺术家型的美学家熟知自己所谈论的内容,他能分清艺术的事物与非艺术的事物,还能说出那些非艺术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妨碍它们成为艺术,又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误认为它们就是艺术”[1](P3)。也就是说,他们对艺术非常敏感,善于鉴别艺术,对他们所谈论的内容非常熟悉,其缺点是不能对艺术深层的原理进行深入的追问。而“具有艺术趣味的哲学家”则相反,“他们令人羡慕地免于讲不出道理,但是要说他们了解自己所谈论的事物,那可就没有保证了。”但是,“哲学家的美学,因为缺乏一种有形的标准,无法判断美学理论在与事实关系中的真实性,只能运用一种形式上的标准。它能检验出某种理论在逻辑上的缺陷,因而予以舍弃,但是它却永远不能主张或提出任何一种作为真理的美学理论”[1](P4)。也就是说,他们能对艺术问题讲出很多道理出来,但这些道理属于哲学问题而非艺术问题。对于具体的艺术,他们的感悟能力非常有限。科林伍德把哲学家的美学称为“学院派的美学”。
实际上,科林伍德所概括的两种倾向不仅适用于美学研究,也广泛地适用于文学批评,不仅广泛地适用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也广泛地适用于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中国当今的文学批评仍然是这两种基本的缺陷和问题。
法国现代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则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种类型:“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大师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我将称之为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看书,从这些书中总结出某种共同的理论,使所有的书,不分何时何地,建立起某种联系。艺术家的批评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批评,作家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一番思索,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2](P3)。对这三种批评,蒂博代还有多种命名,比如“自发的批评”,又称之为“口头批评”、“报纸批评”、“当日批评”、“新闻记者的批评”、“每日批评”、“新闻式的批评”、“专栏批评”、“沙龙批评”。“职业的批评”又称之为“教授批评”、“学院批评”、“求疵的批评”、“雄辩的批评”、“纯粹的批评”、“历史的批评”、“哲学批评”、“道德批评”、“大学的批评”。“大师的批评”又被称为“寻美的批评”、“同情的批评”、“天才的批评”、“作坊的批评”。这些命名强调的是各种批评不同的侧面,当然并不准确,但它们从总体上概括了三种批评的特征。
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批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文学批评”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蒂博代那里,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还缺乏理论上的区分,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美“新批评”产生以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便从理论上区分开来[3](P30—39),它们三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艺学”。这种区分被后来的文学理论所广泛地接受,也为“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理论所沿用,所以,本文中所说的“学院批评”不包括文学理论研究,也不包括文学史研究。
而具体就中国来说,文学批评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蒂博代所说的“贵族沙龙批评”现在可以说完全不存在了。新闻记者的报纸批评现在被称作“传媒批评”,仍然存在,但它在整个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在现代报纸中,文学批评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每日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并且批评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轻松、活泼、幽默、趣味、个人感觉和阅读体验已经不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介绍、政治定性、风格定位,且是文风僵硬而死板。专门的文学报纸少而又少,其中的文学批评充满了政治和爱好的偏见,且十足的学究气。
“职业的批评”已经不再限于大学,大学以外有很多专门的并且体制化了的文学机构,这些机构养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员、文学管理人员、文学组织(编辑)人员,当然还有一批文学研究人员,而这些文学研究人员才是真正的“职业文学批评家”,他们以文学批评为业。与他们相比,大学教授的文学批评反而变得有些业余,因为大学老师以教书为“天职”,学问上则以“研究”为正统,文学批评则为教书的附庸和文学“研究”的延伸,除非是以当下文学作为“专业”的大学老师,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文学专业老师来说,文学批评并非他们的本职。
在蒂博代的著作中,“求疵的批评”属于“大师的批评”范围,但在现代中国,它更属于“职业的批评”。在蒂博代那里,“雄辩的批评”是“职业批评”的重要特点。所谓“雄辩”,当然具有理论上的意味,但蒂博代主要是在语言的修辞学意义上而言的,也即词语的优美和力量以及文风的轻松。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中,这恰恰不是学者的特点,而是作家的特点。所以,蒂博代所说的三种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实际上已经简化为两种文学批评,即“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并且在批评品格上非常分明。当然,我这里所谓“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并不完全是由职业位置决定的,并不是说大学里的文学批评都是“学院批评”,作家协会里的文学批评都是“作家批评”,大学里也有“作家批评”,作家协会里也有“学院批评”。“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的区分主要是根据批评的品格来决定的,大致来说,“学院批评”重理论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作家批评”则是实际研究,表现为一种实践形态。
反省这两种批评,我们看到,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合理性,但同时它们又都存在着相当的不足,并且这种“不足”正是制约和妨碍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
“学院批评”的确具有“作家批评”所不具有的一些优点,表现为:具有历史感和理论的深度,在表述上逻辑性强,周密、严谨,注意用词的分寸,材料丰富。一般地说,属于“学院批评”的批评家大多都受过良好的理论训练,他们大多数是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一路读过来,他们对于中外文学史非常熟悉,特别是对于属于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非常熟悉,他们大多数都系统地学习过西方文论史,这样他们在谈论他们的批评对象时便有一个以理论为“横”以文学史为“纵”的坐标,这种“坐标”非常有效地使他们的谈论具有学术性、规范性、知识性甚而“权威性”。
但问题在于,文学史是发展的,文学是发展的,文学的发展必然导致新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相辅相成,文学理论也应该发展和更新。并且新理论大多数是建立在旧理论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一方面吸收旧理论的合理性因素,同时又克服旧理论缺陷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所以,理论的“新旧”与时装的“新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把运用和借鉴新的理论简单地看作是“时髦”,这是对理论的极大误解。而更重要的是,很多新理论同时也是在对新文学现象的解释和总结中建构起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过分地重视文学的历史形态,过分沿袭过去旧有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方法,文学批评便会在不自觉中变得老化、滞后,便会用旧的批评标准来衡量新的文学,其必然趋势是厚古薄今,其必然结论是今不如昔。在旧的文学理念和旧的文学批评标准之下,反传统的新的文学几乎是先在性地必然会遭到否定、压抑,这是不证自明的。而文学的发展正在于创新,文学批评的职责恰恰在于总结这种创新,扶持这种创新,当然也纠正创新过程中的某些不良倾向。现实却是,有些“学院批评”已经严重丧失了文学批评的功能,不是帮助文学的发展,而是阻碍文学的发展、打击文学的创新。
对于我们的文学批评,很多作家干脆不予理睬,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批评家并没有说到根本上。文学创作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们的批评家却还在用老一套话语进行言说,作家自己感到得意和满意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批评家不满意并批评的地方,批评家所肯定并提倡的东西恰恰是作家已经抛弃的东西,作家新的创造被我们批评家视而不见,作家写作中平庸的东西却被我们的批评家激赏。作品对于作家来说就像孩子,对于写作他们虽然讲不出道理,但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作家还是有感觉的。批评家所评论的和作家的创作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批评根本就没有击中创作的要害之处,不论是说好还是说坏,都不能令作家信服,那作家为什么要买我们批评家的账。实际上,很多作家,都是因为听从了批评家的“指点”和建议,结果写作越来越失败,其作品越来越不受读者的欢迎。杨沫的《青春之歌》初版本来很好,后来按照我们批评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结果却是越改越糟。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本来写得很好,如果作家就这样写下去,《李自成》肯定不失为当代文学的一部杰作,但作家受我们批评家的影响,采纳了批评家的一些意见,结果越写越差,终至以成功开始以失败告终。批评家这种因为不正确的批评而“害了作家”的事,在当代文学中时有发生,在当下可以说正在频繁地发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批评家难道不应该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么?
“学院批评”在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实际出发,由此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理论的陈旧,问题的陈旧,便会导致视野的狭隘,只看到了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和与历史现象非常相似的当代文学现象,而对新的文学现象却视而不见,或者用旧的文学理论标准来评价新的文学现象,即把新的文学现象纳入到历史的框架中去评论,从而导致对新的文学现象的否定。一句话,在理论上过于执守传统和经典,常常会对当下的文学现象缺乏敏感性,特别是对新的文学探索、新的审美意识和形态的麻木。
吕进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新诗研究专家,在新诗文体学、新诗鉴赏、诗学理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之前诗歌创作成就方面也做出很大的成绩。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有创作体验,这加强了他诗歌评论的力度。2002年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4]一文,应该说,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对于“政治论诗学”、“新诗研究观念转变”、“新诗文体”等问题的描写都是很准确的,也很有见解。但也有缺憾,那就是,遗漏了“先锋诗论”,陈仲义先生概括为:“对20世纪后20年代——新诗研究中最活跃部分的整体遗失。”[5]我认为陈仲义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它列举的事实恰恰构成了吕进先生论文的补充。对于先锋诗以及相应的先锋诗评,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先锋诗和先锋诗评这一事实本身却不能否认。吕进先生长期关注诗歌和诗歌理论,我相信他注意到了先锋诗歌和先锋诗论这些现象,我也相信他不是疏忽了这些现象,而是有意地忽略,而忽略的背后就是诗歌观念和文学理论基础。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个人的诗歌偏好,看作是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但这“偏好”和“理解”从根本上受制于理论。
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时时反思我们的理论基础,包括:理论的合适性与不合适性,理论的优长与缺陷,理论是否在总体上已经过时,我们对理论的运用是否过于偏执或僵硬。我们应该关注文学理论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并充分吸收这些新理论的合理成分,这不是赶“时髦”的问题,而是“与时俱进”(可惜这个词现在用得有点滥)。
与上面的情况相反,一些“学院批评”倒是很热衷于引入西方新的文学理论,但却犯了另一种毛病,那就是,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在批评运用中又往往落入生搬硬套的极端。表现为,新的文学理论不是在精神上,而是在形式上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不是因为新的文学现象需要新的文学理论来阐释,而是引入的新的文学理论需要新的本土文学现象来证明从而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也就是说,新文学现象是用来为新文学理论服务的。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不是在解决当下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而是在证明外来理论的普适性,新文学现象成了理论的佐证材料,成了外来新文学理论的附会。笔者充分肯定当下一些“新潮批评”或“先锋批评”的合理性、探索性、理论建设性,但同时也注意到它们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理论与实际在批评顺序上的本末倒置。
当代文学批评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比如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这具有充分的根据,是合理的,积极的。事实上,它对于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它发现了很多问题,对很多文学现象特别是新的文学创作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对于建立新的审美原则具有推动性。但缺憾也是明显的。有些批评理论上头头是道,但和写作实际相距甚远。西方的文学理论有它西方文化、政治、经济背景,有它特殊的文学实践的基础,它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我们承认文学具有某种共通性,但也必须承认中西文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差异的层面上,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具有参考价值,但也有适用的限度。西方新的文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现实,生搬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就会方枘圆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矛盾冲突乃至扞格不入。
现实是,有些“新潮批评”,一味地趋新,对于西方的某些文学理论,自己也只是知道了一点皮毛,但却马上“拿来”,生怕别人抢了先。不是结合实际灵活地运用,而是照搬照抄机械地运用;不是精神和原理上运用,而只是词句上运用,结果充满了缺乏限定和说明的怪异的词句。更令人生厌的是,有些“新潮批评”故弄玄虚,故意语言含混、模糊、不知所云,故意逻辑混乱,结果弄得大家如坠五里云雾中,连学者们都看不懂。有的“新潮批评”完全与文学创作实际脱节,几乎近于玩批评游戏,批评在这个时候完全走向了自我封闭,成了圈子里的自娱和表演,即不是写给一般读者看的,也不是写给作家看的,而是写给“哥们”看的。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理论的泛滥,表现为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纷纷引入中国并被迅速地运用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则是很多文学现象并没有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释;一方面似乎是理论过剩,另一方面又似乎理论还不够。归结起来,还是我们的“学院批评”不够成熟,关键的问题则是理论的先入为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本末倒置。
所以,文学理论既成就了我们的“学院批评”,也害了我们的“学院批评”。“学院批评”手中掌握了很多理论,但这些理论多是外来的,多是经过训练和学习而掌握的,并不是从文学批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原创的。因此,对于“学院批评”来说,我们一方面应该发扬理论的长处,但同时也应该克服学院派过分依赖于理论的缺陷,吸收作家批评的长处。
三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学院批评”很大的问题就是对创作的不熟悉,批评过分依赖于理论从而所谈论的问题只是理论上的,而与创作实际不相符合。而“作家批评”则相反。作家们对创作有很好的理解,有创作经验或体验,他们能很好描述创作过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创作的艰难与辛苦,并且一眼就能看出“出彩”的地方,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过程却不能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他们知道创作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但却说不出为什么好或为什么不好;他们对文学史不熟悉从而导致批评缺乏历史感,表现为,他们对自己的创作以及别人的创作缺乏历史的比较和定位,有些作品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他们却以为很有创造性,反过来,有些作品具有真正的创造性,但他们对其创造性却木然不知;他们对自己很熟悉,对别人却很陌生,他们的批评代表了自己的一种经验,但对于其他创作却并不适应,即他们的批评在理论上缺乏概括性;他们的批评主观性太强,往往以个人的爱好为批评的标准。
多年前,王蒙先生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王蒙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谈论的,他说:“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乃至传之久远的成功之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人,但这很难持之长久。有一些作家,写了一部或数篇令人耳目一新,名扬中外的作品之后,马上就显出了‘后劲’不继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学问素养。光凭经验只能写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经验的东西。只有有了学问,用学问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经验,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体……从而不断开拓扩展,不断与时代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6](P92)其实,作家没有“学问”,其弊端远非这些,它深刻地影响作家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制约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具有深刻思想的人,这正是他们成为大师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缺乏深厚的学术修养,缺乏深刻的思想,这正是当代中国缺乏大师级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作家没有“学问”,更会深刻地影响他的文学批评,主要表现为批评没有理论性,他们对作品的批评往往是现象罗列,读后感,创作谈,停留在写作的层面上,不是纯正的作品细读,缺乏理性的分析,缺乏理论的发现,缺乏思想的挖掘,缺乏艺术的总结和审美性的归纳,在结论和具体论证上缺乏逻辑的严密性、全面性,总体上表现出“浅”的特点、并且不能对批评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
王朔在当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不可磨灭,他以“异类”的方式进入文坛,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阵骚动和震荡。他的创作别具一格,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他的反崇高、消解严肃、幽默、调侃等都对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风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王朔也涉猎文学批评,并且一时也很引人注目,但我们不得不说,王朔在文学批评上总体上非常糟糕,是一个“没知识”、“没文化”的人。
当然首先要说的是,王朔的文学批评也有他的一些优点,并且这优点还很特别,不是一般人能学到的。这优点大略说来就是:很机智,既表现为发现的机智,又表现为表述的机智。很聪明,这种聪明既表现在写作方式上,比如他很善于选择批评的对象,对于具体的批评对象,他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去批评,既要批评又能把握分寸。更表现在悟性上,对于文学的悟性王朔可以说是少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创作上,天生的会讲故事,天生的语言感觉,也表现在文学批评上,他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理论,但却无师自通,看问题有时能一针见血,很能说到要害处。“谎话说多了便成了真理”,文学理论中有很多结论其实都是话语建构,即谎话性的“真理”,王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不相信一些人云亦云的文学信条,而是从个人体验出发,因而有很多发现,也反映了他的独立思考。与上面几个特点相应,王朔的批评很轻松,很幽默,可读性很强。
但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没有学问的底蕴,没有理论的基础,每当涉及到复杂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文学史问题,王朔的思考便捉襟见肘,常常是错误的,且错得太基本。他常常按日常情理来讲高深的学术问题,因此犯错误当然就在所难免,因为学术根本就不是一种情理性的东西。比如他在金庸前加上“专写古代犯罪小说”的定语[7](P8),虽然调侃不失为风趣,但却马上暴露了他对于武侠小说的无知,也反映了他文学爱好的偏狭。王朔的小说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支撑其小说艺术背后的是王朔的审美理念。以自己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追求为标准来否定其他审美理念和艺术追求,非常无理,正如用传统的“高大全”标准来否定王朔一样无理,这反映了王朔不谙文学之基本。王朔批评金庸:“就《天龙八部》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就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料,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8](P137)金庸小说的语言的确够不上优美,可以批评,但却不是这样批评的。说这话一下子就显示了王朔的“没文化”,反映了他对于现代文学“老祖宗”们的不熟悉,所以金庸反唇相讥:“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9](P11)可以说逮了个正着。
如果说王朔对金庸的批评其主要问题还只是文学偏见和文学知识问题的话,那么,王朔对鲁迅批评的错误则完全是由于他缺乏必要的文学理论的训练,一句话,他不懂鲁迅。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并不好,“苍白”、“食洋不化”、“概念化”、“游戏”,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10](P124)。一句话,在王朔看来,鲁迅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真本事”。此外,王朔还对鲁迅思想的深度和鲁迅的人格提出了质疑。鲁迅当然可以批评,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批评,但不能这样批评。从王朔的文章来看,王朔对鲁迅的了解和认识其来源非常可疑,小学课本(应该还有中学课本,因为王朔是读过中学的),儿时的印象,朋友的聊天(并且很多是商业上的朋友,“吃吃喝喝”的朋友),根据鲁迅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他是否系统地、认真地读过鲁迅的作品,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并没有认真地读金庸的作品,就对金庸妄加评论,对于鲁迅,他未尝不可以如法炮制。
而更重要的是,以王朔的学养,即使他认真地读了鲁迅,也未必就能读懂鲁迅。对于鲁迅思想的深刻,他未必能理解。王朔说他读小学的女儿“不学无术”,对于鲁迅,他何尝不也是“不学无术”。并不是鲁迅没有像样的作品,而是对于鲁迅的“像样”,他不能理解。对于《故事新编》,他只看到了“游戏”,而看不到“游戏”之外的东西,对于这种“游戏”的艺术性和创造性,他并不能理解。
对于王朔关于鲁迅的很多结论,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认真辩驳的,不能太去计较。但我这样说,并没有轻视和否定王朔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是非常喜欢王朔小说的,对于他的批评,我也给予一定的肯定,但是,仅凭生活积累以及感觉和悟性可以写好小说,可以成为有名的作家,但仅凭生活积累、创作经验以及感受和悟性绝不能写好评论,绝不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批评家,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批评家需要很多条件,包括对文学作品的良好感觉,欣赏水平,特别是理论的能力。而理论的能力则非一日之功,也绝非聪明能解决,它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积累,需要系统的学习。“作家批评”一个普遍的欠缺就是理论学养不足,因而其批评缺乏深度。这不是王朔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的问题。
我个人很喜欢《白鹿原》,看小说,我想象作家在写作时一定对很多问题思考得非常深刻,我想象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也一定非常独到,对作品一定经过了一番经心的构思。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白鹿原》气魄宏大,它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表现出相当的人性深度。它反映了深层的中国传统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内在张力。它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剖析深刻而细致,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它还反映20世纪中国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与斗争,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理想主义色彩。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读完作者的《陈忠实创作申诉》,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觉得陈忠实不论是对于文学的理解,还是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都比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要浅得多。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些创作谈和评论就是他写的。当他说他为了写这部小说而去看《中国近代史》时[11](P15),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他的小说是成功的,但批评却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并不具备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因而面对批评对象时他讲不出什么道理。据说贾平凹拙于言辞,但我想,在描述、叙述、讲故事方面,贾平凹不会“拙”,在小说方面“拙”对于贾平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恐怕真正“拙”的是理论的表达。在理论上的“拙”正是当今“作家批评”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明显地可以划分为“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两种类型,并且两种批评在品格上泾渭分明,这与当代文学的格局以及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历程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现代文学阶段并不是这样,那时的作家多是学者,搞文学研究的学者也作家化,但到了当代却严重分化。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走的似乎是两条不同的路,从事的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工作,文学研究走的是大学之路、学术之路,被纳入大学和研究所机制,学者对文学的知识和理解主要是通过文学理论教育和文学史的教育获得的。文学创作走的是实践之路,被纳入了行政机构,归作家协会管理,作家对文学理解和知识主要是通过文学创作实践的摸索以及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体验和感悟而获得的。而文学批评则分属于这两种体制,“学院批评”属于大学体制,“作家批评”属于作家协会体制。学者多是通过大学教育的方式训练出来的,他们对文学理论的感觉远好于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感觉。而作家则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是在文学创作实际中成就出来的,他们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文学理论训练,或者说这种训练与他们的创作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正是因为如此,“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在批评上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格。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分裂状况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要提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水平,需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包括,一方面要改变文学教育状况,其中,应该重视学者的文学感受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改变作家的状况,特别是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王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