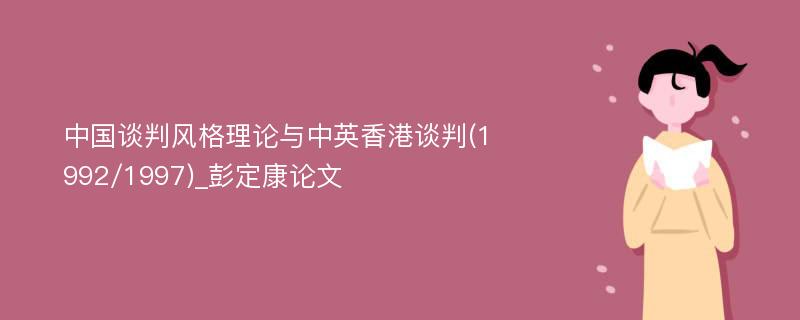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92—199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中国论文,中英论文,风格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不顾中方反对,在香港立法局抛出激进的民主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和中国密切磋商的政策,决定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推行改革。彭定康在中英谈判中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中英关系急转直下。彭定康访华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指责其为“千古罪人”,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中英双方在长达8个月的17轮外交会谈中未能就任何议题达成协议。谈判破裂后,彭定康又将其改革方案直接提交立法局,破坏了两国此前达成的直通车协议。
随着大量历史资料的解密,我们重新审视中英关系中这段不愉快的插曲,就会发现中英冲突的缘起正是英国对中国谈判策略的调整。彭定康在制订对中方的谈判策略时,借鉴了国际谈判研究中的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他的谈判策略就是要以违反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突破中方设定的谈判框架,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民主改革。彭定康以香港的未来作赌注,不计后果地将理论家关于如何与中方谈判的建议付诸实施。这种做法破坏了双方会谈的气氛,毁掉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保障香港政治稳定的直通车协议,使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蒙受了重大挫折。而彭定康的谈判策略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一、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英国谈判策略的调整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在国际谈判研究中颇具影响力。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和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他们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和对美国政治家及商人的采访,对中国在谈判中的表现做出了理论化的归纳。白鲁恂和所罗门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定中国具有独特的谈判风格。这一谈判风格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所罗门指出:“中国的谈判策略非常容易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是可以预测的。”①
两位学者都把中方参与谈判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以探寻其中的规律。白鲁恂把谈判分为启动阶段和实质谈判阶段。② 所罗门则把谈判细分为四个阶段。在启动阶段,中方会和对方发展私人关系,建立有利的议程,让对方接受中方的原则;在评估阶段,中方会向对方施加压力,考验其耐心;在结束阶段,中方可能与对方达成协议,也可能持保留意见,或者放弃谈判;在实施阶段,中方还会提出额外要求逼对方让步。③
白鲁恂和所罗门都希望找到和中方谈判取胜的捷径。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接近,所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同。他们都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中方常用的三种谈判策略,提醒西方人加倍小心。首先,中方总是要求对方先接受其原则,在中方设定的框架下谈判。中方大而化之的原则,其实就包含了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对方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就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其次,中国人重视和谈判对手的私人关系,喜欢给对方戴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高帽。对方如果接受这一称号,就可能背上人情债,付出向中方让步的代价。再次,西方人往往会在谈判中明确告诉对方自己的谈判底线,而中方在谈判中不会轻易告诉对方自己的底线。只要对方还能做出让步,中方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针对以上三种策略,两位学者向西方政治家提出了三点忠告:不要接受中方确定的谈判原则,不要接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恭维,不要轻易向中方让步。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在和中方谈判时要有耐心,要熟悉过去的谈判纪录与细节。有所不同的是,白鲁恂建议西方国家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避免陷入和中方的论战;所罗门则指出要学会宏观把握谈判议题,强调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减少媒体的压力。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虽然在国际谈判研究中享有盛誉,却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丰富多彩的中国的谈判实践。谈判问题专家阿尔弗雷德·威廉(Alfred Wilhelm)指出:“中国的谈判风格正如中国数百年来的历史和传统那样复杂多变。它既没有完全颠覆西方的谈判经验和概念,又确实因其独特性而显得与众不同。”④ 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建议看似言之成理,却很难付诸实施。尤其是他们的三点忠告,并不是和中方谈判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彭定康的做法就证实了这一点。
在彭定康就任前,英国外交部一直全权负责中英谈判。港督麦理浩、尤德和卫奕信都是外交部的“中国通”。经过两国外交官的不懈努力,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直通车协议。如果英国在香港的民主改革与基本法衔接,香港1995年选出的立法局成员就可以直接过渡到1997年。1990年两国外长交换了7封外交信件,双方同意香港立法局的直选议席在1991年为18席,1997年为20席,1999年为24席,2003年为30席,并将这一协议写入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二。1991年9月3日,英国首相梅杰访问北京,和中方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协议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又被称作“第二份中英联合声明”,它规定两国外长应半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同时建立了港督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之间的正式磋商机制。
在中英关系发展顺利的情况下,英国突然要调整对华政策,和“六·四”政治风波后英国政府面临的压力有关。“六·四”事件后,英国外交官遭到来自国内、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激烈谴责,批评他们在和中方的秘密谈判中让步过多,甚至背叛了香港。早在1990年,首相撒切尔夫人即决定委任一位政客做香港最后一任总督。1991年12月31日,英国外交部宣布港督卫奕信将不再继续留任香港总督,却没有公布继任人选。1992年5月,梅杰首相和彭定康在英国首相官邸会见香港激进民主派代表李柱铭和杨森。⑤ 5月底,新上任的负责香港事务的英国外务次官古德拉德访问香港。他建议中方修改香港基本法以适应新的形势。⑥ 这一声明就是向中国发出的政策调整的信号。英方谈判策略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英国决定任命一位在香港和国际社会都能左右逢源的政客,并为之选择了一种高风险的谈判策略。外交大臣赫德解释说:“新的港督要能灵活地应对英国的政局和媒体,和香港展开密切的政治合作。他需要去寻找盟友和支持者,以往的港督没有必要做这些工作。”⑦ 彭定康的改革就是要钻过去中英协议的空子,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民主改革,从香港“光荣撤退”。他上任不久即公开表示:“我将利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间一切可能的空间,让民主植根于香港并得以发展……我相信我可以扩展立法局的民主架构,在短期内又不让中方认为违反了什么根本问题。”⑧ 他在任内频繁出访,要求各西方国家支持他在香港的民主改革。
其次,英国改变了由中方主导谈判议程、以秘密磋商为主的谈判方式。彭定康否认英方在过去谈判中取得的成果,并胸有成竹地放言:“英国人也在不断总结经验,不希望打乱仗,首尾无法兼顾。我已经觉察到中方的强势在于统一指挥,步骤周详,上下一致。”⑨ 彭定康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他将采用外向风格。他说:“我要在办公室之外,花费最多的时间。我在公开场合跟私下里说的都是一样的,人们将会习惯我的作风。过去这个作风曾给我添麻烦,但我没有秘密议程。我希望人们知道,我讲的就是我要做的。”⑩
再次,英国为彭定康确定的谈判姿态更加强硬,树立新港督为了香港的民主改革不惜和中国对立的形象。柯利达指出:“英国议会和媒体都要求英国加速在香港推行直选,还出现了应不顾中方的观点推行改革的主张。”(11) 彭定康在采访中毫不讳言其对中方的强硬态度:“从西方开始和中国打交道以来,有些人就有迁就中国的倾向。这样不仅谈判的结果会很不理想,而且此后中国会变得更难以对付。”(12) 他一意孤行地推行改革,置了解中英协议的英国外交官和香港官员的批评于不顾,甚至宣称:“有些人认为在和中国会谈时不能坚持原则,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很清楚我面临的选择并不是和中方争吵或息事宁人。如果我们不和中方争论,势必遭到来自香港、国际社会和英国在野党的批评。”(13)
彭定康辩解说,英国的政策调整是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根本的转变。英国不准备中断和中方的谈判,仍希望和中方就香港政治体制的直通车安排达成协议。他声称:“双方谈判的风格或许有所转变,谈判的方式可能有些变化,然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14) 而事实上,作为英国政策调整的执行者,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在香港激起轩然大波,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彭定康的谈判策略与中英关系的恶化
彭定康在《东方与西方》一书中回顾说,在他就任前,一位英国外交官建议他不要接受这一职务,因为两国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主要安排都已经谈妥。他会发现自己的工作非常无聊,只要在位子上坐满几年就可以打道回府了。(15) 彭定康不甘心平淡地度过自己的港督生涯。1992年10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踌躇满志地表示:“作为一个老派的保守党人,我相信‘政治就是一场光荣的冒险’。”(16) 彭定康最初的设想就是用打破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和中方谈判,在谈判中运用各种手段向中方施压,孤注一掷,逼中方做出最大让步。
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彭定康认为在和中方谈判时不必遵循一定之规,毫无保留地照搬了中国谈判风格理论的策略。他反复强调说,西方人往往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而着迷,“所谓的中国独特性让我们难以理解中国,也搅乱了政策制订过程……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待中国,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和中国打交道要遵循什么规则”。(17) 因此,他拒绝中方的善意,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原则,运用各种手段向中方施压,不分场合将这种策略付诸实践。
彭定康上任后,几次拒绝了中国对他的访华邀请。按照惯例,港督就任后都会访问北京,就香港政制改革问题和中方协商。彭定康认为,一旦访华受到中国的压力就不便另搞一套,所以选择不和中方接触。他迟迟不向中方透露其改革方案的内容。直到他发表施政报告两周前,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才在纽约的联合国会议上,把他讲稿的概要交给钱其琛外长。中方要求彭定康不要公布他的激进改革方案,英方对此却置若罔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回忆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向他抱怨说,英方故意不给中方回应的时间,很明显他们根本不想考虑中方的意见。(18)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发表施政报告,打出追求“自由和公开的选举”的旗号,宣称民主是他个人信仰的关键要素,力图急剧改变香港的政治体制。(19) 他在演说中强调,为了发展香港的代议制政府,必须将香港的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离。彭定康的改革方案虽然表面上符合香港基本法关于1995年立法局直选议席数目的规定,其内容却从根本上违反了香港基本法对香港政治体制的设计。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指出,彭定康的改革方案推翻了中英过去达成的“循序渐进”的谅解。他将原来协议中功能团体法团投票的间接选举方案改为由不同行业中的所有从业人员投票的选举方案,把功能团体不足10万的选民人数一下子扩充到270万,并把选举委员会由五部分组成的方案改为由直选产生的区议员组成的方案。他还主张取消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的全部委任议席,在区一级议会也搞全面直选。(20)
彭定康的激进改革方案在英国也遭到很多批评。周南回忆说,彭定康抛出改革方案后,英国上议院一位年近90岁的资深议员萧克罗斯公爵专程来香港见他,表示很不同意彭定康的做法。萧克罗斯公爵公开表示:“英国用了400年时间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至今还保留了并非普选产生的上议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超速度的,如果还要再加快,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一点好处。”(21)
彭定康在公布他的改革方案后访问北京。在他离开英国前,英国外交部的官员都没有向他提及两国过去达成的共识。因此,彭定康在制订改革方案时,根本不知道两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协议。这无疑是英国外交部的重大失误。在彭定康访华前几天,他的顾问卢埃林才发现一份文件提到几封他们毫不知情的电报。卢埃林立即和外交部取得联系,彭定康这才了解七封信件的内容。(22)
中方对彭定康的单边行动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彭定康访华前,邓小平做出重要指示:“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绝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23) 邓小平在看了《关于香港总督〈施政报告〉和我们拟采取的对策的会议纪要》后表示很不满意。他说:“态度可以斯文,但语言一定要明确。我以前对撒切尔夫人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24)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会见彭定康时指出:“在你就任前,我曾与三任香港总督和四任驻华大使一起共事。港督麦理浩、尤德和卫奕信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鲁平表达善意说,他希望彭定康也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彭定康就像中国谈判风格理论所建议的那样,拒绝了中方的善意。他表示,历史对他的评价不取决于他和中国的友谊,而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成功地贯彻《中英联合声明》,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香港的生活方式”。(25) 有记者在彭定康会见钱其琛外长后,问他对钱外长没有和他握手的感想。彭定康表示,他根本就没有注意钱外长是否和他握过手。(26) 这样的言论强化了他给中方留下的有意对抗的印象。
1992年10月23日,鲁平召开记者招待会。此前中方仅强调彭定康的改革方案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鲁平指出彭定康的改革还违反了中英两年前达成的关于衔接问题的协议。中方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公开两国政府就这一问题交换的外交信函。如果英方置基本法于不顾,根本不考虑衔接的问题,准备另起炉灶,我们也要另起炉灶。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之间分歧的实质不是民主化的快慢问题,而是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如果对方强调对抗,我们也只有奉陪。”(27)
鲁平的声明有效地应对了彭定康一再强调的“公开谈判”的主张。10月底,中英双方决定公布1990年两国外长的七封外交信件。英国故意违反双方的约定,提前一天公布了有删节的七封信件,试图给国际社会造成他们没有违反协议的假象。(28) 这样的外交手腕表明英方在谈判中缺乏诚意。前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访问英国时指出,《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已经被英方破坏。他说:“人们不禁要问《中英联合声明》还要不要信守?中英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否就一风吹了?”他还明确表示,中国要“合作,而不是对抗。不要指望对抗会让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29)
三、中英关于1994/95年选举的17轮谈判
1992年11月3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表声明,港英政府签订或批准的合约、契约和协议,除了土地契约外,凡未经中方认可者,1997年6月30日以后一律无效。距离1997年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两国关于香港前途有许多重要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因为香港民主改革问题而触礁搁浅。英国政府意识到,彭定康的对抗做法弊大于利,转而开始重新探寻和中国谈判的基础。1993年2月至3月,中英在北京展开密切的外交接触。这段时间的谈判是中英关系的转折点:“两国政府又重新回到谈判的轨道上,像过去那样由中国官员和英国的‘中国通’谈判解决问题。”(30)
中方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双方谈判的前提就是英方撤回彭定康的改革方案。3月12日,彭定康在香港《宪报》刊登他在立法局发表的政改方案,希望用这种先发制人的做法,来突破中方提出的会谈前提的束缚。第二天,邓小平做出重要指示。他说:“英国的企图无非是两手,一手把香港搞成由英国操纵的政治实体,所谓主权换治权,由其代理人来搞;再一手是把一个烂摊子留下来卡我们。两手都办不到!”(31) 3月31日,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做出另起炉灶的具体安排。这次会议决定授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准备工作机构。
中方另起炉灶的策略推进了谈判的进程。英方同意双方会谈的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和两国过去的协议。两国于1993年4月开始了关于1994年和1995年选举改革的正式会谈。在第一轮到第三轮会谈中,中方提出,既然双方已经同意以三项原则作为会谈的基础,中方要求英方首先对双方过去达成的协议、谅解和共识加以确认,这样才能使会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方提出了一份希望双方进行确认的八点内容的措词稿。(32) 英方担心如果认同中方的原则,就不可能推进激进的民主改革方案,对过去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一直不肯确认。彭定康还单方面设立谈判的最后期限,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他宣称他预计谈判应该在5月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否则他将把改革方案直接提交立法局。(33)
在第四轮会谈中,中方开始和英方就实质性议题展开会谈。中方提出了若干主要问题的方案,建议双方先就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的选举安排进行磋商,然后再讨论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遭到英方拒绝。在此期间,英方提出了有别于彭定康改革方案的某些新建议,但仍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坚持彭定康方案的实质,致使双方谈判进展缓慢。
彭定康在谈判期间频繁出访西方国家,试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他于5月访问美国,会见了克林顿总统。彭定康此行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对香港民主改革的支持。克林顿对彭定康在香港的民主改革表示认可。彭定康认为自己的美国之行非常成功,声称:“我希望中方知道,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把香港作为中国能否融入国际社会的试金石。”(34) 他借美国的力量向中方施压的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双方互信的基础。中方对他的做法予以坚决驳斥。
在中英会谈期间,彭定康不断以诡辩的办法推卸责任,坚持自己的改革方案没有违反双方的协议。当中方明确指出他的改革方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时候,彭定康居然反问中方他怎么违反了协议,要求中方明确指出他违反了哪一条具体的规定。当中方回应说他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精神时,他居然要求中方对“精神”一词做出定义,并要中方拿出替代性的改革方案。(35) 这种回避实质问题的态度导致双方谈判始终不能取得进展。
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正式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工作。9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将出版。邓小平要求中央办公厅提前发表他在1982年9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的讲话,“支持一下前线的同志”。(36) 9月2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如果在15年的过渡期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方可能在另外的时间以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对英方做出了有力的军事威慑。
1993年10月,钱其琛外长在纽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赫德,首次提议以“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谈判,先解决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的选举安排,再解决立法局的选举事宜。11月,当中方在区域组织、选民年龄、投票方法和委任议席问题上接受英方的要求,以为可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时,英方却在第16、17轮谈判中,坚持把1995年立法局选举实行单议席制的内容加入协议。单议席制的安排将确保香港民主派垄断香港基层机构的选票,不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中方拒绝接受这一要求。随后,彭定康单方面中止谈判,将部分政改方案直接提交立法局,致使中英谈判破裂。
1994年1月30日,香港《南华早报》一篇题为《伦敦对港督的“赞扬”开始减少》的文章指出,英国三位前首相有两位反对彭定康的政策。英国前工党首相卡拉汉对记者说:“如果你从不那么强有力的地位出发进行谈判,你的对手知道你的实力不过如此,最好不要过分宣扬你的实力。”另一位前首相希思在保守党的一次集会上说,英国目前同中国的敌对状态只能怪自己。文章指出英国上院前不久辩论香港问题时,只有一个人表示支持彭定康。下院议员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彭定康,可是私下许多人对彭定康政策造成的后果表示不满。(37)
1994年6月30日,香港立法局通过了彭定康的改革方案。8月3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另起炉灶组建临时立法局作为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构。中英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直通车安排由于英国的错误政策而流产。此后英方高级官员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愿意与中方加强合作,彭定康在中英谈判中成为边缘人物。两国在1994年先后就军事基地的移交和香港新机场的建设达成协议。英国于1995年委任强调对华经济关系的里夫金德为外交大臣,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调整到经济领域上来。两国在香港回归前展开密切合作,将彭定康的改革给香港带来的损害减到最低程度,确保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四、结论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对国际谈判研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彭定康的谈判策略违背了一些最基本的谈判规律,包括在谈判中必须遵守双方此前达成的默契,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给对方留有余地。英国工党代表罗宾·库克在议会下院辩论中指出:“彭定康在提出改革方案之前,不去访问北京。当中方拒绝接受他的改革方案时,他不顾中方反对,继续推行这一计划。我曾和香港人探讨过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豪赌。”(38) 在英国外交委员会反思中英谈判的时候,驻华大使唐纳德深刻地指出:“我同意柯利达爵士的观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建设性的合作比对抗——特别是公开对抗——要好得多。我也同意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的观点,那就是非正式的外交沟通是最好的解决方式。”(39) 彭定康的做法破坏了中英协议的基础,最终将两国多年来共同努力达成的直通车协议毁于一旦。
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鲁平大度地评论说彭定康是谈判高手,有魄力也很能干。(40) 彭定康在钻双方协议的空子,以及利用各种手段向中方施压上,确实做到了无所不用其极。他把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不接受中方的原则、不接受中国人的老朋友的善意以及不轻易向中方让步的对策建议都用到了极致。彭定康任港督时期的外交谈判,充分说明中国谈判风格理论在实践中的苍白无力。白鲁恂和所罗门过分注重中国在谈判中的特殊性。他们试图用一种刻板的公式,来归纳中国在外交中运用自如的谈判智慧。西方人在和中方谈判时,也许能从这一理论中获得某种启发,然而僵化地套用这一理论,势必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连玉如老师、潘维老师、许振洲老师、印红标老师、梁云祥老师和于铁军老师以及《外交评论》的匿名审稿专家对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建议,谨致诚挚谢意。
注释:
① Richard H.Solomon and Charles W.Freeman,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9,p.10.
② Lucian W.Pye,Chinese Negotiating Style:Commercial Approaches and Cultural Principles,Westport:Quorum Rooks,1992,pp.43-92.
③ Richard H.Solomon and Charles W.Freeman,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p.5.
④ Alfred D.Wilhelm,Jr.,Chines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4,p.203.
⑤ Frank Ching,“Toward Colonial Sunset:The Wilson Regime,1987-1992”,in Ming Chan,ed.,Precarious Balance: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New York:M.E.Sharpe,1994,p.192.
⑥ Joseph Y.S.Cheng,“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on Hong Kong during Chris Patten's Governorship”,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8,No.2,November 1994,p.231.
⑦ Jonathan Dimbleby,The Last Governor,London:Warner Books,1997,pp.11-12.
⑧ Richard Baum,“Britain's‘Betrayal’of Hong Kong:A Second Look”,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No.20,March 1999,pp.27-28.
⑨ 窦应泰:《今昔彭定康》,《同舟共进月刊》,2007年第7期,第47页。
⑩ 《新任港督彭定康谈起政治策略》,[香港]《华侨日报》,1992年7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2年7月7日,第2版。
(11) Percy Cradock,Experiences of China,London:John Murray Ltd,1994,p.228.
(12) Christopher Patten,“Ideas,Political Leadership,and the Lessons of Hong Kong:Conversation with Christopher Patten”,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C Berkeley,April 8,1999,p.5.
(13) Christopher Patten,“The Last Governor”,in Sally Blyth and.Ian Wotherspoon,eds.,Hong Kong Remember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82.
(14)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Douglas Hurd”,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Relations between the UK & China up to & beyond 1997,Minutes of Evidence,February 8,1994,p.214.
(15) Christopher Patten,East and West :China,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New York :Times Books,1998,p.6.
(16) “A Different Style :Interview with Chris Patte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October 22,1992,p.22.
(17) Christopher Patten,East and West:China,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pp.255-256.
(18) David M.Lampton,Same Bed,Different Dream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215.
(19) “Our Next Five Years:The Agenda for Hong Kong”,Address by the Governor The Right Honorable Christopher Patten:at the Opening of the 1992/93 S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7 October 1992,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1992.
(20) 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55页。
(21) 同上,第356页。
(22) Jonathan Dimbleby,The Last Governor,p.170.
(23) 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第357页。
(24)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690页。
(25) John Flowerdew,The Final Years of British Hong Kong: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 Withdrawal,Houndmill,Basingstoke,Hampshire:Macmillan Press,1998,pp.116-117.
(26) Christopher Patten,East and West:China,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p.56.
(27) [香港]《文汇报》,1992年10月24日。转引自齐鹏飞:《邓小平与香港“后过渡时期”的外交斗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9页。
(28) 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29) Tai Ming Cheung,“Hong Kong Embattled Governor”,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ember 26,1992,p.10.
(30) Percy Cradock,Experiences of China,p.254.
(31) 窦应泰:《今昔彭定康》,第47页。
(32) 《中英关于香港1994/95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人民日报》,1994年3月1日,第3版。
(33) Ma Ngok,“The SinoBritish Dispute over Hong Kong:A Game Theory Interpretation”,Asian Survey,Vol.37,No.8,August 1997,p.748.
(34) Jonathan Dimbleby,The Last Governor,p.231.
(35) Christopher Patten,East and West :China,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p.56.
(36) 《张浚生半生心路系香江》,《文汇报》,2004年10月18日。
(37)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
(38) Hansard(House of Commons Daily Debates) ,Column 534,November 14,1996.
(39) “Examination of Witnesses:Sir Alan Donald and Sir Richard Evans”,in 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Relations between the UK & China up to & beyond 1997,Minutes of Evidence,December 8,1993,p.119.
(40) 鲁平:《香港回归的回顾》,《纵横》,2007年第9期,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