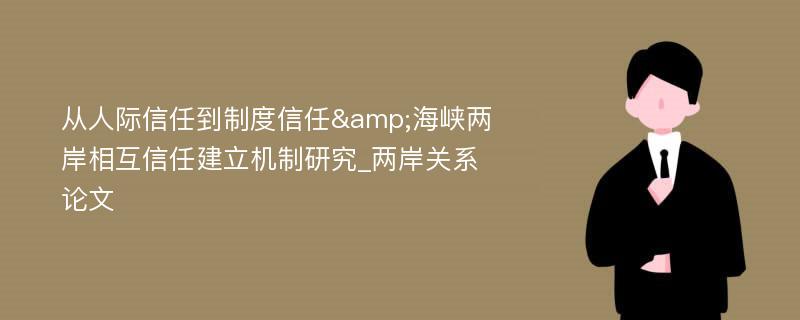
从人际信任到制度性信任:两岸互信建立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论文,人际论文,机制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1-0049-07
两岸互信可以降低两岸双方因信息不充分、发展不确定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增加对对方能够履行责任的信心,从而减少误判,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两岸关系健康发展。所以如何建立、扩大和累积互信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但是既有的研究都是按照经济互信、社会互信、政治互信、军事互信的分类模式来分别阐述。这种研究模式的优点是范畴清晰、目标明确,相对来说也较为通俗易懂,而其不足之处是无法从信任的社会发生机制和中国人信任的特点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尝试弥补这样一个不足,从信任产生的规律和两岸互信的转点出发来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信任”及其建立机制
“信任”是一个非常日常化的用语。通俗地说,信任就是“放心”,就是不担心对方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辜负自己的期望。但“信任”这样一个看似非常明了的用语实际上包含了相当复杂的社会与心理过程,牵涉到很多层面和维度。在社会学领域中最早研究“信任”并为它下定义的是多伊奇(Deutsch)。他的定义是:“所谓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心)是指:他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且根据这一预期作出相应行动,虽然他明白倘若此一事并未如预期般地出现,此一行动所可能带给他的坏处比如果此一事如期出现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要大。”①
这一句子相当难懂,后来霍斯莫尔(Hosmer)曾将之改写成“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得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②这一经典定义道出了对信任的三个基本看法。第一,信任是个体的一种预期,而此一预期会通过某一选择行动反映出来;第二,其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信任是在对未来事件的不可预料中才会有的;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即信任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是当个体在作纯理性的选择时不会做出的行为。
既然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那么信任如何产生?在西方研究信任的学者中,祖克尔(Zucker)相当系统地阐明了信任的主要产生机制。她区分了三种机制:一是由声誉产生信任——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声誉好的人能得到信任。二是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基于如下的信念:相似的社会背景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容易相互理解、在交往或经济交换中容易达成共识。三是由法制产生信任——即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信任。祖克尔分析了1840-1920年期间(此为美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美国经济活动中的信任问题。她发现,在这一时期,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人口流动的加剧及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等因素导致以声誉产生信任的机制相当混乱,有效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理性化科层组织的发展、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使得由法制产生信任的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③
但是信任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信任的建立机制常常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如怀特利(Whitley)便指出,华人家族企业主往往努力发展与主要下属和生意伙伴的私人关系,以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④值得注意的是,怀特利所说的通过关系来产生信任的机制与祖克尔的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的机制并不相同。祖克尔所说的相似性是在人际交往之前便已存在,其重点是个人的特质。而怀特利所强调的则是私人关系的建立,是由人际交往而形成相互的关系连带,从而产生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基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它来自于人际的属性,而非个人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怀特利等人事实上提出了另一种建立人际信任的机制:关系运作,即建立、发展、维持和利用关系的活动。另外,两岸之间在历史上曾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人为隔离和对立,因声誉而产生信任的情况也不明显。
这样,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探讨两岸互信建立机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一种是人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考虑到“关系”在中国人社会中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关系运作可能是两岸建立信任的重要机制。另一种是制度研究视角。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交流交往的机制建设可能会对两岸互信的积累和扩大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信任机制,一种是人际信任,另一种是制度性信任。
人际信任和制度性信任既是两种不同的互信建立机制,也是两种不同的互信类型,它们在性质、形成过程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不同。人际信任是以人与人直接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为基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直接的相互信任。人际信任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往的交往经验,经验完成了对交往对象的信息搜索,从而不假思索地认为:我熟悉的人不会骗我。对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人格自律、熟悉度、习俗。与此不同,制度性信任是当事人双方以制度规范为中介的信任。在以制度性信任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中,信任不是来自于人们彼此相熟,而是来自于对各种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信心。制度互信的保障机制是制度规范的权威性。人们之所以信任一项制度并按照它所确立的行为规范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该项制度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并且相信制度会对违反者予以惩罚。
二、过去30年两岸建立互信的主要机制是人际信任
从1949到1979,两岸隔绝、对立了30年。1979年,大陆宣示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倡议推动“三通”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开始了交流交往、增进了解和累积互信的过程。在这近30年的交流中,两岸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军事层面,信任的主要形式是人际信任,其中既有传统的“人情”色彩,又有理性计算的成分。这样,两岸人际互信的建立就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从人情入手,强化情感关联;二是从理性入手,增加可靠性。
1.由“亲”而“信”——两岸人际信任的情感层面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是人情关系本位的社会,人情是中国人建立信任的主要机制。⑤基于人情的信任常常是一种由“亲”而“信”的形式。所谓“亲”,是指一种牢固的人情关系,它可以是血缘之亲,也可以是非血缘之亲。通过亲情、友情关系,双方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建立相互间的信任。
两岸开放交流以后,台商便开始投资大陆。台资企业这个特殊的空间一方面连接着大陆员工和台商,另一方面也连接着台商与大陆社会的关系,它多少呈现出两岸社会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空间隔离后,重新接触后建立和积累互信的过程。⑥
在经过台湾当局数十年的“反共仇共”宣传教育之后,很多台商仍愿意并敢于到大陆投资,信任是一个基本的条件。这个信任的内涵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其中最主要的基础就是亲情。事实上,台商最初投资大陆很多是在“回乡探亲”的名义下并在其大陆亲友的帮助下进行的。同样,很多大陆人都因为“同根同生”、“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亲缘与血缘关系”而给予台商最初的信任。⑦可见,“血缘之亲”是两岸互信的原始内涵和最初来源。
虽然“同文同种”,但是在台资企业中,来自台湾的老板和“台干”在工作岗位、薪酬体制、用餐、住宿乃至工作后的休息等各个方面,都与“陆干”和大陆员工有着截然清楚的区分。⑧台商与大陆员工以及与大陆社会要进一步扩大和累积互信,常常需要加强彼此的亲情和友情,建立心理情感上的亲密认同。例如一些台商会在有大陆员工在场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在国家的重要日子,如香港回归等,台湾老板和台干也一起收听广播、收看电视。有的台商还会把大陆员工视同自己人,用爱心对待员工,甚至当员工个人发生急难时,也愿意主动协助。很多台商在大陆社会出现急难时,如发生地震,他们也愿意慷慨解囊。通过这些方式,台湾人和大陆人常常很快就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
对于到台湾从事交流活动的大陆人,台湾人的信任建立模式也常常表现为由“亲”而“信”。大陆人最初到台湾去都是以奔丧、探亲的形式进行的。直到今天,当大陆代表团到台湾去,如果将访问定位在走亲、访友,常常能够迅速唤起对方心理情感上的亲密认同,并很快建立起信任。
2.可靠性——两岸人际信任的理性层面
汉语中的“信”字,从人、从言,本义是指“言语真实,诚实不欺”。在古典文献和一些辞书中常以“诚”、“实”、“专一不移”、“不欺”来解释“信”的含义。可见,“可靠性”是中国人“信任”的基本内涵,也是信任建立的基本机制之一。
台湾人常把大陆人的“可靠性”作为能否予以信任的重要依据。我们以台资企业为例。很多台资企业的文化,实际上与日本企业文化相似,强调的是员工终身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作年资较久、经验较老到,或者是特定技术和能力较强的大陆员工常能够受到台商倚重。相反,对于无法长久工作的大陆员工,台商和台干会认为此人不可靠而不予以信任。很多台商和台干抱怨大陆员工经常跳槽。笔者在调查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培养他一两年,可以做事了,只要有另外一个企业给他稍微高一点的工资,他就跳走了。不少台商认为这是大陆干部缺乏诚信、唯利是图的表现,也是不能信任和重用的最重要的原因。
同样,大陆也常常把是否“可靠”作为对台湾人是否可信的一个重要内容。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并迅速赢得了大陆领导人以及普通民众的广泛信任,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战长期坚持反“台独”的立场。在大陆人眼中,连战可靠,因而值得信任。相反,陈水扁在政治立场上一变再变,从“新中间路线”、“四不一没有”,到“一边一国”,再到“公投制宪”,大陆认为陈水扁不可靠,因而不值得信任,只能“听其言,观其行”。
可见,在过去30年中,两岸互信既有基于“人情”的亲密情感,又有基于可靠性的理性计算。但无论是由“亲”而“信”,还是“可靠性”,实际上都以人际关系为核心,是一种由人际关系中所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在这种信任机制下,信任和人际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信任随着人际关系的进展而逐步扩大和积累,而人际关系的进展又是在双方有了一定互信之后,才逐渐深入。
三、和平发展期互信机制的变迁
从2008年开始,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各项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日趋密切,两岸交流也日益机制化。两岸互信机制也将逐步从以人际信任为主过渡到以制度性信任为主,即双方通过共同遵守彼此达成的协议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由此形成以协议规范为中介的互信机制。可以说两岸制度性信任是两岸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和产物。
1.从人际信任到制度性信任的必然性
在过去30年,两岸互信的基本模式是人际信任,但是人际信任的特点注定了这种信任模式无法满足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需要。(1)互信范围的狭隘性。人际信任的对象往往局限于熟人和小团体范围内,而且必须是面对面的“在场”信任,因此信任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受到限制,难以覆盖整个两岸社会。(2)互信建立的经验性。在人际信任模式下,两岸对是否给予对方以信任主要依赖于过去的交往经验,由此常常表现为对熟人关系过分依赖,对缺乏交往经验的生人则过分戒备。(3)互信积累的缓慢性。两岸人际信任的进展是以双方人际关系的进展为前提的,而人际关系的进展又是在双方相互表达了自己诚实、诚意和诚心之后才逐渐深入。这样信任的积累将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更为主要的是,由于人际信任高度依赖于人际关系,当交往对象发生变更,当事人常常要从零开始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信任,这便极大阻碍了信任的代际积累。然而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广泛的两岸交流中来,两岸人员流动的数量、范围都远非过去可比,这使得两岸各界不得不频繁处理毫无交往历史的首次交往活动,不仅要信任亲人和熟人,对大量的陌生人也要给以普遍信任。显然,仅仅依赖人际信任不仅无法满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瓶颈。
相反,制度性信任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的出现:(1)扩大了两岸互信的范围。现代制度要求每一项规范对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因而为每个人的行为设定一定的框架,使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在制度性信任的条件下,即便是陌生人也能在市场上顺利交易,或是进行正常的交往合作。⑨所以,以制度规范为中介,两岸互信便不再拘泥于血缘、地缘的范围,使两岸双方任何个人、组织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2)淡化了两岸互信的经验过程。人际信任常常需要长时期的感情培养或者对彼此可靠性的确证。而制度性信任排除了人情垄断和人品纠葛,通过法律手段,使信任建构所需要的一系列心理负担转由法律承担,从而简化了信任建立的过程。⑩(3)提高了互信积累的效率。由于制度性信任不像人际互信那样依赖于“人”的因素,不必因为信任对象的变更而从零开始重建互信,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人存信在,人亡信无”的困境,实现互信的不断积累。
另外,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经常有一些意外或突发事件发生。这些事件有些是刑事治安案件,有些是社会经济事件,当然也有某些政治势力蓄意制造的政治挑衅事件。在缺乏制度性信任的情况下,突发事件很容易被无限扩大,造成整个两岸人民互信的流失,甚至造成双方的直接对撞和两岸关系的倒退。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各种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问题必然会随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而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人际互信机制的脆弱性将更加明显。
相反,在制度性信任的机制下,各种契约、规范、制度直接作用于两岸双方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活动,能够将双方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规范化和模式化,为彼此间的互动交往提供基本框架,两岸双方以此为尺度,不仅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且可以理解、预期、算计和把握对方的活动,以实现与对方的互动。这样,制度规范的存在同时使两岸体会到一种认同感和安全感,使双方行为变得有更大的可预测性,消除了行动选择的迷茫和信任障碍,而不必再以直接的交往经验或他人的传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
2.两岸协议是制度性信任的基石
制度性信任的基本含义就是当事人双方以规范为中介而相互信任。所以法律规范是制度性信任的基石,两岸要实现制度性信任,就需要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方面都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2005年国共两党达成“五项愿景”,这可以看做是两党之间的协议,为两党之间的互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会谈以来,“两会”共达成14项协议2项共识,为两岸制度性信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2010年两岸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解决功能性议题的同时,对两岸经济活动进行制度性安排,是两岸制度性信任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未来两岸还将在交流的基础上签订其他协议,这些协议将有利于两岸建立制度性信任。
首先是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两岸文化教育交流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热络的经贸往来,两岸文化交流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文化交流之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义不够重视;交流的目的性不明确,随意性较大;单方面的宣传较多,缺乏交互性;缺乏全面深入与大规模的交流,流于表层的活动较多。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将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机制化和制度化,不仅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而且规范各自的行为方式,从而促进两岸社会各领域的互信。
其次是两岸和平协议。海峡两岸曾长期处于政治对立和军事对峙状态。近30年来,两岸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政治层面的进展却艰难曲折。2005年4月,国共两党达成“五项愿景”,其中第二项就是“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将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写入党的正式文件;同年,国民党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列入新党纲之中;马英九上台执政后,在各种场合也多次提及“和平和解”、“外交休兵”,建议就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虽然目前两岸商签和平协议仍困难重重,但这个协议是两岸关系机制化建构的较高境界,(11)将从根本上保障海峡两岸的和平,极大地增加两岸人民之间的互信。
四、两岸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的混融
人际信任具有局部性、私人性的特征,制度性信任具有整体性、制度性的特征,所以人际信任常常被视为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而制度性信任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新型信任模式。按照这样的逻辑,自然就能推论出制度性信任将取代人际信任。而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虽然两岸互信的基本模式将逐渐从人际信任过渡到制度性信任,但是制度性信任并非是对人际信任的简单替代,制度性信任中包含了人际信任的因素,并从人际信任中获得支持力量。
首先,两岸制度协议离不开人情关系。制度性信任的基础是法律规范。在西方社会,法律规范是自主、平等的法人之间斗争、谈判的结果,所以在西方法律理论中,法律规范是私人关系的替代物。在法律规范中没有具体的人,甲方乙方是谁并不非常重要,只要他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执行。所以,在西方社会,制度性信任与人际信任是相互独立的,并构成对后者的替代。但中国人常常是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在情与理的关系中,中国人向来强调情先理后,情主理次,在社会交往中崇尚“合情、合理、合法”。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人社会,两岸之间的协议也倾向于将情、理、法三者综合起来考虑,甚至体现在协议的字里行间,形成具有两岸特色的协议规范。所以,两岸协议常常是人情约定性协议,是人情关系的法律化和条文化,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人际关系的具体内容,起到关系备忘录的作用,而不是私人关系的替代物。既然两岸协议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的人情关系,那么建立在两岸协议基础上的制度性信任自然也就无法祛除人际互信的因素。
其次,两岸制度性信任的保障离不开人际信任。制度性信任的保障是制度规范的外在权威性和内在合理性。“正是制度的这种暗含的规范意义以及我假定它对于其他人所具有的道德合理性使我信任那些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12)这就是说,只有当共享一个制度空间的人们遵从制度规范并理解这些制度所体现的价值,陌生人才是值得信任的。但是两岸之间的协议并没有外在的强制力来保障,无法对违约者施以法律制裁,而且目前也无法内化为两岸人民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制度协议主要依靠人际信任提供动员和支持力量,协议的执行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如果仅仅有契约,其用处是不大的。所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制度性信任主要依靠人际信任来保障,即依赖于动态的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一方验证了另一方也愿意遵守这个协议时,他才会信任这个制度,经过多次的互动,双方才会形成以制度为中介的信任关系。
从这两个方面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虽然两岸建立互信的基本机制和模式将从人际信任向制度性信任过渡,但是制度性信任并不构成对人际信任的替代关系。相反,人们对两岸协议的信任源自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所建立的关系的信任,制度性信任常常体现为人际信任的扩大、提升和固定化。这是两岸建立互信的一个重要特色。
五、以“角色义务”为核心增进两岸互信
如果将人际信任与制度性信任看做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那么建立人际信任和建立制度性信任的基本思路就截然不同:为了建立人际信任,必须加强人际交往和关系;为了建立制度性信任,必须强化制度规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一方面两岸互信逐渐从人际信任向制度性信任过渡,另一方面制度性信任又离不开人际信任,是混融在一起的。建立两岸互信需要以建立制度性信任为重心,但是又离不开人际信任。所以,建立两岸互信的方式就无法单纯追求两岸协议规范的权威性,而必须寻求制度性信任与人际信任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在于彼此都能称职地去履行相应的“角色义务”。
首先,角色义务是人际信任的核心内容。台湾学者杨国枢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三种:家人、熟人、生人。他认为,在家人关系中,彼此要讲责任(即责任原则),而不那么期望对方作对等的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最低)。在熟人关系中,相互要讲人情(人情原则),较会期望对方回报,但是不要求共时性的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中等)。至于生人关系,只能依照当时的实际利害情形而行事(利害原则)。两者之间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对给与取的平衡或公道相当敏感,对回报的期望也很高(社会交换的预期最高)。(13)显然,在家人之间以及熟人之间存在着人际信任。在这两类关系中,感情成分是比较内隐的,也不是人们日常挂在嘴边的,反而对自己“应该”做的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作为家人,就要讲责任,作为熟人,就要讲人情回报。这些不同的角色义务构成了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关键要素。责任的义务会使家人之间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回报的义务会使熟人之间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并且,生人之间在“送人情”与“还人情”的过程中也能变成熟人关系,并建立了相应的互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根源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是否履行了相应的角色义务。中国人信任那些在交往过程的不同关系阶段,能遵循其内隐交往法则并履行其角色规范者。
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角色义务为双方的人际信任提供保证,是两岸人际信任的关键。在两岸交往的过程,大陆履行了自己的角色义务,同样台湾方面也应该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扩大和积累双方的互信。角色义务对两岸人际信任重要性的一个显例是大陆对台“让利”。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大陆不断对台湾释出善意,对台湾民众让利。对于为什么要向台湾让利,温家宝总理给出了一个关键的理由。他说,“要让利给台湾,因为我们是兄弟”。让利给台湾,发端于两岸之间的同胞兄弟之情,大陆对台湾让利实际上是尽一个“亲兄弟”的角色义务。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应该履行相应的角色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增进双方的互信。
同时,角色义务是两岸制度性信任的核心内容。在西方社会,制度性信任主要来自制度规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在两岸关系中,对制度的信任依赖于动态的人际交换的过程。这既体现在法律协议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法律协议的执行上。与西方意义上的制度契约非常重视彼此的权利不同,两岸的协议更多的是规定了双方的角色义务,它实际上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样,与西方的制度契约非常重视权利保障措施不同,两岸的协议更重视如何通过双方“情境互动”来实施。在交换过程中,如果双方都能够依照约定和承诺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那么对约定和承诺的信任程度就高,否则,制度性信任程度就低。
注释:
①Deutsch,M.,“Trust and Suspicion”,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pp.265-279.
②Hosmer,L.T.,“Trust:The Connection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2):pp.379-403.
③Zucker,L.G.,“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In B.M.Staw & L.L.Cummings(ed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eenwich,CT:JAI Press.1986, pp.53-111.转引自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④Whitley,R.D.,“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Organization Studies,1991,12(1): pp.1-28.
⑤许多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包括Whitley,R.D.,“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Organization Studies,1991,12(1),pp.1-28.; Bian,Y.,“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pp.366-385.;杨中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年。
⑥围绕台资企业而发生的两岸互信既包括以台资企业为范围的大陆员工与台商之间,也包括以台资企业为中介的台商与大陆人民之间的互信。本论文并不关注大陆台商与大陆员工以及与大陆社会之间的互信达到了怎样的量化水平(事实上其互信的程度并不理想),而是在这些建立互信以及没有建立互信的经验中找到影响互信建立的关键因素。
⑦邓建邦:《接近的距离:中国大陆台资厂的核心大陆员工与台商》,台北:《台湾社会学》第3期,2002年6月。
⑧刘玉照等:《大陆台企中的组织“断裂”与“台湾人”群体的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9年第3期。
⑨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第243页。
⑩陈昌文:《人情与契约》,《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第36页。
(11)吴能远:《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台湾研究》,2008年第6期。
(12)马克·沃伦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51页。
(13)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杨国枢、余安邦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87—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