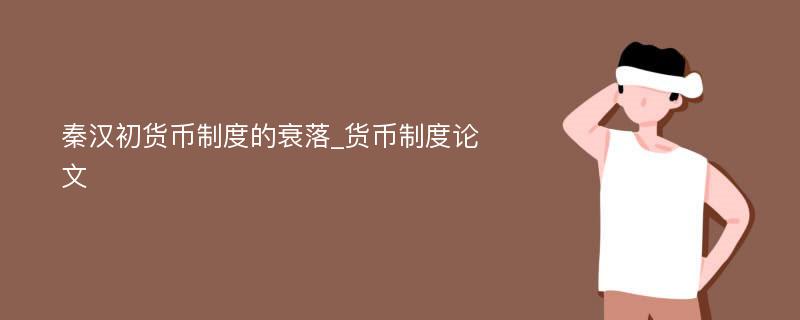
中国秦代汉初货币制度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代论文,中国论文,货币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的货币本身结构及货币流通管理的制度。在以金属货币为主的中国秦代汉初,货币制度一般包括铸币的材质、货币名称及货币单位、货币的铸造权、货币使用中的规定。《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钱律》(以下简称张家山汉简《钱律》)所见中国汉初货币法律,继承了秦律,但比《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以下简称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所见秦代货币立法条文更加细致更加完善。以往学者在这方面研究作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①,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如秦代汉初货币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秦汉之际是否存在从三币制到二币制的变化,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秦代汉初“行钱”的计值单位是什么,黄金的最高衡值单位秦“镒”汉“斤”是否相等,吕后二年以前的汉半两铸造权问题等。下面将在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所见货币法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秦代汉初的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
一、两种货币法律文书文体比较
睡虎地秦墓竹简有关货币的法律文书是《金布律》。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共有15条法律文书,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前5条属于货币法律,后10条是官府财物管理及杂役人员配备方面的法律。后者涉及财物出纳帐簿管理(第6条);都官及其下属官吏杂役人员及相关物品的配置(第7条);官府机构内债务及罚赎款、器物回收及赔偿的管理(第8—11条);县、都官所属器物、传车及大车车轮的修缮或报废的规定(第12—13条);官府隶臣妾、府隶、舂城旦衣物的用料及发放规定(第14—15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总称货币为“钱”,是钱币作为货币总称之始。在货币文书方面对秦代有继承有改进,比秦律更加完善。首先,将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两大部分的内容一分为二。设《钱律》以当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前半部分,即货币法律部分;设《金布律》以当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后半部分,即官府财物管理和杂役人员及相关物品配备的律文。张家山汉简《金布律》约11条,内容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后半部分基本相同,第6—7条律文虽涉及金和钱,但那是在讲罚、赎、债务及官府上缴税款的规定时所涉及的,而不是正面谈货币的文书。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作为一种法律文书载体,已不再兼有记载货币法律的功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设立《钱律》,首次使货币法律拥有专篇文书。
张家山汉简有关货币的法律比睡虎地秦简律文更加细密和完备。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前半部分的货币法律条文只有5条,而张家山汉简《钱律》货币法律条文则有8条。不仅对行钱、行金有具体规定,而对打击盗铸有详细规定。睡虎地秦简秦律虽有打击盗铸的法律条文,却不在《金布律》的货币律文之中,而见于睡虎地秦简《效律》,是作为具体案例出现的。这说明张家山汉简《钱律》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的货币法律比秦律更加完善。
二、从三币制到二币制的变化
在秦代和汉初的法律文书中,人们习惯称法律认可的铜钱、布帛货币和黄金货币为“行钱”、“行布”和“行金”。在张家山汉简《钱律》中所见法定货币为行钱、行金,即为二币制。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所见法定货币为行钱、行布和行金,即为三币制。“行布”仅见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其云:“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②非常明显,在秦代货币流通领域中除了黄金、铜钱外,还有作为货币流通的“布”币③。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来看,汉初法定货币只有黄金和铜钱两类,“布(即缯布)”已不再作为法定货币而是作为一种标准性的商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因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没有将相关内容纳入《钱律》和《金布律》,而是将其纳入《□市律》。在这里尚需要讨论的是: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三币制能否代表整个秦代的法定货币制度?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到张家山汉简《钱律》由三币制改变为二币制在何时?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三币制能否代表整个秦代的法定货币?这个问题与《史记·平准书》记载秦代货币种类的资料相关联。其云:“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④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平准书》既说秦币为三等,却止叙其二,不及中币,不谈布币。《汉书·食货志》抄袭《史记·平准书》改“三等”的三为二,云:“秦兼并天下,币为二等。”⑤这些着实令人生疑。
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被发现以前,人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就是改《史记·平准书》的“三等”的三为二字以合《汉书·食货志》。如现代通行本《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就直接在正文中改“三”为“二”,作“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⑥。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发现以后,人们大都认为《史记·平准书》“三等”的“三”字不误,多主张秦朝为三币制。但秦朝为三币制说者还是面临《史记·平准书》既说秦币为三等,却止叙其二,不及中币,不谈布币的老问题。这就牵涉到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到张家山汉简《钱律》,由三币制改变为二币制在何时?这正是下面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等法律文书,均为墓主人喜生前遗物,据同墓出土的《编年记》所载,喜生于战国末年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从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始进用为地方史官,从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开始在楚国故地先后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喜治狱鄢”,即任鄢地狱掾。《编年记》应是喜的年谱之类的文书,止于喜死之年,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也就是秦统一后的第5年。由此可见,秦律《金布律》三币制实施的上限至迟当在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下限当在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以后,可能就在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死,二世即位“复行钱”为止。“复行钱”,一方面改12铢半两钱为8铢半两钱,对业已变轻变小的秦半两进行规范并牟利。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应是将秦统一前后以降法定的三币制改为二币制。《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之下,只言上币和下币两等,很有可能是在表述秦朝前中期的三币制和后期改行二币制的情况中间有脱简。《汉书·食货志》改为二等当为班固或其父班彪的误解,不合秦朝实际,不足为据。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复行钱”将三币制改变为二币制,中经秦末汉初的社会大动荡不见有改变二币制的记载,直到张家山汉简《钱律》法定货币仍然是二币制。可见,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的三币制到张家山汉简《钱律》的二币制,其改变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复行钱”时。
布币在法定货币中被取消,说明自秦统一以后,一方面铜钱信用度在增加,另一方面,也当与投入流通领域的铜钱量不断增加有关。
三、流通领域中的货币硬件管理
官方对流通领域的货币硬件的管理,主要是对货币的规格、质量方面进行宏观的监控管理及以法律手段加以维护。
其一,对货币的质量标准进行管理。
张家山汉简《钱律》对行钱和行金的质量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磨损),文章(钱文)颇可智(知),而非殊(断)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⑦
“钱径”是行钱质量规定中最重要的内容。“十分寸八以上”,即十分之八寸以上。《汉书·高后纪》:高皇后吕氏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二者分别从钱径和钱重两个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吕后二年所推行的同一种行钱,即:钱径不小于八分的八铢“半两”钱。唐代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⑧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及其它法律条目,均不见规定秦钱钱径的内容,但可从其他记载中得其大概。《史记·平准书》:“[秦]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唐代司马贞《索引》引顾氏按语:“《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⑨这里指的应是秦始皇时代的12铢秦半两,二世时代的8铢秦半两质量规格当与张家山汉简《钱律》8铢汉半两钱相同。从出土实物来看,秦始皇时代的12铢秦半两尚能大体符合质量规格外,8铢秦半两和8铢汉半两的质量规格在实际中存在较大差距,秦末汉初民间铸造小而薄穿孔大的榆荚钱(3铢半两)比较泛滥。
在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行布(布帛货币)为三币之一,故对行布在流通领域中的质量有具体规定。其云:“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复行钱”,废除行布,汉承秦制,张家山汉简《钱律》没有行布及行布质量的规定。
其二,对流通领域中法定货币的择取问题。
在张家山汉简《钱律》中,法律认可的铜钱和黄金货币称为行钱、行金。同时规定:“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但对冒充铜钱的“铅钱”、成色有问题的“青赤”金币有权拒收。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在官府受钱和市场上用钱也有类似规定,其云:“官府受钱者……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又云:“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⑩
在“敢择不取”法定的货币方面,张家山汉简《钱律》为行钱和行金;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是行钱和行布。前者没有行布,后者没有行金,这种差异是秦代和汉初货币种类及货币体系所决定。
其三,不得毁销行钱。
张家山汉简《钱律》规定曰:“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脏)为盗。”(11)这是对流通领域货币的一种保护措施。
四、货币换算及其相关问题
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张家山汉简《钱律》均已表明:汉初的货币体系是二币制(行钱、行金);秦代前中期的货币体系是三币制(行钱、行布、行金)。这在上节已结合传世文献资料进行了对比,以下再就两种法律文书及相关资料对两个时段的货币计值单位、货币换算及相关问题进行对比研究。
其一,行钱的计值单位与进位法。
行钱指法定的铜钱。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所言的行钱是一种记重性货币,其钱文均为:“半两”。前者指秦始皇时代钱重十二铢的秦半两(二世时代改为八铢半两),后者指吕后二年以前钱重八铢的汉半两。两种行钱计值的最小单位是“钱”。这种铜钱计值单位的“钱”与唐代以后取代“铢”而作为计重单位的“钱”有别,秦汉一“钱”指一枚法定的“半两钱”。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有云:“有买及买(卖)也,各婴(系)其贾(价);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因为“钱”是最小单位,所以“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这种作为铜币计值单位的“钱”不仅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法律文书中,而且一直使用到南北朝后期才开始为铜币计值单位的“文”所取代(12)。
行钱计值单位除了“钱”外,还有一个以“千钱”计值的单位“贯”。“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秦和汉是否都用“贯”?有一种意见认为,“‘贯‘作为计算铜钱的单位名称,大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13)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千钱”有单位名使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其曰:“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畚,是一种用草绳或竹篾编织的盛钱器具,这种钱畚是所见最早的一种“千钱”计值单位。尽管这种计值单位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但它是最早受到法律认可的铜钱计值单位。
张家山汉简《钱律》虽不见“千钱”计值单位,但可从相关传世文献中获得一些了解。《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倍)则卑下之,伯(百倍)则畏惮之,千(千倍)则役……子(利息)贷金钱千贯。”这“千贯”的“贯”就是汉代的铜钱“千钱”的计值单位,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铜钱“千钱”计值单位。这样的记载虽然不多见,但还可从相关方面得到验证。《史记·平准书》:“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14)“贯朽”与“不可校”相应,显然这个“贯”与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千钱一畚”的“畚”性质是一样的。秦畚汉贯区别只是载体和名称的不同而已。《史记》同书同篇南朝宋人裴骃集解文本“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15)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二十算也。”(16)进一步证明汉代的“一贯千钱”与秦代的“千钱一畚”是具有承继关系的。
其二,行金的计值单位及其进位法问题。
行金指法定的黄金货币。张家山汉简所见黄金的计值单位有:斤、两、铢。如:《二年律令·具律》:“赎死,金二斤八两。”《二年律令·金布律》:“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皆为其例。睡虎地秦简虽不见黄金计值单位的名称,但从《云梦龙岗秦简·田赢(17)》、《岳麓书院藏秦简(二)·数》及相关传世文献来看,秦代黄金计值单位为:镒(或作溢)、两、垂(18)、铢。
“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的衡制,秦汉一致(19)。汉初以一金为斤既已得到证实,其一金应为十六两。《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下》载秦代“黄金以溢(镒)名。”南朝宋人裴骃《史记》集解引孟康曰:“二十两为溢。”(20)《太平御览》卷810引《淮南子》“秦以一镒为一金而重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21)。若按新出《岳麓书院秦简(二)·数》有关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详见下文)来看,当以后者为是。
其四,不同货币间的比价问题。
黄金自具有货币价值以后,与其它货币的比价总是处于波动的状态。汉初,行金与行钱间的比价的波动状态如何,张家山汉简《钱律》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金布律》第428号简有一条律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皆许之”。而且这个平价还规定时间和地区,即“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可见汉初行钱与行金比价,不仅有时间性的差异,而且还有县域性的地区性差异,处于波动状态。
张家山汉简法律文书没有不同货币间的比价条文,而同墓出土的汉简《算数书·金贾(价)》第46号简有“金贾(价)两三百一十五钱”(22)的内容,据此演算其比价1斤黄金等于5040钱。另外,唐代司马贞《索引》注《史记·平准书》“[汉兴]一黄金一斤”引三国魏人如淳云:“时以钱为货,黄金一斤直(值)万钱。”(23)综合而论,汉初黄金一斤与铜钱的比价大体在五千钱至万钱之间波动,这种波动除其他原因外,可能还与半两钱的轻重有关。
秦代的货币体系是三币制(行钱、行布、行金)。睡虎地秦简《金布律》关于三币间的换算规定为:“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此法律条文除了“钱十一当一布”的具体换算规定外,钱与金的比价没有明确规定,《岳麓书院秦简(二)·数》简0970则有这一比价的内容:“金一朱(铢)直(值)廿四。”也就是说一两黄金比价576钱,当然也会因时因地有所波动。
五、铸币权问题
其一,反盗铸问题。
从张家山汉简《钱律》来看,铸币权为国家所垄断,凡未经授权而私铸者视为盗铸。
张家山汉简《钱律》规定:“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与同罪。”“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知)为及买铸钱具者,与同罪。”(24)综合而言就是要严厉打击盗铸行钱者及佐助盗铸者,从重惩罚知情不报者和捕捉打击不力的官吏。
同时也鼓励盗铸者及佐助盗铸者举告同案犯、捕捉其他盗铸者。张家山汉简《钱律》规定“盗铸钱及佐者,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而能颇相捕,若先自告、告其与,吏捕,颇得之,除捕者罪。”“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有(又)复告者一人身,毋有所与。诇告吏,吏捕得之,赏如律。”(25)
张家山汉简《钱律》还规定:“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26)行金的质地为黄金,凡含金量能达到标准,为成色纯正金黄。所谓“伪金”,应指张家山汉简《钱律》第198号所谓金“青赤者”。也就是说伪铸者伪铸行金时掺杂其它金属,使伪铸品含金量降低,金的成色不正,呈现出“青赤”色。伪铸行金者,“黥为城旦舂”,就是要依法打击伪铸行金者。
睡虎地秦简打击盗铸的条文尚未见有张家山汉简法律细致,但《金布律》及《封诊式》也有相关内容。《封诊式》云:“[爰]书:某里士五(伍)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锫)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丁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锫),来诣之。’”(27)这是打击盗铸的案例,表明秦代打击盗铸的法律也是相当严厉的,凡私自盗铸及佐助盗铸者,都要逮捕法办。
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严厉打击盗铸的相关法律条文及案例表明:从秦代和吕后颁布《二年律令·钱律》前后,铸币权都为国家所垄断。问题是高祖刘邦曾经“更令民铸钱”在何时?又何时将铸币权收归国有?这是下面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其二,吕后二年以前的汉半两铸造权问题。
吕后二年《钱律》颁布以前的汉半两铸造权有一个由放铸到国家统一铸造的过程。何时放铸?又何时收归国家统一铸造?下面进一步讨论。
《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爱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司马迁的这一记述,亦见于《汉书·食货志》。在这条史料中明确记述了高祖刘邦:“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这一律令是对秦代货币的一次重大的改变。除了黄金由最高单位镒改为斤外,就是对铜钱的重量和铸币权的改变。即放弃秦代以降国家垄断的铸币权,允许民间自由铸钱。
关于刘邦“更令民铸钱”的年代问题,可从引文中“汉兴”和“天下已平”两个时间概念入手。《汉书·食货志》有两处使用过的这一对时间概念,后一处与《史记·平准书》相同,前一处“天下已平”作“天下既定”。考《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西都洛阳,司马迁谓此时为“天下大定”;《汉书·高帝纪》载高帝刘邦的诏书作“今天下已定”。《史记》的《汉兴以来诸侯王表》起于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即秦朝灭亡和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之年。由此可见,“汉兴”,“更令民铸钱”,是在刘邦为汉中王以后,楚汉战争期间,即公元前206-202年之间的事。《史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28)《汉书·张陈王周传》亦同。唐代颜师古认为:“高祖初赐张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29)因此,可以进一步说,“更令民铸钱”事,应在该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还定“三秦”之时,或稍后。这与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所记“[汉兴]更令民铸钱”的背景,即“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的情况吻合。
私自铸小钱(或称“秦荚钱”)之风在秦末已起(30),楚汉战争以后,项羽虽为霸王而不能掌控天下全局,私自铸钱之风当已无法遏制,刘汉政权尚属一隅方国,“更令民铸钱”,应是顺其自然并有益于刘邦对项羽的战争。“钱重难用”只不过是借用一个说法而已。从出土的汉初铜钱的钱重(31)及相关文献资料(32)来看,法定钱文仍为“半两”,重量三铢,或更少。既许私铸,又无监控,小钱、轻钱掺进钱币流通领域。肉薄孔大,钱重甚至不足一铢者(33)。其轻如榆荚,因此俗称汉初半两钱为榆荚钱或荚钱。荚钱的大量铸造,一方面,排挤了布帛货币,增加铜钱的流通量。另一方面,铜钱的过量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反而更加导致社会危机。稳定市场,控制货币铸造的问题逐渐突出。
汉初,铸币权何时由放铸转到国家垄断?楚汉战争期间,也就是202年以前是不可能解决的。到天下既定,即202年以后,才有可能。从《二年律令》来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币权已归国家垄断。结合《汉书·高后纪》及东汉应劭注文来看,在该年,始以八铢半两钱取代三铢半两钱。此前,所通行的铜钱为三铢半两的榆荚钱。《唐六典·御史台》侍御史条下原注云,汉惠帝三年,相国奏请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凡九条,其中有“铸伪钱者”(34)。这表明在惠帝三年,即公元前192年以前,朝廷已垄断了铸造权。《汉书·吴王濞传》云惠帝、高后时吴王刘濞依封国内的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之徒“盗铸钱”(35),可为其佐证。若进一步追索,汉初国家垄断铸币权,应是楚项战争结束,“天下已平”之时,或稍后。因为楚汉战争时期,天下是项楚霸王的天下,刘邦只是作为一个地方封国国君汉中王的身份与项羽争天下,为了破坏项楚政权的经济体系,并让自己合法铸钱并在全国大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乃“更令民铸钱”,这是一项极有远见的策略,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天下已平”以后,天下已是刘邦的天下,必然要改变楚汉战争期间混乱的铸币状态,由国家垄断掌控三铢半两钱的铸币权,以匡正和稳定已有货币体系。这正与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所记“天下已平”以后,重农抑商,打击“不轨爱逐利之民”的背景相吻合。
以上在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所见货币法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货币法律文书文体、货币种类、货币硬件管理、货币换算、铸币权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秦代汉初货币制度,并探讨了以下相关问题。其一,在文书文体方面。睡虎地秦简有《金布律》,张家山汉简除设有《金布律》外,另创《钱律》,将睡虎地秦简《金布律》的内容一分为二,以《钱律》为货币法律条文的专门文书载体。其二,《史记·平准书》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之下,止叙其二,不及中币,不谈布币。《汉书·食货志》抄袭《史记·平准书》改“三等”的三为二,云:“秦兼并天下,币为二等”。历来学者皆赞同二币制,睡虎地秦简法律文书面世后,学者们又多认为秦代行三币制,这两种倾向都不妥。本文认为:《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之下,只言上币和下币两等,当是在表述秦朝前中期的三币制和后期改行二币制的情况中间有脱简。《汉书·食货志》改为二等当为班固或其父班彪的误解,不合秦朝实际,不足为据。其三,法定货币由三币制改变为二币制时间当在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复行钱”之时。其四,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是对货币制度的改革。即将秦统一前后以降法定的12铢小孔半两钱改为8铢大孔半两钱。二是将秦统一前后以降法定的三币制改为二币制,即革除实物货币行布,推行行钱、行金二币制新的货币体系。其五,货币计值单位。睡虎地秦简货币为“三币制”,行布的货币计值单位仅为“布”;行钱有:钱、畚(千钱);行金有:铢、两、镒。张家山汉简为“二币制”,行钱计值单位有:钱、贯(千钱);行金有:铢、两、斤。本文对二者相异处,指出行钱的千钱单位名称有“畚”和“贯”;行金有“镒”和“斤”的不同。货币单位间的换算。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行钱,一枚为一钱;秦代“千钱一畚”,汉代“一贯千钱”。行金,二十四铢为两,汉代十六两为斤;秦与汉一金的重量相等,差异只在名称上的不同而已。其六,刘邦“更令民铸钱”,即改变秦代以降国家垄断的铸币权,允许民间自由铸钱。刘邦“更令民铸钱”的年代问题,应在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还定“三秦”之时,或稍后。吕后二年以前,铸币权由放铸转到国家垄断,应是公元前202年楚项战争结束,“天下已平”之时,或稍后。
总之,从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到张家山汉简《钱律》,即秦代汉初这一时段,法律由认可实物货币“行布”到排斥实物货币“行布”,这是货币史上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进步。关于货币方面的法律由初具基础到更加细化,走向完善,为汉武帝时铸造推行五铢钱,从法律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①李均明:《张家山汉简与汉初货币》,载《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闫晓君:《试论张家山汉简钱律》,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6、67号。
③罗运环:《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国秦代的货币研究》,载《武汉金融》2006年第10期。
④《史记》(武英殿本),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80页。
⑤《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2页。
⑥《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页。
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8号。
⑧《汉书·高后纪》,第97页。
⑨《史记·平准书》,第1442、1418页。
⑩《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第65、68号。
(11)《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199号。
(12)参见刘森《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13)陈阿泉:《古代铜钱何以称“贯”》,载《中国粮食经济》2004年第2期。
(14)《史记·平准书》,第1420页。
(15)《史记·平准书》,第1429~1430页。
(16)《史记·平准书》,第1430页。
(17)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18)垂(或作锤),八铢。见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简130、《岳麓书院秦简(二)·数》简0957、0970。
(19)朱汉民、陈松长:《岳麓书院秦简(二)·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简0646、0458;《汉书·律历上》,第969页。
(20)《史记·平准书》,第1443页。
(21)《太平御览》卷810,中华书局影印。
(2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46号简。
(23)《史记·平准书》第1418页。
(24)《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2、203、208号。
(2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7、204+205号。
(26)《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200号。
(27)《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第20号。
(28)《史记·留侯世家》,第2038页。
(29)《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第11-52页。
(30)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31)高英民、张金乾:《中国古代钱币略说》,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32)司马贞:《史记索隐》:“《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铢。”《史记》,第1416页。
(33)《中国古代钱币略说》,第99页。
(34)《唐六典·御史台》卷13,中华书局,第3793页。
(35)《汉书·吴王濞传》,第19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