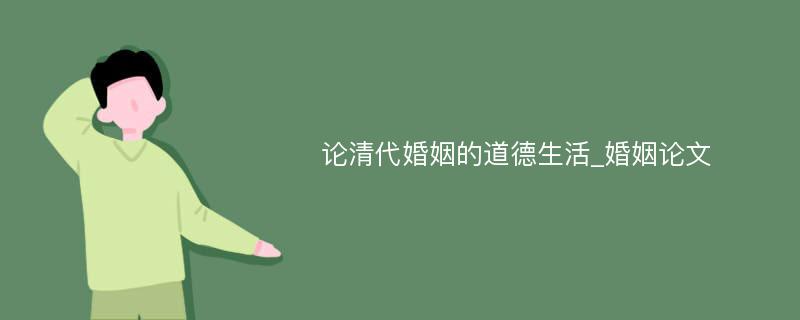
论清代婚姻道德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道德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0)06-0033-07
婚姻是由一定社会制度或者风俗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夫妻关系。它的存续离不开婚姻行为。从动态角度来考察,婚姻行为主要有婚姻选择、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与此相联系,清代婚姻道德生活就是婚姻选择、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中所呈现的道德生活。
一、婚姻选择中的道德生活
婚姻选择与择偶被有的学者当作一回事看待,其实,它们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择偶是结婚当事人的私人行为,婚姻选择则并非都是如此。这种区别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也存在,但远不如中国古代社会那样明显。在清代,婚姻选择的主体几乎都是家长甚至族长,婚姻选择权几乎全部控制在家长或者族长的手里,而结婚当事人却无权自主地决定是否结婚,甚至连决定独身的权利都被剥夺,就更不用说自主地选择配偶了。由此可见,清代的婚姻选择,说到底,就是家长或者族长的选择。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选择的传统。《礼记·昏义》早就规定,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意味着婚姻选择不是男女两人的私事,而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大事,是事关家庭利益乃至家族利益的大事,是家长或者族长的行为,即只有经过家长或者族长的同意,两姓子女才会有婚姻。清朝法律明确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1](P443)
清代婚姻选择并不是自由、开放性的,而是在不可选择前提下的选择。这里所说的不可选择即是对婚姻的边界和范围的规定,是对婚姻选择的限制。这种限制往往具有道德性,可以对之进行善恶评价,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婚姻选择的禁忌。在清代,婚姻选择的禁忌主要有政治禁忌、尊卑禁忌和乱伦禁忌。
第一,政治禁忌。这指的是婚姻选择受到了清朝婚姻政策的限制。这样的禁忌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朝的民族通婚政策。这一政策在清朝的不同历史阶段是有所不同的。从努尔哈赤起至顺治帝当政时,清朝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巩固其入关初期的统治,对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实行允许和鼓励政策,不仅容许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官民自相婚配,而且顺治帝还明确地指示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赤子,欲其各相亲睦,莫如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连姻者,听之。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2]由此可见,此时的清朝民族通婚政策显然是一种团结各民族的政治手段。然而,自康熙朝开始,这一婚姻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清朝继续贯彻满族与蒙古贵族联姻的基本国策,并一定程度地容许满族贵族与汉八旗贵族的通婚,如康熙帝的妃嫔中的年佳氏、王佳氏、陈佳氏,嘉庆帝生母孝仪后魏佳氏,都是汉八旗人;另一方面又严格禁止汉族、满族等民族之间的通婚,满、汉、蒙八旗官民之间的通婚也不例外。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就发布了“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的禁令。为了确保这种禁令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清朝政府对违令私嫁的行为进行严厉制裁。如对违背蒙汉通婚禁令而私自嫁娶者,一经查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其母家,将私娶的民人治罪,对知情的主婚人及说合的蒙古人等都予以处罚。这种禁止民族之间通婚的政策同样是清朝维持其统治的政治手段。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清朝统治者担忧满族因为联姻而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失却自己的“国语骑射”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意识;其次是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如果民族之间通婚,就有可能导致家庭之间甚至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不利因素。然而,民众却不顾清朝的政治伦理要求,违禁嫁娶不断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官员认为应该废止民族之间通婚的禁令,这一看法也被最高统治者所认同。在看了巡抚陈宏谋的奏疏之后,乾隆帝给军机大臣等下了如下一道上谕:“据陈宏谋奏:向例湖南省民人,不准与苗人结姻,后经弛禁,近复禁止,于该处情形,转觉不便等语。湖南沿边一带地方,民苗杂处,从前因苗人归化伊始,梗顽者尚未尽驯,恐与民人交通,汉奸或致构生事衅,是以定例甚严。今苗人向化有年,涵濡日深,渐习耕读,与内地民人无异,若令其姻娅往来,与苗民声息相通,则各峒寨风土人情,或可得其要领,于地方亦属有益。今陈宏谋既奏及此,于理似属可行。”[3](卷712P945)民族之间的通婚禁忌一旦有所松动,就不止于民苗之间,其他民族之间也会如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又在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通婚禁忌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他发布了如下上谕:“国家休养生息,中外一家,本无畛域之分。从前定例,内地民人不准婚娶蒙古妇女,或因民人等暂时出口谋生,在彼婚娶,易滋事端,是以设有明禁。近来生齿日繁,内地民人孑身出口贸易种地者不可胜计。伊等相处日久,往来婚娶,势难禁止。……至民人不得婚娶蒙古妇女,不但此条可删,并可无庸形之章牍”[4](卷128P182)。随着清朝对汉苗、汉蒙等族之间通婚禁令的废止,有关满汉通婚的禁令也有所松动,并最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式降旨开禁,令满、汉通婚。
其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在清代,由于男女人口比例不合理,男多女少,有部分男性难以在当地找到婚配的对象,就不得不去外地寻觅或者购买。为了防止妇女外流,以满足当地男性的婚配需要和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地方官员就会采取措施禁止妇女出境。下面这则禁止稍贩妇女出境的请求就反映了官员的地方保护主义心态:“……本处妇女日少,而贫民之无妻者日多也。民多鳏旷,则不能长其子孙。人稀地皮,日见荒残,蕃庶之盛,何时复睹。卑职身在地方,深切隐虑,除已经一面出示严禁外,但嗣后若有汉属别州县违禁买去者,卑职尚可移关追回。诚恐四川兴安、湖广等处稍贩恶棍,多方略诱,违禁买去,远飏境外。若非仰请宪令,不能禁遏。请于嗣后凡有女之家,如系自幼许配与邻近地多,媒聘有凭,书帖有据者,仍许照常嫁娶外,其一切未经许配之女,务于本处择婿,不许与外境之人通媒议娶。民间孀妇,或招夫入室,或改醮与人,亦止许与本处人成婚,不许稍棍簧诱嫁与境外。至于有夫之妇,其平日不相和谐者,或离或合,许其依律告官酌断。如有本夫私鬻,或奸徒用计买休,图奸图利,嫁卖出境者,本夫、拐犯各遵律例尽法重处。绅士大户所蓄婢女,非嫁为农妇,即配与仆人,亦不许潜卖出境,其买去之人,如系本省,卑职径行关究,不敢频渎宪案。如系隔省,许卑职请咨提拿,本妇仍行追回,身价例不断给,仍治以知情之罪。如此则外境稍棍惕于宪令,庶知敛迹。一妇一女尽配褒民,将见地方之生聚,从此日蕃。即朝廷之版籍,从此日盛。或于地方不无裨益也,可否允行,未敢擅便,除通详外,伏侯宪夺。”[5](P178-179)禁止妇女外嫁,意味着清代人的婚姻选择只限于当地。不过,这样的禁令对清代人的婚姻选择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第二,尊卑禁忌。它指的是婚姻选择受到了尊卑观念和等级结构的限制。这种禁忌早就在发挥作用,在清代,门第、身份、权势等因素仍然对人们的婚姻选择产生影响。清代婚姻选择的尊卑禁忌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良贱不婚。“良”即良民,包括军、民、商、灶四类人。“贱”即贱民,包括皂隶、禁卒、仵作、马快、步快、长随、乞丐、蛋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娼优和奴仆。在清代,良民是歧视贱民的,一般是不会选择贱民来婚配的,而且,清朝法律也禁止良贱联姻,规定:“(文武)官(并)吏娶乐人(妓者)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1](P451),“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主婚人)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指家长言)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妄冒由家长,坐家长;由奴婢,坐奴婢。)各离异,改正。(谓入籍为婢之女,改正复良。)”[1](P452)在实际生活中,尽管清代人以良贱婚配为耻,不过,良贱不婚并不是绝对的,在具体事情上存在着某种权变。定宜庄在对清代婚姻进行考证后发现:“所谓的良贱不婚,只是‘良’女不得与‘贱’男通婚,而‘贱女’与‘良男’的通婚却不禁”[6](P276),并认为,这正是“良贱不婚”的实质内容,也突出地说明清代社会具有视男性血统为惟一标准的特征。这意味着良贱不婚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问题,其结果就必定会如郭松义所指出的那样:“在良贱不能通婚的定制下,清代的奴仆,以及那些归入贱籍的人们,在婚姻选择中,只能局限于同样身份、同一生活圈子的人群。有的像堕民、蛋民等等,即使国家已给豁除贱籍,准与良民成婚,可因所执‘贱业’不改,生活环境没有变更,准婚亦等于是句空话。”[7](P35)
其二是官商、士商不婚。官员、士人、商人虽然都是良民,但是,在“权力至上”、“重农抑商”的清代社会里,商人的社会地位必定会较官员和士人要低,这就必定会造成官员和士大夫歧视商人。不仅如此,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歧视商人,如雍正帝强调士人是“四民之首”,此外,“农为最贵,而工商皆其末也”。虽然有士人论证“农商皆本”、经商是正当职业,如黄宗羲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8](P29)唐甄也论证了自己在仕途失意后经商的正当性,他说:“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之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9](P91);也有商人力图通过乐善好施、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来树立清代商人的良好形象,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商人被歧视的格局却并未因此而有根本的改观。这也决定了,在清代前期,官员、土人就会以与商人联姻为耻,会遭到人们的非议,甚至会招致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斥责。《清稗类钞·婚姻类》中的《赵国麟与刘藩长联姻》就谈及了这种现象:“咸、同以前,搢绅之家蔑视商贾,至光绪朝,士大夫习闻泰西之重商,官、商始有往来,与为戚友,若在彼时,即遭物议。乾隆初,大学士赵国麟与商人刘藩长联姻,为高宗所责。……谕云:‘赵国麟素讲理学,且身为大学士,与市井庸人刘藩长缔结姻亲,且在朕前保荐。朕已明降谕旨,较之仲永檀参奏之事,其过孰为重大?’斥刘为市井庸人,商之为世所轻乃如此。”[2]尽管如此,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官员或者士人与商人联姻的现象却与日俱增,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商人通过捐纳得到了官衔,可以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和建立军功而得到官位的人平起平坐了;其次在于官员或者士人与商人的相互利用,官员因为俸禄少、需要得到商人的接济,士人因为生活贫困需要得到商人的资助,而商人则需要得到官员和士人的保护;再次在于财富在婚姻选择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嫁娶论财的风气开始蔓延。
第三,乱伦禁忌。这历来是古代中国人婚姻选择的限制因素。它主要包括同姓不婚与表亲不婚两方面的禁忌。这两种禁忌被清朝法律所认同。就同姓不婚而言,清朝法律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1](P447)这意味着,无论血缘关系的远近,只要是同姓男女,就不被允许有婚姻选择。然而,这条力图防止乱伦的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执行下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代人基本上是聚族而居的,有的地方方圆几里甚至更宽范围之内所居住的都是同一姓氏的人,在交通不便和清代人交往圈子过小的条件下,人们即使不愿意与同姓为婚都没有办法。在这种无奈的现实生活情况下,清代人既顾不了同姓为婚即乱伦的道德观念,又不惜触犯有关法律规定,而选择与同姓为婚。当然,这种婚姻选择也是有道德限制的,即“同姓者,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不计也。”[2]生活的现实也迫使清朝政府对其原有立场作出调整,向五服以外的没有“尊卑相犯”的同姓为婚者大开绿灯。如乾隆五十四年,湖南东安县发生了丈夫唐化经砍死其妻唐氏的命案。就清朝法律而言,唐化经既违犯了“夫殴妻致死”律,又违背了“同姓为婚”律。然而,司法审判时却只依据前者来定刑。这表明了清朝政府对“同姓为婚”事实的容许。
表亲有两种,其一是姑舅表兄弟姊妹,其二是两姨表兄弟姊妹。与此相一致,表亲婚也有两种。清代社会对于表亲婚有着两种对立的态度。有人认为,就血缘关系而言,表兄弟姊妹比同姓兄弟姊妹更近,正是因为如此,表亲婚比同姓婚更具有乱伦的特征,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表亲婚。清朝政府也持同样的态度,清朝法律规定:“若娶已之姑舅两姨姊妹者,(虽无尊卑之分,尚有缌麻之服。)杖八十。并离异。”[1](P448)由此可见,“尚有缌麻之服”就是清朝法律不许表亲成婚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就是一个伦理理由,实际上是指如果表亲成婚就是乱伦。更多的人则认为,表亲婚并不乱伦,相反,它不仅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天伦”,而且,它由于是“亲上加亲”,就可以巩固和深化表亲家之间的感情,所谓“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如此,事实上,表亲结亲在清代还相当盛行,如洪亮吉的妻子是其母亲的侄女,并让长子娶了其姐姐的女儿。鉴于这种情况,清朝政府不得不于乾隆五年(1740年)修改禁止表亲为婚的法律条文,将其改为“姑舅两姨姊妹(为婚)听从民便”。
这些主要禁忌以及其他禁忌如仇雠不婚、岳秦两姓不婚、潘杨两姓不婚等,是从禁止的角度来规定、限制清代的婚姻选择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婚姻选择实际上是强调“门当户对”,正如康熙朝著名清官于成龙所主张的“结亲惟取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反映了清代人在婚姻选择方面的平等①观念,也意味着清代人把相同的或者一致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乃至生活条件作为婚姻缔结和巩固的基本条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门当户对”并非仅指两个家庭或者家族在等级、权势、地位上的相当,还包括它们在职业、财富上的不相上下。它表明,清代的婚姻选择并非是基于惟一尺度或者标准的选择,不同家庭或者家族选择的价值动因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二、婚姻缔结中的道德生活
在清代,除个别婚姻②之外,婚姻的缔结都有一个过程。其完整的过程依次经过以下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就是男方托媒向女方提亲;问名就是在女方父母同意结亲后,男方父母再请媒人询问待嫁女子的姓名、生辰;纳吉就是男方父母将儿子和该女子的生辰八字相卜,若卜得吉兆,表示婚姻可行,并将此信息回告女方;纳征就是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若女方接受男方财礼,则表示正式订婚;请期就是男方定下结婚的日子,并与女方商量,女方若同意就回帖;亲迎就是新郎于结婚当日迎娶新娘过门。这六个方面就是先秦以来所流行的“六礼”。它意味着婚姻缔结是离不开道德的。如纳采不仅仅是男方请媒人带礼物郑重向女方父母求婚,更重要的是表明该婚姻的缔结是男女双方家庭自愿的行为,并让媒人见证两家的联姻,承担起沟通两家意见的责任,以保证两家共守婚姻诚信。请期也并非只是简单地选定结婚的日子,而是平等观念和尊重意识在婚姻缔结中的体现。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道德是清代以前婚姻缔结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促成清代婚姻缔结的主要因素就并非只有道德了,还有财礼,在某种意义上,财物逐渐取代了道德在清代婚姻缔结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是至清代以后财物才在婚姻的缔结中受到重视。其实,早在明代的部分地区(即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就已经出现婚姻论财的风气,但是,它却远远比不上清代婚姻重财的广度和深度。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人们的逐利意识,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不可否认,道德仍然是清代婚姻缔结的主要因素。尽管清代婚姻缔结的过程中有着多种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但其中使婚姻缔结成功的主要道德因素却是信义。婚姻缔结中讲信义有不同的情形,或者不因男方家境贫穷而改变初衷,如陆射山(陆嘉淑)“欲为其女与寡嫂之女择壻于邑中,得查慎行、许汝霖二人,皆贫而好学。谓其嫂曰:‘查富贵未可必,必成名士。许则八座无疑也。’嫂以女字许,查为射山壻。许既婚,嫂知其家徒壁立,为之哭失明。查竟不能娶,而射山适悼亡,欲远行,佯谓其女曰:‘我与汝至舅家。’遂同乘小舟,至壻门,射山先入,谓慎行父曰:‘我二人儿女长大,可成婚矣。’慎行父亦名士,而拘于礼法,答曰:‘吾虽贫,不能备六礼,然即具酒食一席,亦非仓猝可致者。’射山曰:‘皆不须此,今是吉日,我特送女来。’遂成婚。”[2]或者不因已聘之女人突发恶疾而取消婚约,如新化人艾倬云,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其父艾秉实替其聘定了谢氏之女。但遗憾的是,该女子却突然失明。谢氏之父因为自己的女儿双眼失明、不能持家和侍候人、增加了艾家的负担而主动地辞退这门婚姻。艾秉实以此告之艾倬云,艾倬云果断地回答:“始聘之,旋弃之,不义。妇之所贵者在德,丧明何害?”艾秉实笑着说:“吾特试汝耳,汝果如是,必能兴吾门。”到结婚时,谢氏之父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又以美婢为媵,以此作为某种补偿,也被艾倬云拒绝[2]。婚姻缔结中的信义,既表现为因担心给对方增添麻烦而主动解除婚约(如谢氏女之父的那种做法),又表现为想方设法信守婚约,如“刘以平……初聘关处士女,未娶而女病废,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刘疑其无病容,诘之,媒以实告。刘怅然曰:‘吾聘者,病女也。弃之不义,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归吾家,无复还理,即室吾弟以宽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亲迎后,病遂愈,于是兄弟同日毕姻。”[2]还表现为不夺人已聘之妻,并为对方结百年之好创造有利条件,如:“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奁具甚盛。婚夕,将就良席,妇忽长叹。子问故,妇曰:‘吾初许嫁老儒子,老儒死,家益贫,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适于君。虽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觉失声,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闻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谓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无妇!奈何夺贫子之妻?’即访求老儒子,迎之以归,衣以己之衣,扫除别室,使成婚礼,尽以妇家所装送者畀之。”[2]富家之子的这种态度是婚姻缔结中的信义的最高层次。
不过,就大体趋势而言,道德在清代婚姻缔结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式微,而财物的作用却越来越突出。在某种意义上,财富是清代婚姻缔结的前提条件,是婚姻缔结是否成功的最重砝码,是社会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不仅男方将婚姻缔结作为索取和占有财富的方式,而且,女方也贪图男方的财富,从财富尺度出发来选择何人为婿为夫,如“安化陶文毅公澍夫人在两江制府署时,有人亲见其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问其故,则蹙然曰:‘我出身微贱,少常操作,此手为磨柄所伤耳。’盖文毅少极贫,初聘同邑黄氏女。有富翁吴某,闻黄有姿,谋夺之为其子继室,以厚利啗黄。黄顿萌异志,迫文毅退婚。文毅不可,黄之妻亦不愿,而女利吴之富,其父又主持甚力,遂誓不适陶。会家有养婢,愿以身代,黄妻诺,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疑,即后之膺一品封诰者也。”[2]这是清代婚姻缔结中重财的典型事例。因为男方(即陶澍)家贫,不但女方之父坚决地要求解除婚约,就连已聘之女也因被富翁家财富所诱惑而决定改嫁他人,其结果是自己因惨遭变故而自杀,而其婢女则荣膺一品封诰。
清代这种婚姻重财之风,使正常的婚姻缔结方式发生了异化,导致了多种不正常婚姻的出现。不正常婚姻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是收继婚。收继婚是指寡妇在其丈夫死后被丈夫家族中子侄或者兄弟收继为妻的婚姻。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儿子收娶继母或者父妾,另一类是兄弟收娶已故兄弟的妻子。这种婚姻现象早就在清代以前的部分少数民族中存在着,《史记》中最早记载了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婚姻缔结方式。在清代,收继婚继续存在,相对于以往朝代而言,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再只在少数民族中存在,汉族中也存在这种婚姻;二是不但在穷苦百姓中存在,在贵族中也存在,如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衮霸占其侄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还传说收娶了其兄皇太极之妻子即顺治帝之生母孝庄太后;三是在中国北方较盛行,而在南方相对较少,《清稗类钞·婚姻类》记载了云南所存在的这种婚姻:“吴西春官云南之维西,曾得一讼牍,其词云:‘某家生子四人,皆已婚娶,不幸某年长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理宜以第四子续配长媳,但年齿相悬,恐枯杨不复生荑。特与三党同议,将长子之妻配与二子,二子之妻配与三子,三子之妻配与四子,一转移间,年皆相若,可无怨旷之虞,极为允协,恳求俯准。’吴大怒,拍案,吏请曰:‘此间习俗如是,愿无拂其意。’乃准之。”[2]显然,这种婚姻是违背了传统礼教的,是被人们视为“乱伦”的。清代人之所以甘愿为了收继婚而冒被绞死的危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原因。因为,“一般地说,娶寡妇要比娶未婚女子的花费少得多,而收继自己的寡嫂,又比娶别人家的寡妇更便宜,寡妇如果有子,此举还不致使母子分离,所以,一个男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就是穷得实在娶不起妻子的情况下,也会选择这种婚姻形式。”[6](P39)
其二是买卖婚。买卖婚是以女子换回钱财的婚姻。这种婚姻缔结方式不仅在清代存在着,而且较之以往朝代更为普遍,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为流行。具体来说有两种情况,既有女方父母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和女儿的感受用女儿来换取聘金,又有丈夫将妾甚至妻子转嫁,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当时就有官员指出:“养女之家,或衣食不足,贪得身价以幸一时之饱暖,每以及笄之女,卖与行路之人,……亦有孀妇改适,稍棍止求媒金之厚实,不问买娶为何人,甚至有夫之妇,忽尔生离。……更有绅士大户蓄婢居奇,原非自己所生,不关离别之惨,往往高价远售。”[5](P178)甚至有的家庭或者家族由于“只图多得财礼,而不顾名节”而逼寡妇改嫁,有的丈夫为了养活自己的长辈和儿子不惜将心爱的妻子典租他人。由此可见,买卖婚尽管有出于无奈与唯利是图之别,但就出嫁者而言,其指向都在获利。
其三是劳役婚。劳役婚是男方以其为女方家庭进行无偿劳作代替聘金的婚姻。它虽然表现为男方劳动和生活于女方家庭之中,但却与入赘婚存在明显的区别。入赘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招赘方在其无子或者丧子的前提下,为了延续香火而为女儿招夫;二是招赘方为不愿离开夫家的寡媳或者为照顾患病的丈夫的妻子招夫,前者可以称为“坐产招夫”,后者可以称为“招夫养夫”,其目的在于维持招赘方家庭的存在和延续香火。而劳役婚的目的则不在于此,其目的在于达成婚姻,娶回妻子。在清代,由于男方家庭贫穷,无法给付女方聘金,双方就会在婚书中或者口头上约定好娶妻男子何时去女方家中服劳役、服多长时间的劳役。一般说来,男子服劳役是在婚后进行的,他在其妻子家中的地位较低,不能随意离开妻子的家庭,只有在服完了劳役之后方可携妻子儿女归宗。
其四是兄弟合娶。在清代,这种婚姻现象虽然不如收继婚、买卖婚和劳役婚的比例那么高,但它却同样在全国各地存在着,在贫穷的边远地区更为普遍。人们并不认为它违反人伦,相反,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认可这样的婚姻。造成兄弟共娶一个妻子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贫穷,男方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给予女方聘金,就可能会有此无奈之举;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当地男女比例失调。如“甘肃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妇,比比皆是。同姓者,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不计也。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轮夕而宿。或在白昼,辄悬一裙于房门,即知回避。生子,则长者与兄,以次及诸弟。”[2]
其五是童养媳婚。童养媳婚是某家庭将所领养的年轻女孩与其年幼之子结婚的婚姻。这种婚姻在以往朝代就有存在,至清代则相当普遍。清代童养媳婚的普遍化主要是清代婚姻重财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必然结果。这种婚姻缔结方式是男女方家庭都乐意的。就女方家庭而言,它可以节省养育女儿的开支和置办嫁妆的大笔经费;就男方家庭而言,它不只是减少了娶媳妇的开支,更主要的是让未来的媳妇提前承担家庭的重担。对于这种婚姻对双方家庭的好处,《清稗类钞·婚姻类》是分析得较为全面的,它指出:“燕、赵之间,居民家道之小康者,生子三五龄辄为娶及笄之女。家贫子多者辄利其聘赀,从俗遣嫁焉。女至男家,先以父母礼见翁姑,以弟呼其婿,一切井臼、烹调、缝纫之事悉肩任之。夜则抚婿而眠,昼则为之著衣,为之饲食,如保姆然。子长成,乃合卺。其翁姑意谓雇人须工赀,又不能终年无归家之日,惟聘得贫家女,则所费不多,而指挥工作可以如意。故但计撙节,而子女年龄之相当与否,均置不问。”[2]
其六是抢婚。抢婚又称“劫婚”,它早就存在。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整个婚姻过程的一个环节,如有的少数民族的抢亲就是这样的婚姻行为,它只是一个仪式;另一种指的是男方用暴力手段强娶女子的行为。如果说前者是符合婚姻礼俗的话,那么,后者却是违背礼俗的。这里所说的“抢婚”是后者意义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抢婚有真实的抢婚与虚假的抢婚之分。真实的抢婚是男方在未经女方同意的情况下的强娶,虚假的抢婚则是男女双方为了顾全面子而心照不宣地进行的表面上强娶的行为,前者在寡妇的再嫁中较为多见,后者则往往在女子初婚时出现。不过,无论是何种抢婚,都与清代婚嫁重财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减少男女双方在婚嫁方面的经费开支,也顾全自己的面子,女方就会暗示男方采取抢婚的形式。如张阿福娶妻就采取了劫婚的形式,他是“绍兴人,寓于杭,自幼聘王氏女为妻,年三十矣,贫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屡托媒媪趣阿福婚。媪曰:‘彼贫,奈何?’母曰:‘彼无婚费,我亦无嫁资。无已,其抢亲乎?’媪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于某月日纠众劫女去,母故招集比邻至,张氏夺女,则合卺已毕,贺客盈门矣。媒媪劝曰:‘事已至此,复何言!当令其明日来谢罪也。’母若为悻悻者而归。”[2]
清代这种日趋严重的嫁娶重财之风,对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使有的家庭“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产”③,而且导致有的丈夫因无嫁妆而轻视其妻子,妻子因无聘金而瞧不起其丈夫,以致“妇姑失欢,夫妇反目”,家庭不谐。尽管清代人认识到了婚姻重财的危害,谴责婚姻中的重利忘义,号召人们抵制嫁娶论财之风,提倡合理的婚姻缔结方式,然而,他们却难以扭转这种不良风气。
三、婚姻解除中的道德生活
尽管清代夫妻感情普遍不深,婚姻质量大都不高,然而,其离婚率却较低,家庭结构较稳定。需要说明的是,离婚与婚姻解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婚姻解除有自然解除④与人为解除两种,前者指的是婚姻关系因夫妻中的一方死亡而自动终止,后者指的是婚姻关系因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有意解除。在此,我们只就婚姻关系的人为解除即离婚来论述清代的婚姻道德生活,并主要从离婚的理由来透视这种生活。
清代人和清朝政府基本上认同以往社会所规定的离婚理由,即“七出”与“三不去”。“七出”又称“七去”,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与“盗窃”,只要自己的妻子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丈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弃她。尽管这七个理由是出于礼制的规定,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但是,它们却过分地肯定了丈夫休掉其妻子的权利,使离弃妻子的行为具有相当强的随意性。因此,“七出”本身具有明显的道德缺陷。为了克服这种道德缺陷,限制丈夫对其妻子的随意离弃,以往朝代的人们又规定了“三不去”,如《孔子家语》对妻子不应该被离弃的“三不去”作了明确规定:“有所取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和“先贫贱而后富贵”,即在离婚后无家可归、曾经为姑舅服三年之丧和被娶时夫家贫贱后来富贵中,妻子只要具备一个条件,其丈夫就没有理由休弃自己。尽管清朝法律也将“七出”与“三不去”作为准许离婚与不准离婚的具体规定,然而,清代人离婚的理由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如因家庭贫穷、夫妻不和、丈夫久出未归且音讯全无、妻子有生理缺陷、发现婆婆与人私通等都是夫妻离婚的理由。我们通过这些离婚理由就可以了解清代人是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对待其妻子的。
虽然清代人离婚有多种多样的理由,但是,它们却存在着主要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分。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那些对清代离婚率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可权变的或者不可原谅的理由,次要理由则是可以权变的、可以原谅的、对离婚率的提高没有多大影响的理由。从清代的实际道德生活来看,无子、忌妒、有恶疾、多言(挑拨离间、拨弄是非)、盗窃、夫妻不和、丈夫久出未归且音讯全无、发现婆婆与人私通等都是夫妻离婚的次要理由。如妻子的盗窃实际上是很少可能发生的,因为妻子一般是不允许与外人交往的,这实际上几乎排除了妻子外盗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只有盗窃家庭财物的可能。然而,在父家长拥有支配家庭一切的权力、兄弟同居共财、不允许儿子“私有财”的家庭环境中,妻子内盗的可能性也不大。由此可以推知,妻子盗窃不是清代夫妻离婚的主要原因。妻子的忌妒、有恶疾、多言(挑拨离间、拨弄是非)、夫妻不和等虽然可能会损害到他人的利益或者伤害他人的人格,造成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紧张,影响家庭和谐,但不至于成为影响清代离婚率的重要因素。至于“无子”,有人认为它是清代夫妻离婚的主要理由,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观念环境中似乎是必然的,毕竟妻子没有生出儿子,没有体现古代中国人赋予婚姻“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本质特征。不过,在我们看来,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性人口尤其是适婚女性过少的清代,男子娶到适龄的妻子实属不易,不会因为其妻子生不出儿子而轻易离弃,何况还可以通过过继、领养和纳妾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憾,不至于因妻子无子就断然离婚。当然,在“无子”的情况下,夫妻关系可能会受其影响,妻子的地位可能会遭到威胁,因为在“母以子为贵”的世俗观念环境中,妻子无嫡子,其地位就会或明或暗地有所下降。然而,妻子不得不作出某种让步。由于这种让步也许是妻子出于自责的结果,因而,妻子会为了延续夫家的香火而积极地操办过继、领养等事项,甚至会主动地为丈夫纳妾。《聊斋志异》通过《段氏》篇再现了清代婚姻生活中妻子为丈夫主动纳妾的真实画面。“四十无子”的富翁段瑞环因惧于悍妒之妻连氏而不敢公然纳妾,只好背着她与一婢女私通。后来由于连氏感觉到了有子嗣的重要性,因此,在弥留之际,她“呼女及孙媳嘱曰:‘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夫纳妾。无子之情状,实难堪也!’”妻子为丈夫纳妾大开绿灯,“既避免了丈夫借口无子可能被休弃的危险,同时还能得到丈夫、家人和社会的赞赏,称之为贤惠懂事。”[7](P480)这就更有利于降低清代的离婚率。
导致清代夫妻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不顾父母”、“淫”和贫穷。“不顺父母”是这三者中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它既有可以被客观地度量的性质,如有妻子不服从公婆、顶撞公婆、侍奉公婆不周到等明摆着的事实,又有某种主观的臆测和评价,如公婆对儿媳妇看不顺眼,丈夫认为其妻子侍奉父母不尽心,这从安子的母亲如何对待她的两个儿媳妇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安子“尝寓杭州吉羊巷,事母事兄,无间言。兄早娶,乃以童养媳完姻者,母待之甚薄,日夕自操作,稍不遂意,即以鞭扑从事。迨安子娶妇,妇之母家颇小康,时有馈遗,母心艳次妇之富,时承奉之,而待长妇则如奴仆。安子谂知之,婉谏其母,更慰兄嫂,……安子乃请母弗偏护,母颔之。”[10]但其母亲却一如既往地瞧不起大儿媳妇。正是因为“不顺父母”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就成为了清代人离婚的变数最大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离婚的最主要因素。而贫穷则不同,它是导致清代夫妻离婚的无可奈何的主要因素。在生命与婚姻只能二者择一的时候,夫妻为了各自活命而不得不分手。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丈夫主动卖掉妻子以图活命,如“张克礼因岁饥乏食,携妻挈女,行乞于外,至洪洞地方,欲卖妻女得价,则彼此皆可存活。适有屯民王奇山者,往寻族人催粮,在彼撞遇,自念其妻任氏患疮伤目,不能照管家务,遂听马姓等人说合交价,买回田氏母女二口。……为克礼者,既经立约受价,则夫妇之情已绝,即应视同覆水矣。无何得银易米,旋即复出至奇山家,借买妻作妾为题,硬欲逼领妻女。”[5](P184)另一种情形是妻子出于对家庭的责任而自愿卖身的,如“历城西门外有柴氏妇,其夫贾也,频岁折阅,资尽不能养母,妇诘夫曰:‘母与妻孰重?’夫曰:‘母重。’‘事夫与事姑孰重?’夫曰:‘事姑重。’妇曰:‘然则鬻妇以养姑乎?’夫泣,妇亦泣,邻人乃醵金遗之,妇卒不鬻。”[10]
相对而言,“淫”是清代人离婚的最不可容忍的主要理由。这里所说的“淫”并非是指丈夫的“淫”,丈夫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妻子以外的其他女人发生性行为,可以嫖妓、纳妾、蓄婢,妻子不能因此而提出与丈夫离婚;它特指妻子的“淫”,具体指女人在初婚前与人私通和婚内与人通奸两种情形。这实际上是对女性的贞节方面的要求。在清代,妻子失贞是不可原谅的,因而被离弃就是天经地义的。有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就会在贞节问题上大做文章,逼其妻子就范。如“永平府某县之闺范至严,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人侦之。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宾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阗然,则女之留否,惟夫家为政,不敢与争矣。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情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之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2]假如洞房之夜夫妻“合欢”了,而丈夫又横加诬陷,妻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此可以想象妻子的贞操在清代夫妻关系处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从清代夫妻离婚的各种理由可以看出,离婚的权力并非仅仅掌握在丈夫的手里,而是由夫妻双方、双方父母、家族乃至清朝政府来共同掌握的。除清朝政府明确规定离婚的条件并依据相关法律条文来作出是否离异的判决,以维护离婚双方的公平之外,大量的离婚都是在民间力量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意味着,清代人的离婚是一个严肃的、符合清代正义观的社会事件,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有关风俗、教化的问题。
此外,清代人离婚还是一个涉及利益的问题,准确地说,它涉及到离婚过程中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在离婚过程中,财产的处理不是一个家庭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谁应该成为赔偿者和应该赔偿多少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到清朝法律又涉及到清代的风俗习惯。就风俗习惯而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方是羞于也不敢主张其财产权利的,甚至是否应该得到聘礼或者嫁妆,都由无责任方说了算。为了更有效地处理离婚双方的财产问题,清朝法律作了明确规定,如结婚“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1](P453)这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丈夫是造成离婚的责任者,因而,妻子即使主动提出离异也有权不返还丈夫的聘礼。在其他情况下,妻子都无权得到丈夫家的财产及原有的嫁妆。在蒙古婚姻中,如果“新妇三年内生子,应得外家财产一半,如三年不育,勒令大归,并追还原聘,听其择人再醮”[2],如果妻子三年内生不出小孩,就要被离弃,并要返还丈夫家的聘礼。在藏人离婚过程中,如果男子没有罪过,愿意与其妻子白头偕老,而妻子却坚决要求离婚,那么,妻子就应该按其丈夫迎娶时所出聘金加二倍赔偿;如果妻子没有罪过,且愿意与其夫共度终生,但丈夫却坚决要求离婚,那么,丈夫就应该付给其妻子十二金屑(合九十卢比),并要“按其妻由成婚日以至离婚日,每日夜各用麦六磅计算,其夫又当归尝其妇以奁具之值”;如果丈夫是富人,那么,裁判官可令其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给予妻子,以为她衣食之用;如果妻子是富人,也应当拿出部分财产给丈夫;如果是身为贵族之丈夫与平民妻子离婚,那么,其财产可按二人之“真情与罪状,并其匹配时彼此互赠礼物之数而分享之”,如果是他们都愿意离婚,那么,裁判官就可以不问二人应该各负多少责任而“为之均分其财产”[2]。
注释:
①这种平等并非指人人平等,而是在等级制度下的平等,即同一等级下的人平等。
②如《清稗类钞·婚姻类》中载有如下一桩婚姻:“康熙时,总兵王辅臣叛,所过掳掠,得妇女,不问老少妍媸,悉贮之布囊,四金一人,任人收买。三原民米某年二十未娶,独以银五两诣营,以一两赂主者,冀获佳丽。主者导入营,令自择,米逐囊揣摩,检得腰细足纤者一囊,负之以行。至逆旅启视,则苍然一老妪也,满面瘢痕,年近七旬。”这样的婚姻缔结是无需烦琐的过程的。
③(康熙)《上虞县志》卷2。
④由于婚姻自然解除后,妻子一般都在夫家中生活,因此,这种婚姻道德生活就会不同于离婚道德生活,不会面临着夫妻在离婚中如何相互对待的问题,并被完全转换成了家庭道德生活,如“太原有民家,姑妇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洁,村无赖频就之。妇不善其行,阴于门户墙垣阻拒之。姑惭,假事以出妇,妇不去,颇勃谿,姑益恚,乃诬控之官。官问奸夫姓名,姑曰:‘夜来宵去,实不知为谁,鞫妇自知。’因唤妇,妇果知之,而以奸情归姑,苦相抵。”(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狱讼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收稿日期]2010-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