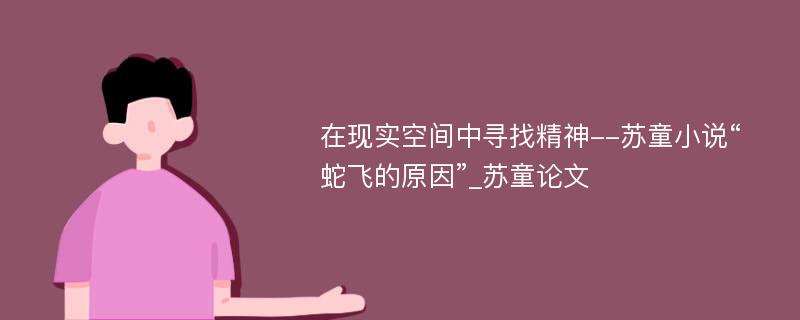
在现实的空间寻求精神的灵动——读苏童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灵动论文,会飞论文,现实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一
我始终认为,苏童不是一位具有写实主义文体风格的作家,而是依靠想象进行创作的 小说家。他喜欢在想象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苏童的想象常常超越现实 的层面,是创造性的,心灵化的,是想象和激情,心灵和诗性激发着他的创造欲望和写 作冲动。所以,若干年前,基于苏童在其创作中充分表现出的对艺术美执着追求的精神 内质,我将苏童称为当代为数廖廖的唯美主义作家,虽然,当我与他面对面提及并加以 论证时他未置可否。我坚持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他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在创作 中大致有两种偏重:一种是偏重于存在经验,一种则是重视艺术想象。对于前者,艺术 创造的要求是,如果没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去带动他的经验,那么,那种经验对他来说就 是死的,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最多只能是生活的本真意义,但这种生活的经验又有 什么意义呢?对于后者,就如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所说,写作就是“幻想、自传、 讽刺、忧伤”,这一点也暗合黑格尔关于想象的观点:“艺术创造最杰出的本领就是想 象,想象是创造性的。”[1](P.352)无疑,苏童更属于后者。可以说,只有想象性经验 才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一种表征。
从小说的美学风格和题材上看,十几年来,苏童擅写拟旧风格的小说,选材多取自历 史或三四十年代及六七十年代,其颓靡感伤的风格,或精致华丽,或耽美幽香。尤其对 历史的凝视、抒写,别有一番奇异风致。这似乎已深入到苏童小说叙事美学的精髓。也 就是说,他的写作风格在不断的变化与发展中趋向稳定、和谐。
近期,苏童在相对沉寂了大约五年之后,带着他的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进入我 们的阅读视野,并痛下决心、语出惊人地宣称:“我确实在破坏我自己,破坏某种我赖 以生存的、用惯了的武器,比如语言、节奏、风格等等。我不再满足于我自己,我想改 变,想割断与自己过去的联系。把以前‘商标化’了的苏童全部打碎,然后脚踏实地, 直面惨淡人生。”[2]我们从苏童诚挚的话语中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作家渴望出新求变、 为读者奉献精品佳构的写作欲望。一个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总处于摆脱困境的焦虑之 中,同时也被真正的读者所期待着。在当代,苏童和余华都是那种让读者期待的作家。 他们作为优秀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早已不可动摇。但在近五六年来,除了苏童每年 的三五个短篇小说外,他们两人都未写出长篇,对于此,人们可以有多种解释或猜测, 但我更同意谢有顺的解释:“写作的难度,正越来越深刻地折磨着那些有责任感、有艺 术追求并渴望探查人类精神真相的作家们。”[3]我相信,苏童和余华一样,都是那种 拒绝一成不变的作家,他们都在寻求打碎或跳跃出自己以及别人为他们的写作设定的窠 臼,因为他们清楚,时代在变,作家自身和读者在变,作家的写作怎么可能不朝三暮四 呢?他们都认为,文学在我们时代,一个作家凭自己对小说技术的娴熟把握,写出几个 高水准的短篇尚且容易做到,但真正能表现实力、有持久艺术魅力的长篇佳构必定是心 血之作,而这一点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则是艰难的。
我们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家及其作品?读者审美层次的分化必然产生迥异的审 美需求,那么作家在面对这样的接受场或审美格局,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我们恐惧和忧 虑的是,阅读和写作的同时沉沦。也就是说,写作应怎样地拯救当代人的阅读呢?或者 说写作需要怎样挑战阅读?
我们以苏童这部最新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为例,审视苏童小说创作所发生的变 化和新的艺术追求。苏童在新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他对文学有怎么新的理 解和感悟?以及这部小说之于他自身的写作意义。
二
台湾学者王德威评价苏童的创作时称其是“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4]苏童在80年 AI写作作《妻妾成群》和《红粉》时凭借他天才的想象力、语言感觉和讲故事的能力,征 服了不同年龄层次和性别的读者,对于这部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苏童又执着地 直面现实,贴住生活本体,在小说题材上大胆求变,对当下现实进行“零距离”表达。 选择现实题材的写作,这对于习惯了写历史、习惯了将思绪沉浸在历史时空中进行想象 性创作的苏童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小说讲述的是生活在世纪之交的若干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理想、 精神现实、命运和人生遭际。这是一个社会的边缘性群落,他(她)们是社会生活中无法 忽略的存在,商业时代的急遽发展变化中,他们的选择、谋生、浮躁、无奈和沉沦,一 句话,他们是当代社会生活现实中“失重”的弱势群落,作家要表现出他们的生死与悲 欢离合。
苏童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的双重视角讲述这一群人的人生故事,叙述中尽量 地保持着不露作者声色的“客观”和从容不迫。
小说中着力描写的人物有七个:克渊、德群、梁坚、疯大林四个男性和冷燕、修红、 金发女孩三个女性。从实质上讲,这些人物都是极其普通的,在生活中时可常见的人物 ,他们的活动空间也不算大。惯常的又各异的人生轨迹呈示着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的 选择,包括为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变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无论人物大小,渴 望得到尊重并生发出做人的尊严,具有自己较为完整的生存、精神出路,是苏童笔下人 物的精神内核。苏童通过娓娓道来的叙述和描绘,伸展到人物的人性空间。惊悚、凄凉 、残烈、感伤的叙述意绪不仅使我们获得小说阅读感性层面的魅力,而且,作品中还透 射出人物真正的生存状态,和凝聚在他们身上深厚的文化积演和历史积淀。这些充分反 映出生命的个体生发、个体张扬、再回归个性、个体,由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逝而衍生 出的人作为“类”的不定性和扩张性特征。
克渊是贯穿全篇的人物。苏童把他写成一个处于沉沦状态的边缘性人物。作家在刻画 他的时候,有意避免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化符号性。但我们还是在这个形象身上体验到过 去生活和历史风雨对他敲击,看到了时间洗涤过的深深印记。克渊和当年“香椿树街” “城北地带”那些少年一样,骨子里积淀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情感方式和品质向度。 从他身上我们甚至能依稀看见《城北地带》中的红旗、《刺青时代》中的天平的影子。 他们之间有着某种近似的血缘、地缘关系,尽管他们从六七十年代的“刺青时代”走进 世纪之交的当代岁月,但生存状态的摇晃无定、在时代主流生活之外的边缘地带游戈、 挣扎,所带给他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沉沦,这也让我们感到这个人物轻薄、顽疾人格 中的几许凝重。作为一个所谓靠吃“社会饭”混迹的讨债公司的雇员,他在精神层面处 于社会的最底层。倚仗和凭借他的“工具性”价值,除获得了他基本的生存保障外,克 渊自我感觉在世俗社会中还颇混出了许多风光。实际上,克渊也是很难把握自己命运的 。千禧年41岁的宋克渊应该是出生在50年代末,在“文革”中长大,童年记忆中充满了 暴力、“革命”和关于历史的朦胧感受。80年代以后又没能赶上时代给他们的“末班车 ”。他最初的“社会生活”只是街头巷尾的少年斗欧和无所事事。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 代生活的急遽变化也并未给克渊这样的人什么机会,对于他,也很难有可以振作起来的 向上的台阶,他也还只能继续生活在社会的缝隙中。德群“发现”了社会与法的所谓“ 真空地带”,开办讨债公司以获得高额暴利。克渊的无根性、依附性、无赖性和凶狠必 然成为德群的首选,所以,克渊被德群封为吃社会饭的“教授”。这种职业注定克渊是 要被毁灭的,尽管他不无些许侠气和善良的天性。因为他骨子里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克渊之于梁坚、疯大林,似乎更“滑腻”些,能够随遇而安,这一点还确有蛇的某种品 性。苏童将其放在一个纷扰多变、浮气上升、良莠杂陈的特定生活情境中,使他体验着 一种命运,而且是一种悲剧式的命运。从整个人类、人性的意义上讲,人是不希望自己 被毁灭掉的,但作为个体的人,克渊最终还是要被毁灭的。这部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梁 坚和疯大林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强烈的方式演绎着另一种现实悲剧。梁坚的“世纪 之跳”让他彻底摆脱了人生的债务绞索,这并不仅是德群、克渊和那些债主所逼,更多 的是一种自我了断和“现实”选择。他认清了自己的生命在现实社会的价值,他已经对 自己的存在做了评估。我们从克渊和梁坚这两人的比较中会发现,他们面对现实,最后 选择的都是及时逃离现场。“逃”的主题意象在苏童小说中曾无数次呈现。《一九三四 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逃》、《狂奔》、《乘滑轮车远去》向我们 呈示了各式“逃”的意象,而长篇小说《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以形而下的方式展示 了形而上的“人生逃亡”,以及极富象征意蕴的某种人生“仪式的完成”。《米》中的 五龙和《我的帝王生涯》中的“走索王”的整个人生历程就是不间断的逃离过程。与这 部《蛇为什么会飞》比较,前者重视的是主人公人生逃离的过程,而后者偏重逃的最后 “疯狂”的结局。梁坚和疯大林显现为更为偏执的精神病态,他们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的 无所适从,而克渊再次表现出在现实面前“屈就”“滑行”的蛇性,乘火车逃离这座城 市。但他精神的卑微与无着注定他永远无法飞翔起来。克渊与梁坚还有一点共同之处, 那就是不同程度的性无能。克渊完全可以看成是《妻妾成群》中陈佐千的后代,与陈的 儿子不同的是,苏童通过后者表现一个家族的颓败,克渊则是智性和灵魂的双重缺失。 不可忽视的还有,小说中的三个女性更是在选择对于职业的“出逃”。
超越现实就是超越痛苦,克渊、梁坚、疯大林都无法超越痛苦,也就无力超越现实, 他们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灵魂的苦痛。可以看出,苏童小说中男性叙事的姿态至今没有 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人物在不同的叙述背景和氛围里有着不同的虚拟。苏童创作的许 多理念或理性仍在小说中被感性化,这也许会为小说带来某种艺术穿透力?多年来,苏 童的写作始终倾向于扑捉人物的人生瞬间或片断,展示人生与世界的凄凉或绚丽多姿, 但与众不同的是,苏童并不探究生存世相和人物选择的哲学深度,即使面对死亡,世界 的种种悲剧,小说的叙述也是呈现平面的状态,或是由意象轻轻覆盖,只涌出若干感性 的游丝。
我觉得,在小说界有“红粉杀手”之称的苏童,在这部小说中对几位女性的叙写和想 象比写作《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时期却有某种程度上的退步。也许是太贴 近现实,苏童创作的想象性天才难以更好地伸展。而对阅读来讲,由于当代现实与人物 在小说中的即时性呈现,审美的近距离造成文本阅读“陌生化”的缺乏,使苏童小说创 作的优势——充满神秘学色彩的暖昧叙事态度,即“中立性审美观照状态”[5](P.179) 大大削弱。人物也就丧失了艺术存在的史学精神基础。也就是说,苏童抛弃了他极为擅 长的“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6](P.129)的套路, 将几位下层女性置于单纯的与命运、宿命抗争的语境中。金发女孩、冷燕和修红虽与男 性都有相互依存或相互冲突的情形,小说也尽力凸现三位女性的欲望与渴求,但她们作 为生命个体,其人生的有限性、悲剧性、神秘性,以及她们在男性世界种种遭遇和压抑 ,并未被清晰、完整、符合逻辑地表现出来,她们内在生命的冲动形式,并未超出生命 负载程度的欲望的消长,向命运的挑战与挣扎都显得松懈无力。冷燕和修红从60年代走 过来,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还局限在“旧日”的时空。冷燕似乎在对现实选择时 更果决,还有那种红尘看破、识时务者的强力姿态。修红则完全“不合时宜”了。她的 没有选择就是她的选择。对这两个女性,也许苏童有意想写出她们在世纪末面临生存危 机、沉沦的命运走向。
有趣的是,生于新时代的“金发女孩”,应该在属于她的时代找到感觉和自信,并奋 斗出一个好的归宿,可她的结局却更为惨淡。人为垫起的高鼻梁的塌陷在深深预示着她 命运的多舛和不幸。无论你是否“生逢其时”,选择的失重和错位,必然会让你吞下难 咽的苦果。我觉得,金发女孩这个人物的命运同样给人一种悲剧感和内心震撼。我们也 从叙述中感觉到,苏童格外重视和喜爱他笔下的这类人物形象。
三
我在苏童大量小说的阅读中感觉到,他的小说从诗学的意义上讲,有这样几个方面的 特征:一是象征、意象、隐喻;二是浪漫、伤感和悲剧性;三是叙述风格上的迷离、传 奇、拟旧。正是这些美学功能确立了苏童小说整体上的审美风格。
意象在苏童许多小说中大量存在而且提升着他小说表现的力度。这篇小说中除了我前 面提到的“逃”的意象外,蛇是作者刻意营造的贯注整个叙述文本的主体意象。前面曾 提及苏童是更倚重想象进行写作的作家,而意象则是他艺术想象的重要载体,那么,意 象也就在苏童小说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作品的审美价值。一群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的所谓“基因蛇”弥漫在城市的诸多个角落,而“美丽城”蛇餐馆的经营与红火似在拉 近人与蛇的关联,特别是冷燕在餐馆中所找到的“蛇小姐”角色,也意在表现人性的某 种衍变。克渊在飞驰的列车上看到的蛇,成为一个悬念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可能会引 发更多的想象空间,仅从人蛇联系的相互表层接触中,还难以感受到两者的某种关联或 隐喻关系,关键在于人性的内涵和张力是否在蛇背景中有什么凸现,而非两者之间简单 的罗列和比附。苏童试图通过蛇光滑的形状象征整个社会的难以把握,象征人性的冷漠 ,这一点给人的感觉多少有些勉强。小说描写蛇餐馆中女人与蛇共舞,冷燕对蛇和生存 环境的双重征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性的变异。苏童喜欢在小说中讲究一种紧张与 舒缓结合的节奏,蛇意象在小说叙述中的游移灵动,也可以说起到了控制叙述节奏的技 术作用。但人性与蛇、人与蛇存在的隐喻关系,并未达到作家期待的那种寓言效果。
世纪钟的象征意蕴较为明显,它可以隔离或分割一个世纪或若干年代,为不同时代的 人标识、警示人与现实的依存关系。时间的错位会使人的存在更荒诞和滑稽。这个世纪 钟无法准确地表达时间的运行而不断出现误差,正如小说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迷 惑和茫然。
对这部苏童寄予深深期待的小说,我认为在语言、节奏、风格乃至人物形象的美感特 征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苏童极力想摆脱的那些内在品质仍顽强地存在于小说的体内 。与以往小说有较大区别的只有几点可以肯定,一是题材选择的现实性、当下性;二是 小说结构方式呈现为放射交叉式结构。三是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对叙事视角的选择没有 象以往作品那样,注重像韦恩·布斯所说的“审美距离”的变化[7](P.179),即“间离 ”效果,也就是作家、叙述人、小说中人物以及读者相互间保持着一种或道德、或智力 、或时间、或情感价值上的审美距离,而是在叙述中透射出难以控制的“情绪化”叙述 。这一点与小说表现内容题材的当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小说语言风格和叙事气韵格调上,我们所感受的依然是地道的“苏童式话语”,只 是语言的音乐性、新奇而含混的隐喻、暗示性略有消弥。小说在行文中仍取消了人物对 话时标点符号的使用,人物语言与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造成阅读感官体味上的流 畅。因此,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言仍然充满“现代文人话语”意味。这方面还是应了余华 那句“能贯穿作家一生写作的只能是语言方式和叙述的风格”。令我们欣慰的是,苏童 在经历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大红大紫”、90年代末的“沉寂与落寞”之后,依 旧保持着叙述的持久和耐心,因为这是一个作家探索新的写作可能性的前提。
中国当代作家真正意识到读者的价值、重视自己的写作与读者的内在关系是80年代末 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天的文化消费时代,作家虽然已不似80年代初那样,可以引 领、营造文学潮流、阅读方向,但面对层次不断分化、分解的不同读者群落,亦不必采 取被动的、媚俗的方式单纯地去适应某种社会大众的需要,而要主动地、清醒地在文化 消费过程中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精神价值系统,继续探索文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发展 途径。写作的困惑与焦虑从另一方面说明写作的神圣性,调整和反思是摆脱重复的一次 脱胎换骨,作家最终的使命是在社会生活审美范畴内建构精神界的平衡。苏童的写作肯 定是执着而独特的写作,其别致的艺术风格是当代小说创作中一道迷人风景,我们需要 提醒苏童的是,不必过于介意“苏童时代”是否会回来,真正的文学经典创造绝不仅仅 是大众追捧或部分读者的一时感奋,时间才是文学的炼金术,我们永远期待那个从容、 自信、潇洒写作的小说家苏童。
收稿日期:200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