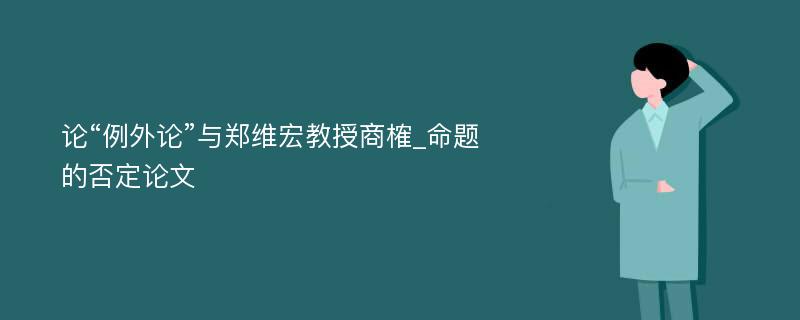
论“除外说”——与郑伟宏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郑伟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因明中有列举同品时须在宗有法外觅取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除宗有法”。但有学者将“在宗有法之外”解释成了“除去有法”“剔除有法”,并认为异品亦须“除宗有法”。现在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同、异喻体亦须“除宗有法”,并由此引出同、异喻体除去宗有法,即为“除外命题”,故陈那的因明不可能具有演绎性质的结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复旦大学郑伟宏教授为代表,他的所有因明著述都贯穿了“除外说”。对这种“除外说”,笔者不敢苟同,故略陈愚见以为商榷。 一、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吗? 所谓“除宗有法”,是指在以因(理由)证宗(论题)的过程中,需要在宗上的有法(主词)之外,另外举出一个事例(同类例,即同喻依)来检证因法与宗法(宗的谓词)之间是否具有不相离的关系,即因法是否真包含于宗法的外延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同品须除宗有法,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即譬喻总是以乙喻甲,而不会以甲喻甲的。如陈那《因明正理门论》云: 又比量中唯见此理:若所比处此相审定,于余同类念此定有,于彼无处念此遍无,是故,由此生决定解。(《大正藏》第32卷,第3页) 这里特地指出,因法须“于余同类念此定有”,即是指因法须有于宗有法之外的同类事物。但是陈那只说同品要除宗有法,不说异品也要除宗有法,因为异品本与宗有法不属一类,并不存在除宗的问题,所以陈那只强调因于异品必须遍无,而不说除宗;如果宗有法在外延上与异品有联系而亦须除去的话,陈那又怎么会不作交代? 但是郑教授是主张同、异品皆要除宗有法的。他完全赞同为陈大齐所发挥的关于异品亦要除宗的论述。他说:“宗异品中亦须除宗有法。因为在举因证宗的时候,宗中有法不过是他异品,并不是共异品,故不能为共比量的宗异品。如立声是无常宗,在敌未了悟此一正理以前,声音亦只是自同他异品。此一他异品若不剔除,则任何正因都将失其为正因。因之遍是宗法,是立敌共许的。宗中有法若列入宗异品之中,便至少有一小部分的宗异品为能立法所依转而不是异品遍无了。如立‘声是无常’宗,以‘所作性故’为因,声音之无一不具有所作性,是立敌共许的。今若以声音列入宗异品之中,则至少此一部分的宗异品是所作的,于是所作的不一定是无常,而所作性便无力证明无常性了。故宗异品若不除宗有法,将使敌者获得一种便利,只要取宗有法为例,即足以使立者的证明归于无效。不过如此返破,亦是一种循环论证。宗同品中既除宗有法以避免循环论证的弊病,宗异品中自亦应当同样剔除,以期论辩精确而公允。”(郑伟宏,2012年,第27页) 然而为郑教授所完全赞同的陈那的这段论述却颇有问题。 第一,陈那:“宗中有法不过是他异品”,“如立‘声是无常宗,在敌未了悟此一正理以前,声音亦只是自同他异品。”此言差矣,他似乎忽略了立宗须“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商羯罗主,第11页)的古训,即组成宗体的两个宗依(有法、能别)必须极成。有法“声”和能别“无常”本为立敌所共许,何来“自同他异品”之说?宗义须“违他顺自”并不影响宗依之共许极成,如果由宗义的“违他顺自”而将宗依指为“自同他异品”,岂不是一切比量皆成自比量或他比量,共比量将不复存在? 第二,陈那由此而主张“宗异品中亦须除宗有法”,因为声音既“列入宗异品之中,则至少此一部分的宗异品是所作的,于是所作的不一定是无常,而所作性便无力证明无常性了”。此说似乎陷入二难的境地:“声音”既然已列入宗异品之中,怎么还能包含于“所作”因?若说声音依然包含于“所作因”,那么将声音作为“宗异品”剔除出去以后,所作因将依何而立,岂不有所依不成之因过? 第三,陈那的“宗异品若不除宗有法,将使敌者获得一种便利,只要取宗有法为例,即足以使立者的证明归于无效”,也是甚玄之论。且不说异品无需除宗有法,即使是同品须除,亦只是举喻证宗时在同喻依上暂除宗有法,宗与因都不存在“除宗有法”的问题。从足目的《正理经》到陈那的《正理门论》《集量论》,都未见有因法也须“除宗有法”的论述(陈那所云因之第二相“于余同类念此定有”,指的就是同喻依要除宗有法。九句因中所说的同品、异品,实为同、异喻依)。所以说,不除便会给敌者以可乘之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在论辩实践中也不会有此实例。 第四,说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不免陷入逻辑矛盾:假设“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这一命题为真,则意味着宗有法既是同品又是异品。然而同一对象绝不可能兼有两种截然相反、互不相容的性质,故知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的命题为假。对于上述逻辑矛盾,我们可以运用归谬律的公式来刻画它:(p→(q∧﹁﹂﹁q))→﹁p。从这一公式可以看到,p(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蕴涵着矛盾式q∧﹁q(宗有法既是同品又是异品),而矛盾式是恒假的,一个充分条件的蕴涵推理不可能前件真而后件假,所以可以否定其前件p真而得﹁p(同、异品均须除宗有法这一命题为假)。 陈那关于异品除宗的问题如上所析乃有不当,然郑教授不仅全盘予以肯定,而且发挥得更其淋漓尽致,且进一步认为同、异喻体也要除宗有法。 二、喻体也要除宗有法吗? 说喻体也要除宗有法,系郑教授的创说,比陈那的同、异品皆须除宗有法更趋极致。其理由是:“宗有法是因同品,同喻体中的能立因法可不必除宗。由于同喻体中的因法和宗法不相离之义,就是同喻依上积聚的因、宗双同之义,同喻依除宗,同喻体中的因同品也不得不除宗。”(郑伟宏,2010年,第18页) 这一诠释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试想,因法与宗法既然“具有不相离之义”,即说明因法与宗法的外延为包含关系,其同喻体的命题形式为“所有M是P”(MAP);而所举的同喻依亦具有“因、宗双同之义”,从正面检证了因宗之不相离性得以成立,怎么可以又从同喻依之除宗有法返求同喻体也要除宗有法呢?同喻体的主项(M)如果除去有法,其命题形式即成了“有的M是P”(MIP),其主谓项在外延上只是交叉关系,这又如何体现因宗不相离的包含关系呢?更何况因的第一相规定因法须周遍有法,即所作因必须真包含有法声,怎么还能从作为同喻体主项的所作中将声剔除出去? 郑教授说:“喻体要除外,说喻体是除外命题,这隐而未显的道理确实不太好理解。”(郑伟宏,2012年,第24-25页)岂止是“不太好理解”,而是根本无法理解这种“隐而未显的道理”。郑教授说在窥基《大疏》释《入论》“同法者,若于是处显因同品决定有性”一句时,“隐含着同喻体也必须除宗有法的思想”。(郑伟宏,2010年,第18页)遗憾的是,郑教授这只是臆测,而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 其实,喻体是不应该除宗的。窥基《大疏》中有一段喻体要不要除宗的问答: 问:“诸所作者皆是无常”,合宗因不?有云不合,以“声无常”他不许故,但合宗外余有所作及无常。今谓不尔,立喻本欲成宗,合既不合于宗,立喻何关宗事?故云“诸所作者”即合声上所作皆是无常,即以无常合属所作,不欲以瓶所作合声所作,以瓶无常合声无常。若不无常合属所作,如何解同喻云“说因宗所随”?(窥基,第136页) 在这段问答中,问者意谓,有人认为喻体“诸所作者皆是无常”不包含“声无常”宗,因为“声无常”宗为敌者所不许。答者慧沼意谓,此说不能成立,立喻本欲成宗,故云“诸所作者”即包含声上所作皆是无常,而不是仅以瓶之所作来合声之所作,以瓶之无常来合声之无常。正是无常与所作具有包含关系,所以陈那指出同喻有“说因宗所随”的伴随关系。慧沼十分明确地告诉咨疑者,喻体是不该除宗的,但是郑教授认为这是“窥基的弟子慧沼未遵师说,在《续疏》中说喻体不除宗有法,不足为训”。(郑伟宏,2012年,第24-25页)郑教授对慧沼答问的否定显然缺乏具体剖析,没有说服力。他大概没有意识到,在同、异二喻的喻体中均除去宗有法,宗有法将无处存身。设同喻体为A集合,异喻体为非A集合,说宗有法既不属A集的分子,又不属非A集的分子,岂非陷入悖论? 三、九句因能证明喻体要除宗有法吗? 为了否证喻体为普遍命题,郑教授又以九句因中的第五句为据。他说: 要证明陈那三支中的同喻体除宗,这只要找到一个实例证明它不是普遍命题就可以了。例如:声常(宗),所闻性故(因),诸有所闻性者,见彼是常(除声外,缺同喻依)(同喻),诸无常者,是彼无所闻性,如空(异喻)。这是以九句因中第五句因组织的似比量。在上述比量中,不缺同喻体。同喻体“诸有所闻性者,见彼是常”,如果不除宗,则此同喻体等于“声常”,用“声常”证“声常”,犯循环论证错误。如果除宗,则此同喻体的主项是空类。这一同喻体反映的普遍原理便不适合任何对象,形同虚设。陈那规定,“所闻性”因不满足第二相同品定有性。正确的同喻依是满足第二相的标志,缺同喻依便缺第二相。仅此一例,便可知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同喻体也是除宗有法的。(同上,第29页) 郑教授提出来的这个新论据在喻体是普遍命题的问题上并不能起到证伪的作用,因为同喻依须在宗有法外举例正是为了证明有法从属于宗法,更不能将其从喻体中“剔除”。兹以经典的共比量“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诸所作者皆是无常,如瓶”为例来说明,“声是无常”宗乃为立敌所诤,在举譬证宗时自然要在有法声之外的同品中去觅取,瓶就是“声”的同类事物。同品瓶上有所作性和无常性是立敌共许的,声上有所作性也是立敌共许的,由此可推出声亦有无常性。陈那并由声、瓶等都有所作与无常之属性且所作与无常具有包摄关系(不相离性)而扩展到全类:凡所作者皆无常,即声、瓶等一切所作的事物皆从属于无常这个集合,无一例外。如此,怎么可能在“总摄一切”即得出普遍命题以后还要将有法声剔除出去呢?这样浅显的道理是不难弄明白的。 现在再来分析郑教授引以为据的九句因中的第五句。第五句即因于同品非有,于异品非有。因于异品非有不违反第三相异品遍无的规则,因于同品非有则违反第二相同品定有的规则,故有不共不定过。此例是从佛家的立场出发设立的。佛家认为声论所立的“声常,所闻性故”,其因法“所闻性”唯在声上有,除声之外别无他物为耳所闻,所以此因缺同品,违反因的第二相。郑教授抓住所闻因缺同品这一点,认为正是由于除去了有法声才导致缺同品,由此可证同喻体“诸有所闻性者,见彼是常”中的“所闻性”是要除去有法声的。如此,则其喻体不再是普遍命题,而是除外命题,即“(除声之外,)诸有所闻性者,见彼是常”。郑教授还用二难法来加强他的论证:“如果不除宗,则此同喻体等于‘声常’,用‘声常’证‘声常’,犯循环论证错误,如果除宗,则此同喻体的主项是空类,这一同喻体反映的普遍原理不适合任何对象,形同虚设。”(郑伟宏,2012年,第29页)在这里郑教授作了过度发挥,因为在九句因里,陈那只讲因与同、异品的关系,并未涉及到喻体。其所说之二难推理亦都是从剔除有法的角度来说的。第五句因本是似因,用二难法去质诘又有什么必要呢?再说,郑教授补设的同喻体“诸有所闻性者,定见无常”亦并不需要剔除有法声,它的过失只是在举不出同喻依而已。既然喻体不必除去宗上有法,故此例中的喻体主项“所闻性”也不会成为空类。再说在因明中空类概念称为无体,概念的有体、无体是以立敌双方是否共许为划分标准的。“所闻性”既是立敌共许为声上有的,就是共许因,亦即有体因,怎么到了喻体中就变成无体(空类)了呢?如上所析,九句因中的第五句因并不能证明“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同喻体也是除宗有法的”。 不仅如此,郑教授还将除宗问题扩大到了九句因各句。他引述其学生汤铭均的话说:“假如允许同品不除宗,则九句因中四、五、六句因不存在,因为这三句中的同品不再是没有因;假如允许异品不除宗,则九句因中二、五、八句不复存在。因为这三句中的异品不再是没有因。”郑教授在引述汤生的话后还下了断语:“同、异品不除宗显然违背九句因理论。”(同上,第26-27页) 关于同品除宗的问题,笔者在上文一再强调,必须厘清这个“除”字的含义。按陈那所说因法“于余同类念此定有”,此中的“余”字是指“在宗有法之外”,说作“除宗有法外”亦可,意思别无二致。然而“余”绝无“除去”或“剔除”的意思。同品要在宗有法外去觅取,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若主张同品须除去宗有法,甚至主张喻体也要剔除宗有法,这就大谬不然了。而郑教授断言“同、异品不除宗显然违背九句因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后一种意义上的。这里面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郑教授将陈那所说的“于余同类”,说作同品要除去、剔除有法(而且并非暂除),这是偷换概念。其二,进而又说同品不除宗会如何如何,其言下意思乃指喻体之除宗有法,这是偷换论题。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无的放矢地作出“假如允许同品不除宗”的设问。至于异品除宗的问题,笔者已在上文作了具体剖析,宗有法(如声)与异品(常住不坏之物如虚空)本不在同一个集合,又何除之有?故不可能出现“九句因中二、五、八句”不复存在的情况。 综上所述,将同、异品是否除宗视作决定九句因存亡的主要因素,未免过于夸张。九句因穷尽了因与同、异品的各种关系,为厘定正因相,建构因的第二、三相打下基础。除宗有法(不是除去有法)只是九句因涉及的有关选择同品的一种方法,而与异品无关,更非决定九句因存废的关键,所以郑教授断言“同、异品不除宗显然违背九句因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是除外命题还是普遍命题? 郑教授一再强调同、异喻体都要除宗,说同、异喻体都是除外命题。那么,陈那新因明中的喻体是不是普遍命题呢?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考稽陈那的论旨。 陈那《理门论》对胜论派等“世间外道”的五支式有一段批评说得很明确: 此说但应类立义,无有功能,非能立义;由彼但说所作性故所类同法,不说能立、所成立义。又因喻别,此有所立同法、异法,终不能显因与所立不相离性,是故但有类所立义,然无功能……以同喻中不必宗法、宗义相类,此复余譬所成立故,应成无穷。(《大正藏》第32卷,第3页)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若如世间外道那样仅以实例“瓶等”为譬喻的话,譬喻便只类同于宗法无常,缺乏普遍涵盖的功能,非如我所说的因的第二、三相中所揭示的譬喻作为前提的那种涵义;由于它只说如瓶,因瓶上有人工造作的属性,故与有法(声)属于同品类的事物,而不揭示因与宗的不相离关系。又如果将因与喻分离,同、异二喻也只同、异于宗法无常,这就不能显示所作因与无常宗之不相离的关系,所以仅仅类同于宗法无常是没有用处的。也正是由于古师所立的同喻中不揭示因法与宗法的不相离性,而只以同类例来成立宗,这就有譬喻辗转无穷的弊端。 陈那对古师的批评很深刻,他清楚地表明,新因明的同、异二喻体现了因、宗之不相离性,在以同喻依瓶证宗时,并以“诸所作者皆是无常”的普遍命题为同喻体,这就涵盖了所喻的全类事物。而古师只是以瓶喻声,以二者均有无常性作类比,就会辗转无穷,类比不尽。对此,《大疏》释云: 我若喻言“诸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等”,既以宗法、宗义相类,总遍一切瓶、灯等尽,不须更问,故非无穷成有能也。(《大正藏》第44卷,第110页) 郑教授在《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一书中对这段话译述如下:“如果我把喻说成‘诸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等’,就使因法与所立法相联而不分离,把瓶、灯等一切类比对象统统囊括进来,不必再问,因此不是以没完没了的类比来成立能立。”(郑伟宏,2010年,第263页)这段译述是与原文论意基本一致的。 陈那的论述、窥基的诠释都充分地揭示新因明是以因宗之不相离性为推理基础的,其喻体是普遍命题,“总遍一切瓶、灯等尽”。对此,郑教授在译述时也做到了忠于原意,但是,当他说起“除外”来,却又臆说窥基“隐含着同喻体也必须除宗的思想”。(郑伟宏,2012年,第20-25页)又说“窥基在解释同、异喻体时明言除宗以外”。(郑伟宏,2010年,第65页)一会儿是隐含着要除,一会儿是明言要除,甚至冒称异品除宗有法是陈那因明体系的题中之义云云,就是拿不出陈那和窥基的原话作依据,不过是郑教授的假想罢了。 陈那的论述、窥基的诠释都充分地揭示新因明是以因宗之不相离性为推理基础的,其喻体是普遍命题,“总遍一切瓶、灯等尽”。陈那既明言因宗之不相离性为其比量的基础,这就体现了以类为推的思想。要在这种类推的逻辑系统里对喻体动手术,从普遍命题里剔除有法,说为除外命题,降作存在命题,这是不可思议的。 五、陈那的因明只是“最大限度的类比”? 郑教授“除外说”的目的是要将陈那因明的逻辑性质贬低为“最大限度的类比”,即认为陈那的新因明与古因明并无本质差别,只有量变上的不同而已,陈那的因明离“演绎推理尚有一步之遥”。也就是说,郑教授从同品须除宗有法,主观地延伸至异品亦须除宗有法,乃至同、异喻体亦须除宗有法,并由此引出喻体是“除外命题”的结论,从而否定陈那在印度逻辑史上首创演绎法的历史功绩。说到这里,我们不免联想起郑教授早年受许地山的影响。许地山将古因明分为比论法与演绎法两种。(参见许地山)然其所谓的演绎法仅举出《顺中论》中的一例,且是经过他改造的。这是将个别现象当做定式来论列了。他认为演绎推理在古因明中早已有之,所以不同意将“改造喻支,增设同喻体,从而把类比推理变成演绎推理作为陈那因明的一大贡献”。(郑伟宏,1986年)后来又改口说“无论从陈那的正面论述还是对古师的批评,都看不出陈那有从毫不例外的全称命题推出个别结论的演绎思想”。(郑伟宏,2008年,第57页)这一进一退,观点截然相反,但在否定陈那创立演绎法的历史功绩上却是别无二致的。 作为印度中世纪逻辑之父,陈那创立新因明,将印度古典逻辑从古因明的类比论法推进到带有归纳论证的演绎论法。陈那的因明是印度逻辑史上的里程碑,这是历史的定位,不是哪个人可以凭一己之价值取向予以否定的。 这里再征引陈那的论述展开来分析。陈那在《正理门论》云: 喻有二种:同法、异法、同法者,谓立“声无常,勤勇无间所发性故,以诸勤勇无间所发皆见无常,犹如瓶等”;异法者,谓“诸有常住见非勤勇无间所发,如虚空等”。前是遮、诠,后唯止滥;由合及离比度义故……复以何缘第一说因宗所随逐,第二说宗无因不有,不说因无宗不有耶?由如是说,能显示因同同品定有、异品遍无,非颠倒说。(《大正藏》第32卷,第2页) 陈那的这段论述,清晰地揭示了三点:第一,他所建构的三支论式中的同、异二喻,均由喻体和喻依两部分组成,其同、异喻体都是普遍命题,喻依则为实例。以普遍命题为推理的前提是演绎法的标志,这就大不同于古因明仅以事例为喻体的类比法。第二,同、异二喻的喻体是按合作法和离作法建构的,即同喻体必须先因后宗地与同品相合,异喻体则必须先宗后因地与异品相离。二者紧密结合,由此得以比度宗义(推导出论题)。第三,“说因宗所随,宗无因不有”是同、异二喻的公式,充分显示第二相同品定有和第三相异品遍无这两条规则,绝对不容颠倒过来说。所以陈那又以偈颂强调:“说因宗所随,宗无因不有,此二名譬喻,余皆此相似。”(同上)这最后一句警示人们,如果违反了第二、三相的规则,那就是似喻。 上述三点足以体现陈那的演绎思想。他对因明的改革,不是一种改良,而是一种革新。他建立起了一个开放性的演绎系统,为了加强其论证的力度和保持印度传统的论辩习惯,所以他保留了喻例(喻依),以此来保证喻体的真确性。喻例的存在标志着陈那的因明中含有归纳论证的成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陈那因明的主要性质是演绎(郑教授认为法称取消了喻依才达到演绎的程度;但法称时并未真正取消喻依,故此说亦是臆断)。所以郑教授认为“陈那新因明仍然是在类比推理的范围内提出并解决了最大限度提高结论可靠程度的理论方案,离演绎推理只有一步之差”(郑伟宏,2008年,第55-56页),显然曲解了陈那的因明理论。 出于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郑教授也不同意陈那的因明具有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性质: 必须指出,演绎与归纳合一说是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既不敢原原本本地按照陈那因明的体系,与传统的演绎说作彻底的告别;又总想在“演绎”的三支作法中找出归纳的因素,以此作为因明与西方三段论的区别。事实上,演绎与归纳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是演绎就不是归纳,即便是归纳,也只有完全归纳才达到了演绎的效果。(郑伟宏,2012年,第28页) 郑教授的上述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演绎与归纳是按不同的评价标准(演绎有效、归纳强度)来划分的,但并不妨碍二者的结合。郑教授所谓的“是演绎就不是归纳,即便是归纳,也只有完全归纳才达到了演绎的效果”,说得过于绝对。在现代归纳逻辑中,因果陈述句逻辑(即因果模态逻辑)就是因果条件句研究与模态逻辑的结合,是在一阶谓词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逻辑模态词和因果模态词的演算构建的公理系统。它的推演就具有逻辑必然性。虽然对归纳逻辑而言,从整体上说依然未能冲破概然性的局限,然其某些系统的公理化、形式化,说明它与演绎有效论证并非是不相容的。 我们应该将视野进一步扩大,从广义逻辑的层面来考察陈那的因明。我国已故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一贯主张要用大逻辑的观点来研究语言交际活动,沈剑英教授运用语言逻辑的方法从语法、语用、语义三个维度来剖析陈那的因明,鞠实儿教授提出广义论证的概念,将主体性、社会文化性、规则性、目的性和语境依赖性等都列入其研究视野,日本著名佛教逻辑学者桂绍隆(K.Shoryu)教授更认为:“使用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逻辑术语来界定印度逻辑,包括陈那的逻辑,毫无意义。我以为印度逻辑与图尔敏模式有更多的相似之处”。(Toulmin)以法学为模型提出一个复杂的论证模式,在欧美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弗雷格开创数理逻辑,即逻辑的第一次转向以来的又一次转向,也即逻辑的实践转向的开端。这些主张和实践都是值得肯定的,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借鉴。 因明作为一门绝学,需要众多学人来呵护,对它作深入的研究,将其奥微的义理加以具体诠释和阐发,且应忠实于陈那的原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纵向探究其渊源和沿革,从横向比较剖析其与诸家逻辑之同异。而且由于陈那的因明是一个开放性的逻辑系统,它不仅有严密的语法规则来规范论式,而且有语用和语义上的规定来保证论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从形式逻辑的层面上来考察它,也不能单纯用数理逻辑的方法将其符号化,而应该从广义的论证逻辑角度对其作深入的研究,还因明以本来的面目,还陈那以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