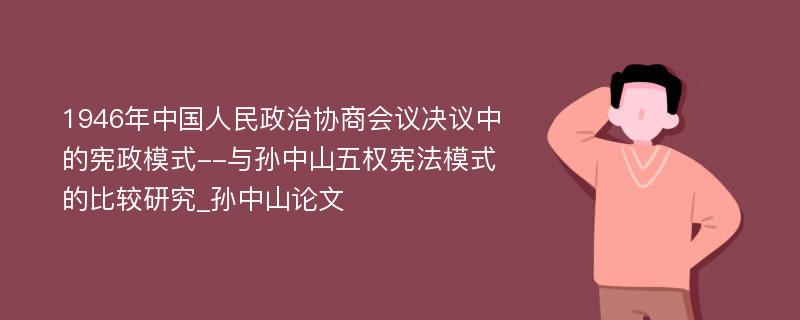
论1946年政协会议决议案中的宪政模式——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模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决议案论文,政协会议论文,宪政论文,宪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3)03-0067-04
1946年1月10日~31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等有关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大会通过了五项决议案,其中宪法草案案中的宪草修改原则,集中体现了中间党派对中国宪政模式的设计。
众所周知,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和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是孙中山在政治学上的三大创举,也是孙中山五权宪法论的三大基石。中间党派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彻底舍弃了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仅仅保留了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中的外在形式,基本遵从了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原则。
第一,关于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民权发展的历史后,发现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在民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是无能;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反而有能。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孙中山发明了一个新的学理——权能分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国家的权力划分为“政权”和“治权”两大系统。所谓“政权”,即“人民的权”或“管理政府的权”,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人民行使四权的途径:在地方,通过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直接行使四权;在中央,通过国民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间接行使四权。而国民大会是由充分自治的县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代表国民对中央政府官员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对法律行使创制权和复决权。[1](P326)所谓“治权”,即“政府的能”或“政府替人民做功夫的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与五权相对应,中央设置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1](P351)权能分治的另一项内容是“政权”对“治权”拥有支配权,就是说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而是单向的主权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即只存在执行者对主权者负责,不存在执行者对主权者的干预。由此看来,孙中山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其目的是把国民大会设计成为一个代表国民掌握实际权力的机关。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有关国民大会的规定,完全改变了孙中山设置国民大会的初衷。首先,从国民大会的组成来看,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缺少有关国民大会组成的具体规定,足见中间党派在制定宪草修改原则时,对设置国民大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从政协会议通过的国民大会案中看,国大代表是由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组成,[2](P473)这与孙中山所设想的国大代表由实行地方自治的各县选一名代表组成是有明显区别的。其次,从国民大会的职权来看,政协宪草修改原则规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曰国民大会”[2](P482),至于国民大会怎样代表国民行使四权,既无原则规定,更无具体说明。从选举权与罢免权来看,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的总统及政府五院都不是产生于国民大会。总统“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各级选举机关选举之”,“总统之罢免,以选举总统之同样方法行使之”[2](P482);立法院“由选民直接选举之”;监察院“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司法院“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的大法官组成;考试院“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的委员组成;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2](P483)。另外,总统与五院的工作都不对国民大会负责。这样,国民大会就失去了对中央政府官员的选举权与罢免权,也就失去了“人民的权”对“政府的能”的监督与控制。从创制权与复决权来看,只有“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2](P473),而以后的国民大会对于法律的创制权,则“另以法律规定之”[2](P482);又由于政协宪草修改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2](P483),这表明,国民大会只拥有“制宪”权,其他创制法律的权力则属于立法院,而不属于国民大会,即取消了国民大会对法律的创制权。政协宪草修改原则还规定:“宪法修改权属于立法、监察两院联席会议,修改后之条文应交选举总统之机关复决之。[2](P484)这实际上又取消了国民大会对法律的复决权。可见,政协宪草修改原则名曰国民大会代表“全国选民行使四权”,而实际上国民大会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虚设机构,即“无形国大”。另外,由于应掌握“政权”的国民大会没有掌握实际权力,而使其职权移至应掌握“治权”的立法院和监察院,这样,政协宪草修改原则就打破了孙中山关于权能分治的职权划分原则,从而使孙中山权能分治的政体构想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荡然无存。
第二,关于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是孙中山为了纠正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弊端而探索出的一种新型的政体方案。他认为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共和国,即使宪法最“完善”的美国,也有很大流弊。其一是西方各国任用人才,没有考试制而实行委任制。如美国“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总统进退”,造成“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3](P638)。其二是西方各国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国家的监察权为立法机关所兼有,由此产生无数弊端。“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4](P331)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孙中山融会贯通了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之精华而熔铸出了独具一格的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他认为,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是“各国所没有的政治学说”,“是破天荒的政体”[4](P320)。由于孙中山所讲的五权之间的关系是地位平等、分工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分权意义上相互的全面的制衡关系,这就使得“五权宪法”中的大总统作为行政首脑和国家元首,不受立法院的牵制,拥有了一种比议会制下的行政首脑更高的地位,比总统制下的总统有更高的权威,从而形成了总统集权;又由于“五权宪法”中国民大会的设置,是用来确保整个国家权力的民主性的,这就使得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既有浓厚的总统集权色彩,又有鲜明的民主性,是民主性的总统集权制。
中间党派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完全改变了孙中山这种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首先,五院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协宪草修改原则打破了“五权宪法”中“权能分治”的职权划分原则,使得“五权宪法”中分掌政府“治权”的五院那种地位平等、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立法院由“五权宪法”中的一个立法技术性部门,上升到“西方民主国家中议会”的地位,这就使得立法院不仅拥有立法权,还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和对国家财政的管理权;监察院由“五权宪法”中拥有的监察权、弹劾权扩展到对政府其他各院的官员有同意任命权;行政院虽然仍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但它已不是“五权宪法”中与其他各院地位平行,不受任何牵制,只对国民大会负责的行政院,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行政院受立法院牵制,对立法院负责;司法院为国家最高法院,但它不是产生于国民大会,并对国民大会负责,而是由经监察院同意的大法官若干组成,不对任何机构负责;考试院也已不是“五权宪法”中对国民大会负责、行使考试之权的独立机关,它实际上成为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业务性机构。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的五院已不是“五权宪法”中地位平等、分工负责的五院。立法院和监察院的地位已明显高于其他三院,它们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监察机关,而且具有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特征;同时,立法院对行政院,监察院对司法院和考试院还有同意人事任免的制约关系。其次,总统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五权宪法”中的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行政首脑,而且比西方国家总统制下的国家元首和议会制下的行政首脑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权威,这是一种总统集权的中央政制。而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的总统只具有国家元首的地位,不具有行政首脑的权威。因为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行政院手中,总统颁布命令得“经行政院议决”;总统任命政府官员需经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同意。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五权宪法”中总统集权的中央政制。因此,可以说政协宪草修改原则只保留了“五权宪法”中五院的设置和名称,而实质内容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总统集权中央政制已迥然不同。
第三,关于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地方制度问题,是民国以来政制史上的一个难题。孙中山集中外地方制度之精华,独创了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制度。其要点: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取既不偏于中央集权,又不偏于地方分权的均权主义;二是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反对20年代初期地方军阀实行的所谓“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由此有人认为,孙中山重视县自治,而不主张省自治。”[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悖于孙中山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主张的本意。首先,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无论采用集权制、分权制还是均权制,其前提条件是与中央划分权限的这个“地方”,必须是自治的主体,也就是说,地方自治是中央与地方划分权限的基础。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定:“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6]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省”就是与中央均权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必然是自治的“地方”,即自治的省。另外,孙中山还指出:“先以县为自治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础,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7](P189)。这里提及的“单位”,一般意义上理解,应该是一种组织的最低位,即起点,而不是最高位,终点。那么,孙中山上述所讲的实质是:地方自治以县为起点,从而扩大到省;省同样享有自治权,是自治的主体。其次,孙中山曾反对20年代初期地方军阀推行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这是因为“实行联省自治者,其所谓一省督军、总司令、省长等”,只“知有一省而不知有邻省,亦不知有国”,这“无异于一国皇帝总统”,并“与挟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8](P14)。可见地方军阀搞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主义的地方自治,而是军阀割据。孙中山当然要反对这种“省自治”和“联省自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反对正确意义上的省自治。《建国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到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大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6]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则更明确规定:“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8](P20)。这些都说明,孙中山不仅不反对真正意义上的省自治,而且把省作为自治的主体。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地方制度是以县为自治基本单位,省为自治主体并与中央均权的地方制度。
中间党派对孙中山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制度“很表同情”。他们认为,“县以上之省,自应于宪法上容认其自治之权”。这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问题。其原因之一,省是一个拥有实力的独立单位。我国的省制,可上溯到元朝的十一中书行省,历经明清两朝,一直延续到民国,可见其历史悠久。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5年的护国运动,1917年的护法运动,“无不以省为发动之地”,其“历史实力皆非可侮者也”。原因之二,各省也具有一定的自治经验。清末,各省就设立咨议局;民国以后,设立省议会,拥有本省的立法权、预算决算权,显然各省“已具有自治人格”。如果无视上述事实,不积极扶植各省建立自治制度,而强行剥夺各省已具有的自治形态,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统辖的轨道,势必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民国以来,各省能自募兵;自筹饷;自设银行、发行纸币;甚至能与外国办理交涉。其权如此之大,有的“大至现代国家”。这是中央政府推行极端集权主义,不给地方任何自治权,而造成物极必反的结果,以至“成为民国以来政治上极大病态”[9]。中间党派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建立省自治制度,并划清中央与省的权限。因此,中间党派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明确规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2](P483)。由此可见,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有关地方制度的规定,基本遵循了孙中山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原则。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中间党派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彻底舍弃了孙中山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仅仅摄取了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制的表面形式,基本遵从了均权主义的地方自治原则。即“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用英美宪政之实”[10](P64)。中间党派之所以设计出这样一种宪政模式,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代议制政体模式中的责任内阁制一直是中间党派所追求的政体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蒋介石的个人集权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但出于在政协会议上与国民党斗争策略的考虑,中间党派在制定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过程中,始终打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旗帜,以便使他们的这一宪政主张得以通过。中间党派天真地认为,通过这样一种转换,他们的宪政理想就能实现。事实上,惯于个人集权、一党专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绝对不会允许“分权制衡”的政体模式在中国实施的;另外,宪政体制的维系并不在于一纸宪法的制定,它更多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价值取向以及相关的政治法律制度等诸多因素。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并不具备上述这些实施宪政的条件。因此,中间党派设计的这套宪政模式很难在中国变为现实。但中间党派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而不懈地努力和不断地追求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设计的这一宪政模式曾对中国民主宪政的走向产生很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3-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