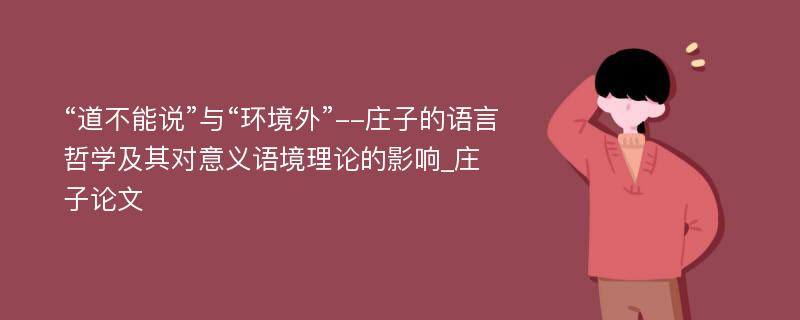
“道不可言”与“境生象外”——庄子语言哲学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意境论文,其对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7)03—0015—07
一、道不可言
道与言的关系,是庄子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在道与言的关系问题上,庄子与老子的态度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名言与道之间是相离、相悖的关系。庄子在《知北游》中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齐物论》中也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其意思都是在说,道不可言,言不及道,“道”一旦被明确“道”出,“道”便不再是“道”了。
老、庄之“道”之所以不可“道”,不可“言”,一方面是由“道”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名”的特性决定的。综观老子对道的论述,老子之道有三大特征:“法自然”,“为无为”,“体无形”。老子对道的言说,可以说整个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展开的。同时由于“自然”是与“人为”是相对的,而“人为”又是与“无为”相对的。“自然”与“人为”相对,而与“无为”相应,“自然”“无为”虽然二者所说的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但由于二者具有一致性,“自然无为”又因此经常被联系起来作为道的一种属性来谈论。这样一来,道的特征又可简括为二:自然无为,混成无形。《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十四章“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四十一章“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正集中说明了道的这些特征。
庄子与老子同为道家,庄子之“道”与老子之“道”,既有明显的渊源承继关系,也有明显不同。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老子之道,主要为理想的“治世之术”提供本体论依据,庄子之道主要为“逍遥自适”的人生实践奠定本体论基础,老子更加看重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征,庄子更加看重道的“无为而自适”的特征。这种由外在功利价值向内在个体价值的转向,使得庄子哲学具有明显的审美化倾向。尽管有这些明显的不同,庄子之道仍然明显秉承了老子之道的基本特征,他也是强调道的“自然无为”、“浑沌无形”的特征的。庄子在《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大宗师》)“有情有信”是说道真实存在,可以验证,“无为无形”正是对道“自然无为”、“混沌无形”这两大根本特征的总括。《庄子》全书涉及其本体论与价值论的两个最重要篇章《逍遥游》与《齐物论》,也正是分别集中说明道的这两大根本特征的。《逍遥游》主要是说明道自然无为,逍遥自适;《齐物论》,则主要是说明道浑沌无形,万物齐一。庄子之“道”之所以不可言,正是因为,在庄子看来,名言的特性正是与“道”的这两大特征直接相对的。如果说道自然无为,混成无形,名则是人为的造作,是有形的区分。道“无为无形”,名“有为有形”,二者在性质上截然相反,相离相悖,这是道不可名、道不可说的主要原因。庄子的“道不可言”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理路来展开的。
《庄子·天道》中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庄子·天道》)这种“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的语言观,正是一种人为语言观,表明庄子认为名称与实在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人给事物一个名称,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并且,名称具有约定俗成的力量,给你一个名称,若不接受,是会“再受其殃”的。这与孔子的“命之必可言”,即命名必须有道理、有依据、可以言说的观点正好相反。
庄子在《齐物论》中也曾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又说,“夫言非吹也”。所谓“使其自己也”郭象注曰:“自己而然,谓之天然。天然尔,非为也。故以天言之。”[1](P50) 而所谓“夫言非吹也”,也就是说,人的语言不同于自然界的风吹,自然界的风吹虽各不相同,但都发乎天然,不是有意而为。但人的语言,却是“机心所发”,充满人为的成见。这意思也是说,人的语言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
对庄子来说,道不可言,不仅由于名是一种“人为”的造作,还由于名意味着一种“有形”的“切割”,它与混沌无形的道不相符合。在庄子看来,“名”是与“形”相当的,名与形与声色属于同一个层次,都是形而下的东西,而形而下的名言是无法谈论形而上的道,是不足以达至形而上的大道之“情”的。《庄子·秋水》中写道: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庄子·天道》中又写道: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庄子·天道》)
综合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在庄子看来,世界上有四种不同的存在:“言”;有形的“物之粗者”;无形的“物之精者”;无形的“不期精粗者”。那无形的“不期精粗者”即是“道”,而“意”则属于无形的“物之精者”,有形的“物之粗者”即指具体的存在“物”,再加上“言”,就形成庄子语言哲学具有层级性的四元结构:道、意、物、言。在这个四元结构中,言与物、形与名相当,那无形的没有精粗之分的道既不能以言论又不能以意致,名言所能谈论、所能达到的只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物”的领域。“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则阳》)“形色名声”是不足以达道之“情”的。但世人却不理解这一点,或因“贵言传书”,或“喋喋不休”,沉溺于形色名声世界之中而不知返。对此,庄子表现出了类似柏拉图在类似情境表达出来的“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之情。
而“形色名声”之所以不足以达道之“情”,则是因为“名以定形”,而“有形则有分”。(王弼《老子注》)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讲的“是与非”、“彼与此”、“有与无”、“然不然”、“可不可”等等是非纷争都是由“言”区分出来的。而道之体混沌无形、通而为一,它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是不能被有形的区分性的语言来谈论的。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轸。”(《齐物论》)所谓“轸”即界限和区分。道本没有什么固定的边界,言本没有什么恒常的定论,只是为了争论一个“是”字,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界限和区分。有了分界,就有了局限。“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有了区“分”,就会有是非之争,有是非之争,混整的大道就会受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因此,庄子极力反对用区分性的名言概念对混沌未分的大道进行谈论。“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徐无鬼》)《应帝王》中那个“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故事,更说明了区分性的语言对于混沌未分的道所具有的灾难性。以区分性语言表达混沌未分的道,只能带来有限的知识和无限的是非纷争,只有带来对大道的破坏与毁损。只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辩”,才能返归那混沌未分的、道通为一的无穷之境。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庄子坚持一种“人为语言观”和“形分对应论”,认为名言既是一种人为的、有心的运作,又是一种有形的区分和切割,它是无法言说自然无为、混沌无形的大道的。但道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既然不能废弃语言,只有在言语方式上下功夫,以探求解决道言悖论的出路。既然道不可言的原因在于,道自然无为、混沌无形;名有心有为,有形有分,而要突破道不可言的困境,一是要破除名言的人为性,使之成为自然的、无心的语言;二是要破除名言的区分性,使之成为混整的语言。这种自然语言、无心之言,就是“无言”。这种破除了名言概念区分性的混整性语言,就是“象”化语言。由此,庄子突破道言困境的基本出路就有两条:一是以“无言”的方式言,一是以“象”的方式言。前者可称为“言无言”,后者可称为“言象言”。庄子语言哲学的四元结构、“道不可言”的语言观念以及“言无言”与“言象言”的言语方式,对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以及诗体形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诗学中“意境”范畴和“境生象外”命题更是与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二、意境与道境
众所周知,“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自从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境界”以来,它也是众多诗论家、艺术家热衷探讨的课题。但今人对意境的解释历来不一。有的强调“境界”与“意境”之间的基本区别,但大多数人则对境界与意境不加严格区分,提到“境界”时,心里也往往是把它当作“意境”的同义语。在意境或境界论产生的时间上,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境界的历史无限地回溯。总之,须有史的定位意识。境界一词,是佛教的用语,这为研究界所公认。”[2](P202) 与之相反,也有学者指出:“时人议论‘境界’久矣,多矣。群言竞起,各有创获。但至今鲜见有循‘大象’—‘逍遥’—‘意境’一线做溯源工作者。而这一工作告阙,便不明中国意境论的要义正在于从形而下的物象直指形而上的体验,正在于泯灭主客界限而获致物我同一,以完成精神超越”。[3](P222) 意境与境界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意境”与“境界”共同包含的“境”,又使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意境论的全面展开和确立,作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的确得力于佛教的传入,但把意境仅仅看成“佛教”的一个脉系,忽视它在本土哲学尤其是庄子语言哲学中的根源,的确是意境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阙失。这种做法使人既不能充分认识意境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性,也不能深入理解意境的宇宙本体论意义。
意境作为一个诗学范畴最早见于王昌龄的《诗格》。从意境在《诗格》中的最初含义来看,意境的宇宙本体意义非常明显。《诗格》中写道: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物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用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关于这一段文本的理解,向来存在着众多分歧。分歧之一在于,意境是诗境的最高层次,还是诗境的一种形态?分歧之二在于,意境与诗境是从属关系还是等同关系?[4] 这一段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歧义的话,为什么解释起来会存在如此重大的偏差?归纳起来,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意境概念的后来发展往往会干扰解释者对意境原意的辨析;二是解释者往往联系文学现象进行对号理解,而不能追溯哲学语境进行考察。
《诗格》所提到的“物”、“情”、“意”三境,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所关注的几个方面。如前所述,庄子哲学中就存在着一个四元结构:“道”、“意”、“物”、“言”。在这四个元素中,意的含义是最不确定的。“意”在庄子哲学中不是一个最高范畴,在大多数语境中,“意”是低于“道”的。如《秋水》篇中的“意之所不能察致”之意,《天道》篇中的“意有所随”之意,《庚桑楚》篇的“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之意,显然是与“道”不同的。为了通达那最高的“道”,“意”与“物”与“言”都属于庄子“遣之又遣”的范围。但仅有在《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中,意的含义和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此中之“意”不是指一般的知性思维,意念思虑,心意情感等,而是指语言所表达的“道”的“意义”,其在本体地位上与“道”是相同的。“得意而忘言”,也即“得道而忘言”。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虽然是以《周易》中的言、象、意关系作为问题形式,但在内在精神上却与道家的道不可言、与庄子的“得意而忘言”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言意之辩”中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实际上主要是先秦道家“道不可言”、“言不及道”问题的延续。因此,“言意之辩”中的“意”并非一般的“情意”之意,而是“真意”、“道意”和“玄妙之意”。尽管只要被称作“意”,它总是与“心”有关系,道意也是人心体悟到的,但只要是为道家、玄学家所肯定的“意”,它就不是一般的心意情感,而是一种虚静玄妙的、具有超越性的心灵之思,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从王昌龄《诗格》中把“意境”与“情境”进行区分,突出“意”与“情”的不同,强调“意”与“真”的关联来看,《诗格》的意境论应是在庄子语言哲学和魏晋玄学的思路上提出来的。尽管《诗格》中“意”的含义也不统一,但其中“意境”之“意”当是庄子的“道”意之意,玄学家的“妙意”之意,或者是禅宗的“第一义”,而不是一般的“情意”之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些具有本体意义的对宇宙人生的本真体悟,才称得上是“真意”。陶渊明《饮酒》中有“其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昌龄的“意境”之“意”也应是指这类“真意”,而不是指一般的“情意”,否则,“意境”与“情境”将没有必要进行区别了。恰恰相反,在王昌龄看来,“意境”与“情境”是不同的。王昌龄对“意境”、“情境”、“物境”的划分,或与庄子对道(意)、意(情)、物的划分一样,也是存在着层次的。但不管是否存在着层次,以“情景交融”来界定意境,都是存在着重大偏差的。从意境产生的最初内涵来看,它突出的主要是与宇宙本体的关联,而不是与情感的关系。就像韩林德所说,“一些学者(包括南宋范晞文、明谢榛、清王夫之以至近人王国维)则舍‘虚’而就‘实’,倾心于从‘情景交融’的角度来阐述艺术意境(意象)的美学特征,这一探讨,虽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但总的说来,这些学者的立论,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艺术意境对宇宙本体或世界实相的追求。从美学思辨的角度讲,理论层次有所下降。”[5](P178)
而当我们恢复“意境”与道家语言哲学的源发关系时,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意境”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从意境的源发境遇来看,“意境”实际上就是“道境”,它与“情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但“道境”并非“道”与“境”在字面上的简单复合,“境”本身就是“道”的题中之意。因为道家之“道”尤其是庄子之“道”已暗含着“境”,或者说庄子之“道”本身就是一种“境”。“境”“构成庄学要义之一”[3](P198)。庄子语言哲学不仅影响着意境论对“意”的最初理解,也体现着意境论中“境”的原初含义。意境的确从佛教用语借用了“境”,但如果要对“境”一语做词源学的追溯,它的最初含义已经潜存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尤其是庄子语言哲学之中。
《庄子》中直接提到“境”的地方有三次,直接提到“竟”的地方有七次。“境”、“竟”的原始含义就是“空间”。《齐物论》曾两次直接提到“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齐物论》)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晋人崔譔注本,“竟”原作“境”,二者系古今字。竟与界本可互训,它意谓“空间”。如果“竟”即“空间”,“无竟”就是“无尽空间”。[6](P273—278) 庄子哲学中的这个“无尽空间”,实际上也就是指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作为无限的时空统一体而存在的“太空”或“太虚”。“太空”或“太虚”就是混沌未分的“大一”,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之境域”。在庄子哲学中,与“无竟”类似的“无尽空间”的喻指比比皆是。《庄子》中经常出现游于“大莫之国”(《山木》),游乎“尘垢之外”(《大宗师》),游于“无极之野”(《在宥》),游于“六合之外”(《徐无鬼》),游于“无何有之乡”(《山木》),游乎“无有”(《应帝王》),其实就是指游于“道之境域”。“道之境域”,亦即“天地之境”,它是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也是人的自由精神“逍遥游”时所能达到的无限境界。《诗格》中说:“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由此亦可看出“意境”与“道境”的关联。
三、境生象外
“意境”作为“道境”,其根本特征就是“无”、“虚”、“空”。没有“空”,就没有“境”,“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正因为境的虚、无、空的特性,它才能为精神和肉体提供寓居之所,为人的精神意识“游履攀援”。“空”、“无”、“虚”不仅是佛家用语,也是典型的道家语言。庄子说“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唯道集虚”(《人间世》),又说“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外物》)都说明了道的这一特征和含义。如前所述,在庄子看来,以“虚无”为体的“无为无形”的“道”是不可名言的。“夫道,窅然难言哉!”(《知北游》)。道不可言,道开辟出来的无限精神空间,也即“窅然空然”的道境,也是超越于名言之域、言象之表的。所谓“妙境希夷,视听断绝,故审状貌,唯寂唯空”是也。(成玄英疏)[1](P760)
道作为一种空寂玄妙之境,用一般的名言概念无法言说,但也并非彻底不可造极。要造于这玄妙之境,对庄子来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不言”、“无言”、“忘言”;一是以“象”的方式言。庄子“不言”的直接和最高含义,是“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庄子·田子方》)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天地万物只是把自身的美展示给人看,而不用语言言说。就像孟子所言:“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达到天地之境的“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不为、不作,不言、不说,正是“观于天地”的结果。因此,庄子“不言”的最高含义,当是“只以目视,不以口说”,它让人抛弃一切人为语言的羁绊,只在眼睛的观看中,达到与天地之境的直接相合。这一点对艺术意境的视觉化倾向,对艺术意境追求“言外之意”具有直接的意义。
但庄子所谓“不言”,也并非一味地让人彻底缄默,而是让人以自然的、无心的方式说。因为对于庄子来说,道不可言,首先在于道“自然无为”,名“有心有为”,而要突破道不可言的困境,首先就是要破除名言的人为偏见,使之成为自然之言、无心之言,这种自然的无心之言,就是“无言”。以自然的、无心的方式说,就是“言无言”。“言无言”的理想方式就是以“卮言”言。庄子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所谓“天倪”,就是“自然的分际”,“曼衍”就是“无心”,所谓“卮言”,也就是因随着事物的变化,合于自然的分际的无心之言。以这种“卮言”言说,表面上是人在说,实际上是事物本身在说,是自然在说,是道在说,也是“语言在说”。既然是用自然本身的语言言说,而不是“我”在说,语言也就不会损害万物之间的齐同,也就不存在道言之间、物我之间的差别了。“卮言”之言,入于天均,合于天道,玄同万物之间的人为差别,消泯道言之间、物我之间的人为界限,在日出日新的日常言说中,引领人进入大道的无限广阔和自由的境界。因此庄子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又说“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齐物论》)
对于庄子来说,要想达至无穷的道境,一是以“不言”言,一是以具有混整性的“象”的方式言。道家这种“象”化的言语方式,为老子所开创,为庄子所发展。《庄子·天地》篇有这样一则寓言: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天地》)
这里“玄珠”喻指“玄妙之道”。“离朱”即“目”,它意味着“有形”;“知”即“致诘”,它意味着“有分”;喫诟即“言辩”,它意味着“有名”。玄妙之道,混沌无形,有形有分有名的“离朱”、“知”和喫诟,自然是无法得到它的。“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因为“象罔”的特征正好是与“离朱”、“知”、“喫诟”所意味的东西相对的。如果说“离朱”、“知”、“喫诟”意味着“有形有分有名”的话,而“象罔”则意味着“无形无名无分”,它恍恍惚惚,浑浑沌沌,几与大道同。从“象罔”的这些特征来看,庄子的“象罔”实际上是与老子的“大象”相通的。老子说:“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王弼注曰:“有形则有分。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王弼《老子》第四十一章注)。而无形的“大象”作为“天象之母”,“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王弼《老子》三十五章注)正因为“大象”具有“不寒不温不凉”、“包统万物”的特性,它与老子“不可致诘”、“混而为一”的大道正好相适合,所以老子之“道”虽不可“名”,但“可象”。只是这里的“象”不是一般的“小象”、“物象”,而是无形的“大象”。与此相类似,庄子“象罔”得道的故事同样说明了庄子之道虽然不能以纯粹的感官来把握,不能以区分性的知性思维来致诘,不能以有形有分的名言概念来获得,但还是可以通过混沌无形、恍惚不定的“象罔”来达致的。所谓“妙境希夷”也并非完全不可企及。象罔可以得道,也就意味着通过“象罔”可以达至“视听断绝,唯寂唯空”的“道之境域”。“象”作为庄子达道的又一方式,在这里也是为解决道言之间的悖论而存在的。实际上,在庄子的道、意、物、言的四元结构中,不仅言与道之间存在着悖论,言与意之间也是存在着矛盾的。因为“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则阳》)不仅大道玄妙,绝于言知,就是一般的属于“物之精”的“意”(如情意、心意等)也不能以言尽,更不用说根本就不是一物的“玄妙之意”(亦即真意、道意)了。庄子“象罔”不仅是解决道言悖论的手段,也是解决言意矛盾的方式。只是庄子隐含的“立象尽意”的思想,象作为“意”与“言”的中介,只有经过王弼以意、象、言理论的卓越阐发,才显得更加清晰。
这样一来,“言象言”与“言无言”一样,都是庄子达至道之境域的方式。而庄子“言象言”不仅指以无形无名无分的“象罔”从整体上隐喻道,而且还指通过比喻象征、对反之名、反复循环等一切具体的言语方式来打破名言概念的区分性,确定性,以与混沌未分的大道相接近。[7] 但“象”言之言与“不言”之言有所不同的是,“不言”之言是“自然之至言”,是“合道”语言,它与海德格尔的“大道言说”、“语言言说”相似。意象语言、混整之言则是“几道”语言,与“无言”之言相比更属于“技”。人们即象求道,由象至境,但有形的具象本身还不就是道,就是境。因此,人们通过象来达到道,但却不能过于执着于象。得意、得道的目的一旦达到,“言”与“象”就像“蹄”与“筌”那样可以放在一边。亦即庄子所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玄学家王弼在充分肯定“立象尽意”(“象”能尽“意”)的基础上,又把庄子“忘言”、“忘象”的意思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一方面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另一方面又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这样,王弼就由承认“言象”的工具价值,又走向主张彻底超越“言象”了。而佛学家竺道生所谓“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慧皎《高僧传·竺道生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沿着这一思路,不尽之意(道),不可能见于“言”内,无限之(道)境也只能生于“象”外。这样一来,从庄子“道不可言”、言不尽意(道)、立象尽意(道)的语言哲学之中,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境生象外”的命题来。而“境生象外”作为一个诗学命题最早由刘禹锡提出来时,也的确表明了它与庄子语言哲学的关系。刘禹锡说:
“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世。”(《董氏武陵集记》)
从这里可以看出,“境生于象外”是与“义得而言丧”相关的。“义得而言丧”尽管也与玄学“言意之辩”以及佛学语言观相关,但它最根本的理论源头还是庄子的“得意而忘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的根源则是“道不可言”。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境生象外”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语言哲学的核心命题“道不可言”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自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以来,也一直存在着从言意关系角度探讨意境的倾向。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都是在谈“文字声韵之外”(罗根泽)的境界的。北宋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南宋诗人严羽说:诗歌妙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明朱承爵在《存余堂诗话》中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这些都是在说明意境是在言象之外生成的。王国维虽然强调“意境”与“情”“景”的关系,但他在批评宋代词人姜白石的作品“不于意境上用力”时也说过:“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人间词话》22)他批评“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不如“境界”更能探诗词之本,而他所谓“境界”与“沧浪所谓‘兴趣’”一样,也是用于说明诗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人间词话》79)而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所说的“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如果用来说明“隔”与“不隔”是恰切的,但如果用来作为对“意境”的界定,则是对意境原意的极大偏离,是意境发展的低俗化,实在不能代表对意境的成熟看法。从意境论发展的主导倾向来看,“意境”之所以生于“象”外,正由于“道不可言”、“言不尽意”,“道”“意”超越于言象之表决定的。“境生象外”这一命题实际上正是在道家语言哲学、玄学言意之辩以及作为“玄学同道”(汤用彤)佛学语言观的思路上展开的,其中庄子语言哲学处于至为根本的地位。这使得意境论包含着宇宙本体的思考,具有鲜明的宇宙本体论意义。当代学者对意境的阐释,不能“有意无意地抛弃艺术意境对宇宙本体或世界实相的追求”,把“意境”简单地看成是“情景交融”的问题。
突显原初“意境”论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强调意境与单纯的情境、物境的区别,并非完全否定意境与其他二境的关系。如果诗歌只有“意境”而没有“物境”和“情境”,就会像失败的玄言诗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但如果诗歌只有“物境”和“情境”而没有“意境”,就会停留在过于质直的形下世界,缺乏深远的意味。“意境”作为诗歌境界的最高层次,它应以“视境于心”、“故得形似”的“物境”,以“张于意而处于身”、“深得其情”的“情境”为基础,通过“张于意而思之于心”,达到对宇宙人生的某种“真”意的了悟,实现“道”、“情”、“物”、“象”的完美统一。忽视最初意境论中所包含的宇宙本体意义,仅以情景交融来界定意境,不仅会导致美学理论层次的下降,还会导致文学创作品味的降低,使其缺乏对终极之道的关怀,难以抵达超越性的形上之域。王国维在在评价姜白石的词时曾经说“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人间词话》13)细细品味,不难发现,王国维所最爱的这两句词正可谓有意境的典范。因为它前一句,情景交融,后一句意味无穷。皓月冷山独化于玄冥之境,它给我们的不仅是鲜明的视觉感受,充沛的情感体验,而且更有对宇宙本体的领悟,让我们看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流行。
收稿日期:2007—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