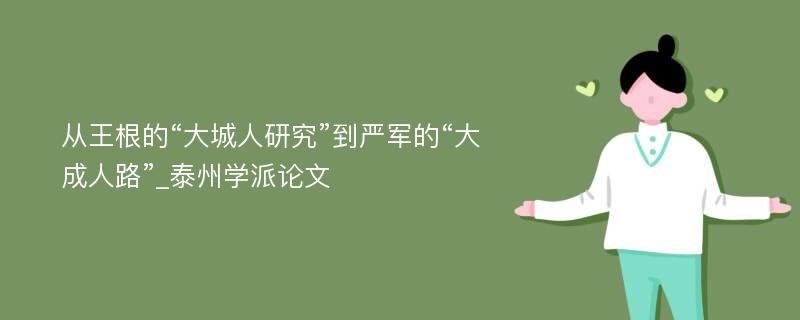
从王艮的“大成仁学”到颜钧的“大成仁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成论文,仁道论文,仁学论文,到颜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是作者对泰州学派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主要研究颜钧对王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认为颜钧之“大成仁道”在王艮的“大成仁学”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立体自由、儒学(实为心学)的平民化和实践性。
关键词 王艮 颜钧 大成仁学 大成仁道
颜钧(1504-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避明万历帝讳改为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人。颜钧是泰州学派的主要传人,一生颇富传奇。其早年不慧,后受次兄钥启蒙得阳明良知学,于是心醉神放,嗣后受教于王艮嫡传弟子徐越(字子直、号波石),又得王艮亲授“大成仁学”,遂终生以布衣从事讲学,弘扬泰州思想。曾出奇计倒溺倭冠,又被捕于狱中,几死三次,经营救而充军福建,旋参与平海盗,晚年从事著述。终其一生为泰州学派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清人黄宗羲《泰州学案》云:“泰州(指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充分肯定了颜钧在泰州学派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艮晚年,逐渐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整理归纳,一反其“王公(指王阳明)论良知,某谈格物”的结论,把自己的思想浓缩为“大成仁学”。所谓大成仁学,实际上是王艮集孔子古典儒学的“仁”与阳明良知学的“心”相融合,心中有仁便是圣,以仁教化天下便是大成圣。王艮认为这是对儒学二千年的总结,在他逝世前一年曾作《大成学歌》,阐发其旨。鉴于原文过长,恕不引录。在这歌中王艮把一生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概括:以悟致学,以尊身尊道而达到格物致知,以物格而使心中有仁,以仁觉天下,使天下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中,于是天下大成。从而体现了泰州学派的主体自觉和平民哲学思想。
颜钧在继承“大成仁学”的同时,认为大成仁学是“以仁天下人心”的“至德要道”,而把“大成仁学”上升为“大成仁道”,把王艮一系列思想都放到“道”的层面上,不但继承了王艮哲学思想,而且发展了王艮哲学。其主要特点是把王艮哲学体系中的主体自觉上升到主体自由;把王艮的平民哲学发展到儒学平民化;把王艮的“王道”、“仁德”社会理想实践化。
一、从王艮的主体自觉到主体自由
王艮从“万物一体”和“体用一原”的一元论宇宙观出发,阐发了他“人之天,即天之天,天人同体”,人性之体即天性之体,不假安排,不涉外物,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快乐的思想,从而提出尊身即尊道,安身要安心的主体性哲学思想,体现出对主体存在的价值和主体自觉的唤醒。
王艮的主体性哲学是建立在一个“仁”字的支点上的:
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
故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袁承业:《王心斋先生遗集》《勉仁方书壁示诸生》,以下简称《遗集》)。
同样是从“仁”出发,颜钧把王艮的主体存在和主体自觉发展到主体自由,从而更加突出了主体性地位。他面对四十多年来邦本逐溺、生业颠覆、灾异趵突、专制苛烈、黎庶不饶的社会,开出的救世之方只有一个字:“仁”。他说:“为今急谋行道者上策,只要一个仁。”(《颜山农先生遗集》《急救溺世方》,以下颜钧引文皆出自山农遗集,不另注)怎么得到仁呢?他认为:“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论大学中庸大易》)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即至矣,”最后归结为“体仁之妙,即在放心。”(《颜山农先生传》)
颜钧的“仁”,实质就是“以仁天下仁心”的“至德要道”,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仁”呢?他把王艮的主体性上升到二个高度:
第一是自我。“为仁由己”就是自我意识,“岂由人哉”就是摆脱一切外界束缚和限制。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仅表现了他对王艮主体意识的继承,还表现了他对王艮主体性意识的发展。这种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实际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杠杆。他在解释传统儒学的《大学》、《中庸》、《易》时就体现了这种思想。什么是大学、中庸呢?他说:
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衍署大学中庸之义》)。
如果说,从大学中庸中悟出尊身尊道,修身之本,保身爱人,是王艮与宋明诸儒的重要区别,是王艮打开宋明理学缺口,吹进近代启蒙思想春风所作的重要贡献,那么从大学中庸中衍署出“自我”,颜钧则是千古一人。他把王艮打开的缺口变成了溃堤之水,使名教望而兴叹,无法羁络。可以说,颜钧的“自我”意识,已不再停留在王艮的主体存在和主体自觉阶段,而是呼唤出主体自由的强烈心声。他认为,如果天下人都有这种自我意识,那么就会:“大自我大,中自我中,学自我学,庸自我庸,纵横曲直,无往不达。”(同上)也就是说,“信使人人身有”自我的主体性意识,就会在思想和行为中达到纵横曲直,无往而不达的自由王国境界,这是对宋明理学中否认人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扼杀人性的教条的强烈鞑伐。他所表现出来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想,远远超出欧洲早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第二是自由。“我欲仁,斯人即至”,就是说,能不能达到“仁”,应该由主体的意向决定,不受外界限制。“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什么是“放心”?就是主体状态应调整到解除心理羁绊、率性自由的境界。解除人心所系的心理羁绊又不能强解,“灭人欲”就是强解,是不能达到“仁”的。因此他认为,“制欲非体仁也”,从而与宋明理学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何心隐正是继承了颜钧的这一思想,提出“寡欲、育欲、与百姓同育”的主张,实际是对颜钧“放心”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具体化。
如何理解颜钧的“放心”就是主体的率性自由?颜钧的弟子贺贻孙在《颜山农先生传》中记叙了一段颜钧为罗汝芳治“心火”的情况。罗汝芳参加乡试未能得中,很郁闷,以为只是要求克制人欲,即可除去心头炎火。颜钧告诫他: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惟有顺应自然,放开思想自由,卸掉扼杀自由的压抑,才能率性发展。
“放心体仁”就是要求人们解放自我压抑,使主体意识完全达到自由、率性而为的境界,这种自由境界是对人的欲望充分肯定,不扼杀人性的自由,是要求主体精神的内在自由。
颜钧“放心体仁”的主体自由思想是建立在“贵心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心是人身和世界的主宰,是最高的逻辑范畴,也是认识世界,立身处世的起点。他在辞别王艮、踌躇满志、买舟西江准备大干一番时,首先就提出“贵心论”主张:
窃谓天地之所贵者,人也。人之所贵者,心也。人为天地之心,心为人身之主。
参赞者知贵之所在,而立学以养心,立教以养人。人而囿于教,心闲乎学,斯得所贵,而安身尊道,柱之宇宙,无不持载覆帱者也。(《急救心火榜文》)
颜钧在这儿的“心”不是指肉体之心,而是主体意识。他对主体意识“统率性融”和“应酬日用”的作用看得比王艮还重,他认为如果认识不到“心”的“本体作用”,就会“道不明不行”。只有弘扬大成仁道,以养心养人,做到心安而身安,才能“安身尊道”,才会柱立于宇宙,“端天下大本”。他面对当时“世降风移,王者迹熄,圣学蓁芜,人心汩没,致流覆辙,莫逾今日”的状况,认为首要的是除却人们心头炎火,要“先正其心,完复天真”。因此他要像王艮那样,以先觉觉后觉,用自己的讲学宣传去“耕心樵仁”,甚至为自己起了“耕樵”的名号,要“专辟形骸凡套之缰锁,舞之以尽神而尽涤性上逆障碍”以便使世人“咸归中正,正端心学”。
尽管颜钧也是从心性修养的渠道去拯救道义,开启治世良方,但他由于主张解除心理的一切枷锁,以恢复和完复人的天真和率性,强调主体存在的价值和颂扬主体自由,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很高的价值。
二、从王艮的平民哲学到儒学平民化
王艮的大成仁学本身就有平民化倾向,他认为“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惟其简易,才能够为平民大众所接受,因此王艮的大成仁学以平民百姓为本位,“百姓日用即道”、“尊身立本”、“淮南格物”都是这一指导思想下形成的简易儒学。这也是王艮对儒学的重要变革和泰州学派的新学术风格,即平民学风。
颜钧作为王艮传人,自称“受传而造有获,自成仁道”,宣称“千古正印”,他的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简易儒学的特点,而且有着更为鲜明的儒学平民化倾向。他不但从理论上建立起人人都可以进入儒学殿学的通道——性情神莫,作为主体精神的悟道能力(本文不及详述),而且对儒学理论本身进行了至简至易的独出心裁的诠释,构建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他称之为“仁神正学”。
什么是“仁神正学”?颜钧认为就是孔子晚年讲学于杏坛的内容,其精髓被概括为“五在四绪六龙”,实际上是把“大成仁道”的理论核心口诀化,把儒学从浩繁的经典册轶中简易化为几个概念(具体的内容见《论大学中庸大易》),这样做确实方便了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广大平民掌握。为了使“仁神正学”的内容为更多人掌握,颜钧又进一步创立了“大中之学”,通过大中之学使儒学的大门向广大平民敞开。
什么是“大中之学”?它其实是由儒学经典《大学》、《中庸》书名变化而来,但已不是对这两部经典书名的解释,也不仅是宥于论述这二本书,而是颜钧对儒学的平民化诠释。我们知道,《大学》、《中庸》自宋以来被列为儒学主要经典,而《大学》则是进入儒学之门的第一个台阶。王艮对《大学》极为推崇,其许多思想都是对《大学》的悟道。他曾强调指出:“惟《大学》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吃紧处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本旨。……诸贤就中会得,便知孔子大成学。”(《遗集》《答补遗》)颜钧王艮的旨意,架起了一条由大中之学通向大成仁学的通道,他在《衍述大学中庸之义》中说:
必先致知以入门,格物以为柄,则诚意以实格致之功,正心以宰诚致之固,修身以成立本之学。故曰大本立而齐治平之道犹反掌耳。大本既立,学在我矣。我中独立,庸于国家天下也,将亲亲仁民爱物贯通无碍,孰不争与尊亲焉。
这种把《大学》、《中庸》四个字拆开,分别作为独立范畴,加以释义,用这种类似卜卦的拆字法去衍述儒学内容和精神,确实是匪夷所思,虽然不免失之简单化和牵强,但它又确实是亘古未有的新解,尤其是它的平民化作用更是显而易见,他把大成仁学很自然地过渡到大中之学。
我们且看颜钧是如何诠释的?根据程学颜记载,颜钧赋于其各自的涵义是:
大: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
学: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
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
庸: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
在这里,颜钧突出强调了“自我”,强调了主体存在的地位,充分体现了颜钧重视自我的思想,而这种衍述方法,正是泰州后学所承王艮遗风,是王艮“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的治学方法的典型产物。
颜钧诠释并没有仅停留在拆字的阶段上,他又进一步将其相互间加以错综演绎,生发出更多的意义,形成“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的类似文字游戏的系列思想,从而完成“大中之学”的平民化构建。他认为“如此晰大中大易,以变化学庸”才能扫除千百年来对古典儒学进行注集所衍生出来的蓁芜麋滥。我们且不看“大中之学”本身是否有可取之处,就颜钧构建“大中之学”的目的而言就很有价值。千百年来,经生文士们捧着一套儒学典籍,小心翼翼地注疏训诂,文字越来越繁琐庞大,内容越来越陈腐麋烂,把本来很好的东西窒息得毫无生气,多少人穷精皓首,不能自拔。颜钧的“大中之学”简易便捷,士农工商不需要高深学问,都能通过悟道而登堂入室。
我们今天当然用不着去演绎大中之学的错综之义,因为我们已解除了理学的桎梏。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颜钧讲学一反理学家那种板起面孔,繁琐论证的麋滥之风,以唤醒人心良知重视自我,以把握自我为宗旨,强调“精神活如水”、“达己达人”的学风仍然是值得推崇的。按说,我们从《大学》、《中庸》里并不能直接读到对主体地位、自我意识的强调,因此在正宗儒学看来,颜钧哪里是在“心印孔学”,分明是背离孔门的奇谈怪论,是违背儒学经典的“小人之无忌惮”的胡言乱语。但是从学术生命力更新的观点来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颜钧的衍述正是明朝中叶继阳明学、王艮泰州学之后又一股清新的平民化治学之风,是对理学的反动。用颜钧自己的话说,“如此晰大中大易,以变化学庸”,必然“自将迸灭百蓁芜,千家注集之糜滥也”,这种胸襟,确实横扫荡涤着理学教条习气和糜滥烦琐之风。
三、从王艮的王道、仁德理想到理想社会实践
王道社会是王艮及泰州后学的社会理想,也是大成仁道的最终目标。王艮在晚年的《王道论》一文中描绘了王道社会的理想,认为这个社会应是尧舜在位,比屋可封,刑措不用,教养有道,衣食足而礼义兴,民有定业而风俗淳,天下无虚糜之费。上下以德行任人,人人为善,国脉畅通,日新月异。王艮长期生活于下层人民之间,他看到战乱、灾害、饥荒、苛刑、民无定所,风俗日下的现实。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远不如他“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志向那么清晰,也没有颜钧那么冲动和有切肤之痛。原因就在他比颜钧更加理性,而颜钧的追求更富性情、理想更趋于实践性。因此王艮认为,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时机尚不成熟,他虽然提出均田之法,并且也在家乡上书过均分草荡条策,但他又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具备这种土地改革的实践可行性,必须先通过教育以淳民风,于是终生设教授徒,从而透出他思想的成熟和冷静。颜钧则不同,他一方面企图通过讲学以教化民风,达到王艮所要求的“人心和洽”;另一方面又同时把这种王道理想变成自己的实验园地和救世之方。
颜钧理想社会的首次实践是在家乡建立“三都萃和会”。那是颜钧悟阳明良知学以后,招集家族及乡间老壮妇男近七百人,讲耕读作人,使全乡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晚聚宿联榻究竟,以图乡风民俗得到改变,再现唐虞。虽然当时颜钧“力学年浅”,但其实践精神却一直贯穿于一生。
颜钧理想社会的典型是他根据当时社会的黑暗开具的救世处方,他自亲受王艮传道后,便从此离开家乡,跳出永新中陂的狭小天地,把他的理想社会实践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舞台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活动。“大成仁道”的理性使命感和人民性立场的感性驱动,使他渴望王道理想社会的实现。面对百孔千疮的社会和倒悬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指出这是“近代专制,黎庶不饶”,之所以如此应该“责在君臣”!(《遗集》《耕樵问答》)从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他提出:“大赉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复民性”(同上)的改良方案,以救民于水火。而要实现王道仁政,他认为最根本的是“为今急谋行道者上策,只要一仁”。(同上)具体措施是先取天下巨宦之银,听需国用,然后:
诏蠲天下贡赋,三年免征,大苏民困乐有余,随领洗牢,恩赦一切,原恶重狱,均与其生。次查怨女、旷夫,激逐漂流,三种无告者,尽行四方,寓豪土民各量力,命其周护以为之。
颜钧的这一王道社会的理想,既有经济手段,又有政治方案,还有教育措施,显然比王艮的王道理想要具体,更富于实践性。但是,王艮也好,颜钧也好,他们共同建构的这种“大成仁道”,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存在于道德理想中。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政治理想,是对“近代专制”的否定,尤其是它体现了颜钧追求理想社会的实践精神。它说明了王艮的“大成仁学”对颜钧来说,已不再是纯观念上的东西,它已成为实践目标和行为对象。“王道”,已不是完全停留在思想上的东西。
颜钧理想社会的实践性还表现在他的讲会组织。颜钧讲学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组织性。他不但讲学,还到处组织建立讲会。他主张“圣人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遗集》《杨城同志会约》)因此他每到一处讲学,总要着手建立一处讲会。颜钧倡立的讲会已具有初步的章程和规范,以及活动计划、制约条文等。如《杨城同志会约》就规定有活动开始、结束的时间、活动周期,还制定了具体的组织法,尤其是对开门授徒的传道活动有较严格的要求,为此专门制定了《道坛志规》,在规中对讲学老师和听讲弟子都提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做到“六道六洗”。“六道六洗”摒除了当时书院的师道尊严,折射出要求平等友善,取义斩利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启蒙思想精神。自颜钧以后,泰州学派讲学活动一直有会的形式存在。这种“讲会”的形式虽然没有宗教组织那么严密的机构和教规严格约束,但又有类似宗教组织的神秘性;虽然是讲学的组织,但他的一些“志规”却又超出当时普遍存在的书院所要求的内容,而且分布极广;虽然完全不同于民间的一些秘密帮会,但又有较多的活动规定和组织法,要求不管天气条件、路途远近都必须按时参加听讲和活动。至今许多学者仍在探究而无一致看法。鉴于篇幅有限笔者于此不加探讨。但是“讲会”毕竟是颜钧在讲学中的重要社会实践内容,使他把传道与组织民众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了与平民的联系,使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至时人称之为“山农游侠”,而泰州后学李贽则赞之为“雄视一世”。
颜钧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其著作和思想被湮没近四百年,以至于使泰州学派研究产生断层。直至1993年方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得以刊刻出版,昭示天下,为泰州学派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今年是颜钧逝世整四百周年,作此文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