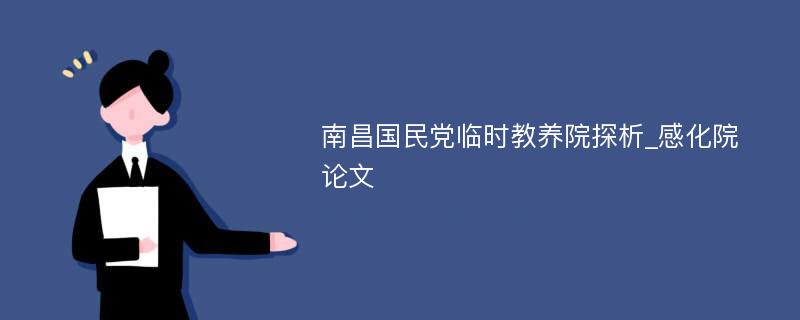
国民党南昌临时感化院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感化院论文,南昌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蒋介石在遭到四次“围剿”的失败后,痛定思痛,认真检查,重新调整了其反革命手段。他抛弃了过去单纯用军事“围剿”红军的方针,确立了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原则的反革命“围剿”新方略。南昌行营南昌临时感化院(以下简称感化院)的设立,正是实施这个反革命新方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剖析感化院设立的目的、内容及其作用,对于我们探索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渊源意识,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自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
感化院隶属南昌行营第四厅,它于1933年8月6日奉命开始筹备。为了及时配合国民党军事上的行动,整个筹建过程紧锣密鼓,有关各方为其大开绿灯。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感化院便在南昌城外西南隅的老营房正式登台亮相了。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办事方式,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国民党机关中实属罕见,它反映出蒋介石对感化院寄托了重任和厚望。
南昌行营十分重视感化院的工作,特地制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临时感化院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感化院的教育方针、机构设置、各机构的职能、感化对象及工作内容和要求,做了详细规定和说明。
根据《条例》规定,感化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具体工作则由院长办公室负责处理。院内还设有总务科、训育科、工艺厂、医务所等机构,并办有其机关刊物《感化月刊》。
总务科,主管文书、庶务、会计及维持全院一切秩序事宜。
训育科,主管实施感化教育,并担任辅助教育及被感化人一切管理事宜,实施感化教育则是工作重点。该科除设训育、处理等室外,还根据感化对象的来源,设计了三个部。一部,又称投城部。专门收集、感化投诚人员。所谓投诚人员,实际上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二部,又称俘虏部。专门收集、感化俘虏人员。三部,是后来由江西反省院并入的,又称反省部。专门收集和感化在感化期满后,国民党认为“其思想言论行为”尚未“彻底觉悟”(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临时感化院条例》见《感化月刊》第一期)之人员,直至其觉悟时为止。所谓未彻底觉悟者,实际上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各部之下,设有班、组。一般以50人为一班,各班都配备了教育长和训育员,以便进行管理。
工艺厂,主管被感化人员之技能教育、工厂管理及采办工业材料、销售物品一切事宜。并按地方情形,附设相当手工厂。工艺厂既有感化功能,又有经济功能。
医务所,主管被感化人员的诊疗和疾病预防之职。医务所既是保证感化院这一机构正常运行的条件,更是为感化院装点门面的摆设。
感化院接收的感化对象,主要是第五次“围剿”时期(包括前、后期)投诚和俘虏的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官兵中的四种人员,即:“一、无家室,无职业恒产,又无产谋生者;二、在恢复‘匪区’(即苏区)尚未安定之前,因特殊情形,未能回家,或尚须限制其自由者;三、曾在‘匪区’担任重要工作,尚须经过相当期间之考察者;四、经裁定应受感化者。”(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对于上述人员,感化院经过审问和履行入院手续后,根据各个不同情况,将他们分别送往训育科各部。各部则依据被感化人文化程度的不同,以及受共产党影响程度的深浅,将他们分成四级,编成若干个班,采取不同的感化教材和感化方法。
感化院进行反革命感化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造谣诽谤。感化院训育人员对感化对象拼命灌输反共思想,大肆宣传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正统性、合理性,污蔑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是非法的。他们把共产党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作法,说成是“遂心愿私欲”,是“盲人骑瞎马”,胡说什么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在分配不均,而在土地之未垦殖与荒芜。”(注:见江西省档案馆卷宗43—24—2502—2504)国民党企图通过造谣诽谤,来挑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及其政策的不信任,引起人民群众对红色革命正确性的怀疑,使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行动丧失信心,从而破坏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第二,欺骗恫吓。感化院筹建之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之际。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仅用3 个月便吞并了我东北三省,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又出兵占了山海关、热河一带,并继续进犯长城各口,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号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却置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捕杀爱国志士,“集中党政军民意志与政、经、心、军事力量”,(注:台湾《反共勘乱》上篇,蒋纬国)进行反革命“围剿”战。感化院的训育人员,奉主子令行事,恶毒攻击“中国的大患”是红军,“现在所难者,就是我们不能使国家平安,大家不能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有一种相当的职业,同时政治上有许多好计划,都无法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匪’(指红军)扰乱内部。”(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如果不赶紧消灭红军,中国就要“亡国”、“灭种”、“变为禽兽的国家”等等。感化院的这种做法,是企图替国民党政府推脱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本应承担的责任,掩饰他们对内残酷镇压,对外软弱无能的丑恶面目,嫁祸于共产党人。这是反革命派玩弄的一贯伎俩。
第三,现身说法。为了加强感化效果,感化院的负责者费尽心机。他们把被感化的人,也就是那些革命的叛徒,视为感化对象的榜样,让他们现身说法,或是以报告和交谈的形式与感化对象面对面的交锋,或是以文字的形式,在《感化月刊》上发表所谓的心得体会。这些革命的叛徒,由于熟悉感化对象的生活环境,了解感化对象的思想状况,知道感化对象最主要、最迫切和最关心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因而在实施感化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现身说法的感化手段虽然有直观性和生动性的特点,但是,国民党反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这种集身教和言教于一身的感化效果只是暂时的,对于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来说,这种现身说法的感化,丝毫不起作用。
(二)
感化院以蒋介石所谓的“为救青年于危殆,为保全国家之元气,不忍一一置其于绝境,才本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设立感化院以感化教育,除其顽劣使成善良。”(注:《感化月刊》第三期)为宗旨。用抚缓和教化两套手法,来感化和笼络被感化者,消除他们头脑中的革命思想,灌输所谓的“三民主义”,瓦解其革命意志,使之成为“出院后能用本所薰陶应用于社会”(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的人,甚至能与国民党“同心一德致力于剿匪任务之配合”(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从而“消除剿匪军事后顾之忧,补国家教育所未逮。”(注:《感化月刊发刊词》见《感化月刊》第一期)达到蒋介石彻底摧毁红色政权,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的最后目的。
感化院设立的宗旨和目的能否实现,关键在训育人员。训育人员的思想观点和行为规范对被感化人员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论语·子路》)尤其是,感化院是一个特殊的说教机构,训育人员与被感化人员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教育机构中的师与生的关系。训育人员在进行感化教育的同时,一部分意志坚定的红军官兵,必然会用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情感和唯物主义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感化活动。因此,感化院必须建立起一支忠于国民党反动政权,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训育队伍,以确保感化成效。
感化院从设立起,对训育员的挑选就十分严格。训育人员由反动军官担任,对国民党来说,这些反动军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是无须置疑的。当感化院因工作需要向外招聘训育人员时,院方的审查是严格细致的。这些外聘的训育员除了要接受一般的基本情况调查外,还要接受院方有关人员的特殊的全面考核。考核的内容有:中国需要何种政治;何以必先剿匪而后抗日;谁是我们唯一的领袖及其理由。这些内容主要是考核训育人员对蒋介石及其政策是否忠诚。外聘人员能否任聘,这是第一关。如果这一关有卡,其它的就免谈了。考核的内容还有感化的意义和感化院的使命;怎样去训育被感化人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考核训育人员的业务素质。训育人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毕竟不能相互替代。如果对感化的意义重视不够,对感化的使命了解不透,对感化的手段掌握不多,感化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外聘人员能否任聘,业务能力又是一关。体力、品行也是影响外聘人员能否任聘的考虑因素。感化院之所以如此严格挑选训育人员,就是为了实现蒋介石感化院为反革命围剿战争服务的宗旨。
训育人员上任后,并不是万事大吉了。在“革命化、团结化、纪律化”的原则下,南昌行营要对训育人员进行定期的训练。训练大纲规定,国民党党义,国内外政治经济概况,“匪乱”原因及其崩溃之必然性、地方自治与自己管理方法、本院各种法规及新生活规律等课目,为训育人员训练的必修课程。对训育人员的定期训练,对于提高训育人员的工作动力和能力,“把握感化人,籍以增进训育效率,而利于感化业务”(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而言,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正因为感化院是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新方略的实现,是以为反革命围剿战争服务为宗旨,因此,感化院不同于国民党的其它反动机构,它具有特殊的职能。第一,军事的职能。感化院从建院的第一天起,就带有军事机构的性质。训育人员是由反动军官担任,感化班级每班都配有上尉训育长一名,中尉训育员二名,感化院还设有卫兵排(后改组并入总务科)。军人主政,赤裸裸地暴露了感化院对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军事镇压的性质。为掩人耳目,感化院由军事机构改为行政管理机构。但是,感化院的军事职能并没有变,它的目的,依旧是配合蒋介石的“围剿”战争,感化院的人员,不过是脱下军装,换上一套便服而已。被感化人员,一律是按军队条例进行管理。他们每周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军事训练。被红军俘虏后又参加红军的原国民党官兵,经感化后重新被送回国民党部队,充当炮灰。
第二,法院的职能。被感化人员从入院到出院,要通过严格的审讯,院方根据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处理。当被感化人员从四面八方被送至感化院时,是进院感化还是直接回原籍,并不依被感化人员的意志,而是院方经详细审讯后定夺。入院感化者经三个月的感化后,对是去是留,去向何方,也不是依被感化人员的意志为据,而是院方强制性地作出裁决。院方认为被感化者思想言论行为能彻底“觉悟”者,也就是对国民党的现行统治不再构成破坏因素者,“依法”遣散之。被遣送出院的人员,有的是被送回原籍;有的被送往国民党军队,充当“围剿”红军的走卒;有的被送到相应的工厂当劳工。院方认为被感化者的思想言论行为尚未彻底“觉悟”者,也就是坚持革命立场者,则被延长感化时间,直至“觉悟”时为止。院方认为不可感化者,则被送往南昌行营军法处论罪。由此可见,感化是假,镇压革命是真。
第三,监狱的职能。在感化院接受感化期间,入院感化者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无条件地受到院方的监视。被感化者想学什么,做什么,由不得自己,他必须接受院方的安排。感化院的大门,也不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感化院实际上是不挂名的监狱。
第四,工厂的职能。感化院为了感化的需要,“按照被感化人之程度,授以相当手工技艺,并按地方情形,附设相当工厂”,(注:《处置投诚俘虏及被感化人之审查训育及资遣程序》见《感化月刊》第一期)使“无产谋生者”在离院后能够拥有一门手艺谋生或留厂当劳工,使之“安分守己”,不再从事“赤色”活动。国民党在这里犯了一个颠倒本末的错误。人民之所以革命,并非是人们缺乏技艺,无以谋生,而是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纵有特长,日夜工作,也难以生存,人民才不得不揭竿而起。但是,感化院这种用小恩小惠收买民心,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安于维护现状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欺骗性的。此外,感化院所设的工厂实质上就是国民党榨取被感化人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掠夺被感化人员劳动果实的场所。
(三)
感化院从1933年8月开始筹建,到1934 年底随着第五次“围剿”的结束而撤销(后迁往九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强行接受感化者的人数,从1933年10月首批接收的500多人,发展到1934年8、9 月间的12,000多人。感化院这一集“军队、学校、工厂、法院”为一体的特殊机构,在它存在的短暂时间内,极尽威胁、利诱、造谣、诬蔑之能事,为蒋介石反革命新方略的实施和第五次“围剿”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感化院的设立配合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在红军战俘中展开了一场政治“围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对历史发展“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由于战争由人民来进行,所以战斗行动的积极性和坚决性主要取决于人民对战争的态度。(注:《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一版,89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众所周知,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战争,但实质上它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与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之间的阶级大搏斗。这场搏斗的结局并不取决于一个战役或一场战争的胜负,而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争取民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基于这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不但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安抚民众、借以笼络人心的改良措施,而且想方设法在被俘的红军官兵及苏区干部群众中展开了政治攻势,妄图实现既俘人又俘人心的目的,从而最终彻底消除“匪患”。感化院的感化活动,实质上是政治诱降,它积极配合了军事上的“围剿”。
第二,感化院的活动,转化、瓦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一部分意志不坚定分子,削弱了一些人的革命意志,这些人的变质,在社会影响方面,对革命造成严重的消极作用。感化院的感化对象主要是红军中投诚者和被俘人员。无论这些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失节变质,他们都曾经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人。如果有时间和条件让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接受锻炼,他们有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可能。但是,感化院强制实行的感化活动,把他们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去了,使他们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其结果,是反革命队伍得到加强,革命力量遭受削弱。而这些曾经革命最终叛变革命的人,对于在社会尚持中立态度的人,起了消极的影响,在他们的心理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他们对革命的疑虑更加加重了。
第三,感化院的设立,掩盖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性。为了更好地实现蒋介石设立感化院为反革命“围剿”战争服务的宗旨,院方在对被感化人员进行反共宣传和教育的同时,实行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如,授以技能、介绍职业,收留无家可归人员等,对被感化人员进行抚缓和拉拢,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军队“师其所至,带至民众,伤之残废,疮痍满目”(注:蒋介石《庆祝剿匪胜利之意义》1934.12.10)装点门面,为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套上一个善良的假面具而已。即使是在冠以感化这一动听言词的感化院内,国民党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本性也是难以掩饰的。入院感化人员,没有良好的待遇,没有人身自由,伤病人员得不到治疗,许多人因此死亡。据1934年1月《感化月刊》透露,在1933年12 月至1934年1月间被感化人员就有191人在院内死亡,占当时入院人数的17.19 %。从感化院出来的人,他们的归宿并不理想。不过,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感化院的蒙骗作用暂时还是可以存在的。
感化院在贯彻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中,是不遗余力的。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的111名被感化人员中,被资遣出院者349人,被遣送回国民党部队15人,保释7人,三项出院人数共371人, 占总人数的33.39%。1934年8月至9月间,在院人数12933 人, 出院者5132人占总人数的39.68%。从这一组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 大多数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群众,经受住反革命严峻的考验,坚持了革命立场。与此同时,感化院在配合国民党军事“围剿”红军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蒋介石虽然用心良苦,但感化院的结局,就象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一样,最终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