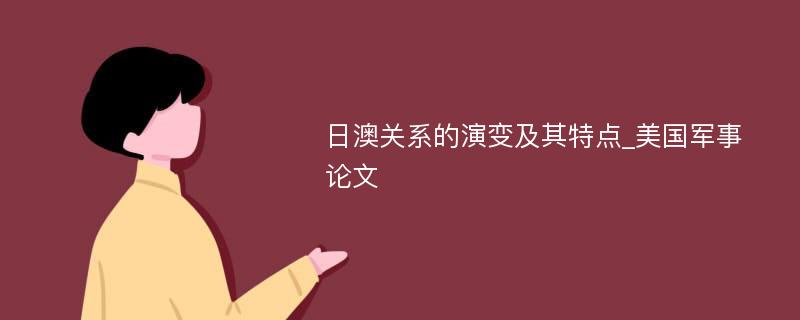
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两国在各自的区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在保持与美国紧密同盟关系的同时,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从经济逐渐向政治、安全合作等方面发展,战略同盟的色彩日益浓厚,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冷战时期的日澳关系:以经贸关系为重
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曾经遭受过日本的侵略,这对澳大利亚的日本政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即使日本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改造后,澳大利亚仍然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对日本抱有一定的戒备心理,这自然会影响日澳双边关系,包括双边经济关系。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澳大利亚在对日贸易中采取了严重的歧视政策。1957年和1958年,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的商业协定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1962年和1963年两次修改之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因为澳大利亚消除了对日本的歧视性条款而进入了完全互惠的时期。自此之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联系的增强为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70年代,日澳双边关系转入迅速扩大和深入发展时期。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国际突发事件的发生以及日澳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增强①。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收缩和英国放弃英联邦特惠制、加入欧共体,迫使澳大利亚把外交目光转向日本,希望双边关系得到发展。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也把目光投向了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在上述背景下,日澳关系在70年代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双方希望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其标志就是1976年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the NARA Treaty)的签订。条约确立了日澳两国间以及两国国民间永久和平与友好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确定了这样的目标:促进两国间以及两国国民间的了解,发展在相互关心的事项上合作来扩大和加强两国关系。具体规定有: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在经济、贸易以及通商领域中的合作;扩大能源方面的贸易和开发方面的合作;互相给予对方国民在入境、逗留、旅行、离境以及进行事业、职业活动方面公平而同等的待遇,其待遇不得在对方国民和第三国国民间有所歧视,等等②。该条约是日澳关系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奠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该条约签订30周年之际,有澳大利亚学者评价指出这是日澳平等公正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框架性协议,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③。
在这一条约的指导下,日澳双边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70年代中期起,日本就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80年代,两国确认了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的依赖关系,而且澳大利亚还在日本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中与日本进行了紧密的协作。1980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举行会谈时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主张“应当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文化合作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合作关系”,在得到澳大利亚的赞同之后,大平正芳在墨尔本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时代的创造性合作关系》的讲演,认为“太平洋地区已具备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的条件”,应着手实现“承认并尊重各国文化独立和政治自决的区域合作”、“适应全球社会时代的开放的区域合作”,公开了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④。其基本主张对以后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0年9月,由澳大利亚和日本发起成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在堪培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展现了环太平洋合作的雏形,后来演变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1982年5月,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访问日本时表示双方“基本上一致同意要进一步推进”两国倡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中曾根内阁的大洋洲外交,着重以发展日澳关系为中心。1985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澳大利亚,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会谈中提出了亚太合作的四原则:即(1)在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2)以民间为主导;(3)合作体制是开放性的,而不是排他的;(4)以东盟为主导进行合作。并提出两国不仅要发展经济关系,而且在核裁军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以相互合作的“伙伴”形式,建立两国间的成熟关系⑤。澳大利亚对此表示完全赞成。日澳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日本很快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促成了日澳首脑互访和部长级会议的定期举行,两国不仅双边关系得到协调,而且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逐渐增加。
冷战后至21世纪初期:日澳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澳经贸关系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1989年1月,第十届两年一度的日澳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首次提出了建立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鉴于日本在澳大利亚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1990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日时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称澳大利亚对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柬埔寨或者海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是可以接受的。霍克宣称,“日本的国际政治影响不能匹配或者应该落后于它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的时日应该成为过去。”⑥ 1991年5月,第十一届日澳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同意在安全领域尤其是确保双方所在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维持和加强自由和开放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寻求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环境保护以及全面深化双边关系等四个方面展开合作⑦。由此看来,日澳合作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双边的范围。外交上,两国高层领导人也不断互访,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分别在1992、1994、1995年三次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1993年访问了澳大利亚。其中,1992年9月基廷访日期间在联合公报中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要求,并重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则支持澳大利亚关于召开“亚太国家政府首脑会议”的提议⑧。1993年起,澳大利亚开始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实现离不开日本的有力支持。
为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1995年5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了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是对《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的修订和完善,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肯定以及21世纪两国关系的规划”⑨。两国政府认为,两国的经济合作、人民的友谊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决心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一道“促进繁荣,减少冲突,加强政治合作”,“日本政府欢迎澳大利亚为它在本地区的未来所做的决定以及重申澳大利亚在地区性事务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伙伴”,肯定了澳大利亚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⑩。所谓“建设性伙伴关系”,就是在提升双边关系质量之外,在多边事务论坛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以及协调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政策等方面,形成日澳磋商的轴心机制(11)。1996年和199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进行了互访,日本方面提出了每年举行总理会晤以及18项双边和多边合作议程,双方都强调了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的义务以及不断提升两国防务关系的愿望。日澳两国新的伙伴关系并不表现在贸易方面,而表现在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升级。在政治方面,两国同意每年定期举行首脑会谈。两国政府首脑决定,将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纳入两国“伙伴关系”之中(12)。
90年代,日澳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1990~1999年,日本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年均增长2.2%,进口年均增长0.4%;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出口年均增长0.6%,进口年均增长2.1%(13),日澳经济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虽然双方在经贸领域有一定的摩擦,但这种摩擦“被积极的政治同盟、牢固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以及对正在进行的地区性合作的坚定的支持所抵消”,两国政府都表示要继续加强“持久而牢固的伙伴关系”,并把这种“最亲密的伙伴”关系带入21世纪(14)。
21世纪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军事同盟色彩日益浓厚
进入21世纪,日澳关系除了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继续平稳向前发展外,双方之间也日益重视安全合作,战略同盟的色彩日益浓厚。
早在1997年,两国政府就决定进行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进入21世纪,这种合作进一步发展。2002年5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澳,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主要内容为双边自由贸易和澳、日、美三边安全合作(15)。日本是澳大利亚的最大出口国。澳对日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煤炭、矿石、肉类、铝和石油等,农产品出口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比例,主要是受到日本国内保护政策的限制。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要求与日本达成包括农业在内的自由贸易协议,但是澳大利亚此前的努力屡屡受挫。日本政府首次主动开始与澳大利亚政府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并以此为突破口,与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同盟。小泉在与霍华德的会谈中,讨论了澳、日、美三方安全合作问题,准备由三方高级官员以年会的形式进行对话。
日、美、澳三方安全对话最初是在2001年7月日本和澳大利亚在越南河内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时由澳大利亚和日本官员提出。同年8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澳时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会谈时再次提到了三国安全对话。该提议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积极响应。唐纳强调,日澳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稳定有重要意义;美国则看重推动同太平洋地区两个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开展更广泛地区对话的必要性;日本则想以三国安全对话为借口发展军事力量并与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同盟。唐纳和鲍威尔均强调,这种三国间安全对话机制不会作为正式机制存在,也不会发展成同联盟构架同样稳固的机制(16)。美、日、澳三国之所以建立这种安全对话机制有其深刻背景。第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多边机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作用日趋削弱。第二,美、日、澳三国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忧心忡忡。第三,出于对诸如全球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的担忧,澳日两国保守政府最终下定决心,与美国结成三方同盟,共同应对上述威胁。三方安全对话在2002年开始启动,并一直保持在副部长一级。2005年美澳外长双边会谈中讨论了伊拉克问题和反恐问题,提出将会谈“提升”至外交部长级别,澳大利亚希望敦促日本调用更多的技术专家和资源,用于打击东南亚的极端势力。2006年3月,首次美日澳三国部长级安全对话在悉尼举行。这是三国安全会议机制建立以来最高级别的磋商。
为了落实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日澳双方在安全上密切合作。九一一事件后,澳、日都积极支持并参与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两国都派兵到阿富汗参战。日本还派军舰为美国提供后勤支持。伊拉克战争之后,日澳两国都参与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澳大利亚军队为驻扎在伊拉克的日本自卫队提供安全保护。与此同时,澳、日又都向东帝汶派驻军队,并肩参加维和行动。此前,两国还在柬埔寨监视停火、东帝汶联合国维和等行动中合作过。2004年12月印尼苏门答腊地震时,两国军队一起开展过救援活动。2006年9月,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时宣布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
21世纪初以来日澳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的签署。2007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了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宣言在“强化合作”主旨之下,澳大利亚承诺支持日本对朝鲜的交涉立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各自在本国法令范围内,加强和深化“安全与国防部门的合作”,合作的领域包括:打击跨国犯罪、边境安全、反恐、裁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和行动、交换战略局势的有关情报、海上与空中安全、人道救助、紧急应变计划等。为了达成这些合作,双方将交换人员、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并致力于“建立区域能力”(regional capacity building)(17)。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宣言可使两国合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签署澳日安保宣言意味着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安全关系将仅次于澳美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份共同宣言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的安全协议,将为日澳两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正式的军事交流和更紧密的合作扫清障碍。除了签署安保宣言外,两国还就建立“外长+防长定期会晤机制”(“2+2”机制)达成一致。目前日本仅同美国有此机制。这一宣言签署后,日澳两国可能共享情报,日本自卫队也可以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参加演习。该宣言的签订,可以看作是日澳向着同盟发展的一个原则性文件,为21世纪日澳安全关系上的合作指明了基本方向。
日澳关系演变的特点
第一,浓厚的地缘政治经济色彩。
一般来讲,地缘政治学认为空间或者地理环境对国家战略与国际关系有一定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大国竞争的枢纽地带,或者资源丰富的地区,尤其是资源丰富的战略地区,往往成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关键,也成为现实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如果国家有在国际上发挥重要或领导作用的意愿,这些地理区域的获得或丧失,可以增加或者削弱国家实力,则该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权力及地位会相应增加或受到削弱。而地缘经济学则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间存在一定关系。它意味着,凡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关的一切地缘变量均属于地缘经济学探讨的范围。这些地缘因素至少包括以下方面:自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分布状况;自然生态环境;特定地缘范围内人口构成中的人文背景;特定地缘范围内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历史及现实关系等(18)。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澳大利亚是孤悬在南半球的一个类似岛屿的大陆,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对日本而言,要提高对本地区的主导权,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希望得到作为西方国家一员的澳大利亚的支持;而澳大利亚也可以借助日本实现其“面向亚洲”的政策,提高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由于距离对国家实力的侵蚀作用(距离与国家实力成反比例关系),两国互相借重自然在情理之中。此外,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有丰富的铁矿和铀矿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铁矿石大量出口,铀的储量则占世界已知储量的1/4。这对资源贫乏但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资源因素。
第二,建立了较稳定的制度化合作机制。
按照罗伯特·基欧汉的解释,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19)。就正式的规则而言,日澳双方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在经贸、政治、安全等方面建立双边或者多边的协商合作制度。为协调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1963年2月,作为两国商人之间互相联系和交流情报的论坛——日澳经济委员会成立。1967年10月,在日本首相访澳之后,两国建立了两国外长每年定期磋商机制,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70年代初,为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由外交部领衔包括其他七个部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随着上述措施的逐步落实,1972年,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召开。此后,这种定期轮流主持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成为日澳政府间讨论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问题的最重要的常设机构。日澳两国政府领导人互访极为频繁,首脑会晤机制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国在地区安全和防务中也紧密合作,与美国一起建立了三方安全会晤机制。日澳《安全合作共同宣言》决定两国建立“外长+防长定期会晤机制”(“2+2”机制)。在亚太地区国际事务中,日澳双方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建立了预先磋商机制。
第三,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制约。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霸权国家,称霸全球是冷战后美国国际战略的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与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双边或者多边的联盟体系,以抵消距离对美国影响力的侵蚀。在亚太地区,美国与第一岛链的日本以及地缘战略地位重要的澳大利亚都缔结了安全联合保障与军事条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都在冷战后加强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澳关系虽然带有内生性的经济利益驱动,美国也没有干涉日澳经济关系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和主导,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会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在现有的国际形势下日澳双方的力量还是不够强大,美国在与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机制就是在美国的提议下进行的,进而日澳双方签订《安全合作共同宣言》,破除了三边关系中日澳之间互相排斥的双边同盟网络。美国甚至想把印度拉进来组成一个四方联盟。
第四,冷战后日澳军事同盟色彩渐浓。
格伦·施奈德(Glenn H.Snyder)认为,同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的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被明确地写入条约澳大利亚政府也许不这么认为,但它愿意与日本签署安全协定以在双边或者多边安全协议中平衡中国的力量(20)。
当然,日澳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日澳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日本国内对高度受保护的农业部门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2002年,当澳大利亚首次提出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时,遭到日本的拒绝。此后日本选择的自由贸易协定伙伴一直限于那些对日本仅有少量农产品出口的国家。澳大利亚一直希望日本降低牛肉、大米和奶制品等农产品的关税税率,但日本仍将把部分农产品排除在同澳大利亚的谈判之外。另外,中国对日澳的安全合作保持着警惕,这对日澳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态度形成了某种压力(21)。
从上述演变过程、特点和原因来看,日澳关系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安全在内的双边关系的整体,双边关系的演变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既有它们自身的需求,也跟外力因素即美国的作用和中国的崛起密切相关。沿袭现在的演变态势,日澳是否会逐渐走向正式的军事同盟,与美国一起形成西太平洋地区的“小北约”(little NATO或者mini NATO)令人关注(22)。考虑到日本、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图谋,日澳关系的发展必将给亚太安全形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487页。
②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489页。
③See Drysdale Peter," Did the NARA Treaty Make a Difference? "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December 2006,Vol.60,Issue 4,pp.490-505.
④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574页。
⑤刘樊德:《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⑥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Australia' 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3,p.229.
⑦Ibid.,p.228.
⑧贺晓琴:《面向21世纪的澳大利亚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39页。
⑨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⑩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Australia-Japan Partnership,May 26,1995.http://www.mofa.go.jp
(11)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eds.,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2.
(12)Alan Rix,Australia-Japan Political Alignment,1952 to the Present,New York:Routledge,1999,p.40.
(13)Report on Japan-Australia Stronger Economic Relations,March 2001.http://www.meti.go.jp/english/report/data/gReAuste.pdf
(14)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第258页。
(15)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nd Prime Minister Junichiro Koizumi.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204/joint.html
(16)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Powell,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Rumsfeld,Admiral Dennis C.Blair,Foreign Minister Alexander Downer,Minister of Defense Peter Reith,and Admiral Chris Barrie,Joint Press Conference,AUSMIN 2001,Canberra,Australia,July 30,2001,pp.1-10.
(17)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March 13,2007.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joint0703.html
(18)丁志刚:《新兴地缘经济学独特的地缘战略视角——大国地缘经济战略争夺的新态势》,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2期,第21~26页。
(19)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5.
(20)Richard Tanter," 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s,March 17,2007.
(21)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希望有关国家在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时,能够照顾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切和利益,多做有助于增进本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及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参见《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载《人民日报》2007年3月14日。
(22)西方学者对此早有探讨。See 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 Japan,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4,No.2,August 2004,pp.265-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