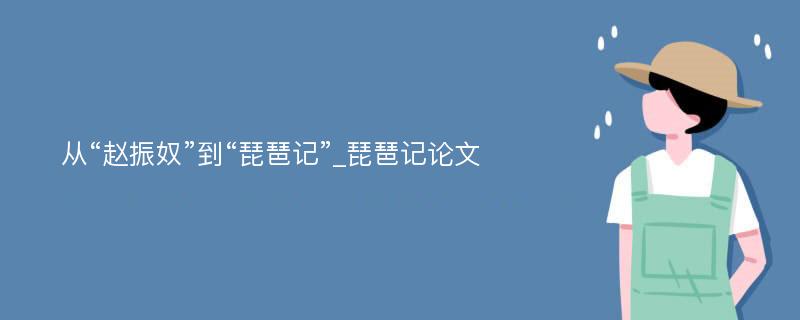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贞女论文,琵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琵琶记》是高则诚根据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重新创作而成的。
明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徐渭《南词叙录》也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徐渭在该书“宋元旧篇”内著录第一种便是《赵贞女蔡二郎》,并注云:“即旧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
《赵贞女》原作已佚。据各种记载拼接,其情节大致如下:蔡伯喈中状元后入赘相府,背亲弃妻。其妻赵贞女在家乡独力奉养公婆;饥荒年岁,公婆双亡,贞女剪发买葬,罗裙包土,修筑坟台。后来,天上降下一面琵琶,贞女便怀抱琵琶,弹唱为生,上京寻夫。但伯喈不仅不认其为妻室,而且放马踹死赵贞女。这一行为人神共愤,逐雷殛蔡伯喈,以悲剧收场。
这种以书生负心婚变为题材的悲剧性创作,在早期戏文中颇为常见。今可考知名目的即有《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陈叔文三负心》、《李勉负心》、《张资鸳鸯灯》、《崔君瑞江天暮雪》、《王十朋荆钗记》、《王宗道负心》等多种。这些戏文,今天只有《张协状元》一种尚存。其中《王十朋荆钗记》,今传明刊本与《琵琶记》相同,作不负心结局,但据《瓯江逸志》记载,原作写十朋与妓女钱氏的婚变故事,十朋中状元发迹后抛弃了钱玉莲,玉莲投江而死,则亦以悲剧收场。上述诸篇因宋元相传,随时而增删,流传至明代,大多已经难以判明具体创作时间。但从故事的形成看,其最初撰入戏文,应均在宋亡以前。如《王魁》、《赵贞女》已有祝允明、徐渭的记载;而《武林旧事》记宋代官本杂剧,已有《李勉负心》、《王宗道休妻》诸目,均可为证。另外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宋代说话艺人的表演:“噇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蒙羞。 ”其中所列“传奇”类即有《王魁负心》,“负约”类有《王魁负约,桂英死报》、《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即《鸳鸯灯》之本事来源)等,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四则有《李云娘——解普杀妓获恶报》、《陈叔文——叔文推兰英堕水》等。而陆放翁《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之四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诗作于1195年。放翁所听到的鼓词,其敷演的也正是关于蔡伯喈的负心故事。这说明负心婚变是当时戏曲小说等民间伎艺所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
《赵贞女》、《王魁》也是宋代有关书生负心婚变悲剧性创作的代表作品。以《王魁》为例,有关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几乎遍及宋代各种民间伎艺,流传极广。王魁,实有其人。本名俊民,宋嘉祐辛丑(1061年)状元,曾任徐州判官、南京发解官。因患狂疾,自刎不殊,后误服药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话本与戏文中,他与妓女桂英的婚恋纠葛是这样的:王魁下第失意之时,得到妓女桂英的资助,相约结为夫妻。在再度上京赴试时,与桂英在海神庙焚香为誓,决不相负。后王魁状元及第,授徐州判官,嫌桂英寒贱,背盟负心别娶。桂英遣仆送信,王魁叱而不受。桂英愤极自杀,其鬼魂偕鬼卒追捉王魁至海神庙,证其负心,索命而去。这里,王魁的负心,不仅是感情上的背叛,而且是道义上的相负。桂英的怨愤和疯狂的行动,之所以赢得世人的同情,是因为正是由于桂英的温情和金钱的资助,才使得王魁重新振作起来,高中魁首。没有桂英,也就没有王魁之今日。负心兼忘恩,才构成了道德上的巨大缺憾,使得王魁的作为与桂英的心愿及社会期待之间,形成激烈的冲突,从而构成一幕真正的悲剧。不过,这里表现的是书生对个别女性的背负,并以女性自身的复仇为结束。
《赵贞女》的悲剧设置,则超越了这种个体的恩报复仇框式,转而诉诸“天理人心”。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较多地诉诸渗入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教伦常,并以这种伦常道德观念作为构设悲剧的基础。孝养双亲,独行丧礼等等,都是礼教中最为敏感,也是最能打动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人的心灵的高尚行为。赵贞女的作为,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恪守礼教规定的妇道,而是达到了贞烈的境界,堪称妇道之典范。这样的女性,在社会民众的心目中,理当苦尽甘来,善有善报,得到发迹后的丈夫的礼遇,得到朝廷的旌奖,获得官诰霞帔。这也可以说是由社会的期待所构成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而这样的贞女,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报答,反而被中状元的书生抛弃,甚至放马踹死,才显得无比的惨凄,令人为之呜咽、为之愤慨,为之心潮难平;才在道德的神经上,构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悲剧,人神共鉴,非天殛之不足以平息这种道德的义愤了。
所以说,桂英的被负,只是个体的被负:其报复,只是个人的复仇。而《赵贞女》中,这种被负,已经不再属于个体的被负,而是蔡伯喈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蔑视和对抗;他所受的报应,不是赵贞女个人的复仇,而是道德天理的谴责。因此,在悲剧的构成中,社会的伦常道德观念成为重要的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赵贞女蔡二郎》中,对赵贞女的刻划,必然会按照礼教的要求而予以强化。可以想见,正如后来在《琵琶记》中的表现一样,赵贞女是按照礼教妇道的要求,默默地尽到自己责任的。丈夫不在,面对饥荒,宁愿自己受苦,也尽一切努力,使公婆得以维持生活。公婆死后,苦心营葬,罗裙包土,筑造坟台。这也是替丈夫尽孝,免使丈夫遭不孝的罪名。“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养老和送终,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既是礼教孝道的涵义,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上,赵贞女的作为确实称得上一个贞烈的孝妇。她应是温柔敦厚,纯朴善良,任劳任怨的。所以她不会作出桂英那样疯狂的举动。她的柔弱、善良,更反衬出蔡伯喈的卑鄙。同样,最后的报应,也只能由上天来主持正义,而不能由孝妇来作报复。这可以使赵贞女始终保持温柔敦厚与纯朴善良的形像,也使得道德的反差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在《赵贞女蔡二郎》中,赵贞女是一个完全符合礼教的有贞有烈的孝妇。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形像是图解礼教概念之后敷演出来的,而是说,这一动人的形像的具体行为,同时也是符合礼教社会的最高要求的;而且也可以推想,创作此戏的书会才人们,也是有意识地按照礼教的观念对此作了强化的。如果不是过分纠缠于书生是否负心及不负心事件是否“真实”,人们不难发现高则诚把它转化为“只看子孝共妻贤”的一夫二妻故事,其实并无多少“强扭”的痕迹。只是《琵琶记》不仅继续保持了赵五娘有贞有烈的品行,而且把男主角也改成合符礼教的孝子,即不过是继续把礼教道德内涵作为新的悲剧构想的基础而已。由此可见,高则诚并没有以“图解概念”的方式,“注入”礼教内涵来“狂热宣扬封建礼教”。他只是在《赵贞女》原有的对于孝妇的肯定性描写的基础上,改造了蔡伯喈,使之同时也成为一个合符礼教的志诚的孝子而已。
将蔡伯喈改写成一个志诚不负心的孝子,某种意义上说,倒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因为历史人物蔡伯喈确以孝著称。《后汉书·蔡邕列传第五十下》云:“邕性笃孝,母尝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十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
从《琵琶记》的描写看,高则诚是充分地参照了《后汉书·蔡邕本传》的,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史实,因为完全按照史传事实是难以构成一部情节生动的大众化的戏曲的,何况原有的传说也已经深深印入观众的心底而难以改变。高则诚所做的只是在《赵贞女》故事框架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改造。对负心的“蔡二郎”,依照“历史真实”变成了“性笃孝”的蔡伯喈。剧中也记叙了蔡伯喈夫妇“庐墓三年”,“相驯白免走坟台”“连理木分两枝跨”,这种将史实与虚构故事相结合,大处为虚,细节逼真,故事非真,品性从实,正合乎历史剧创作中虚实相生的辨证法。因为中国戏曲中历史题材的创作,多数并不在乎史实,故事不妨杜撰,不妨附会,强调的是作品“境界”的完整性,追求的是人物的神似而非形似。而且这所“似”的也仍只是作者心中之模样,而非史书所刻划的形象。高则诚一面似乎是替蔡邕“雪谤”“辨诬”,还其孝子本来,另一面却仍坐实了蔡伯喈入赘相府,一夫二妇,以及未能直接完成终养及丧葬之事。在重史实的明人看来,后者仍是对于蔡伯喈“无中生有”的“厚诬”,便殊觉“不可解”了。
这确实是难事,若“辩诬”改成孝子,但不改变故事,则仍不脱“厚诬”;但若放弃原有故事,据史实干巴巴的敷演,则不仅毫无意趣,而且也改变不了民间仍以原来形式传演的事实,即还是不能“雪谤”。故从“辩诬”的角度而论,高则诚注定是“在夹缝中计生活”的了。幸好“辩诬”固然是高则诚的出发点之一,却并非唯一目标。
《琵琶记》改变了《赵贞女》背亲杀妻的结局,换成一夫二妇和睦相处,但并没有背弃原作对于负心婚变行为的道德谴责。从负心婚变悲剧故事表现的角度而论,或许高则诚认为,正面的歌颂照样可以达到劝惩的目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方式比之敫桂英的疯狂的复仇、赵贞女的悲惨,更切合于中国传统,更能为礼教社会的观众所接受。何况将一个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变成一个不顾廉耻的负心汉,将赵贞女这样善良的人物置于马踹而死的惨境,于心何忍。
对于高则诚这样的幼读《春秋》,深知“圣人笔削大义”的“长才硕学”之士,其笔下渗透了儒家的伦常观念与审美观念,应当说是不足为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残存的诗文,就有《王节妇诗》、《华孝子故址记》等篇;在处州时有申请旌奖丽水陈孝妇的经历;据《南词叙录》,则诚还作过《闵子骞单衣记》一剧。所以他进一步张扬了《赵贞女》中对于礼教孝道的肯定性内涵,也就无足奇怪了。我们虽然无从知道《赵贞女》戏文对赵贞女的具体描写,但从早期戏文的稚拙情况看,《琵琶记》对赵五娘的温柔敦厚、含怨负重的合于妇道的性格的准确把握,更多地是出于高则诚的再创造。牛氏小姐这个在封建妇道的严格培养中成长起来的相府小姐,虽然受到今人的多方讥议,却也确实是在封建时代的现实中可以找到若干例证的,虽非典型,至少也达到了“类型化”的水准。若与赵五娘易地相处,牛氏同样会做出赵五娘那样的举动。那种过分强调两极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认为封建的相府小姐决不可能接纳这位贫贱之妇的说法,其实只是以阶段斗争框式为指导而致的自说自话,不值一驳。
根据来自西方的美学观念,悲剧,是审美的最高范畴。明清以降廉价的大团圆形式的自欺与欺人,使人厌恶。所以人们更加向往宋代戏曲中悲剧涌现的局面,而悲叹明人对于悲剧的扭曲与消解,并提高到“国民性”的高度,进行反思和批评。笔者以往也甚为推崇宋代《赵贞女》、《王魁》等“彻底”的“悲剧”,以戏曲初兴而悲剧大盛,叹息其后盛况难再。静而思之,《王魁》、《赵贞女》未必便是中国悲剧的最好范式,它们头上的光环,只是后人根据故事的悲惨结局而幻化出来的。它是今人的“创造”,而非历史的真实。后世的《秦香莲》系列作品,也有作“纯悲剧”式处理的,但并未见其高明。而宋代的《张协状元》的稚拙情况,也可以推见当时作品所能达到的水准。故单以主人公结局的死亡为悲剧的标志,以西方悲剧观念而作“观照”与“投射”,幻设已佚剧目之本真,实未见其可也。
艺术创作自有其规律。主人公死亡的结局虽比团圆不死更能震慑人心,但以主人翁死亡为结局的未必就是“好”的悲剧。作品的成就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创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式”悲剧也仍有待于重新认识。解题的钥匙仍需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不必据西方悲剧观念遽下结论。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这是一个巨大的跃进。徐渭说,自《琵琶记》出,“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琵琶记》实际上成为整个元代戏曲(包括杂剧与南戏)的殿军。它的成功,预示了南戏传奇的兴盛和北曲杂剧的行将衰落。《琵琶记》由此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品,一如西方中世纪但丁的《神曲》。面对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琵琶记》返回到《赵贞女》的时代,而这又仅仅是为了一个“负心弃妻”的结尾?
从《赵贞女》式的以谴责书生负心为中心的表达,走向《琵琶记》的以“只看子孝共妻贤”为中心的表述,也并非高则诚的独创,而是时势使然。
因为,宋代那种直接的谴责性表现,在元代后期,已经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转化。更迎合普通民众的“大团圆”故事,已日渐流行了。
如《王魁负桂英》,元初有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杂剧,据题目应仍保持悲剧收场,而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内已列《王俊民休书记》,从“休书”关目看,应已与《荆钗记》的孙汝权套书一样,改作不负心了。故元未明初人杨文奎有《王魁不负心》杂剧,无名氏有《桂英诬王魁》戏文,早已为明代《焚香记》导夫先路了。
再如《王十朋荆钗记》,如前所述,据《瓯江逸志》,现存本的王十朋不负心团圆故事,也是属于后来所编。而《张协状元》、《江天暮雪》等作品,要么以宋代的原型悲剧收场,一如宋代的《王魁》、《赵贞女》,只是到元代以后才受到转换;要么是其原本已经具有转换型的特征,才在元未明初仍得以继续流行。而《李勉负心》等剧,则因为没有获得这种转变,入明以后日渐湮没无闻。
事实上,在元代中后期,负心婚变故事的谴责性主题,已日渐向歌颂性主题转化。所以同类作品如《秋胡戏妻》,原为其妻深感羞辱,耻于与不忠不孝不义之徒为伍,以刚烈的行动投水自杀,但在石君宝的杂剧中,结局已化作夫妻和好。又如,朱买臣休妻故事,原是其妻嫌买臣贫迂而离异重婚,在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中,已变成一出逼婿赴试的闹剧。在宋代,人们构设负心婚变悲剧,多有诬良为娼的现象,如蔡伯喈、王俊民的情况即是。可谓是悲剧创造的欲望所至,任意驱遣:而元代中后期,对于书生负心问题,则更多地是开脱、辩护、调和、化悲为喜。
元杂剧中的悲剧作品主要出自前期作家之手。到元代后期,已难以寻觅悲剧创作的印痕了。从悲剧创作的角度而论,可以说元代杂剧后期创作中,悲剧的失落,既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杂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末明初作家,不是制作轻松的喜剧,便是以表现神仙道化为洒脱。但元杂剧前期作家中以写神仙道化剧著名的马致远,他的神仙道化剧大都包含着对丑恶的现实的不满、愤慨和揭露,是痛苦的现实中无可奈何之余而借仙道以自解。而元末明初作家则纯粹是为歌颂仙道而描写出世,缺乏对现实的批判。前期作家如关汉卿,他的剧作,浸透着对现实的批判,泼辣而慷慨,而后期作家则向风流韵事的轻喜剧发展。积极入世、抗争、悲怆激烈的精神的丧失,既使得内容贫乏无力,也必然导致悲剧的失落。故高则诚说:“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强调戏剧应“关风化”,追求“动人”,便是有感而发的。
负心婚变主题在元代的变迁,其实也仍是社会的变迁在文学中的折射。
元代后期负心婚变故事的转变风潮,主要地是由书生地位的变迁决定了的。此外戏曲创作者阶层的身份地位、社会观念和同情对象的转换等,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在宋代,人们不惜以悲剧,以魂追、天谴来摧挫负心的书生,毫不假以辞色。这是因为宋代书生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美好的仕进前程,可谓天之骄子。无论是得意,还是潦倒,生活都向他们敞开大门,世界充满着阳光。然而,到了元代,书生们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之中了。
首先,元代科举之路不畅。
科举是封建时代书生得以发迹的唯一的也是最畅达的康庄大道。而蒙元王朝,除蒙古窝阔台的时期曾经开科取士外,科举中断长达78年之久。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重新开科取士,但也不是十分正常,如英宗时就一度中断。
元代科举取士名额极少。少则几十人,多者也不过百余人,而且其中蒙古、色目人古半。它只是笼络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政治手段,如明初叶子奇所说,“殆不过粉饰之具耳”(《草木子》卷四)。考试制度又规定汉人与蒙古人试卷有别。录取汉人时,又有汉人(北方地区)南人(南宋旧地)之别。南人更受压制。宋代负心婚变悲剧的勃兴,本与南方科举仕进之盛有关。元代既然科举之途不畅,南人又加倍受压,一般人发迹更是极其困难,谴责寒士发迹负心弃妻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社会的现实意义。而元后期,杂剧中心南移,杂剧与南戏并立于江南,它们在创作、改编上向喜剧化转变,即源于同一种现实。
事实上,元代即使侥幸通过科举登上仕途,也很难有所作为。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州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条)在民族歧视政策下,仕途并非坦途。
其次,元代以吏取士,元代官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刀笔吏升迁而来。而刀笔吏本是饱学的秀才们不屑一顾的事,更非他们之所长。
科举的不畅和以吏取士制度,元代书生们被堵塞了仕进之路,也失去了谋生之道。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虽然并非事实,但从宋代的天之骄子到元代与丐倡并提,却正道出了他们的辛酸处境。唐宋时代妓女与书生的恋爱故事,如《霍小玉传》、《王魁传》等,妓女都是仰视书生,哀惋可怜。而元人杂剧中,即转而变成妓女俯视书生了:杜蕊娘对于韩辅臣(《金钱池》),谢天香对于柳永(《谢天香》),都是如此。最常见的是潦倒的书生被鸨母斥逐,被商人用金钱夺去所爱。而妓女也瞧不起他们,宋引章说,跟着潦倒的安秀才,一辈子唱“莲花落”(《救风尘》)。一般女子与才子相恋的情况也是如此。唐代《莺莺传》中莺莺中夜忽放悲音,期望借誓言拴住张生,被弃后,也只能自怨悲泣。而元杂剧中,更多地表现为女性占据主动地位。谭记儿的泼辣,显出白敏中的软弱无能(《望江亭》),刘倩英瞧不起温峤,而温峤只能自诩志诚以求得欢心(《玉镜台》)。所以,宋代以悲剧摧挫书生们的傲气,而元代以喜剧抒写书生们的幸事,以显示自怜和被怜。
宋代虽有科场失意的书生偶尔进入书会才人行列,但他们也愈容易因为自己的困厄而产生对发迹变泰后的书生的不道德行为的不满,为谴责书生薄幸的悲剧浪潮推波助澜。元代则是饱学之士仕途潦倒无望之际,大批地走入下层社会,进入艺人们中间。如关汉卿即以杂剧创作为“我家风月”。这些曾为小吏的文人,用他们本应去做诗求功名的笔,撰写杂剧作品。如马致远曾为江浙行省务官。他们犹如被宋仁宗逐出试场,“且去填词”,而干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永),以戏曲为消解心中垒块的酒杯。他们成为元代戏曲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创作中更多地抒发浸透着血泪的身世之感,诉说仕途的困厄、恋爱的磨难,借前代文人浪子的得意之事,以慰抚饥渴的心灵;另一方面则悄悄地避开,渐渐地泯去往日书生得意之时留下的劣迹,代之以正面的歌颂,这也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文学也是一种理想,一种借以自慰的白日梦。文学总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对于大众化的艺术来说,尤其是这样。
在元代书生隐入窘境,自救不暇的时候,再揪住他们在往日得意时的劣迹,便如伤口抹盐,于心不忍。所以元代戏曲中,书生实际上成为同情的对象。虽然也叙写了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仍让他们志得意满,完满收场。这是社会同情的结果,也是人们聊以自慰的画饼,从中流露出对往昔盛世的深深的怀恋。所以,写仕途困厄,如《荐福碑》、《范张鸡黍》等,虽然命运摧挫,小人作弄,历经波折,但结局仍是如愿得官。写恋爱,必让张生高中状元,满足老夫人“三辈儿不赘白衣秀士”的愿望,为团圆作好铺垫。写与妓女的爱恋,一波三折,最终还是苦尽甘来,柳永终于娶了谢天香,杜蕊娘还是嫁给韩秀才。连既无文才也无前途,只是“志诚”而已的穷措大安秀才,最后也还是娶到了宋引章——因为富户周舍娶到宋引章,便转脸虐待她;而推究剧情,百计把宋引章弄到手的周舍,实在好没来由地忽然如此对待引章。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要表明:不要只看财富,不要只看外貌,只有书生才是真正的志诚辈!
既然书生们从被告席上撤了下来,成为社会同情的对象;既然只有书生才是志诚辈,那么,对宋代流传下来的表现书生负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造也是必然的了。悲剧转变成喜剧,其中书生一律都变成不贪富贵、不恋高枝、不忘糟糠妻室、爱情和道德至上的志诚种子。原来具有必然的悲剧冲突,变成了因误会而致的误解性冲突,不过是丞相的“牛气”(如《张协状元》)和小人的挑拨掀起的波澜(如《荆钗记》),歌颂志诚的“正面教育”,代替了暴露性的描写,既隐涵了对负心行为的否定,又弘扬了伦常道德,而且给人以善人善终皆大欢喜的结局。
至于朱买臣休妻故事,当初其妻是羞于买臣过于嗜书、行为乖张而求休的。在科举畅达之时,人们以买臣妻为笑谈。而在元代,不如说正好触到书生们的痛处了。改为激婿上进的喜剧,庶几可免却这种窘态(《渔樵记》)。同样,秋胡故事,《列女传》中,秋胡是婚后五日即“宦于陈”,官至大夫,属于书生之辈。在《秋胡戏妻》杂剧中,秋胡出行已是被勾兵而非求官。这样,桑下悦女的行为多少属于武人的蛮行而与温文尔雅的书生无涉。而赵松雪诗中所记的“不是别来浑未识,黄金聊试别来心”的传说,更是完全为这位鲁大夫开脱了。这两则故事的转化,也足以证明元代书生地位的困窘和对书生的同情,对负心婚变悲剧的转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高则诚改《赵贞女》的谴责为歌颂,也是时势使然。既然社会的变迁已经使谴责书生负心失去了直接的针对性,那么,对蔡伯喈这样的“笃孝”人物的“厚诬”便显得更为突兀和无谓了。一旦使男主角蔡伯喈“恢复”笃孝品行,便与《赵贞女》为增强悲剧效果而贯注的伦常道德的涵义融合成一体,可谓水到渠成,并无多少轩格难融之处。如果说《赵贞女》的写法代表了那一时代的呼声;那么,《琵琶记》的出现,也同样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
如此看来,当代一些否定《琵琶记》思想价值的意见,多少夸大了《赵贞女》与《琵琶记》的区别,甚至将两者截然对立了。他们并未注意到其间的共通之处,遂将“宣扬礼教”作为高则诚的首创;他们看到了《琵琶记》一夫二妇旌表结局对于负心杀妻遭雷殛故事的改变,却未曾关注整个元代风尚的转换,缺乏历史内涵的批评其实也只能是失去针对性的自说自话而已。
《琵琶记》在元末的出现,在戏曲舞台上,宛如月上中天,使满天繁星顿即失去光彩。后人瞻仰膜拜,视为“南曲之祖”或“南曲中兴之祖”,遂以为诸事皆首创于高则诚。功既归之,祸亦随之。誉之毁之,众说异辞。“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则诚秋夜辍笔之时,亦曾嘱意“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但作品一经问世,便只能交付读者与时间了。他又如何管得自己的“身后是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