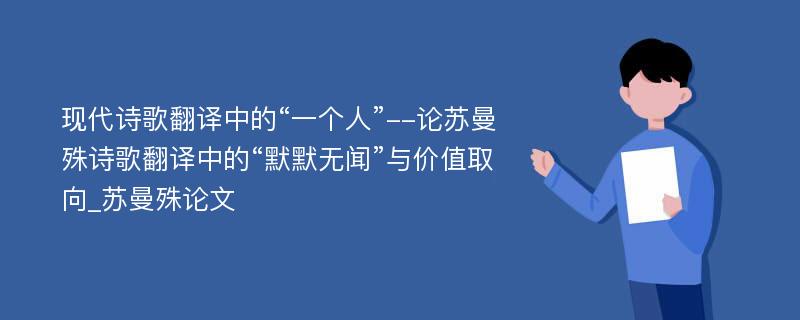
现代诗歌翻译的“独行之士”——论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行论文,之士论文,诗中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现代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1-0068-12
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辟专章论述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其中主要的翻译家有四位:严复、林纾、马君武与苏曼殊;[1:88-95]柳无忌在《苏曼殊传》一书中引用他人的话,称苏曼殊应该获得除严复、林纾之后,“第三大翻译家的地位”。[2:183]谢天振也认为,“真正开创外国诗歌翻译风气并引起国人对外国诗人、诗歌注意的,当推苏曼殊的……《拜伦诗选》”。[3:37]足见苏曼殊在文学革命以前对翻译的贡献。有学者称,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是“石破天惊的创举”。[4:19]
1914年,胡适在自己着手翻译《哀希腊》的时候,仔细对照阅读了之前的各个译本,称马君武的翻译“失之讹”,苏曼殊的翻译“失之晦”;并认为“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5:92]但是,胡适评论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或翻译手法上的侧重与差异,实则反映了苏曼殊独特的翻译功能观和翻译理念的取向。笔者认为,苏曼殊的译诗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是清末民初近代文学翻译规范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即从翻译的功利性标准到泛功利性标准和学术性标准的转变与过渡,是文学翻译政治化模式向艺术化模式的转变与过渡。
一、苏曼殊译诗中的“晦”
在胡适以后,各论家几乎众口一词,批评苏曼殊译诗语言的古奥与晦涩。泪红生曾言:“曼殊所译摆轮诗,中多奇字,人不识也”。(泪红生.记曼殊上人)[6:Ⅳ140]张定璜在高度肯定苏曼殊译诗引进了“异乡的风味”时,也承认其译诗不仅有“疏漏”,而且“晦涩”。(张定璜.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ey)[6:Ⅳ226-230]1925年鲁迅认为,苏曼殊的译诗“古奥得很……流传倒并不广”。[7:122]1927年,罗建业在长文《曼殊研究草稿》中,对苏曼殊译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大师所译拜轮诗最坏,只可作为说文一类的小学书读罢。文贵易晓而难为,像这样的艰涩古怪,又何苦来呢?”(罗建业.曼殊研究草稿)[6:Ⅳ391]其后,柳无忌、郭延礼等,均持类似的见解。[8:16][9:315]苏曼殊的译文的确显得古奥和艰涩: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
情文何斐亶,荼辐思灵保。
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苏曼殊.译拜轮哀希腊)[6:Ⅰ79]
仅从这一节我们就能看出“斐”、“陵夷”均太古雅,非一般人所能求解。有些措辞,即便像柳无忌这样研究苏曼殊的专家,也“遍查字典与词源而不得,无法究其意义,直至最后以译诗与原文逐字对照,始恍然大悟。”[8:16]译诗中“酃渌”(酒名,因产地而得名)、“天维”(天纲)、“彭亨”(骄满貌)、“樾”(树阴)、“娄离”(古之明目者)等,[8:16]均超越一般读书人的理解能力,而他用四言诗经体翻译的《赞大海》文辞更加古奥。丰华瞻就称,“译文相当艰深……必须查《辞海》才能找到。”[10:46]
但是,文字艰涩并非苏曼殊诗文的一贯风格,试比较同期的创作: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6:Ⅰ45]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6:Ⅰ47]
与译诗比较,其诗文创作要通俗得多。可以看出,苏曼殊的“晦”实际上揭示了他政治思想态度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诗歌翻译观念的变化。
二、从革命者到诗僧
早年的苏曼殊与马君武一样,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曾参加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同盟会、兴中会等,主张用狠辣的手段(暴力、暗杀)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甚至准备用手枪行刺保皇党人康有为。1903年年底,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翻译加创作的小说《惨世界》,流露出明显的抨击满清、崇尚暴力的倾向。但从1903年12月开始,苏曼殊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戏剧性地退出上海的活动舞台”,到香港后,“过着一种清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意气沮丧,心情沉重”。他“从一个目光远大的青年革命志士变成一个乞求施舍的和尚”。[2:30-31]柳无忌认为,也许是由于经济的压力,或者逃避家庭安排的婚姻,苏曼殊“从寺院回来后,原先抱有的革命热情也已冷却下来。在22岁以后,他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转向教书与写作”,[2:33]苏曼殊
虽然继续和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来往,并且偶尔也发出爱国的呼号,但他对政治已开始失去兴趣,并且再也没有参加反政府的活动。这种根本的变化,致使后来的人们已经看不出他青年时代早期的革命性了。[2:37-38]
苏曼殊政治态度与思想的转变,暗示并决定了他从入世转向出世、从激进革命转向消极遁世、甚至厌世的人生态度;从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转向个人内心体验。其文学创作,包括文学翻译,则从明确的社会功利观转向个人表现与艺术审美。
其实,苏曼殊与拜伦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不仅在创作中吟咏爱情,描写女性,而且一生风流多情,交游女子甚多;她们不仅是他们创作的灵感,也带来流言和攻击。拜伦是“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或政治的。他不知道怎样或哪里他是到了极端。”(柳无忌.译苏曼殊潮音自序)[6:Ⅳ35]与此相似的是,苏曼殊同样是独行之士,虽是激进的革命者,但他并不受革命纪律的约束;虽出家当了和尚,但率真任性,“沉溺于非佛教徒的娱乐……几乎抛开了一切宗教义务”。[2:131]苏曼殊曾赋诗一首: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轮。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苏曼殊.题拜轮集)[6:Ⅰ53]
这其中表现出的“宏阔的意境,慷慨的情怀,热烈而悲壮的情绪,实在是出自他与拜伦精神上的深刻理解与契合。”[11:227]
三、审美的政治化转向艺术化
1907年苏曼殊与生母河合氏在日本重聚后,一直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柳无忌曾如此描写1908年5月以后苏曼殊的境况:“从此以后,他赋予自己的形象是一个经常哀愁、孤独、感情脆弱的诗僧”,其抑郁和沮丧在1910年给刘三的诗中生动地表现出来: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
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做诗僧。[2:55]
在对政治失去热情之后,贫病交加的苏曼殊似乎将佛教与文学作为自己唯一的兴趣和追求。在1908年的2、3月之间,苏曼殊“几乎用所有时间专门读拜伦的诗……试图了解拜伦精神的整体。”[2:61]1909年1月,苏曼殊在日本开始翻译《拜伦诗选》,5月完稿。
早年的苏曼殊与马君武一样,充满爱国和革命热情;但到1909年他开始翻译《拜伦诗选》的时候,其动机与梁启超、马君武等已大不相同。梁启超、马君武的翻译更多地承载着民族救亡的使命。梁启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9:226]以“救燃眉之急”。(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12:113]马君武在翻译《哀希腊》时则称,“裴伦哀希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13:438]从拜伦哀希腊到梁启超、马君武哀中国,再到救中国,其中启蒙救亡的功利性非常明显。
苏曼殊对拜伦的热爱和崇拜绝不亚于梁启超或马君武。他认为“拜轮足以贯灵均太白,师梨足以合义山长吉;而沙士比,弥而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灵界诗翁也。”[6:Ⅰ225]苏曼殊在“灵界诗翁”和“国家诗人”之间刻意做出区别,将拜伦、雪莱和李白、李商隐、李贺置于莎士比亚、杜甫等之上,表露出“他重内在性情(所谓‘至性之作’)和浪漫气质的诗歌价值观”,他“用超时空的眼光,将中、西文化和文学纳入人类精神的共同性中。”[14:110-111]可以看出,苏曼殊推崇的是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拜伦。在其《潮音自序》中,苏曼殊称,拜伦的诗歌,“在每个爱好学问的人,为着欣赏诗的美丽,评赏恋爱和自由的高尊思想,都有一读的价值”。(苏曼殊.潮音自序)[6:Ⅳ37]苏曼殊在阅读拜伦诗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他与同时代的人都能从中感悟到家愁国恨,如他所言,“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飞锡.潮音跋)[6:Ⅳ38]但是,1909年苏曼殊翻译《拜伦诗选》时,其关注的焦点已从民族国家的救亡转向内省,转向对佛学和诗歌的研究,译诗的动机基本上是非政治化的。在《潮音自序》的末尾,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我赋在此书的工作”,完全是为了让拜伦的诗“为读者所欣赏”。(苏曼殊.潮音自序)[6:Ⅳ37]有学者称,政治家的梁启超、马君武重视政治启蒙,“发现的政治家的拜伦,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个体;而重视心灵世界的苏曼殊发现的却是艺术家的拜伦,是感性的、审美的个性,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相似。”[4:20]苏曼殊译诗的意图带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超功利色彩。
如果说苏曼殊翻译的《哀希腊》还多少流露出爱国或革命的情绪,他翻译的其他诗歌则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哲理化的思考。如拜伦的《赞大海》(The Ocean)、《去国行》(My Native Land-Good Night)、《美人赠束发埔带诗》(To A Lady)、《星耶峰耶俱无生》(Live not the Stars and the Mountains),彭斯的《颎颎赤墙靡》(A Red,Red Rose)、豪伊特(时译豪易特)的《去燕》(Departure of the Swallow)、雪莱的《冬日》(A Song)、歌德题《沙恭达罗诗》(Sakontala)以及印度诗人达特(时译陀露哆)的《乐苑》(A Primeval Eden)。这些译诗与早期的翻译《惨社会》所表现的主题,大相径庭。前期的译作眼光在社会现实,关注的是政治意图,期望的是社会效果。后期的译诗眼光则在个人情感,关注内心感受与自由,期望的是艺术审美,追求人性的升华。这是苏曼殊从外向内、从群体到个人、从现时到永恒、从政治到艺术的转变。苏曼殊在《拜伦诗选自序》中就写道,“尝谓诗歌之美,在乎气体;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如纳旧译颎颎赤墙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赠束发埔带诗数章,可为证已。”[6:Ⅰ125-126]可见,苏曼殊将上述诗人视为“为爱情和自由的理想而献身的诗人”,[2:184]他想传达的是永恒的主题:恋爱与自由。
如果说他前期的译作是应时、应事、应景而作,是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翻译,那么后期的译诗则是求真、求善、求美;是艺术审美对译诗的诉求,是没有外在压力的内心追求。
四、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文学翻译是异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文学翻译所塑造的形象具有三重意义:1、异国客观的形象;2、一个民族(社会文化)构建的形象;3、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5:25]乐黛云称,对于异域的文化形象,人们通常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16:101]一个文化尚且如此,一个诠释个体也是如此。
梁启超、马君武等的翻译构建了拜伦的中国形象。经过了一大批翻译家的不懈努力,拜伦逐渐成为“社会集体想像物”;是“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部分地与事件、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相联”。[16:24]中国化的拜伦与所谓的社会集体想像物,即莫哈所谓的意识形态形象类似,其特点是“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16:35]这也就是说,梁启超、马君武等塑造的拜伦形象有助于整合和维护群体的价值观念,而苏曼殊译诗中的拜伦则是他感性个体独创的形象,是乌托邦形象。与意识形态形象的整合功能相反,乌托邦形象“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念的功能”,[16:36]“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16:34]苏曼殊的译诗代表了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背离的倾向:超功利的翻译观、非政治化的主题选择和典雅的译诗语言。
苏曼殊超功利的翻译观使其译诗主要着眼于诗歌的艺术审美。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文学界,文以载道、以文治国是主流思潮。有学者称:“所载之道为新道——变法和革命,所用之文为新文——如新民体小说,改良体诗歌和散文……以文学为变法救国的工具,理论上提倡,借翻译以支持,且身体力行。”[17:105]梁启超节译《哀希腊》(时译《端志安》)就发表于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上。他对时局和政治的关怀,远远超过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一方面小说(文学)的功能被神化,另一方面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特征被忽略、被歪曲。主流意识形态使译诗成为政治的附庸。
而苏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则旗帜鲜明地赞扬“创造与恋爱的崇高情感”,称拜伦“一生的生活,境遇,与著作,都缠结在恋爱和自由之中”。(柳无忌译.苏曼殊潮音自序)[6:Ⅳ36]佛莱蔗在为《拜伦诗选》所写的序言中,高度赞赏的,除了中外文学交流和影响之外,就是拜伦的诗“为中国民众的自由文学做了必要的补充”,自由思想“通过思想家和诗人的作品”而日渐“深入人心”,“广为普及”。(佛莱蔗.拜轮诗选序)[6:Ⅳ31]这里的“自由”是指与社会群体相对的个人的自由,显然与严复、孙中山、梁启超、马君武等人鼓吹的自由大相异趣。
苏曼殊的翻译与同时代的人相反,完全是“兴之所至”,“既缺乏理论”,“也没有目标”,[11:232]是超功利的艺术审美和内心的升华,几乎不带政治功利。这与他耿介和孤傲的个性密不可分。正因为他“太于狷洁”,“是非太于分明”,孤芳自赏,因而他与拜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心灵的相通,张定璜在评述苏曼殊的译诗时称:“拜轮诗毕竟只有曼殊可以译……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轮诗……他们的多难的境遇,他们为自由而战为改革而战的热情,他们那浪漫的漂荡的诗里,最后他们那悲惨的结局:这些都令人想到,唯曼殊可以创造拜轮诗。”(张定璜.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ey)[6:Ⅳ227]张定璜意识到,苏曼殊与拜伦的相通是一种气质上的相似,他的译诗是对文学独立审美的追求,是超乎物外、超越一时一地的政治情势的人性追求。
第三,译诗超功利性与主题的非政治化,使苏曼殊译诗的形式与语言不仅有别于同时代的翻译家,也有别于自身的诗歌创作。冯印雪在《燕子龛诗序》中称:“窃怪曼殊所为诗,只五言七言绝句,译诗则出以古体,律诗未之见。意以为排比对偶,桎梏性灵,弗若绝句古体之自鸣天籁耶?”(冯印雪.燕子龛诗序)[6:Ⅳ93]此言不虚。苏曼殊在《拜伦诗选自序》中又说:“今译是篇,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侧,事辞相称。”(苏曼殊.拜轮诗选自序)[6:Ⅰ127]冯印雪道出了苏曼殊不愿受汉语诗词格律的约束;苏曼殊自己的翻译主张则反映出他也不愿屈从英语字词句法的左右,希望探索一种能随心所欲表现原诗精神(其中也包括了译者自我)的艺术形式。一般说来,五言古体是他最常用的译诗形式。
与此相仿,他译诗的语言同样背离了当时的主流诗学,成为苏曼殊抒发个人内心世界、实现文学审美价值的载体。晚清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将文学当作变法维新的工具,要求诗文要“易诵”、“明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8:223]陈平原曾经说,提倡通俗易懂的文学“贴近谋求政治变革的时代主潮”,然而就语言的审美功能而言,“则文言优于白话”。[19:12]文言“雅驯、含蓄、合文法、有韵味”。[19:14]苏曼殊既然将译诗视为艺术审美对象,注重自我情感的自由抒发,他未必将译诗的说教、鼓动功能置于首位。从艺术审美来看,苏曼殊也许更赞同严复的观点:
夫著译之业,功候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之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丈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20:141]
苏曼殊用古雅的文言译诗,试图使“创造同恋爱底崇高情感”,(柳无忌.译苏曼殊潮音自序)[6:Ⅰ35]超越“旦暮之已化”的命运,译诗自然“不能载以粗犷之词”,“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20:141]译诗的语言自然有别于政治化的诗文、小说,更有别于“报馆之文章”。
苏曼殊译诗语言的驯雅、乃至艰涩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初学古诗者的谨慎与局促。根据柳无忌的考查,苏曼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读书时,“尽管相当勤奋”,但学业才能“并不出色”:
当他二十岁左右到上海报馆做事时,他的文章写得很差,同事们还得帮他修改。直到1907年,他在章炳麟等人鼓励下,才开始认真尝试做诗。在一个做诗才能普遍早熟的国家,他当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却还是一个新手。[2:165]
如果苏曼殊到1907年才认真尝试做诗,到1909年翻译《拜伦诗选》毕竟只有二、三年时间;苏曼殊也许意识到自己做诗的根底不深,便刻意追求译诗形式与语言的完美;再加上整日浸润在以传统诗学为主导的象牙塔中,深受章太炎、黄侃等古文字家的影响,甚至还有他们修改、润色,其译诗背离当时国内的译诗主流规范、独树一帜、显得艰涩和古奥就不难理解了。
苏曼殊的译诗尽管比较晦涩,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却不能低估。柳无忌在比较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的译诗以后,认为“在韵律和格式的整齐、语言的凝练和艺术性、优美而又值得引用的诗句数量之多等方面,苏曼殊的译诗似乎都胜过一筹。”[2:183]苏曼殊译诗中的“晦”只是他个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追求的一个表征,他的译诗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同时也是贵族化的;是当时意识形态形象的对立与补充,代表了边缘化的译诗倾向,与王国维的自由主义文学和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哀情文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苏曼殊的译诗“代表了近代译诗从前期的政治化模式向着文艺模式过渡与转化”。[21:185]诗如其人,译诗也如其人。这位毕生试图摆脱社会羁绊、追求自由的诗僧,在《拜伦诗选》的翻译中同样是一位“不从流俗”的“独行之士”,(杨鸿烈.苏曼殊传)[6:Ⅳ164]坚持和守护着求真求美的译诗信念。
注释:
①本文系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5-YW04)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标签:苏曼殊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拜伦诗选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哀希腊论文; 梁启超论文; 马君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