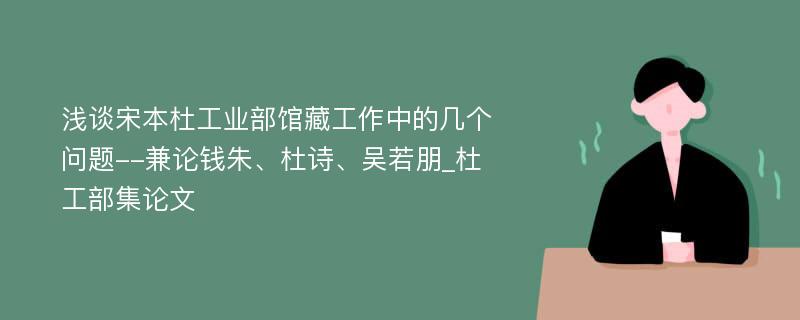
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部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简论论文,钱注杜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刊行的《宋本杜工部集》(注:《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其缩印本1994年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是后来所刊行各种杜集的祖本。因它把“王洙、王琪本(注:即北宋宝元二年(1039)由北宋王洙(字原叔)编集《杜工部集》二十卷,北宋嘉祐四年(1059)再由王琪校订后所刊行的杜集版本。现此书全面已失传。)”的原貌保留至今,所以在本世纪的杜诗研究史上,它以其业绩最大而备受海内外研究者注目。一九七八年所编集的杜诗新注本《杜甫全集》就是以《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的(注:张忠钢《〈杜甫全集〉校注工作情况介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文献价值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
但是,《宋本杜工部集》并不是一个完整版本,它是由数种版本组合而成的,这数种版本都有各自的来历,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研究《宋本杜工部集》时,这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实际上,关于此书已有多位学术前辈从文献学方面进行过研究。
本文就此在整体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介绍有关《宋本杜工部集》到现在为止的研究成果;另一部分是对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通称《钱注杜诗》)、以及主要是与《宋本杜工部集》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钱注杜诗》作为一种范本与《宋本杜工部集》联系密切,本文将由《宋本杜工部集》和《钱注杜诗》的分析入手,进而对杜甫诗文在文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一、《宋本杜工部集》的研究状况
1.《宋本杜工部集》概要
《宋本杜工部集》在卷末附有毛戾(注:毛晋(1599—1659)、毛扆(1640—1713)父子为明末清初的藏书家、刻书家。)所写的跋文,其大致内容如下:
毛扆之父毛晋,从他人手中借到了宋代王洙编集的《杜工部集》,便命仆人刘臣进行了影写。毛扆继承父业之后,发现这个影写本杜集在《东西两川说》一文的开头仅存六行,其后缺佚,尤其是卷十九也缺了首二页。
二十多年以后,毛扆从吴兴(今浙江吴兴市)商人处购得宋刻杜集残本三册。这本杜集残本在《东西两川说》一文的开头也仅存六行,卷十九也缺了首二页,所缺的行数字数,与从其父毛晋手中得到的影写本杜集完全一样,于是毛扆始知杜集的残本即为影写本杜集原本的一部分。杜集残本所缺的部分是王为玉从影写本杜集中影写补充的。
下面是《宋本杜工部集》影印刊行的主持人张元济先生所写跋文的要点:
毛氏汲古阁所藏的宋本杜集,经潘氏滂喜斋(注:滂喜斋为清末藏书家潘祖荫的藏书室。)而归上海图书馆。这本杜集是由两种类型的杜集组合而成的。这两种类型的杜集是:
○宋刻第一本
→卷一的三、四、五页,卷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补遗。
(卷一的六页以下,卷二——九、卷十五——十六是毛扆从王为玉处抄补的部分,相当于第一本。另外,卷一的一——二页,卷十九的一——二页,以及补遗的七、八页是从北京图书馆藏本(注:关于“北京图书馆藏本”, 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记载“《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杜甫撰,清初钱会述古堂影宋抄本”。钱会(1629—1701)为清代藏书家,“述古堂”为其藏书室。
此外,《宋本杜工部集》开头所载王洙《杜工部集记》的第一、二页也是从北京图书馆藏书中补上的。)中补写的)。
○宋刻第二本→卷十、十一、十二
(卷十三——十四是毛扆从王为玉处抄补的部分,相当于第二本。另外,卷十二的二十一页后半部分是从北京图书馆藏本中补写的)
所以,第一本、第二本的两种范本是由以下版本决定的。
○第一本
→南宋绍兴年间在浙江重刻的王洙、王琪本。
○第二本→吴若本(后述)
(以上为概要)
下面将就第一本和第二本的各种研究状况加以介绍。
2.关于“第一本即重刻王洙、王琪本”
张元济先生认为第一本是重刻王洙、王琪本的特殊根据是:
(A)“完”、“构”字缺笔,因此推测所刻时间为南宋初期。
(B)版心所见到的刻工姓名,在南宋绍兴(1131—1162 )初年浙江地域刻行的其它版本中也能见到。
对此,元方在《谈宋绍兴刻王原叔本〈杜工部集〉》(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三期,1962年版。)一文中认为,第一本为绍兴年间的刻本,因为南宋时期的刻工往往在当地刻书,由此可推断第一本为在浙江地域上所刻(注:此推断的根据是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古代版刻图录》(周采泉编《杜集书录》上卷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元方的论文对第一本即是绍兴年间重刻王洙、王琪本之事并不持异议,但是安东俊六在《“甲本=重刻王琪本”说质疑》(注:《杜甫研究》,日本风间书屋1986年版。)一文中认为,甲本(第一本)并不是王洙、王琪本原封不动的重刻,而是另外还有一本。安东的结论是,《宋本杜工部集》各卷开头目录的诗歌数量,与实际上这卷所收的诗歌数量完全不一致,如果说得详细一点的话,实际上的诗歌数量比目录上的诗歌数量要多,而且这种不一致性主要集中在第一本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本作为底本,有的杜集诗歌数量是和其目录所载的诗歌数量完全一样的,实际上它是补充了一些新收到的杜诗。作为底本的书权且叫作“目录本”,这个“目录本”与王洙、王琪本并不是同一本,王洙的《杜工部集记》和王淇的《后记》中的记述等就是例证。从这个考察可以看出,安东的论文并不认为第一本是王洙、王淇的重刻本,两者中间还存在着一个“目录本”。
3.关于“第二本=吴若本”说
“吴若本”是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的底本,(注:《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载:“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它本不及也。……若其字迹异同,则壹以为吴本为主,间用它本参伍焉。”)如按附在《钱注杜诗》后的“杜工部集后记”所说,这个版本是南宋绍兴三年(1133)吴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府学刻行的杜集。但是,“吴若本”的名字在《钱注杜诗》中并没有出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洪业在1929年的《〈杜诗引得〉序》(注:《杜诗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提出了“把‘吴若本’作为范本是钱谦益的伪作”之说。
1957年《宋本杜工部集》的出现把这个疑惑消除了,(注:洪业在《宋本杜工部集》刊行后,撤回了“吴若本=钱谦益伪作”之说。(见《洪业论学集·再说杜甫》中华书局1981年版))《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是以“吴若本”为依据的,对此张元济先生在跋文中写到:
复考配本(第二本),间有“樊作某”、“晋作某”、“荆作某”、“宋景文作某”、“陈作某”、“刊作某”、“一作某”等,与钱牧斋谦益笺注所载吴若《后记》云“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若合符节,是必吴若刊本可无疑义。
也就是所看到的第二本,校语所记载的文字虽有异同,但《钱注杜诗》所记与吴若《〈杜工部集〉后记》的记述完全一致。
“吴若本”是王洙、王琪本没有使用过的数种杜集与王洙、王琪本合校而成的,从详细记述文字异同这一点来看,其文献价值是很高的。因此《宋本杜工部集》卷十、十一、十二及卷十三、十四的抄补部分只选以“吴若本”为主。在《钱注杜诗》的全卷中是以“吴若本”为底本的。随着《宋本杜工部集》的出现,《钱注杜诗》的文献价值也得到了确认。
但其后下面的三位学者却对“第二本=吴若本”之说提出了疑义:
(1)元方《谈宋绍兴刻王原叔〈杜工部集〉》
(2 )黑川洋一《关于王洙本〈杜工部集〉的流传》(注:《杜甫之研究》。《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77年版。)
(3 )曹树铭《宋本〈杜工部集〉非‘吴若本’考》(注:《杜集丛校》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
三位学者把《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与《钱注杜诗》(=吴若本)进行对应的比较、点检,指出了两书之间的异文校语和诗句的注语有许多不一致之处。(注:三者调查的结果其所提供的数值分别有所不同。)三位学者一致认定“第二本是与吴若本极为相近的范本,只是时代比吴越本略晚些。”黑川文在元方考证刻本的基础上,推测出第二本的刊刻时间约在绍兴末年。他指出了两点:A、 《钱注杜诗》(=吴若本)没有第二本中的注语,也不包括王安石、黄庭坚、苏轼等北宋名家的注语。B、在《钱注杜诗》(=吴若本)第二本中没有注语, 但有误注及常识性的注释等。它从一个侧面推断出“第二本是在吴若本之后,删去了一些不适当之处,把新的北宋名家之注附注上的重刻杜集。”
4.其后的“吴若本”研究
前面元方的论文认定《宋本杜工部集》第一本是重刻王洙、王琪本,其理由是在第一本中收录了在宋代其它杜集所看不到的杜甫自注,因此第一本的文献价值是很高的。但另一方面又有第二本不是“好本”,吴若本也属“劣”本的评价。元文虽就后者列举了吴若本的注语(《钱注杜诗》中的吴若本注)误注及其理由,但对前者的根据并没有明言。可能是第二本中误收了后人的注语,所以才判断为不是“好本”吧!
邓绍基《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注:《江汉论坛》1982年6期。)一文,在否定洪业“吴若本=钱谦益的伪作”的同时,对元方“吴若本=劣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邓文列举了《宋本杜工部集》第一本(=王洙、王琪本)中所见到的杜甫自注,在吴若本(=《钱注杜诗》中也都能见到,王洙、王淇本的长处即是吴若本的长处。
蔡锦芳在《吴若本与〈钱注杜诗〉》(注:《杜甫研究学刊》1990年4期。)一文中提出了以(A)作品排列的体裁(B)文字的勘考(C)诗题下面及行间的注文三个方面作为检验标准,认为《钱注杜诗》的底本是和吴若本的原貌相似的。在这个论证中有几个引人注目之处是需要指出的。
(1)《宋本杜工部集》第一本(=重刻王洙、 王淇本)与《钱注杜诗》(=吴若本)在基本体裁,即杜诗古体、近体分类、年代的排列顺序上是相同的,杜诗的编年顺序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王洙、王淇本七十四年之后刊刻的吴若本,在体裁上看不到什么进展。
(2)在《钱注杜诗》正文下用“一作×”表示异文, 与《宋本杜工部集》(=重刻王洙、王琪本)的正文一致之处颇多,吴若的《后记》“称‘刊’及‘一体’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和王洙、王淇本的“黄鲁直、晁以道诸本”是极为相似的。
(3)《钱注杜诗》中的吴若本注, 是引用了综合宋代其它杜集的王洙注的。这个王洙注为后人伪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蔡文在程千帆《杜诗伪书考》(注:《古诗考索》。《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伪王洙注出现于宋南迁(1127)之后的基础上,推测为吴若是在绍兴三年(1133)刊刻杜集之时,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其它杜集语注加在了自己的杜集之中。
一九九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林继中辑校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一书,从中可以看到它只引用了郭知达编的《杜工部诗集注》,关于赵次公的杜注,是在近年发现的明代钞本残卷和引用其它杜集的赵注基础上复原的全书。林氏在《前言》中对该书的成立过程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林氏推测赵次公是用了与“吴若本”相近的底本。其根据是《前言》列举了①在《钱注杜诗》中所引用的“吴若本注”的注文和赵次公本的夹注之间的一字一句差不多的例子很多。②在《钱注杜诗》中“吴本作×”所表示的异文与赵次本的正文有多处一致的地方。
二、《钱注杜诗》与吴若本
1.《钱注杜诗》中的“吴若本”处理
在第一部分中,虽然谈及到了《钱注杜诗》的文献价值,但《钱注杜诗》果真是保留了吴若本的原貌吗?本节将就(A )杜诗的文字异同,(B)注文,(C)杜诗的排列三个问题进行考证:
关于(A)、(B)两点,钱谦益认为:
杜集之传于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它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注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壹以吴本为主,间用它本参伍焉。(注:《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载:“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它本不及也。……若其字迹异同,则壹以为吴本为主,间用它本参伍焉。”)
关于(A),在《钱注杜诗》中, 有象“吴作×”这样的表示异同文字之处,也就是吴若本的正文并不是作为《钱注杜诗》的正文,而是作为异文提示的。(注:如杜甫《洗兵马》(《钱注杜诗》卷二)中“紫禁正耐烟花绕”的“禁”字,“吴本作‘驾’”。又如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钱注杜诗》卷八)中“我之曾祖姑”的“祖”字,“吴作‘老’”。)此事表明钱谦益并没有把吴若本当作底本使用,他只是偶尔采用它本的文字用于自己杜注本的正文而已。这也与他所说的“若其字迹异同,则壹以吴本为主,间有它本参伍焉”的意思相同。
关于(B),钱谦益认为,吴若本题下和行间有细字注文, 这些注文是杜甫的自注和他注混在一起的,自注用朱字、他注用白字加以区别。只是在清康熙年间静思堂刊刻《钱注杜诗》原刻本(《杜工部集》)中,这种“朱字白字”的区别已看不到了,(注:笔者所见版本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即在《钱注杜诗》题下和行间的细字注文中,既有“吴若本注”的明记,也有什么明记都没有的。前者是他人所注,后者是杜甫的自注,钱谦益是能看明白这些的。例如杜甫的《宿赞公房》(《钱注杜诗》卷十)题下有“京中大云寺主,谪此安置”的注文,而吴若本也有“京中大云寺主,谪此安置”的注文,钱谦益认为这句话是杜甫的自注。又如杜甫的《闻斛斯六官未归》(《钱注杜诗》卷十一)诗中对“锉”字的注释有“吴若本注:蜀人呼釜为锉”,而吴若本的注文也是“蜀人呼釜为锉”,钱谦益认为这个字是他人所注。
在《钱注杜诗》中,“吴若本注”所引用的注文,即是钱谦益所判断的“不是杜甫自注”的那部分,他检索出52条这样的内容。这本“吴若本注”明显的误注有不少,当然也有钱谦益自身的误注。(注:如《钱注杜诗》卷一《丽人行》的“衱”字;卷九《赠李白》的“飞扬跋扈”,卷十三《寄董卿嘉荣十韵》的“君牙”等等。)
关于(C)杜诗的排列问题,钱谦益认为:
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
如前所述,吴若本和王洙、王淇本有相同之处,杜诗古体、近体分类以及按年代排列的体裁正是被《钱注杜诗》所沿袭了的,特别是《钱注杜诗》和作为范本的“吴若本”极为相近,在《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中,所收录的杜诗,其创作时间在卷头都已标明,它是和前面钱谦益所说的内容一致。由此可以看到,钱谦益基本忠实地沿袭了吴若本的杜诗排列和编年,如按“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所说,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了一些订正而已。现再举杜甫的《次行昭陵》为例,钱谦益并没有把此诗看做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在了《钱注杜诗》卷十中,但在《宋本杜工部集》卷十(相当于第二本)中,却又找不到此诗,也就是说钱谦益在给杜诗进行排列、编年时,并没有完全依照吴若本。
从(A)、(B)、(C)三点来看, 《钱注杜诗》并没有完全照搬吴若本的原貌。换言之,钱廉益虽以吴若本为《钱注杜诗》的底本,但他也对此做了某种程度的删改。
但是,作为“最为近古”的吴若本,其一贯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形式,使得钱谦益自身在认定有误时并没有删除吴若本注,而是仍收录在《钱注杜诗》中。也就是在吴若本中,杜诗的自注和他注是混在一起的,后者虽有明显的误注,但在原来的吴若本中,它是和杜甫的自注同样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钱谦益对删除这些内容还是有所顾忌的。
从杜集的编纂史(注:关于宋代杜集的编纂史主要参考了以下作者的观点:
许总:《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
吉川幸次郎译《杜甫Ⅱ》后记。(《世界古典文学全集》二十九,筑摩书房1972年版)。)来看,北宋王洙、王琪本的《杜工部集》开创了杜集的基本框架。到了南宋时,郭知达编的《杜工部诗集注》、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等为杜甫诗集全书做注的书籍便开始出现了。南宋的“吴若本”可以说是“杜诗为杜甫自注,并附有他人零星注释”的书籍,它处于向杜甫诗集全书注释过渡的位置。
钱谦益因为非常珍惜吴若本,所以尽可能地保持吴若本的原貌,并且加自己的笺注而著成《钱注杜诗》。但正如前如述,因吴若本具有“过渡性”的特点,故它是一个稍稍有些复杂的范本。而且《钱注杜诗》在某种程度上对吴若本进行了删改,其复杂性也就进一步增强了。
“吴若本”至今并没有完地保留下来,因此《钱注杜诗》成了考察“吴若本”原貌最重要的文献。但从本节的考证来看,《钱注杜诗》并没有生吞活剥“吴若本”的内容。
2.《钱注杜诗》的问题
下面将举《钱注杜诗》的几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
〔问题一〕
钱谦益对“吴若本”的注文处理——关于杜甫自注与他注的界限问题。谢思炜在《〈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五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岳麓书社1985年版)。)一文中曾对此做了极为有益的考证,谢文认为在《宋本杜部集》第一本(=重刻王洙、王淇本)中所看到的注文应该是杜甫的自注。《宋本杜工部集》第二本(=吴若本)所看到的注文,分别是杜甫的自注和附在第二本上的他注,后者应该是很清楚的。
谢文还认为《宋本杜工部集》第一本所看到的注文,是《钱注杜诗》引用“吴若本”的,即钱谦益既没有自注杜诗,也没有引用别人的注释,所看到的注释全是杜甫的自注。这其中所包括的钱谦益误注和“吴若本注”,谢文认为是钱谦益在内容注释上有些不恰当的判断而引起的,经详细考证确认是杜甫的自注,这也是读杜诗时所必须要有所了解的东西。
钱谦益提出的严格区别是否是杜甫自注的问题,《钱注杜诗》所看到的杜甫自注和吴若杜注的问题,都是有必要进行个别细致研究的问题。
〔问题二〕
清代朱鹤龄辑注的《杜工部诗集》(注:《杜集又丛》第四册。(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卷十三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题下有“吴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注文,即朱鹤龄注释为“吴若本的《咏怀古迹五首》分别是《咏怀一章》和《古迹四首》。”但《钱注杜诗》卷十五的此诗下面并没有象朱鹤龄所指出的那样的文字,那么吴若本是否是分为了《咏怀一章》和《古迹四首》呢?
说起来最初《钱注杜诗》和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在成书之时是有以下原因的,钱谦益在明亡之后,把自己未完成的注原稿托付给了朱鹤龄,但朱所完成的杜注本,却否认了钱说,并且没有按照钱的要求注释杜诗,其结果两人关系决裂,并分别刊行了自己的杜注。在朱鹤龄完成杜注的过程中,他是翻阅了钱的所有的吴若本的。实际上,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所引用的“吴若本注”,与《钱注杜诗》所引的内容是一致的。因而关于《咏怀古迹五首》按朱鹤龄的注释,吴若本写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可能性也是较大的。
那么(1):为什么《钱注杜诗》没有写作《咏怀一章》、 《古迹四首》呢?或者说(2):为什么没有解释“吴若本作《咏怀一章》、 《古迹四首》”呢?
首先,关于(1),正如前如述, 《钱注杜诗》对吴若本加以某种程度的删改,并且涉及到(A)文字的异同,(B)注文,(C )杜诗的排列三个方面。基于这个事实可以推测出“‘吴若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杜诗五首’,《钱注杜诗》从他本改为《咏怀古迹五首》”,这种情况包含了(A)、(C)两个方面。这虽是属于稍稍特殊删改的例子,但决不是不自然的。
其次,关于(2), 有①:关于钱谦益的注释意图并没有记载下来;或②:钱谦益的注释在刊刻时漏掉了两者可能,笔者认为①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钱谦益对杜甫在夔州时AI写作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连章组诗,一贯主张应从各组诗整体构成上来解释其意图,即对各组诗要有一个有机的一体性、整体性的态度,并且钱谦益也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连章组诗。因而推测出关于《咏怀古迹五首》,钱谦益是把吴若本《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五首杜诗,当成了由“五首组成的连章组诗”来读了。正因为如此,钱廉益没有从吴若本之说,也没有附记上“吴若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解释。
在《咏怀古迹五首》中,第一首与其它四首之间在内容上可以认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松原朗在《杜甫〈咏怀古迹〉诗考》(注:《人文科学年报》第二十一辑。1992年版)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种情况,这是在清代浦起龙解释朱鹤龄“吴若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基础上提出的观点。即第一首是纯粹的“咏怀”,与“古迹”没有关系。(注:浦起龙认为:此《咏怀》也,与《古迹》无涉,与下四首,亦无关会。(《读杜心解》卷四之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吴若本把《咏怀古迹五首》当做了《咏怀一章》、《古迹四首》,两首诗本是各自为一体,而合成为一首诗则属于后来的误收。
松原论文认为,第一首以外的其它四首也属于不同性质作品的组合,这种差别与其说是杜甫的意图,倒不如说是在《咏怀古迹五首》中贯穿了不同性质作品的明确主题。由此看出《咏怀古迹五首》在内容上互不联系的主题也就解决了。
正如浦起龙所指出的那样,在宋代编纂杜集时,因内容上的互不联系,《咏怀古迹五首》分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存在于杜集之中,这种假设也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吴若本也属于其系统中的一本。
吴若本在《钱注杜诗》中属最重要的文献,并且如前面所研究的那样,吴若本把《咏怀古迹五首》分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钱谦益并没有遵从此说,而且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注释。这个假设的事实,使得钱谦益对作为连章组诗《咏怀古迹五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地超过了对吴若本的热情。
